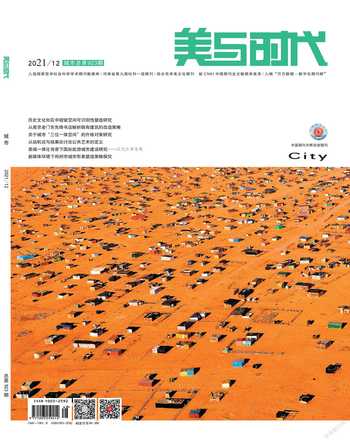從動機論與結(jié)果論討論公共藝術(shù)的定義
朱珈儀


摘 要:在當前公共藝術(shù)的相關(guān)資料中,對于公共藝術(shù)詞源以及概念形成多有模糊,多數(shù)論述從空間、場地、發(fā)生背景、創(chuàng)作形式、歷史關(guān)聯(lián)等不同視角出發(fā),試圖對于公共藝術(shù)進行全面的定義,但這樣一來,創(chuàng)作時間、創(chuàng)作形式、創(chuàng)作動機、公眾效應(yīng)的不同使得“公共藝術(shù)”一詞愈發(fā)難以定性。基于此,從藝術(shù)家或藝術(shù)團體的創(chuàng)作動機出發(fā),結(jié)合其作品產(chǎn)生的公共效應(yīng),探討形成公共藝術(shù)概念的基本問題。
關(guān)鍵詞:動機論;結(jié)果論;場域;公共藝術(shù)
一、關(guān)于動機論與結(jié)果論的判斷視角
(一)關(guān)系簡介以及類型劃分
對于“公共”一詞的定義存在兩方面的討論。從場域論出發(fā),各種客觀關(guān)系存在交織的網(wǎng)絡(luò)組成了一個相對的社會空間,在“公共”層面上不僅僅應(yīng)滿足社會環(huán)境作為客體的因素,還應(yīng)當將以人為本、互相交織的社會關(guān)系以及與周邊環(huán)境的互動關(guān)系作為主要因素進行考慮。在公共藝術(shù)中,作品本身具有的公共屬性應(yīng)從以下幾點出發(fā):第一,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作品時是否需要與特定(如室外場地或是商場、車站等廣義上具備公共空間定義的)空間發(fā)生關(guān)系;第二,當無需與特定的空間發(fā)生關(guān)系時(如藝術(shù)品被放入展廳),藝術(shù)家是否將其作品作為公共藝術(shù)作品進行創(chuàng)作;第三,當無需與特定空間發(fā)生關(guān)系,且藝術(shù)家或設(shè)計師在創(chuàng)作目的上并非完成公共藝術(shù)本身,就結(jié)果而言該項目或作品是否具有公共性(如城市規(guī)劃、社區(qū)項目等)。
基于以上根據(jù)創(chuàng)作者的動機以及作品完成后的結(jié)果判斷,根據(jù)公共藝術(shù)的形式則可將其區(qū)分為以下五種類型:一是特定公共藝術(shù)作品的植入,如城市雕塑、紀念性建筑、景觀裝置等(屬性一);二是基于公共關(guān)系的思考創(chuàng)作,并由此引起了一定公共信息反饋的作品(屬性二、三);三是通過相關(guān)行為、概念參與等不同的活動形式,實現(xiàn)公眾參與的實踐類項目(屬性一、二);四是,公共藝術(shù)在社會環(huán)境、公共設(shè)施、政府項目建設(shè)改進時的參與(屬性三);五是大地藝術(shù)(屬性一)。
(二)對于社會參與程度的評判
在以上的分類中,最難以被界定的便是基于公共關(guān)系的思考創(chuàng)作,并由此引起了一定公共信息反饋的作品,與此關(guān)聯(lián)緊密的是社會公眾的參與程度。這類作品在創(chuàng)作之初便以“公共”為素材或是靈感來源,但作品完成之后并不與特定的場所發(fā)生關(guān)系,而是在美術(shù)館或展覽中進行展出。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經(jīng)由藝術(shù)家的轉(zhuǎn)換后,公眾進行評判、參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品本身或被賦予更多元的價值與意義,或被賦予更為深刻的精神內(nèi)涵。
在當下這個傳播媒體如此發(fā)達的時代中,私人與公共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不清,藝術(shù)家在此類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頗為耐人尋味。《當代藝術(shù)的主題:1980年以后的視覺藝術(shù)》一書在討論場所主題時提到,臥室如果每天24小時被放在網(wǎng)上供人觀看的話,它就比雜貨店更具有公共性。同樣的,當一件反映公共關(guān)系的作品在博物館或是美術(shù)館內(nèi)展出時,盡管失去了公共藝術(shù)傳統(tǒng)上的在地性,但其涵蓋的信息量遠遠超過了同一場所內(nèi)展出的其他藝術(shù)作品。作為一件公共藝術(shù)作品,其本身無論就形式還是內(nèi)容而言,對于互動性、公共性的標準一定比其他展出的藝術(shù)作品更高,那么對其含有公共性的評判標準便應(yīng)從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創(chuàng)作該作品時的社會參與程度、作品展出后的公共參與意識出發(fā)。
例如,在喬志兵的收藏中,有一件傅丹的裝置作品《侗亭》格外引人注意。由于創(chuàng)作者將侗族的建筑元素與語言挪用到了不屬于其原本環(huán)境的展館當中,所以該作品不同于其他的視覺作品。藝術(shù)家利用侗亭本身具有的公共庇護所的屬性作為創(chuàng)作元素,使觀眾在體驗作品時能夠參與到作品當中,在亭中小憩,而且該作品中懸掛的裝飾物會根據(jù)場館所在地的特征進行選擇,這一特點與公共藝術(shù)的原始定義中對于所在地域文化的照應(yīng)不謀而合。
當然,藝術(shù)家本人并未對此作品是否具有公共性作出解釋,但就根據(jù)克勞斯在1979年的文章《擴展領(lǐng)域中的雕塑》中的論述,《侗亭》這件作品滿足克勞斯論述中“場地建設(shè)”概念的條件,只不過并不滿足公共藝術(shù)中對于“特定空間”的限制。如今,哈爾·福斯特根據(jù)公共藝術(shù)的現(xiàn)狀,提出應(yīng)跳出克勞斯圈定的原有概念,并在一個擴大的跨學科領(lǐng)域內(nèi)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對作品采用的創(chuàng)作、研究方法必定會引發(fā)對原有陳舊程序的質(zhì)疑。
在美術(shù)館這一特殊的公共空間內(nèi),時下的藝術(shù)品變得越來越具有互動性,且當部分藝術(shù)品被以其最完美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在世人眼前時,它們會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場域,觀者只能參與其中,并成為其構(gòu)成的一部分。根據(jù)公共藝術(shù)當下的定義,這些作品缺乏在地性——因為任何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策展人,都能夠營造這一場所。可是相對的,在這一類作品中,部分作品正如同上文的《侗亭》,擁有強烈的公共文化背景、語義以及公共空間關(guān)系,相較于部分在地植入的、更趨向于裝飾性的城市雕塑,這類作品的公共文化內(nèi)涵有時會深刻得多,但由于場所的限制,其往往單單從形式上被定義為裝置作品。
本文認為,公共藝術(shù)不應(yīng)僅僅作為一種藝術(shù)形式被提及,由于其表現(xiàn)形式的多樣,題材內(nèi)容的豐富,加之日益擴展的公共領(lǐng)域,當下的公共藝術(shù)應(yīng)更趨向于一種藝術(shù)類型。判斷其是否為公共藝術(shù)的標準不應(yīng)僅僅局限于形式,更應(yīng)從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以及產(chǎn)生的公共效應(yīng)出發(fā),更多元、更直接地從本質(zhì)出發(fā)對當下的公共藝術(shù)進行定義。
二、公共藝術(shù)與公共參與意識
(一)從大地藝術(shù)出發(fā)討論公共參與意識——大地藝術(shù)的詞源及其定義
大地藝術(shù)起源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歐美地區(qū)。一方面由于極簡主義的盛行,大多數(shù)藝術(shù)家對于返璞歸真的表現(xiàn)形式、簡約天真的藝術(shù)手法燃起了狂熱的興趣,這一興趣增添了藝術(shù)家們對于史前藝術(shù)的了解與探索;另一方面,由于藝術(shù)品市場呈現(xiàn)千篇一律的頹勢,畫廊等機構(gòu)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流水線逐漸格式化了藝術(shù)家的個人風格以及思想,市場與資本的過度干預使得藝術(shù)家們想要逃離這一系統(tǒng)的干預,大地藝術(shù)在這樣的條件下應(yīng)運而生。由以上兩點看來,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之初并沒有將公共性囊括其中,相對的,大部分大地藝術(shù)作品都由私人出資創(chuàng)作,并且地理位置偏僻,在欣賞時存在一定的名額限制,因此其中大多數(shù)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之初并沒有“做一件公共藝術(shù)作品”的動機。但大地藝術(shù)之所以能夠在當下的藝術(shù)形式中成為公共藝術(shù)極其重要的一個話題,是因為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承擔的角色以及公眾在觀看、評論的過程中對于作品的參與。
(二)大地藝術(shù)與公共藝術(shù)的關(guān)系
在大地藝術(shù)中,以符號為媒介,藝術(shù)家在自然和社會當中起到轉(zhuǎn)換者的作用,在這一創(chuàng)作過程中,藝術(shù)家本人的創(chuàng)作過程與平日里或許并無太大差異,但是就公眾而言,藝術(shù)家代替他們充當了認知與發(fā)現(xiàn)者的角色。有人提出,正是這種在歷史層面上與物理層面上的遙遠距離使得大地藝術(shù)能夠以更投機的方式產(chǎn)生共鳴。事實上,今天觀眾的想象力可能是大地藝術(shù)占據(jù)的最大優(yōu)勢。
大多數(shù)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與認知的發(fā)展,對于社會與自我認識的構(gòu)建逐漸定型,擁有了一套固定的規(guī)則與符號體系,難以跳出原有的視角觀察外界。但大地藝術(shù)與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媒介不同,對于自然物的應(yīng)用使觀眾在觀看此類作品時更容易擁有似曾相識的探索感受,更容易激發(fā)大眾的同理心。此外,由于個體間認識、評判標準與理解能力的差異,這些大地藝術(shù)作品在經(jīng)過攝影、錄像或是觀眾的親身體驗后被社會公眾評判,重新被賦予更加多元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就大地藝術(shù)而言,盡管其剛開始是作為藝術(shù)家出于個人偏好進行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類型,其實際包含的公共性遠比設(shè)想的要大得多。
(三)公共藝術(shù)與公共參與意識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大地藝術(shù)中的公共參與意識相較于空間上的在地性更為明顯,而這一現(xiàn)象不僅僅體現(xiàn)在大地藝術(shù)中。當特定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植入某一已擁有成熟生態(tài)的公共空間時,在地性確實是其表現(xiàn)形式,從造型上凸顯其內(nèi)涵意蘊,參與周邊環(huán)境的文化語境,但真正使其擁有公共性的是在該場所下,其落成后引發(fā)的公共效應(yīng)。優(yōu)秀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應(yīng)為周圍的環(huán)境帶來良好的生態(tài),無論是物質(zhì)層面上還是精神層面上。
因此,形式上的在地性成為了衡量公共藝術(shù)作品優(yōu)劣的關(guān)鍵,如坐落在山東青島“五四廣場”的標志性雕塑《五月的風》、四川省成都市的活水公園項目便是公共藝術(shù)帶動周邊生態(tài)的典型案例。
三、不與特定空間發(fā)生關(guān)系的作品
(一)無法規(guī)定的公共空間
藝術(shù)家越來越多地回應(yīng)著迅猛發(fā)展的技術(shù)帶來的各種轉(zhuǎn)變,而傳播媒體迅猛發(fā)展,大規(guī)模地滲透進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沒有任何場所能夠完全擺脫開公開展示或與外界交流的可能性。同樣的,越來越多的藝術(shù)形式也需要利用空間場所的屬性或是發(fā)起公眾參與以完成作品,在這之中,只有極少數(shù)的空間作品能夠完全規(guī)避與公眾之間發(fā)生關(guān)系,單純利用空間這一要素達到表現(xiàn)目的。其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無論是作品還是相應(yīng)的藝術(shù)元素,都能夠在不同的公共場合產(chǎn)生不同的藝術(shù)效應(yīng)。在此,不與特定空間發(fā)生關(guān)系成為了當前時代創(chuàng)作公共藝術(shù)的又一特征。
(二)無法逃避的公共關(guān)系
在藝術(shù)作品的形成過程中,作為公共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被收藏或是放置于展示空間展出時——由于在地性的缺失以及陳列空間的互動,我們往往難以對其是否具有公共性給出明確的定義。
那么對于作品是否能夠被作為公共藝術(shù)的標準,便轉(zhuǎn)而由是否具備相應(yīng)的公共參與意識進行評判。公共參與意識除了藝術(shù)作品自身與其周邊的環(huán)境、來往的公眾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場域以外,更包含了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藝術(shù)家與公眾、公共文化發(fā)生的關(guān)系,以及作品完成后在公眾意識、社會文化中產(chǎn)生的影響。前者在安尼施·卡普爾、安東尼·葛姆雷、洛克希·潘恩、關(guān)根伸夫等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都有體現(xiàn),而后者的代表則有奧斯卡·穆里略、理查德·朗等等。
(三)當下公共藝術(shù)與新媒體的關(guān)系
當下互聯(lián)網(wǎng)與新媒體的快速發(fā)展給予了公共藝術(shù)更多的發(fā)展思路與立足空間。無論就形式還是創(chuàng)作內(nèi)容而言,公共空間與公共關(guān)系的文化語匯在新媒體時代被重新定義。依托新媒體或互聯(lián)網(wǎng)存在的作品是否自誕生始便包含了一定的公共性呢?在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中什么樣的空間才能被定義為“非公共”的呢?相信這一系列的問題將在未來公共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得到相應(yīng)的重視以及探討,甚至生成一套嶄新的系統(tǒng)。
四、公共屬性中的側(cè)重
可以看到,在當前已有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中,能夠達到“具有公共性”目的并被世人銘記的作品都至少同時滿足了三項公共屬性中的兩項。但在較為具有“公共藝術(shù)性”的作品中,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時是否有意識地將作品作為公共藝術(shù)作品進行創(chuàng)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件作品內(nèi)容的公共性以及它的社會影響力。
假設(shè)一位公共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時有意尋求該作品的公共屬性,最后作品被放入美術(shù)館中,無人問津。那么其從內(nèi)容而言還是一件公共藝術(shù)作品,但在表現(xiàn)時缺乏了完整性,因此這是一件極為失敗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同樣的,通常情況下,當任何類型的作品被放入美術(shù)館中籍籍無名時,它們都不會是那么的成功。因此,在這一類型的公共藝術(shù)作品中,滿足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性或是達成一定影響力,僅僅是一項衡量該作品是否成功的條件,而并非該類型公共藝術(shù)作品的目的。
同樣的,當面對一件公共藝術(shù)作品時,其在地性以及對周邊環(huán)境的影響確實是衡量一件作品優(yōu)劣的重要標尺,而對于其所在場域的文化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由藝術(shù)家本人在創(chuàng)作時對于該地文化的了解以及自身對于公共文化的運用構(gòu)成的。因此,公共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是否注重對于公共文化的運用,帶有一定的目的去創(chuàng)作公共藝術(shù)作品就變得格外重要。
五、結(jié)語
公共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作有別于其他藝術(shù)類型的關(guān)鍵不僅僅在于其作品本身創(chuàng)作時形成自洽,更應(yīng)當在所在場域中形成屬于自己的邏輯閉環(huán),從空間、人文背景、社會關(guān)系等諸多因素出發(fā)進行探索。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公共藝術(shù)在未來的發(fā)展中將擁有更為多元的機遇與挑戰(zhàn)。
從時下不斷更新的表現(xiàn)形式以及技術(shù)手段,追溯到20世紀中期蓬勃發(fā)展的公共藝術(shù)生態(tài),我們可以看到公共藝術(shù)的系統(tǒng)正在不斷完善。但由于其整體的文化架構(gòu)以及社會意識建立在歐美地區(qū)的文化語境之下,因此我國當前的公共藝術(shù)發(fā)展應(yīng)當從目前已知的理論系統(tǒng)出發(fā),在進一步探討我國的公共空間、公共環(huán)境、社會關(guān)系、文化語境等要素的基礎(chǔ)上加以實踐,尋找到屬于中國的公共藝術(shù)發(fā)展方向。
參考文獻:
[1]王東輝.中國當代公共藝術(shù)的現(xiàn)狀、問題與對策[D].北京: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2012.
[2]羅伯森,麥克丹尼爾.當代藝術(shù)的主題:1980年以后的視覺藝術(shù)[M].匡驍,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
西安美術(sh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