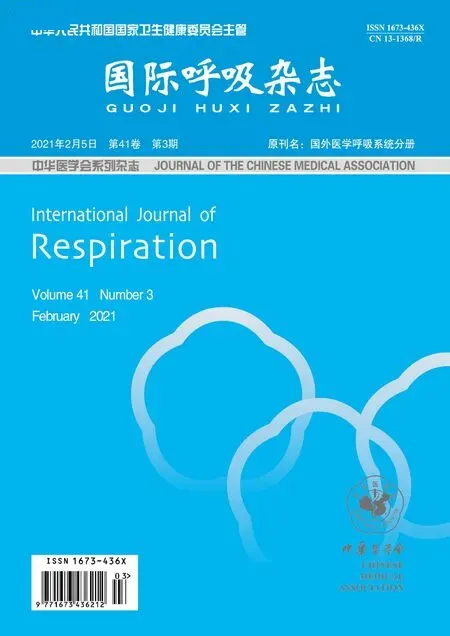422例成人病毒感染肺炎臨床特征分析
趙春柳 郭翎茜 韋棟 張欣欣 周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盧灣分院呼吸科0000;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0005;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臨床病毒研究室0005
病毒在呼吸道感染中占有重要地位,隨著病毒檢測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及每年流感病毒不同程度的播散,尤其是2019年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呼吸道病毒可以是肺炎的直接病原體,也可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2種情況均不乏重癥患者。重癥病毒感染的治療是目前臨床的重點和難點,也是病毒感染肺炎醫療費用的主要支出部分。本研究對真實世界中病毒感染肺炎臨床特征及促進病情進展的相關因素進行探索,為臨床制定更精準的治療措施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住院且呼吸道病毒檢測陽性的成人肺炎患者。從瑞金醫院病毒研究室數據庫中獲得呼吸道病毒檢測陽性數據,根據入組標準,最終篩選出422例患者納入統計,年齡范圍為19~99 歲,平均年齡 (68±17)歲。其中男256 例,平均年齡 (67±18)歲;女166例,平均年齡(63±17)歲。本研究得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件號:(2017)臨倫審第(205)號。
1.2 入組及排除標準 入組標準:住院患者,痰液經瑞金醫院病毒研究室多通道實時熒光定量PCR 檢測病毒陽性,影像學顯示新發肺部滲出、浸潤影,結合臨床急性呼吸道癥狀,伴或不伴發熱。排除標準:年齡<18 歲;最終診斷為非肺部感染性疾病。病毒檢測使用Light Mix Modular呼吸道病原體多重熒光PCR 檢測試劑盒 (美國Roche公司),所測病毒包括:流感病毒A 型和B型、副流感病毒1~4 型、冠狀病毒OC43 型、HKU1型及229E 型、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人鼻病毒、腸道病毒、人博卡病毒。
1.3 方法 收集所有入組患者的臨床信息,包括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吸煙史、合并癥、住院期間治療情況、實驗室檢查結果以及預后情況等。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0.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s 或M(P25~P75)表示,組間各指標的平均水平或分布差異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Mann-Whitney U 檢驗比較;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及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檢驗進行比較。相關性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病毒分布 159例甲型流感病毒 (簡稱 “甲流”)陽性,占37.7%;人鼻病毒次之,為78例,占18.5%;其他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A 型39 例(9.2%),人偏肺病毒36例(8.5%),乙型流感病毒(簡稱 “乙流”)33 例 (7.8%),冠狀病毒OC43型29 例 (6.9%),腺病毒22 例 (5.2%),副流感病毒3型19例 (4.5%),呼吸道合胞病毒B型16例 (3.8%),腸道病毒及人博卡病毒各5例 (1.2%),副流感病毒1 型和2 型各1 例(0.2%)。其中同時檢出2種病毒陽性者17例,3種病毒同時陽性者2例。副流感病毒4型、冠狀病毒HKU1型及229E型未檢出。
2.2 2組一般情況比較 根據我國成人重癥肺炎診斷標準[1],422例患者在住院過程中出現重癥病情者174例,占41.2%。重癥患者與非重癥患者性別構成比及>60 歲患者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重癥患者中有吸煙史的患者比例、體質量指數<18 kg/m2的患者比例均高于非重癥患者 (χ2值分別為11.074、13.418,P 值均<0.05)。63.2%(110/174)的重癥患者有氣促癥狀,高于非重癥組[20.2% (50/24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χ2=80.534,P <0.05),其他呼吸道感染常見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咳痰等,2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肺部影像學顯示,重癥患者主要以多肺葉病變為主,占所有重癥患者的93.7% (163/174),與非重癥組 [64.9% (161/248)]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433,P <0.05)。見表1。
10.9% (19/174)的重癥患者合并心力衰竭,高于非重癥組[5.6% (14/24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946,P <0.05)。重癥組高血壓患者的比例(41.4%)低于非重癥組 (52.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364,P <0.05)。其他慢性疾病,如哮喘、COPD、腫瘤、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糖尿病等,2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微生物培養 (血液或痰液)顯示,54.0%(94/174)的重癥患者細菌或真菌培養陽性,顯著高于非重癥組 [10.1% (25/24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χ2=97.519,P <0.05),見表1。所有樣本共檢出鮑曼不動桿菌50例,肺炎克雷伯桿菌44例,嗜麥芽窄食單胞菌23例,金黃色葡萄球菌16例,銅綠假單胞菌和大腸埃希菌各15例,溶血葡萄球菌8 例,流感嗜血桿菌和肺炎鏈球菌各1例,真菌19例。

表1 重癥組與非重癥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
2.3 重癥組相關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吸煙、高血壓、多肺葉累及、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以及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與重癥病毒感染肺炎相關(表2)。
2.4 2組病毒檢出情況 重癥組檢出率較高的病毒是甲流病毒 (59 例,33.9%)、人鼻病毒 (46例,26.4%)、 冠狀病毒 OC43 型 (21 例,12.1%)。重癥組人鼻病毒及冠狀病毒檢出率均高于非重癥組 (χ2值分別為12.430、12.495,P 值均<0.05),而2組甲流病毒檢出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3。
單一病毒感染中,冠狀病毒感染者細菌或真菌培養陽性率最高,為45.8%,鼻病毒(31.9%)次之,但均低于多重病毒感染者(47.4%)。見表4。
2.5 2組免疫細胞與細胞因子水平比較 重癥組外周血淋巴細胞計數低于非重癥組 (Z =-6.440,P <0.05),見表1。93例重癥患者及53例非重癥組患者檢測了CD3+、CD4+及CD8+細胞絕對計數,統計結果顯示,重癥組總體水平均低于非重癥組(P 值均<0.05),見表5。90例重癥組患者及37 例非重癥組患者檢測了血清細胞因子IL-2R、IL-6、IL-8、IL-10、腫瘤壞死因子α 水平。重癥組IL-2R、IL-6、IL-10 水平均高于非重癥組 (Z 值分別為-2.457、-3.554、-2.339,P 值均<0.05),而2組IL-8及腫瘤壞死因子α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6)。

表2 重癥病毒感染肺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3 重癥組與非重癥組患者病毒檢出情況 [例 (%)]

表4 不同病毒感染患者細菌或真菌培養情況

表5 重癥組與非重癥組患者免疫細胞計數比較 [個/μl,M(P 25 ~P 75)]

表6 重癥組與非重癥組患者免疫細胞因子水平比較 [ng/L,M(P 25 ~P 75)]
3 討論
病毒是呼吸道感染常見的病原體,病毒分布具有季節差異和地區差異,流感病毒是目前國內最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病毒[1]。422例病毒檢測陽性的住院肺炎患者中,甲流病毒陽性率最高,而乙流病毒陽性率僅為7.8%,低于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人偏肺病毒。甲流病毒抗原性易發生變異,根據變異幅度大小分為“抗原漂移”及“抗原轉變”[2],使病毒易于逃避宿主免疫系統,導致感染流行,威脅公眾健康。因此,對流感的防治,尤其是甲型流感,一直是我國疾病預防與控制的重要課題。與此同時,不可忽視其他呼吸道感染病毒的存在,如檢出率僅次于甲流病毒的鼻病毒。尤其在慢性呼吸道疾病,如COPD 急性加重期,鼻病毒更是最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病毒[3-5]。本研究統計顯示,重癥組鼻病毒的檢出率是非重癥組的2倍,提示鼻病毒感染導致的疾病負擔并不亞于流感病毒。在健康個體,鼻病毒感染主要導致上呼吸道癥狀,較少累及下呼吸道[6-7]。但由于COPD 患者對鼻病毒易感及鼻病毒感染后增加細菌在呼吸道上皮細胞的黏附[8],損傷巨噬細胞的免疫應答[9],易繼發細菌感染,是導致急性加重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數據顯示,31.9%鼻病毒單陽性的患者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高于甲流病毒單陽性者。呼吸道基礎疾病的存在以及相關合并癥的影響也是導致患者病情較重的原因。冠狀病毒的總體檢出率不高,但重癥組冠狀病毒的檢出率明顯高于非重癥組,且近一半冠狀病毒單陽性患者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考慮冠狀病毒感染可致患者對細菌或真菌更易感,具體機制需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驗證。
除病毒本身外,病毒感染肺炎的病情嚴重程度還與宿主健康狀況和免疫狀態有關[10]。重癥組中有吸煙史的患者比例高于非重癥組,多因素分析也顯示,吸煙與病毒感染后易發生重癥肺炎相關。吸煙是導致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首要因素。煙草煙霧中的細小顆粒物逃避呼吸系統的抵御,直達呼吸系統最遠端的肺泡,并能穿透肺泡進入血液,使肺、血管和周圍組織受損,誘發炎癥反應[11],最終可導致肺功能損傷。臨床上雖也存在肺功能正常的吸煙者,但香煙煙霧導致的氣道慢性炎癥反應及組織損傷依然存在[12],病毒入侵進一步加重組織損傷,這可能是造成吸煙者病毒感染后病情較非吸煙者嚴重的原因之一。
既往普遍認為,肥胖是病毒感染肺炎預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本研究數據雖顯示,重癥組肥胖(體質量指數>30 kg/m2)患者的比例高于非重癥組,但差異未達統計學意義。而重癥組低體質量指數(體質量指數<18 kg/m2)患者的比例高于非重癥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消瘦患者可能存在更高的重癥風險,但多因素分析未顯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這需要今后繼續完善數據進行相關分析。
重癥組高血壓患者比例低于非重癥組。既往有研究指出,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的使用是降低老年人肺炎住院風險的獨立因素,研究者認為與血管緊張素酶的基因多態性有關[13]。在中風患者的觀察中發現,ACEI降低肺炎住院風險的作用與劑量相關,而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未顯示這一保護性作用[14]。美國一個針對中年高血壓人群的研究提出,噻嗪類及親水性ACEI可降低肺炎風險[15]。但我國一個隊列研究顯示,ACEI與氯沙坦比較,并不能降低肺炎發病率和病死率[16]。本研究數據缺少高血壓相關用藥記錄,無法進行分層分析,且ACEI類藥物是否對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具有保護性作用仍缺少前瞻性研究的支持,故尚不能認為高血壓是重癥肺炎的保護因素,未來將繼續關注這方面的研究。
累及多肺葉的肺炎患者更易進展至重癥,臨床上對于這類患者,需更加密切關注病情進展,及時給予積極治療措施以期改善疾病預后。重癥組54.0%的患者痰或血培養發現細菌或真菌生長,且遠高于非重癥組,多因素分析提示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也是導致病情加重的因素,主要為醫院獲得性肺炎的常見致病菌,如鮑曼不動桿菌、肺炎克雷伯桿菌、銅綠假單胞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臨床微生物培養陽性率普遍較低,這一數據是被低估的。因而在臨床上需要密切關注患者癥狀、體征以及相關實驗室數據、影像學的改變,早期發現合并感染的征象,及時給予適當抗菌藥物治療,也是改善病毒感染肺炎預后的關鍵。
病毒感染肺炎病情嚴重程度也與淋巴細胞數量相關。重癥組外周血淋巴細胞總數及CD3+、CD4+、CD8+細胞計數均明顯低于非重癥組,提示病毒感染進展過程中存在適應性免疫受損。CD3、CD4、CD8是T 細胞受體識別外來抗原的輔助分子,表達這些分子的淋巴細胞是抗病毒免疫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細胞數量的減少提示機體抗病毒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細胞因子風暴”的出現,又進一步加重病情。“細胞因子風暴”的首次提出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指伴隨器官移植出現的一種病理狀態,也叫“移植物抗宿主病”[17]。之后發現多種疾病均存在這種病理狀態,尤其是病毒感染時大量促炎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產生和分泌,導致過度炎癥反應,造成更嚴重的病理變化,如彌漫性肺泡損傷、透明膜形成、纖維蛋白滲出和纖維化,細胞因子還可溢出至循環,導致多器官功能障礙[18]。但在季節性流感及輕癥流感患者中,很少出現細胞因子風暴[19],也提示細胞因子風暴的出現與病情嚴重程度相關。本研究統計的數據中僅包含IL-2R、IL-6、IL-8、IL-10和腫瘤壞死因子α,結果顯示,重癥組血清IL-2R、IL-6、IL-10 水平均高于非重癥組,提示重癥病毒感染患者存在部分細胞因子異常釋放現象。但不同病毒感染刺激產生增加的細胞因子可能不同。2003年的SARS疫情之后的研究發現,細胞因子風暴參與SARS 患者感染后的免疫損傷,患者血清干擾素γ、IP-10、IL-6、IL-8、IL-18、轉化生長因子β、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干擾素γ誘導單核細胞因子等細胞因子水平顯著升高;且死亡患者IP-10、IL-18、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及干擾素γ 誘導單核細胞因子水平高于存活患者[20]。IL-8以及IP-10、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巨噬細胞炎性蛋白1水平也被發現在甲型H5N1 流感的致死病例中異常升高,其中IL-8水平升高尤其顯著[21]。對2019年底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研究顯示,ICU 患者血漿中部分細胞因子顯著高于非ICU 患者[22]。本研究數據中包含的細胞因子類別較少,故無法深入研究不同病毒感染之間細胞因子水平的差異,但這是今后研究的方向。除早期有效抑制病毒復制外,減少免疫介導的組織損傷也是改善病毒感染預后的重要措施[23]。明確不同病毒感染相關的細胞因子,有助于為病毒感染的免疫治療提供理論依據及相應靶點,以探索更精準的靶向治療。
綜上所述,甲流病毒是目前國內最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病毒,但不可忽視其他病毒感染的存在。除患者自身因素,如吸煙等,多肺葉累及、合并細菌或真菌感染以及病毒感染相關的自身免疫功能異常是導致病情危重的原因。在研究抗病毒藥物的同時,給予適宜的抗菌治療方案,以及探索更多的免疫治療方法將有助于進一步改善病毒感染肺炎的預后。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1)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不可避免病例來源的偏倚;(2)檢測的細胞因子類別少,缺少不同病毒感染特異相關的細胞因子數據。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尋找不同病毒感染相關的細胞因子,為病毒感染的免疫調節治療提供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志謝本研究得到了高水平地方高校協同創新團隊的支持和幫助
作者貢獻聲明趙春柳:研究設計、數據整理、統計分析、論文撰寫;郭翎茜、韋棟、張欣欣:數據整理;周敏:研究指導、論文修改、經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