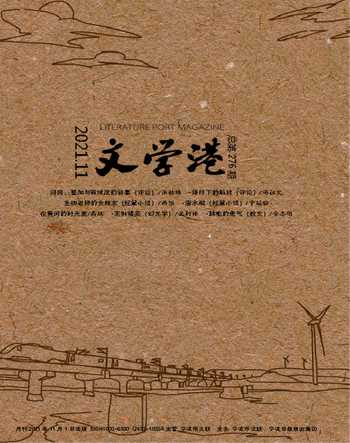房間
月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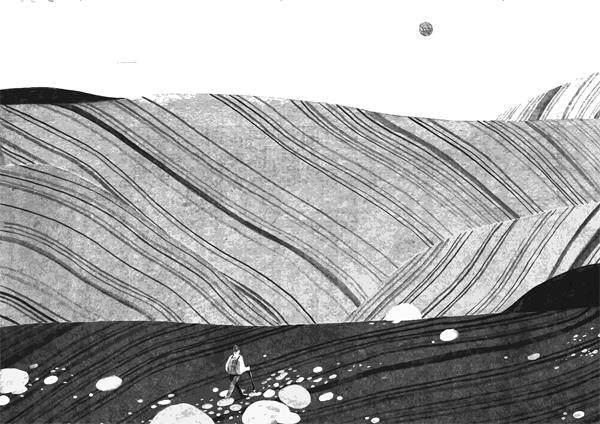
林奈幼時養過一只與眾不同的寵物。說寵物似乎鄭重了點。當時,母親抖開清早剛從菜市買回來的一把上海青,“呀”了一聲,順手摘下,遞給剛剛能夠到桌沿的林奈。受了驚嚇,蜷縮入殼,林奈以為手心里躺了枚小石頭。
這是蝸牛。母親說。
蝸牛。林奈聽過那首兒歌,蝸牛背著重重的殼啊,一步一步往上爬。她湊近了,緊盯著小石頭看,正碰上它緩緩吐出兩只透明纖弱的觸角。四目相對,林奈像見證了什么石頭開花似的了不得的奇跡。
一座移動的屋宇,堅硬厚重,耐熱抗寒。這是幾年后上小學的林奈在百科全書上讀到關于蝸牛殼的注解。等到二十六歲的林奈幾經波折,搬進屬于自己的小公寓時,回想起那個鵝卵石般的外殼,心底又涌起了另一番滋味。但四歲的林奈看著眼前花蕊似的觸角,只滿心憂慮。這殼得多重呀,得有孫悟空背上的五指山一樣重吧?那果凍條似的身體不會被碾的變形嗎?
那只蝸牛林奈養了兩個多月,直到某個清晨醒來,忽然不知所終。紙盒一壁歪斜著長長一條白印,如實記錄了它漫長的逃亡路線。時隔許久,久到幾乎忘記了這件事時,林奈在書桌下的最里角發現了一只風干的空殼。她捏住,有些失神,平生第一次體會到一種失去和告別的惆悵。卻又有幾分釋然,它終于像孫悟空一樣,從大山下逃出去了。
如今,林奈而立之年,站在這個曾獨居了幾年的小公寓里,四下環顧,不禁再度被當年那種悵然若失之感包裹。
房間里,一對陌生的青年男女正四下打量,目光跳躍似躲避林中陷阱的兔子。黃昏將盡,屋內幾盞燈盡開,陳設一覽無余。豆綠色的墻紙還是剛住進來那年貼的,接縫處已輕微翹起;精心挑選的窗簾上,藍青色的葉片經盛夏久曬,褪成頹敗的藍灰色;至于那套耗費林奈一整個周末才組裝好的奶油色桌椅,四角也輕微脫了漆。待會兒,這些會成為他們討價還價的籌碼。如果再找下去,說不定還能發現某處疑似的霉點,或是一道若隱若現的裂縫……林奈心里也吃不準——雖自住時維護得很用心,但婚后房子就租了出去,兩年下來,難免有她不知情的損耗——不過臉上仍擺出事先琢磨好的并不熱切,亦不至冷淡的表情。
這是他們第二次來了。頭一次是女孩兒自己來的,這次還帶上了男朋友,說明挺中意。如果順利,說不定今天就能拍板。
這是個酒店式布局的公寓,總共四十平米,一眼便可望盡全局,兩個人卻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看了足足半個鐘頭。這會兒,男孩兒正拿著一根自帶的測電筆,半蹲著檢測插座。可真夠細致的,林奈有點不耐煩地想。接著,又多少有些羨慕。當初她買這個房子時,因父母在外地,又時逢弟弟備戰高考,從看房,拍板,到過戶,全憑自己奔波。要是那會兒認識方焯就好了,林奈想,有個人可以幫襯。但轉念一想,要這么一來,這房子說不定就買不了了——家里本來就不支持買房,尤其是父親。倒非經濟條件不允許,只是囿于觀念。女孩兒買什么房呢?父親說,以后結了婚自然有地方住。林奈不以為然,要是買了房,萬一哪天離了婚不也有地方住?父女倆為此還鬧了點不愉快。大概也是為此,父親雖資助了一筆錢,卻從未提過來看看房,把把關什么的。
男孩兒收起電筆,移步衛生間。女孩兒緊隨其后。真要是那會兒就認識方焯,林奈又想,他恐怕也幫不上這些忙。丈夫是個粗線條的男人,她實在想象不出他蹲在地上,拿著測電筆一一測試每個插座的樣子。她有時抱怨起他的粗心,他還大言不慚,自詡為男人不拘小節,惹得她很窩火。但他或許會關注點兒別的問題,比如小區門禁嚴不嚴,或是屋子里裝火災報警器了沒有。有一次,那是戀愛半年左右,她出差晚歸,手機又沒了電,半夜提著心走在回家必經的一段偏僻小道,遠遠看見一個男人坐在路牙子邊抽煙。走到跟前,男人猛地站起來,她嚇得想撒腿就跑,卻聽到他說,“你終于到家啦,我被蚊子咬了一腿的包。”
倒也不是全無用處,林奈做出結論,忍不住笑了笑。
女孩兒從衛生間轉了出來,邊走邊回頭同男孩兒小聲交談。吳儂軟語,也聽不出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中介有些心急,說,“你們就別猶豫了,這種小戶型啊,總價低,以后或租或賣都好出手,特別適合你們這樣的小兩口買來當個過渡。”
聽到“小兩口”時,林奈注意到女孩兒的臉紅了一下。果然,女孩兒立刻搶白:“什么小兩口呀,還沒結婚呢,是我要買房子。”男孩兒倒是笑瞇瞇的,接口道:“遲早的事嘛。”她一聽,又嬌嗔地瞪了他一眼。
女人似乎總是對這樣的事格外敏感,好像某些詞匯必須與某些確鑿的事實掛鉤,否則用起來就不夠慎重。男人卻不,他們脫口而出,那么自然,簡直像壓根沒往心里去似的。她記得跟方焯戀愛那會兒也是這樣。旅游頻道播放瑞士小城的雪景,方焯說,我們結婚就去那兒度蜜月吧。廣告里一個俏皮的小姑娘蹦蹦跳跳,方焯又說,我們以后的小孩肯定跟她一樣可愛。她不搭話。這種篤定究竟是出于信心呢,還是盲目呢,抑或更糟的,輕率呢?幸好,林奈想,幸好事遂人愿,修成正果。
又是幾句聽不懂的嘀咕后,女孩兒說要回去同家里再商量一下,就這一兩天給答復。
中介有些失望,說行,但要抓緊,這房子搶手得很。林奈一聽,“嗯”一聲,順勢把臉上并不熱切的意味強調了幾分。
沒那么熱切倒也不全是裝的。最初,林奈沒想要賣房。前一任租客退租后,她聯系上先前合作過的中介,打算重新租出去。中介說:“姐,這房子我勸你賣掉算了。房齡老,面積又小,很難升值的。”林奈心想,那是,賣房拿的傭金自然比租房多了。中介又說,姐,現在學區房一天一個價,你把這一小套賣了,去學區房付個首付,不比收這點兒租金劃算?林奈這才有些動心。她跟方焯婚后磨合了近兩年,此時正有邁入人生下個階段的打算。她正在服葉酸,方焯也在戒煙戒酒。明年,說不定今年,家里就有可能新添一個小成員。有了孩子,自然要考慮學區。他們現在住的是一套三居室。面積寬敞,地段也還算便利,唯獨學區不好。買賣置換一下,似乎是個不錯的方案?她本著賣賣看的心態,報過去一個頗為理想的價格,不料竟十分搶手。接連幾天,她下班后都忙著帶人看房子。今天的兩個人看得格外仔細,等她緊趕慢趕回到家時,天已徹底黑了。
一進門,餐桌上已放好了幾樣菜。婆婆正彎腰將一碟蒜苗炒肉絲放在木質隔熱墊上,抬頭,目光穿過紫菜蛋湯裊裊升騰的熱氣,“囡囡到家啦,怎么這么晚?”
方焯端著碗米飯從廚房里出來,“正要給你打電話呢,今天加班了嗎?”
林奈含糊應了一聲,洗手吃飯。
晚餐照例是三菜一湯,葷素搭配,主食輔以紅薯、玉米等雜糧。比起在外面吃,既營養又健康。婆婆新近退休,多出大把時間,便主動請纓每天過來做一頓晚飯,三個人一起吃。早先,小兩口下班晚,沒空做飯,都是去一刻鐘車程的婆婆家吃。跑來跑去的,趕上晚高峰反而耗時更久,婆婆覺得她的時間不值錢,過來做飯小兩口更方便。林奈說,怎么能這么麻煩你呢。婆婆說,哎呀,這有什么麻煩的,我正好趁便回來跟老鄰居嘮嘮嗑呢。林奈便不好再拒絕了。
這套三居室,是方家的老房子,一家三口住了十幾年了。前幾年,方焯父親因病去世,剩下母子倆相伴。方家另有一套小兩居,留給方焯做婚房用。談婚論嫁時,婆婆說,自己一個人沒必要住三室,不如搬去小兩居,把這套讓出來當婚房。雖然客觀上來講這樣更合理——以后添了孩子空間肯定不夠用的,但方焯心疼母親,林奈也覺得過意不去。她心想,實在不行,把小兩居和自己的單室套都賣了,換一套大三居。可還沒來得及提議,婆婆就偷偷收拾了東西搬進小兩居去了。老太太是個通情理、識大體的女人,一輩子低聲細語的。這么一來,小兩口便住了進來。
剛住進來那會兒,婆婆時常來訪。她很中意這個兒媳,希望能同她成為朋友。林奈便陪她說說閑話,嘮嘮家常。坐了一會兒,婆婆站起來,走到小書房。呀,改成衣帽間啦。林奈說,是呀。婆婆點點頭,挺好的。又走到大房間,你們怎么不住這間呢,多寬敞。林奈說,方焯那間就挺好,省得東西挪來挪去的,麻煩。婆婆沒應聲,仰頭看著掛在墻上的照片,輕輕嘆了口氣。照片上是方焯一家三口。方焯父親走得很突然,胰腺炎,一兩天的事。聽方焯說,老夫妻倆感情很好。
“你公公人可好了,”婆婆指了指照片上那個表情溫和的中年男人,“可惜沒福氣活到今天,不然看到你啊,肯定喜歡得不得了。”說著眼睛就紅了。林奈不安地站在一邊,鼻子泛酸,也不知如何安慰,只能不住摩挲婆婆的后背。后背枯瘦,像撫過陳年的舊瓦。
婆婆常來,也常向林奈講起亡夫的細碎過往,那么這照片自然是不能,也不該取下來了。可她也不想對著這張二十寸大的笑臉睡覺,多別扭啊。此時若再提出換到兩居室去住,也不太合適,像是在避諱什么。“要不,”有一次她向方焯提議,“咱們把這套三居室賣了,換一處新房?”方焯直搖頭,“那我媽怎么想啊,剛讓出來咱們轉臉就給賣了。”也是。太不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這次換學區房,林奈其實還存了點別的私心:他們終于可以搬到屬于自己的房子去啦。到時候她要好好布置一番,像當初布置自己那個小窩一樣用心。也恰恰因為這個原因,賣房的事她選擇秘而不宣。塵埃落定前,還是不提為妙。
三人默默吃著飯,婆婆夾了個藕圓子,遞到林奈碗里。“我今天啊,去了趟廟里,給你們求了個簽。廟里師父說,明年出生的寶寶撞太歲,最好避開,能今年生最好了。”林奈低頭扒拉了一口飯,把嘴巴塞得鼓鼓的。
這么說,婆婆知道他們備孕的事了。她從方焯面前的菜碟里夾了筷蒜苗,順勢瞄了他一眼。他像什么都沒聽見似的,只顧“咕嘟咕嘟”喝湯。林奈就有點不開心,但是沒流露出來。她能理解孤兒寡母間不同于旁人的特殊情感,可這個方焯嘴巴也太大了點。她在桌子下悄悄踩了他一腳。方焯猛地抬頭,一臉莫名其妙地看向她,隔了幾秒才反應過來。
“哦,媽這你就別管了,咱們順其自然,什么犯不犯太歲的。”
林奈臉紅了,這個笨家伙。但婆婆似乎絲毫不在意,仍是輕聲細語的,“也是,也是,順其自然就好。”
林奈又有些內疚,老人家不過是出于關心而已。比起她的許多朋友,林奈和婆婆的關系算不錯了。小兩口偶爾鬧了矛盾,婆婆也總是不偏不倚。真要說起來,甚至偏袒林奈多一點呢。其實,有那么幾回,看見婆婆對著照片落寞的笑容,林奈甚至想提議讓她住到一塊兒來。可想想朋友家里幾代同堂后的雞飛狗跳,還是忍住了。再說,就算提了,自愛如婆婆,恐怕也不會同意吧。
這么想著,林奈又夾起一塊紅燒帶魚,送到了婆婆碗里。
晚飯后,方焯照例送母親下樓,林奈便收拾了碗筷去廚房。他們倆約定好,家務事一人一半,公平公正。若是林奈洗碗呢,方焯就負責洗衣服。反之亦然。這是小兩口經歷一段漫長的磨合期后,找到的最融洽的相處方式。婚姻可不比戀愛,總是在為一地雞毛蒜皮而苦惱。再者說,原本慣于獨處的兩個人,突然生活在一個屋檐下,成天抬頭不見低頭見,很容易多出些“無中生有”的矛盾。有時候,前一秒還甜甜蜜蜜的呢,后一秒就劍拔弩張了,兩者間的轉變時常毫無過渡。有一回,兩個人窩在沙發上玩手機。方焯刷他的籃球論壇,林奈倚在他肩上看一檔采訪類節目。說日本的一對夫妻,結婚后仍平攤房租,因口味不同用兩口鍋做各自的飯,連睡覺都是兩張單人床拼在一起,鋪各自的被褥。至于興趣愛好,更是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知曉。可饒是如此,記者問起來,兩個人卻一致表示過得很幸福。看他們臉上的笑容,倒也不像摻假。林奈覺得有趣,便把手機舉到方焯面前,笑道,“你看,這兩口子還挺有意思。”
方焯默默看了兩分鐘,來了句,“這不是有毛病么。”
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慢慢撤回。“怎么就有毛病呢?”
“這哪叫夫妻啊,這叫室友。”
“我覺得只不過是生活方式不同而已,為什么所有人得是一個樣子呢?”
說著就爭辯起來,從家庭觀念的出現,至個體的獨立性,最后具化到家務事該如何分攤上。
“好歹他們家務活兒也是各自分擔呢,你平時都做什么了?”
“我確實太忙了啊。”方焯說。
“那我就不忙?”林奈反問。
談話到此只能結束了。兩個人都知道,若再談下去,爭辯就將變成爭吵,爾后冷戰,直至和好。他們已經培養出一定的默契,懂得繞開那個損耗的過程,直抵結果。
兩個人各自歪在沙發一端,眼睛盯著手機屏幕,心里揣度對方看進去什么沒有,以及什么時候若無其事展開下一個話題更合適。通常,他先求和。有時候,則是林奈認錯。果然,幾分鐘后,方焯慢悠悠湊過來,嬉皮笑臉的。林奈仍在氣頭上,決定今天怎么也不搭理他。見她不理,他忽地嚴肅起來。
“囡囡,”他的語調鄭重其事,“我覺得吧,結了婚,就是夫妻了。夫妻,是睡一張床,吃一口鍋里的飯的,是一家人。我想跟你成為一家人。”
一家人。頃刻間冰融雪消。林奈也跟著融化了。誰說粗線條的男人就說不出動人的情話呢?
如今回想起來,或許就是從那個時刻起,林奈真正下定決心,要不計后果、不留退路地投入熱火朝天的生活,那種一家人該有的生活中去。
水池邊,操作臺上的手機突然震了一下,打斷了林奈的思緒。她關掉水龍頭,用擦手布擦干手上的水,撿起手機看了一眼。是中介發來的。
“姐,我探了探客戶的口風,她說很滿意,我覺得你那邊可以著手準備交易材料了。”
林奈心里一松,很快回復過去。丟下手機,把碗碟放進消毒柜,操作臺擦擦干,又拖了遍地,滿意地環顧一圈,這才步履輕快地走回客廳。正抹著護手霜,方焯回來了,一看見她就問,“你笑什么呢,這么開心。”
林奈往沙發上一坐,故作神秘地等待了幾秒,說,“跟你講,我打算把我的小公寓賣了,剛剛談了個好價錢。”
“賣了?為什么賣了?”方焯的表情很驚訝。
“那套房面積小,留著升值空間也不大,不如賣掉做別的用。”
方焯沒做聲,顯然還沒從驚訝中回過神來。
“咱們……不是準備要小孩兒了么,我想賣掉湊個首付,買套好點兒的學區房。”
方焯咧嘴大笑起來,“你都考慮到學區房啦?!”
這讓林奈感到有些掃興。她掏出手機,悻悻地刷起朋友圈。
方焯走過來,在林奈身旁坐下,伸手摟住她的肩打趣道,“我以為你要把房子賣掉還錢呢。”
“還錢?還什么錢?”林奈被問糊涂了。但脫口而出的瞬間,她明白過來。
當初,父親不同意買房,父女倆爭執了一番。說到臨了,父親說,你還有個弟弟吶。語氣里除了為難,多少有點兒責備的意思。林奈就不吭聲了。她算了算手上的存款,轉頭從姨媽那兒借了一部分湊首付,又叮囑她別跟家里說。錢還沒借來,家里就知道了——又怎么能不知道呢?問清數額后,父親把錢打到了她卡上。那筆錢對家里說大不大,但到底不是個小數目。林奈收了錢,賭氣寫了張欠條遞過去。父親倒也賭氣接了。
按理說,林奈本不該賭這個氣的,但當時確實覺得有些委屈。畢業后,她一直同大學同學合租一個兩居室。同學人不錯,相處也算融洽。后來同學交了男友,時常來留宿,添了些不便,但也沒什么。有一天,同學加晚班,只剩她和那個男友在。男友洗完澡,從林奈房門前晃悠著經過,林奈無意間一瞥,竟發現他一絲不掛。她吃了一驚,趕緊悄悄鎖上房門,思前想后,第二天將此事告知了室友,哪知卻被扣上妄想癥的帽子,這才下了買房的決心。父親知道裸露癖的事,但只一味說重新租個單室套就好。這讓林奈感到傷心。認識方焯后,談及租房時的奇葩事,委屈又上心頭,不禁將這些原原本本傾訴了一番。其實事后想想,林奈覺得不該賭氣寫欠條的。但人總是容易重蹈覆轍,就像事后想想,覺得不該把這件事告訴方焯一樣。
她撣掉方焯的胳膊。“那是開玩笑的,我爸媽還能真叫我還錢啊。”
“我知道,這不是在逗你玩么。”
林奈沉著臉不說話,自顧自看手機。
“我是沒想到你考慮得那么遠。孩子還沒出生,你都想到學區房了。再說,學區房那么貴,你那個小房子賣了也不夠首付的。”
林奈一聽,“好好好,都是我瞎操心好吧。房子我不賣了,孩子我看干脆也別生了,你那煙也不用戒了。”
這下不妙,方焯趕緊湊到跟前來道歉。越是討好,林奈越是生氣,“說好備孕戒煙,你戒了嗎?每天借著送你媽下樓的由頭好偷偷抽一根,真以為我不知道?老說將來我們怎么怎么樣,我看你就是隨口說說。”說著說著,氣氛不經意間轉變為傷心。
時不時,會有這樣的瞬間,讓林奈覺得,那些方焯口中信誓旦旦的“我們”,與其說出于憧憬,不如說源自一種習焉不察的觀念。戀愛,結婚,生子,跟衰老和死亡一樣自然,都是始終要來的事,用不著期盼,也大可不必規劃,它就在前頭等著呢。誓言一經解構,言語的碎片殘尸滿地,那么曾附著其上的情感還是真的嗎?
“我怎么是隨口說說呢?”方焯急忙辯解,“我剛才沒抽煙。”說著湊過來要哈氣,“真的沒抽,不信你聞。”林奈別過臉躲開,“這根本就不是抽沒抽煙的事。”
“那是為什么呢?要不咱們一會兒就上網看看學區房,好不好?要是首付不夠,我就把股市里的錢拿出來,咱們一次性換個大房子,好不好?”
林奈憋著淚不說話。方焯頭湊到這邊,她便將臉別到那邊;湊到那邊,她又將臉換到這邊。但最終,還是“噗嗤”一聲笑了。這就是愛了。順水推舟的愛當然也是愛。如果她再別扭下去,就是使小性子,就是不懂珍惜愛了。過日子,哪能一直使小性子呢?說到底,她和他,都是一樣的人,都愿意順生命之流而下,過一種沒有難度的生活。她不是也一樣嗎?父親收下那張欠條,除了賭氣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她永遠不會細究。至于愛,當然是真的。也許不如她想象的那么濃烈,那么純粹,但它依然是真的。
晚些時候,兩個人洗漱完倚在床頭,興致勃勃查起學區房信息來。
第一梯隊的學校最先排除,一來房價過于高昂,二來,夫妻倆不希望孩子的童年被過于高強度的學習所壓榨。他們從第二梯隊的學校中挑出幾所,分頭搜集信息,從招生規模,到師資力量,到課程特色……不了解不知道,一查才發現,這里面的名堂簡直夠寫出一篇學術論文來。直看到兩眼昏花,兩人仍沒能篩選出一個最優選擇。
林奈把手機往被子上一拋,“算了算了,明天再看吧,看得我頭昏腦脹的。”
方焯立刻表示同意,“我得玩一局消消樂緩緩,這比上班還叫人頭疼。”
剛伸了個懶腰,被子里的褶皺抖了一下,林奈拿起手機,看了一眼,立刻氣呼呼扔了回去。
“怎么了?”方焯問。
中介又發來消息,說剛收到買家一條情真意切的消息:她剛剛工作沒多久,積蓄不多,家里幫助也有限,確實是心儀這個房子,希望賣家能再讓個一兩萬。
“上次看房已經讓了兩萬了,這個點兒了又來還價,可真夠煩人的。”
“那就跟她說不能讓了,愛買不買。”
林奈坐著不動,接著抱怨,“你不知道,看房時,那個男的恨不得拿個顯微鏡出來。”
“這倒是正常,你想,又不是買把小菜,自己將來要住的房,肯定得慎重啊。”
“又不是他住,是他女朋友要買。兩個人還沒結婚呢。”
“那說明這男的細心又靠譜呀,換了我,你不希望我這么上心么?
倒也是。林奈消了氣,又把手機撈了起來,“最多再讓五千,不能再多了。”
隔了會兒,中介回過來,“好的,他們說明天一早就給答復。”
關機,充電,林奈收拾妥當后縮進被子,“睡吧,明天還得上班。”
方焯手里消消樂碎裂的音效響個不停。他應了一聲,心不在焉道,“不過啊,我看這女孩兒挺精明。”
“嗯?怎么說?”
“你想啊,兩個人感情挺好的,還非要自己先買個房,生怕變成婚后財產。”
林奈愣了一愣,把被子往下拽了拽,露出下巴。“我倒沒想到這個。”隔一會兒又說,“那我也很精明嘍?”
屏幕上最后幾顆小草莓“嗞啦”一聲消盡,方焯越過林奈,把手機擱在床頭柜上。躺回去時,低頭在她的臉頰上飛快啄了一下,“你啊,你就是個小傻瓜。”
她長長地“嘁”了一聲,表示不屑,等隔了幾分鐘再說話,旁邊卻沒動靜了。推了兩下,他嘟囔幾句,很快發出均勻的呼吸聲。她只好躺回來,對著黑暗中的天花板發呆。街上的路燈越過墻頂與羅馬桿的間隙照進來,屋內充溢著稀釋過的灰水泥般的色澤。貼近窗簾一端的天花板灰中泛著白,很像今天小公寓里被陽光曬褪色的墻紙。果綠色不經曬,以后選墻紙,還是得換個顏色。房子賣掉前,床也得處理掉。那女孩兒不喜歡別人睡過的床。其實這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知道那女孩兒是哪兒人,聽口音像是蘇州人。她的一個大學室友是蘇州人,好像就這么說話。她跟男孩兒說方言,兩人肯定是老鄉。說不定是高中同學,青梅竹馬,約定考到一個城市來的。很有可能,看起來感情就很好。所以怎么可能想到婚前財產這種事嘛。再說,真準備結婚了,女孩兒一樣可以把房子賣掉,兩個人合買個大房子啊。她不是就曾提議過,把小公寓和兩居室賣了,換一個大三居嗎?思緒至此突然顛簸了一下,像潺潺的溪流途經礁石,冷不丁跌了個踉蹌。她提議過,對吧?她想了想,確定自己提議過。方焯當時說,等忙過這兩天再說。那是婆婆搬走前,還是搬走后的事?她記不清了。她想得有些頭疼。
推開被子,她輕輕坐了起來。然后,鬼使神差地,拿起床頭柜上的手機。側眼看去,他睡得正香。她曾經撒嬌說,你的手機得錄上我的指紋,便于隨時檢查。方焯笑著遞過來,來來來,自己錄。她從未用自己的拇指開過鎖,有什么可看的呢?點亮,屏保是他們的結婚照,大夏天在海邊拍的,修了圖仍看得出兩人大汗淋漓。拍照間隙,他頂著西裝,為她遮住火辣的陽光。她幾乎想鎖屏睡覺了。可她覺得指尖虛弱,幾乎按不動鎖屏鍵。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將她的影子按在墻上,像一幕滑稽的皮影戲。墻那邊,如果有人要收拾東西搬走,怎么會不被墻這邊的人察覺呢?可她以前卻從沒想到這一點,多可笑啊。或許,就在她身處的這個房間,曾發生一場私密的對話。是誰的主意?母親的?還是兒子的?抑或不謀而合?
方焯突然翻了個身,發出一些含混的囈語。她立刻把手機倒扣在被子上。睡夢中,他的手下意識地摟了過來,攬在林奈的腰間。剛搬過來那會兒,她有些認床,睡不熟。半夢半醒,總喜歡找方焯的手,找到了,就一下一下摳他掌心的那塊繭。多年的老繭,又厚又硬,簡直像蝸牛殼一樣硬。她想起得到那只蝸牛的那個清晨,她纏著母親從新鮮菜葉里再尋出一只來,給它做伴,卻沒能如愿。母親說,它晚上睡覺就縮回自己殼里去了,不會孤單的。那會兒弟弟還沒出生,林奈每晚摟著母親睡。她想不通,一個人縮在黑乎乎的殼里,怎么能不孤單呢?
手機的光熄滅了,房間復歸稀薄的混沌色。總會有蛛絲馬跡的,只要她著意去找。但她沒有再解鎖,因為沒有意義。
防備和算計存在過。她知道。也許如今已煙消云散,但確定存在過。她同樣知道,在打開手機的那個瞬間,她也已踏入了同一條河流。一切都不一樣了。
她把手機放回床頭柜,輕輕滑身躺下。現在是凌晨一點。如果那個女孩兒起得早,或許五六個小時后就會發來消息。如果睡了懶覺,那就要等更久些。閉上眼,黑暗終于完全籠罩下來。那一瞬間,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全心全意,等待一個令人失望的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