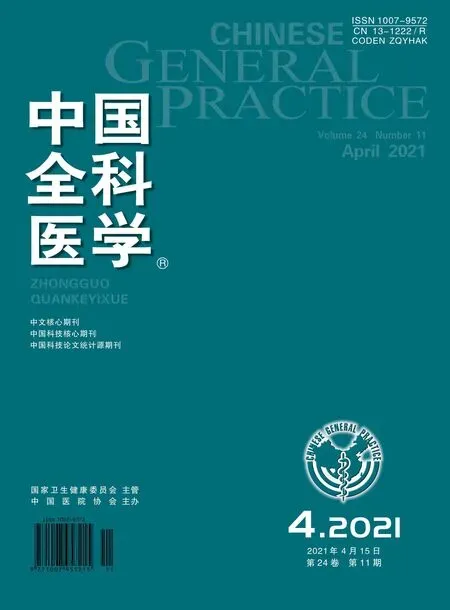抑郁癥與心血管疾病共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王明鑫,李素霞,宋濤
抑郁癥是一種以情緒低落和快感缺失為主要特征的常見精神疾病。在世界范圍內,幾乎每5 人中就有1 人曾在一生中的某個時間點經歷過抑郁癥的折磨[1]。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一組以心臟和血管異常為主的循環系統疾病,包括心臟和血管疾病、肺血管疾病及腦血管疾病,是目前全球居民主要致死原因[1]。大量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表明,抑郁癥與CVD 之間存在著雙向關聯,即抑郁癥患者比健康個體更易罹患CVD[2],同時CVD 患者比健康個體也更易罹患抑郁癥[3]。此外,抑郁癥還是預測CVD 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4]。盡管上述關系已經得到證實,但是二者共病機制仍不十分明確。
本綜述概述了抑郁癥與CVD 患者的流行病學發現,并介紹了可能解釋這二者之間聯系的病理生理機制,包括生活方式、炎癥等因素。最后,本綜述還討論了抑郁癥患者的治療對CVD 患者遠期預后的影響,并描述了可能的未來發展方向,包括對發行機制的研究和對共病患者的篩查、檢測及管理。
1 流行病學
早在上世紀30 年代,關于精神疾病的兩項縱向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因CVD 死亡的風險更高,但這種關系并未得到重視,直到上世紀80 年代人們才對抑郁癥在CVD 中扮演的角色產生興趣。此后,世界各地開展了大量關于二者相互關系的研究,證實二者之間確實存在高度共病現象[5]。
首先,與健康個體相比抑郁癥患者的CVD 發病率明顯增高,死于CVD 的風險也更高。在美國,抑郁癥患者的CVD發病率較對照組高出近3 倍[2]。HUNT 2 研究[6]通過對57 953 名未患過CVD 的健康人群進行平均11.4 年的隨訪,結果發現在對相關風險因素進行校正后,自我報告抑郁或焦慮癥狀,特別是癥狀復發,與罹患急性心肌梗死的風險中度相關。另一項基于美國國家研究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抑郁癥患者罹患致命性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比為1.5[7],這意味著抑郁癥患者的CVD 患病率比健康個體高出了50%,這一結果在校正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及其他危險因素后得出。另外,一項基于在丹麥登記的550 萬人的隊列研究中,由于單相抑郁癥及雙相情感障礙入院的患者,其因CVD 死亡的標準化死亡率(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SMR)為1.6,即他們死于CVD的風險比其他丹麥人高出了60%[8]。另一項基于瑞典人群的類似研究中,單相抑郁癥患者的SMR 也達到了1.6,而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的SMR 則高達2.2[9]。
此外,CVD 患者比健康個體更容易患上抑郁癥。對心肌梗死恢復期、心絞痛發作、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及冠狀動脈腔內成形術患者的研究表明,住院患者中有12%~20%符合抑郁癥診斷標準[10]。另外,嚴重心力衰竭[11]、心房顫動[12]和心肌梗死患者[13]罹患抑郁癥的風險也明顯增加。
2014 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發布了一項聲明,將抑郁癥確定為預測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14],這一聲明得到了多項研究的支持。例如一項基于歐洲的大型前瞻性隊列研究證實,在經過多變量校正后,抑郁癥與CVD 死亡率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而與全因死亡的相關性較小[15]。在另一項納入了16 項研究包括10 175 例心肌梗死患者的Meta 分析中,發現對人口統計學特征、吸煙、糖尿病、體質指數等危險因素進行校正后,心肌梗死后抑郁癥可以以程度依賴的方式預測之后發生的心血管事件[16]。另外一項2011 年的Meta 分析也表明,在過去的25 年里,抑郁癥一直與心肌梗死預后較差相關[17]。
因此,鑒于抑郁癥與CVD 之間的高度共病關系,研究二者共病的潛在機制尤為重要。
2 潛在機制
盡管抑郁癥與CVD 在流行病學上的聯系很緊密,但目前還無法找到將這二者聯系起來的具體機制。抑郁癥的發病機制復雜,涉及多個系統。事實上,抑郁癥更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全身性疾病,而不是一種簡單的有關于情緒的心理疾病。因為一旦診斷為臨床抑郁癥,患者體內則會出現一系列生理變化,包括免疫系統激活、神經內分泌變化和氧化應激反應等,以上均會對心血管系統產生負面影響。此外,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
2.1 生活方式 抑郁癥通過多種方式增加發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風險,其中可能包括抑郁癥患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吸煙、酒精濫用、使用非法藥物及不遵醫囑等[18]增加了罹患CVD 的風險。一項納入1 024 例冠心病門診患者的橫斷面研究發現,出現抑郁癥狀的患者發生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明顯升高,而且這種聯系似乎是由社會經濟狀況和行為(包括缺乏運動、吸煙、飲酒等)所決定的[19]。在另一項針對經歷過急性心肌梗死的抑郁癥患者的“促進冠心病康復”(ENRICHD)研究中,缺乏運動的患者發生致命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明顯高于定期運動的患者[20]。
2.2 炎癥 炎癥則是另一項潛在的重要機制。大量研究證明炎癥可加速動脈粥樣硬化進展,而炎性因子也被發現在抑郁癥患者體內明顯升高[21]。一項關于抑郁癥與炎性因子的Meta 分析顯示,抑郁癥患者體內C 反應蛋白(CRP)、白介素1(IL-1)及白介素6(IL-6)水平均升高,且抑郁癥與這些炎性因子之間存在顯著的劑量-反應關系[22]。還有學者采用累計Meta 分析的方法來評估一些特定的免疫標記物與抑郁癥之間的關聯強度,包括IL-6、IL-1β、腫瘤壞死因子(TNF)-α 和CRP 等,結果表明IL-6、CRP 與抑郁癥之間存在著劑量-反應關系,且這種關聯最為穩定,而另外幾種標記物則與抑郁癥之間關聯較弱[23]。另外一項英國的大型隊列研究也證實了這一結果,研究人員采取孟德爾隨機化方法對冠心病的危險因素與抑郁癥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冠心病的危險因素,尤其是IL-6、CRP 及三酰甘油水平,可能與抑郁癥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24]。
一項納入了6 126 名捷克居民的橫斷面研究顯示,出現抑郁癥狀的受試者外周血CRP 水平要比無癥狀者高0.43 mg/L,即使在那些沒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受試者身上,這種聯系仍然存在[25]。這一結果也得到了芬蘭一項研究[26]的支持。另外,在一項納入18 例未經藥物治療、處于緩解期的女性抑郁癥(MDD)患者和18 例對照者的研究中,MDD 患者體內CRP 水平明顯升高,這說明CRP 水平的升高與抑郁癥狀及藥物干預無關[27]。同樣,一項關于患有抑郁癥的癌癥患者的研究,發現患有抑郁癥的癌癥患者血漿IL-6 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者[28]。
盡管有大量研究表明一些炎性標記物水平在抑郁癥與CVD 患者體內均有升高,但很難確定這類標記物是否同時作為二者的誘因,是否是導致這二者共病的機制之一,還是因為這二者共同作用導致了這類標記物水平的升高。
2.3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軸異常 HPA 軸是一個直接作用與反饋互動的復雜集合,包括下丘腦、垂體及腎上腺。在應對應激時,下丘腦首先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 和精氨酸加壓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這些激素接著刺激垂體前葉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最后ACTH 刺激腎上腺產生腎上腺皮質激素(主要是皮質醇)[29],而皮質醇反過來又抑制CRH 及AVP 的釋放,同時也可以直接抑制腦垂體產生ACTH。
聯想到當今教育,從家庭到社會,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重升學而忽視真善美的教育,正在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最近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幾件丑事,發人深省。諸如,列車上“博士強占女人的座位”;又如,廣州某大學幾位博士、教授為爭名奪利而發生的謀殺案等等,似乎印證了“高學歷低人品”的不良趨勢。這無疑是向家庭,向社會敲響了警鐘:抓為人教育,從小孩到成人,一層一層,一刻也不可放松。
HPA 軸是神經內分泌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參與控制應激反應,同時在焦慮、抑郁及認知功能障礙等病理生理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30]。例如,在相當一部分抑郁癥患者血漿、尿液以及唾液中檢測到皮質醇水平升高,以及垂體和腎上腺體積增大[31]。另外,一項納入361 項研究(包括18 454 例受試者)的Meta 分析顯示,抑郁癥患者表現出了明顯HPA 軸功能亢進的傾向;與健康受試者相比,抑郁癥患者體內皮質醇及ACTH 水平明顯升高,但CRH 水平沒有明顯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并未因性別而有所改變[32]。目前,這種抑郁癥患者體內HPA 軸活性的增加被認為主要與“糖皮質激素抵抗”有關,也就是與內源性糖皮質激素負反饋抑制功能減弱有關[33]。簡而言之,即內源性糖皮質激素主要通過與HPA 軸內的糖皮質激素受體(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及鹽皮質激素受體(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結合,從而對HPA 軸活性進行負反饋調控[34],而抑郁癥患者體內GR功能障礙,從而導致HPA 軸負反饋調節受損,進而導致HPA軸功能亢進。這一說法已經得到相關研究支持。例如,抑郁癥患者口服合成糖皮質激素地塞米松并不會抑制HPA 軸活性,然而在健康受試者身上,即使是很小劑量的地塞米松也可以抑制HPA 軸的功能。另外,在抑郁癥患者的外周組織中,例如外周血中的單核細胞及皮膚細胞,GR 的功能也有所減退;更為有趣的是,抗抑郁藥的應用增加了GR 的功能,減弱了糖皮質激素抵抗[35]。同時,使用激動劑或者拮抗劑來控制GR功能也起到了抗抑郁的作用[35]。
而在CVD 的發生發展中,糖皮質激素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過量的糖皮質激素,無論是內源性(如庫欣綜合征)還是外源性攝入過多,不僅會誘發CVD的危險因素(例如高血壓、高血糖、胰島素抵抗及體質量增加),還會加劇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36]。
2.4 自主神經功能障礙 在抑郁癥與CVD 的眾多共病機制假設中,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生機制。盡管目前抑郁癥與自主神經系統之間的直接影響作用尚不明確,但可以通過心率變異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來間接評估自主神經系統的功能。HRV 是指逐次心跳的周期變化情況,是反映交感-副交感神經張力及其平衡的一項重要指標。交感神經張力的增強或副交感神經張力的減弱均會使HRV 降低,而反之則會導致HRV 升高[37]。
盡管抑郁癥與HRV 之間的關系尚未完全闡明,但已有大量研究證實抑郁癥與HRV 的降低存在著一定聯系。VAN DER KOOY 等[38]學者對老年抑郁癥患者的HRV 特征進行分析,發現抑郁癥患者的全部心搏間期的標準差(SDNN)、全程相鄰心搏間期之差的均方根值(rMSSD)及低頻段(LF)顯著降低,而且高頻段(HF)也比對照組更低,這意味著老年抑郁癥患者的總體HRV(SDNN)更低,而且迷走神經張力也受到明顯抑制(rMSSD、HF)。與這一結果相似,KEMP 等[39]學者也發現未服藥的抑郁癥患者HRV 明顯降低,這一結果在同時患有焦慮癥的患者身上體現更為明顯。進一步的Meta 分析證明抑郁癥嚴重程度與HRV 存在負相關關系,亦即HRV 隨著抑郁癥嚴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同時也發現應用抗抑郁藥物后抑郁癥狀得到了緩解,但HRV 的下降并沒有得到逆轉[40]。然而LICHT 等[41]學者發現HRV 的變化可能由使用抗抑郁藥物所引起。
HRV 降低是發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危險因素,已得到了廣泛認可[42]。美國國家心臟、肺和血液學研究所曾公布CVD 的8 個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糖尿病、膽固醇異常、吸煙、缺乏運動、肥胖、年齡及家族CVD 病史[37]。而THAYER 等[37]學者通過總結既往的研究數據發現,這些危險因素大多與HRV 降低有關。
3 治療
目前抑郁癥的治療主要包括物理、心理及藥物治療,其中藥物治療是抑郁癥的主要治療手段,但抗抑郁藥物在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中的應用仍然存在爭議。
有研究證實抗抑郁藥物在這類患者中表現出有效性及安全性。一項韓國的隨機、雙盲、對照研究中,研究人員對近期發生過急性冠脈綜合征且伴發抑郁癥的患者用艾司西酞普蘭進行干預,結果顯示干預組患者在隨訪期間發生嚴重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明顯低于對照組[43]。ALMEIDA 等[44]學者也試圖通過研究來闡明抑郁癥、抗抑郁藥物及心血管事件之間的關系,隨訪12 年發現使用抗抑郁藥物降低了老年男性抑郁癥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而在未患抑郁癥的老年男性身上則沒有這種效果,這說明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降低可能是由抗抑郁藥物導致的抑郁癥狀改善所引起的。
但仍有一些研究顯示,在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中應用抗抑郁藥物并不會改善預后。MOOD-HF 研究[45]顯示,在慢性心力衰竭伴發抑郁癥患者中,與安慰劑相比,艾司西酞普蘭治療組并沒有明顯降低全因死亡率或住院率,而且抑郁癥狀也未得到明顯改善。另一項關于舍曲林對心力衰竭與抑郁癥共病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研究發現,盡管對于重癥心力衰竭患者來說是安全的,舍曲林并不比安慰劑顯著改善抑郁癥狀或心血管狀況[46]。OSTUZZI 等[47]學者所做的工作也證實了這一結果,他們發現在減輕抑郁癥方面,抗抑郁藥物比安慰劑更有效,但對于改善生活質量、降低死亡率及心血管事件方面,抗抑郁藥物與安慰劑相比并沒有明顯區別。
綜上,對CVD 伴發抑郁癥的患者,進行針對遠期心血管結局的抑郁癥干預措施是否有必要尚無定論,還需要更多高質量的臨床研究提供證據。同時,在選擇藥物之前要考慮到CVD 患者正在服用的多種藥物的相互作用,此外也要考慮藥物對患者基礎CVD 的不良反應。
4 結論
現有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抑郁癥與CVD 之間存在著高度共病關系。一些生物學因素,例如炎癥途徑、HPA 軸及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等可能是很重要的中介因素。同時,許多抑郁癥的標準治療方法在CVD 患者中的安全性已被證實。盡管對抑郁癥與CVD 之間關系的認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是機制問題:本課題組意識到了包括炎癥途徑在內的一些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關于這些因素是如何導致抑郁癥與CVD 之間的關系如此緊密仍不明確。接下來的研究可以著眼于與抑郁癥相關的血小板活性、炎性因子表達及血管內皮功能的病理生理變化。同時,遺傳及表觀遺傳因素可能也在抑郁癥與CVD 之間的復雜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需要通過研究去明確。這些研究的結果可以提高臨床醫生對這二者之間復雜關系的理解能力,以制定相關的治療方案。
目前,關于抑郁癥的治療是否會影響CVD 遠期結局這一問題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是,這并不會影響對于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的臨床管理,因為不管抗抑郁治療是否會改善CVD 的遠期結局,對于共病患者來說抗抑郁治療是必要的。因此,評估CVD患者抗抑郁治療的安全性可能更有意義。
其次,是否需要常規的對每一位CVD 患者進行抑郁癥篩查,以及應該如何對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進行綜合管理尚無定論。在進行藥物治療的同時,生活干預也是必要且有效的。但是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藥物依從性、改變生活方式及維持住健康的生活方式均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集中在如何協調醫院、社會、家庭對患者的支持,使得患者能夠規律用藥、開始并維持住生活方式向健康方向的轉變。本課題組提供了一種可能的以患者為中心的綜合管理模式(見圖1),以求提高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的生活質量。首先是抑郁癥的篩查,根據AHA 的建議,CVD 患者均應使用兩項患者健康問卷(the 2-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2)進行篩查,陽性者則使用9 項患者健康問卷進行進一步評估[48]。其次是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的管理,這需要專科醫生、社區醫院及家庭的共同協作用。

圖1 CVD 與抑郁癥共病患者的分級管理模式Figure 1 A tiered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depression
綜上所述,抑郁癥是CVD 患者的常見共病,可以通過篩查CVD 患者是否同時患有抑郁癥來識別出短期及長期不良心血管事件、過度醫療支出及不良生活質量風險較高的患者。盡管相關研究尚未明確對抑郁癥與CVD 共病患者進行抗抑郁治療是否會有明顯的心血管益處,但仍應堅持引進運動、行為認知療法及藥物治療來減輕患者的抑郁情緒,因為抑郁癥本身就是患者生活質量的基本決定因素。許多問題仍然存在,未來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闡明二者之間潛在的病理生理機制,并制定最佳的管理策略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
作者貢獻:王明鑫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撰寫論文;李素霞進行論文的修訂;宋濤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