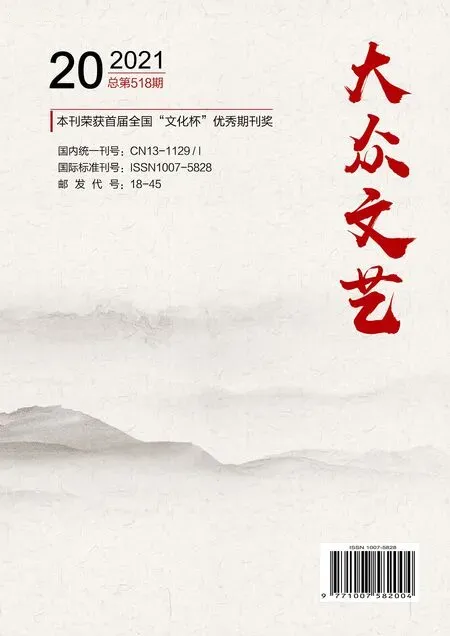也談古樂記譜之精確與模糊
(上海音樂學院,上海 200443)
一、古譜之模糊記譜
我國的古樂譜大都沒有現代意義的節奏標記。例如古琴文字譜、減字譜,二者都在譜面上標示出了音位、弦位、指法、樂句、樂段。減字譜還附有題解、后記等信息。但無論是文字譜還是減字譜,皆未標節拍節奏。工尺譜亦如此,只標譜字間的相對音高和形態概貌,而拍子則由演奏時的板眼加以演繹,但板眼在譜面上并無時值劃分。因此,工尺譜也被視為是一種框架型樂譜。
這些無節奏標識的記寫方式即“模糊記譜”。而模糊記譜的古樂譜須有懂譜之人加以解讀講授,否則僅憑譜面信息是很難對其進行研習的。因此,“口傳心授”“言傳身教”“傳、幫、帶”的教學模式成了傳統音樂的必備,而樂譜在這一傳授過程中只是一種輔助材料。近代以前,很多傳統戲曲的教學都無須樂譜,全靠師父逐句教唱。也因此,“模糊記譜”與“口傳心授”二者常常是共存的,否則便會出現傳承的斷層,即使有樂譜流存,今人也再難解讀,譬如被世人稱為“天書”的敦煌樂譜即是如此。
二、模糊記譜的原因
有人認為“模糊記譜”是古譜在草創時期的必經階段,但也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歷經千年傳承的古琴音樂卻依然“回避”節拍的標記,必然有更深層的文化內因。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于模糊記譜形成原因的各種推測,產生了“文化傳統說”“儒家哲學說”“道家哲學說”等不同意見。
1.文化傳統說
傳統音樂文化包括文人音樂、宮廷音樂、民間俗樂等。
古琴是最能體現我國古代文人音樂特質的樂器,“模糊記譜”亦是古琴藝術最典型的標簽。元代李冶《敬齋古今黈》云:“諸樂有拍,惟琴無拍。衹有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①在李冶看來,“琴樂無拍”是琴家“故意為之”。雖然李冶這一觀點有些牽強,但至少在其所處的時代,琴家們已經有了“音樂是否需要節拍”的觀念。而琴家“回避”節拍的行為可視之為一種“文人尚古情懷”。文人以雅樂為正統,視俗樂為“鄭衛之音”。而鄭衛俗樂最大特點就是節奏明快,因此,文人琴家們以回避節拍的方式來區別于鄭衛之音。
當然,創作、譜曲、記錄之人散見于社會各個階層,“固非文人學士所能專擅,亦非歌伎樂工所能獨攬”。②其他階層的記譜人更多則是受到了民間傳統的影響。這從散見于民歌、戲曲中的大量散板、拖腔就能看出,我國民間音樂對于自由節拍是非常偏愛的。雖然“拍板”“均拍”“節奏”等詞在我國古已有之,但我國傳統音樂中的“拍板”“均拍”更多是用來劃分樂句,而非劃分時值。加之民間音樂有很強的即興性和靈活性,而框架型記譜也給了這些音樂更大的發揮空間。
另外,也有人認為古樂譜不標節拍應與“一字一拍”的演唱傳統有關。對此,目前學界尚未達成共識。譬如對于姜夔以俗字譜記譜的《白石道人歌曲》中的節奏,楊蔭瀏、陰法魯在所著《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③一書中,就反對“一字一拍”說,而認同“失拍”說。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一書中也認為:“唐之俗歌絕非一字一音、一句一拍”。且“一字一拍”僅限聲樂,未含器樂,無法解釋為何那么多器樂譜也不標注節拍。
2.儒家哲學說
前述所引李冶《敬齋古今黈》這段文字,除體現“文人尚古情懷”外,也是儒家哲學“崇雅貶鄭”理念最典型的表現。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爾”,提出“放鄭聲”的主張。孟子“惡鄭聲,恐其亂樂也”。可以說,儒家哲學觀對古琴藝術影響至深。
而古琴音樂的中堅力量——文人士大夫階層,自漢代以后,就以儒家哲學為標桿,從各個方面影響了琴學的發展和傳承。漢代劉向《說苑·修文》云:“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即儒家認為,君子“以琴修德”,而傳承古琴之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德行,否則不足以托付琴學。明代琴家朱權就堅定地保持這一理念,其《神奇秘譜》臞仙神奇秘譜序:“使師之所授者,必擇其人而傳焉……不經指授者恐有訛謬,故不敢行于世以誤后人”。即古琴研習須經師門相授,不得妄傳。這種將古琴視為一種君子文化而不容褻瀆的音樂觀,造就了古琴“口傳心授”的傳承模式。師與生須直接交流,才能考察所傳之人的道德品行。而不同師門又有不同的演繹風格,這也使同一琴曲在不同流派有不同傳譜。各家琴派所傳樂譜,靠“面授”傳承,這種傳授模式使得節奏的記錄就不那么重要了。
3.道家哲學說
“大音希聲”是道家最經典的音樂美學觀。也是道家心中最理想的音樂形態,如《道德經》所言:“聽之不聞名曰希”。
三國時玄學家王弼《老子指略》云:“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為物也則混成,為象也則無形,為音也則希聲,為味也則無呈。”④這段文字將道家音樂美學觀概括得非常透徹——無形之樂是一切音樂的宗主。它不宮不商,無法感知。
道家“崇本息末”,不為奇淫巧技所迷惑。這與中國傳統音樂的審美極為契合,如主張“黜俗歸雅”的古琴音樂就極重音樂意境之本,視節拍節奏如“淫哇之聲”。①認為沒有了節奏的束縛,那些細枝末節的奇淫巧技也就無法擾人心智了。
道家哲學追求“物與形”之外的無盡世界,這種哲學觀在中國傳統音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譬如戲曲之潤腔、古琴之泛音,這些音樂形態的無盡表現力是現代錄音技術所難以復刻的,而“模糊記譜”卻恰好為此提供了無盡的空間。
無論是未標節拍的文字譜、減字譜,還是只記“框架”之工尺譜,在道家眼中,譜面信息都只是“物與形”,更廣闊的則是“無形無盡”的譜外之“大音”,它們不為譜面所標識,卻是音樂之根本。
三、古樂之精確記譜
“精確記譜”的理念始于近代,隨著五線譜、簡譜的傳入,傳統音樂的節奏記寫觀念逐漸發生了轉變。加之近代以后,“口傳心授”已無法滿足音樂普及的需求。傳統音樂開始逐漸改用簡譜記譜,僅保留部分傳統符號以供某些特定音樂種類提高記寫的準確性。因此,改變傳統記譜方式成了當代眾多藝人琴家的探索目標。而“既能保留傳統,又能做到精確”是其中的主要課題。從早期參照西方記譜方式的“四行鏡譜”“三行七弦琴譜”,到當代將五線譜與減字譜結合的“兩行譜”,這些新型記譜方式被逐漸開發了出來,使得傳統音樂被現代樂譜“量化”“固定”了下來。而樂譜也由此成了一種“精確而標準化”的學習教材。
“定腔定譜、統一范本”成為傳統音樂一種新的記譜模式。其進步性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畢竟,現代社會需要高效而快捷的音樂傳承模式。而且,在錄音技術、網絡媒體等手段的加持下,音樂想不“不精確”都難。然而,我們又不禁要問:傳統音樂作為一種“活態”藝術,它真的需要被“精確”和“量化”嗎?
四、傳統音樂是否需要被“精確記錄”
近代音樂家劉天華在其所輯《梅蘭芳歌曲譜》“凡例”中寫道:“皮黃唱腔變化甚多,往往同此一句,而個人之唱法時有不同。”在傳統戲曲中,同一出戲,不同流派常有不同演繹。同一人在不同場合亦會有不同發揮,可謂是流派紛呈,常演常新。“即興性”是民間音樂的一大特色,而現代記譜法是無法做到完全精確記錄這些即興演繹的。
無獨有偶,除了漢族傳統音樂,我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在現代社會也同樣面臨著“是否需要被精確”的問題。
周吉在《關于維吾爾族十二木卡姆樂譜記錄的學術思考》一文中提出:“對于某個樂種、某首樂曲與眾不同的‘個性’,一定要寧‘詳’勿‘略’,以期盡可能充分地用樂譜反映出它的獨特風貌神韻。”⑤
誠然,精確記譜有助于音樂的傳承和保存。很多瀕臨絕跡的民族民間音樂正是因為有了現代記譜手段才得以被搶救了回來。但是,很多民族民間音樂在結構、樂調、節拍等方面都非常復雜。譬如上文新疆維吾爾族十二木卡姆音樂,就存在四分中立音、散板自由的序唱節奏、演唱者時值的即興發揮等現象。且除了復合節拍、混合節拍,其中還存在一種極為特殊的增盈節拍。此外,還常常出現“游移和顫動”的“潤音”“活音”等“不準”的音。這些都增加了精確記譜的難度。
而且,這些“活音”真的需要被“精確記錄”嗎?在維吾爾族人看來,“正是這些所謂‘不準’的音, 給維吾爾族音樂帶來無窮的韻味……音樂的表現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活音’體現出來的。能否出色地演奏或演唱‘活音’被人們當成衡量樂手、歌手水平高下的一個重要標準。”⑥藝人們求新求變的即興發揮,使得這些“活音”有了無限可能。這一次的“精確記譜”未必會發生在下一次藝人的表演之中,也許譜中記錄下的恰恰是某個藝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即興發揮。即使每一次的即興創作都能被精確記錄,面對如此“海量”的樂譜,后人在傳承時又該選擇哪個即興“版本”?
五、結語
“精確記譜”模式除用于搶救民間音樂、便于音樂傳承之外,是否適用于所有傳統音樂?那些以“即興”為特色的民間音樂,是否真的需要被“精確”記錄?傳統音樂中那些韻味深長的泛音、潤腔等“活態”特征若都被現代樂譜“定量”規范了,那它原本的藝術魅力還存在嗎?
任何樂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即使是現代錄音技術,也只是錄下了一時一刻之形態,音樂的表現空間是無限的。現代記譜理念是否應該跳開那種“必須精確”的思維束縛,去回望一下古樂譜中那浩瀚而又“無形無盡”的“大音”之美,探索一種既便于傳承又能保留傳統的記譜方式呢?
注釋:
①(元)李冶撰,劉德權點校,敬齋古今黈[M].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2月第1版,第182-183頁.
②任中敏.敦煌曲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79頁.
③楊蔭瀏,陰法魯.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頁.
④(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⑤周吉.關于維吾爾族‘十二木卡姆’樂譜記錄的學術思考[J].音樂研究,1994年第1期,第29-33頁.
⑥杜亞雄,周吉.也談維吾爾族音樂中特殊調式的稱謂[J].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1期,第60-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