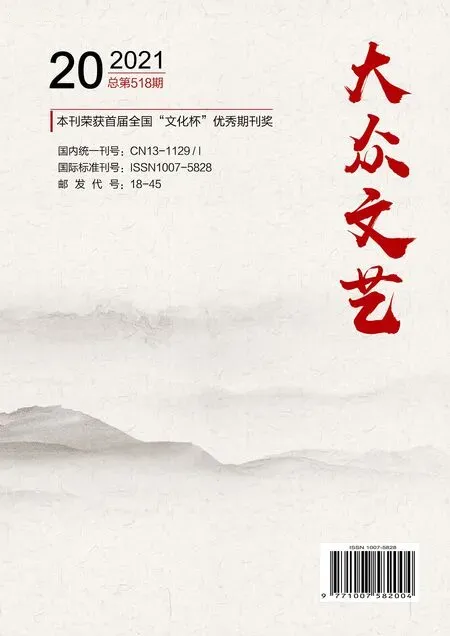藝術學視域下的中國音樂史
(四川音樂學院學報社,四川成都 610021)
一、中國藝術學發展歷程概述
中國音樂史的發展,得益于現代藝術學的發展。中國藝術學學科的正式建立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時期,由于其時社會條件的巨變刺激和有識之士的推進共同推動了其從中國傳統學術形態轉變為現代藝術學形態。整個過程始于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上半葉蓬勃發展,直到21世紀已趨向穩定并逐漸走向獨立。一直以來,其不但肩負著對傳統學術資源傳承的重任,同時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汲取優秀外來文化,尤其是深受近代西方科學藝術的影響,逐漸形成了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并面向世界的視野。
在20世紀之前,中國已有一套自己的藝術史料和與其相關的著述,但這些著述多不成體系,仍屬于局部、不連續的敘述,并未能真正地進入到整個藝術學到研究范疇中。20世紀早期,“西學東漸”使“藝術學”被介紹到中國,其中包括典型的日本學者黑田鵬信《藝術概論》,以藝術本體為中心對藝術鑒賞和批評進行探討。其后,俞寄凡《美學綱要》(1922)和豐子愷《藝術概論》(1948)為“藝術學”增添了豐富的語意,后者詳細地論述了藝術的起源、形成、分類、制作和本質等問題,此后,隨著張澤厚《藝術學大綱》(1933)的出版,中國有自己第一部以藝術學命名的著作。
20世紀上半葉是“藝術學”在中國引入的繁盛時期——盡管在學科體制上一直未能確立其標準的模式,但眾多學者的努力一直未停止探討其內涵和學科構成。自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的藝術學發展經歷了幾次轉型,直到20世紀初90年代初,藝術學在中國人文學科序列里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儼然成為一門真正的藝術學,不但帶有新時代烙印,同時還富含人文社會科學屬性,可以說一個嶄新的藝術學時代正式拉開序幕。[1]
21世紀是藝術學理論發展的鼎盛時期,同時,該時期標志著藝術學逐漸走向獨立并且具有獨立的科研內涵。就藝術學基本理論而言,其可以說是不同門類藝術史論的基礎,諸如舞蹈學、電影學、戲劇學、美術學以及音樂學等門類學科的理論研究,均為藝術學提供了豐富的內涵。而,藝術學的總體視野,始終規范和影響著旗下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史學觀點。
二、作為藝術學分支的中國音樂史
就總體而言,各門類藝術史論是藝術學重要的組成部分,藝術學為其他門類的藝術史學論提供了豐富的藝術基礎理論,其中涉及了藝術評論、美學、史料以及原理等內容。以藝術原理為例,其主要涵蓋了涉及各種藝術現象的本質特征,發展規律以及由社會功能所得出的基本理論等內容。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如音樂、表演等理論等分支學科的發展,并為其提供理論基礎。各學科和藝術史是基于不同類型藝術史的歷史研究,是建立在各門類藝術史基礎上的史學研究,緊密相連、相互啟發、相互構成。
音樂史和廣義的歷史研究之間存在一定差異,音樂史與人類的審美史直接相關。與其他類型的歷史研究不同,音樂歷史本身具有獨特性,因此具有時代性和歷史性雙重特征。音樂不僅源于音樂的誕生,其審美和歷史通常也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音樂美就是音樂美學史,兩者并無實質性差異。就音樂史而言,其和其他史學門類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原因在于研究對象的不同。把音樂看作研究對象,其存在多種屬性,例如復雜的可變性和不確定性,這些屬性無法用清晰的語言來表達或交互。其不但需要妥善處理美學和歷史之間的關系,還涵蓋了包括科技、經濟制度、政治環境以及歷史發展等在內的社會因素。以中國古代音樂史為例,該研究通常側重于音樂活動以及創作歷史,但是幾乎很少涉及特定作品,抑或是作曲家的歷史。
中國音樂史的特殊之處使得其與西方的音樂史的研究有所區別。一方面,中國傳統民間音樂歷史悠久,保存了許多古代音樂元素,研究需要整體把握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文化傳統的不同,讓中國的音樂大部分帶有特有的文人氣質,以及對人文意境的描述。我國真正開始對音樂史學進行研究的時間與藝術學的興盛時間相同,近代以來,由于在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國,不但帶來了國外先進的理論與技術,同時還引入了西方音樂,并對中國傳統音樂進行研究,如蔡元培、蕭友梅、王光祈、黃自等主張“以西為師”,以期通過西方優秀的作曲方式,來豐富我國傳統音樂理論,從而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音樂體系。[2]不僅如此,在交叉學科思想的影響下,我國音樂史學家開始將研究的方向轉向音樂圖像學、音樂文獻學以及民族學等領域,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將其運用至音樂史的塑造之中,為中國音樂史提供了多角度、深層次的視野。
三、具有審美特征的音樂史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藝術審美可以說是人類最為原始的直覺,而這種直覺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不斷進行變化,所以,站在這個角度來說,美學與歷史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而關于美的定義、意識以及形成都囊括了兩方面因素,針對不同時期的美學觀念,均存在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意識、音樂史實以及音樂作品等內容。[3]進而可知,藝術和歷史具有內在的聯系,其連接 橋梁為審美特征,它存在于所有藝術作品之中。
在音樂史寫作中,大部分都是沉浸于歷史敘事的客觀性、連續性和準確性,并經常將音樂史視為獨特的歷史范疇而忽視其屬于藝術史范疇,具有特殊的歷史和美學維度的特點。音樂史很難通過簡單地敘述時間來使音樂史得以完整重現,所以非常有必要把音樂史進行結構性的劃分,只有這樣方能實現深刻認知以及理解,而美學可以說是歷史美學與歷史維度之間的結點,是塑造結構音樂史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如卡爾·達豪斯(Karl Dalhaus)在《音樂史原理》中所說:“歷史與藝術是一個二元論的概念。”在研究音樂史時,非常有必要在歷史和藝術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只有音樂史和音樂美學相結合才能產生互動效果,才是結構音樂學研究的節點——歷史與美學之間的和諧畢竟是人類審美意識的起源,而個人只能依靠客觀現實,才有可能產生審美意識。作為藝術作品,音樂作品自身則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在對作品進行解析時,既要避免僅僅從主體的范疇進行闡述,也要避免添加過多的主觀因素,進行一意孤行的解讀。
當然,在處于歷史上不同時期時,對于音樂的審美觀念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各個時期的審美標準均有可能作為撰寫整個音樂通史的基礎。審美作為音樂史的特征,存在于史學史為美學發展的提供基礎,為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基礎以及理論支撐,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歷史可以看作為音樂美學的載體,而美學則又是社會史實的體現,所以,不同時期的美學觀念,具備與之相對應的審美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指引著社會文藝的發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中審美觀念也隨之而變化。這些審美的標準,成為研究音樂史的研究中的重要特征和因素。
四、藝術學視域下的反思
自從進行二十世紀以來,我國音樂史學可以說歷經了百年的發展,不管是通史性著作,抑或是斷代史和專題探析,都實現了較大突破,碩果頗豐。但是需要強調的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瑕疵。我國學者劉再生提出:“盡管學術觀念在不斷地變化,音樂學各分支學科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古代音樂史學實現了長足進步,然而,要想打破《史稿》的史學結構和局限,務必要對斷代史進行深入探析,從而為音樂充當文化的歷史載體奠定夯實基礎。”而學者項陽則提出“關于我國音樂文化史的撰寫,既可從欣賞、審美的角度來進行,同時也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結合音樂演變特征來進行。”
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下雖然藝術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然而站在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其依舊類屬于新興學科。因此,關于學科建設和學科理論的討論仍然不斷。作為藝術學下的分支,中國的音樂史也在20世紀涌現出一系列經典著作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從藝術學的視域下看,它的擴展不僅包括整個文學藝術背景下的學術發展歷史,同時還囊括了基于特定藝術類別的發展歷史支持學術歷史的許多學術歷史內容,揭示了音樂史的發展過程,并在對文獻歷史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各流派的學術觀點,科學地揭示其在歷史研究史上的學術成就和不足。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關于對藝術學歷史的研究,可借助對應的方式來進行,詳細解釋來說,就是將各門類藝術看作研究對象,把其所涉及的專論以及原理視作分支理論,以此來進行深入研究。就藝術學與音樂史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而言,可以看作為母系統和子系統的關系,但是它們也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均基于美學的方式,來深入剖析事物的本質、發展規律以及社會功能等問題,因此站在這個角度來說,音樂史和各門類藝術之間,其核心界定必然具有緊密的聯系。
作為藝術學下的分支,中國的音樂史也在20世紀涌現出一系列經典著作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并影響至今。基于時代的發展,學者們從深度化學以及學科發展等不同的角度,深入剖析了音樂史所得的一系列成果,這也是音樂史研究領域的基本學術意識。從功能的角度出發,可以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研究,從藝術學的視域來書寫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探索背后所產生的年代、受眾人群、社會特征等問題,彰顯出了當代學者們對于音樂史發展的敬重以及學術追求。在撰寫我國音樂史時,非常有必要對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歧路引以為戒,不斷發展觀念和拓展觀念,針對時代進行變化,在藝術學視域下更新方法的基礎上做出更先進的應對,立足中國傳統以探索中國音樂文化史的研究觀念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