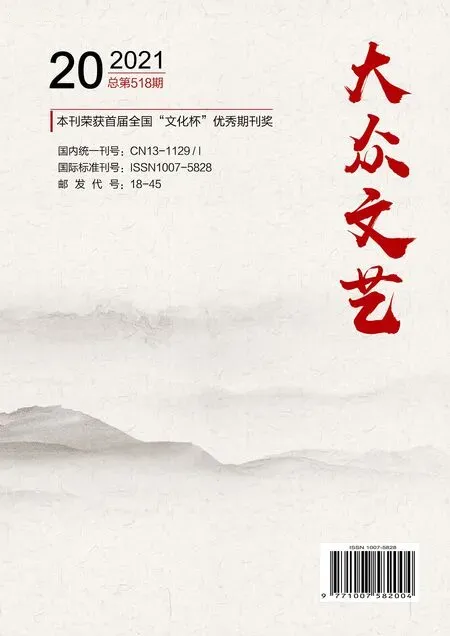癡情錯(cuò)付多情郎 求愛不得怨女現(xiàn)
——賞析能樂《葵之上》中的物哀美學(xué)
(武漢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湖北武漢 116600)
能樂是一種帶有鮮明時(shí)代的特征的日本古典戲劇,在世阿彌和觀阿彌父子的大力推動(dòng)下,能樂由最初的藝能轉(zhuǎn)變成一種集舞蹈、音樂、辭章為主的古典戲劇模式。自1401年,世阿彌寫成《風(fēng)姿花傳》以來,這種具有強(qiáng)烈寫意性的戲劇模式有了更為貼切的美學(xué)觀即“物哀”“風(fēng)雅”和“幽玄”。而《葵之上》這部能樂作品,就是以物哀之美見長的集三種美學(xué)風(fēng)格為一體的經(jīng)典作品。它作為一部題材耳熟能詳、劇情扣人心弦、演出難度極高的能樂經(jīng)典,在劇目大量流失的能樂舞臺(tái)上,多年來一直不斷上演。[1]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文學(xué)家以此為藍(lán)本進(jìn)行二次創(chuàng)作和模仿,很多電視劇和電影中都有它的影子。本文將從物哀美的美學(xué)角度賞析這部經(jīng)典作品。
一、能樂中的物哀美
“物哀”是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種美學(xué)概念。這里的物指的就是人類本身所處的外部世界,簡言之就是客觀事物的存在。而哀指的就是人類對外部世界的一種主觀表達(dá)。它包括但并不僅局限于“哀傷”。物哀美的內(nèi)涵是個(gè)體對世界萬物有一種獨(dú)特的審美意識(shí),這種審美意識(shí)能夠促使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內(nèi)在情感達(dá)到和諧美的高度統(tǒng)一。所以說,物哀美不是理智的邏輯思考和分析,而是在體悟世界的過程中由心流露出的真感情。這種感情轉(zhuǎn)瞬即逝且難以捕捉,所以它細(xì)膩、真摯、風(fēng)雅。這種物哀美學(xué)符合了日本人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一瞬間耀眼燦爛的美要遠(yuǎn)勝于一生的庸碌平凡。簡言之,物哀是一種微妙的感受力。
物哀這個(gè)詞首先出現(xiàn)在日本第一部文學(xué)作品《古事記》里,后來《源氏物語》中也多次提及了物哀這個(gè)詞。而“物哀”作為一種美學(xué)觀,是最先由本居宣長在《日本物哀》這本書中提到的:“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風(fēng)流雅趣,就是要有貴族般的超然和優(yōu)雅、女性般的柔軟細(xì)膩之心,就是要從自然人性出發(fā),不受道德觀念束縛的對萬事萬物的包容、理解與同情,尤其是對思戀、哀怨、憂愁、悲傷等刻骨銘心的心理情緒有充分的共感力。”[2]這種日本傳統(tǒng)美學(xué)觀念不僅在文學(xué)作品上能夠略見一二,能劇表達(dá)方面也更是讓人印象深刻。能劇之所以能和物哀美學(xué)高度融合,這是與它的表現(xiàn)方式密切相關(guān)的。能劇劇情簡單且沒有強(qiáng)烈的矛盾沖突,其核心不在于傳達(dá)高調(diào)張揚(yáng)的熱鬧情緒,而在于平靜地審視生命和死亡的真相。沒有表情的“能面”下面其實(shí)蘊(yùn)藏著的是日本人對于生命哲學(xué)的領(lǐng)悟和對于死亡終極意義的探索。當(dāng)能劇在反復(fù)訴說生命短暫且人生無常的時(shí)候,自然而然就會(huì)流露出哀傷、凄婉、毀滅、消亡等復(fù)雜情感,進(jìn)而就會(huì)傳遞出一種濃厚的“物哀”之美。
除此之外,能劇深受日本禪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響。能劇大多都在表現(xiàn)一種永恒的流動(dòng)和短暫的停留。在日本人看來,只有死亡才能消解這種無常的變動(dòng),也唯有死亡才能讓生命達(dá)到一種永恒。在這種生死觀和世界觀的影響之下,能劇在不斷追求一種人物合一之時(shí)所產(chǎn)生的和諧美感。這種美感是無常變化之中的片刻永恒,就是物哀之美。
二、六條妖女形象的物哀美
《葵之上》這部能劇取材于《源氏物語》中的六條御息和光源氏的故事。世阿彌對這一故事進(jìn)行了改編,縮減了光源氏和葵之上這兩個(gè)主要人物,僅將六條的怨靈作為了整部能劇唯一的主角。除此之外,《葵之上》這部戲劇將六條御息所的心理情感變化作為了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脈絡(luò)。由最初的怨念憂郁到后來的因妒生恨,六條這種糾結(jié)且扭曲的情感變化也通過能面道具的變化展現(xiàn)出來。她雖然是妖女,但是卻有著自己刻骨銘心的情感體驗(yàn)。可以說,六條的形象是日本傳統(tǒng)文藝作品中女鬼形象中最特別的那一個(gè)。
首先,六條之所以會(huì)變成妖女,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對光源氏的愛和對葵之上瘋狂的嫉妒。這種復(fù)雜又矛盾的感情凝聚成一股怨氣深埋在她的心底。當(dāng)這股怨氣隨著受到光源氏的冷落和別人的鄙夷,就會(huì)變得愈加沉重,以至于到最后她已經(jīng)無法控制,失去理智,變成了惡鬼“般若”。逐漸地,六條淪落為了自己情感的奴隸。
其次,六條的怨靈并不是死后之人亡靈作祟,而是活人所凝成的來自心里最深處的怨恨和不甘。原本的六條是高雅出眾的女子,絕非歹毒陰險(xiǎn)的小人。但當(dāng)她愛而不得又受到別人侮辱的時(shí)候,她就從一個(gè)人變成了一個(gè)“妖”。在這種復(fù)雜情感的驅(qū)使之下,她做出了傷天害理之事。也正是因?yàn)檫@個(gè)原因,才使得《葵之上》這部能劇里妖女六條的形象有了一層物哀之美。這種物來自光源氏對她的冷落和拋棄,而哀就是基于這種現(xiàn)實(shí)情況下的愛而不得。世阿彌以他敏銳的心緒和對古典文學(xué)的消解再造的能力,塑造了這樣一個(gè)兇惡但不殘忍、可悲但不可恨的癡情女子形象。[3]
在舞臺(tái)呈現(xiàn)方面也有著物哀美的體現(xiàn)。六條是整個(gè)舞臺(tái)上唯一身著華美精致和服的人。她手執(zhí)折扇,面帶泥眼假面,雖氣質(zhì)高貴但備受煎熬。當(dāng)她凄婉地在臺(tái)上訴說自己為情所困的境遇的時(shí)候,她儼然變成了一個(gè)焦慮且無奈的癡情人。六條的人物形象就是“物”與“哀”的完美融合。
隨著劇情的開展,巫女已經(jīng)無法鎮(zhèn)住六條的怨念,她由泥眼面變成了怒目圓睜、尖角獠牙的般若面。雖然六條的面具可怖嚇人,但是她的幾縷頭發(fā)在額前散落,給觀眾呈現(xiàn)出一種無法言說的悲苦和凄涼。變成惡鬼般若的她也并不是讓人完全恐懼和厭惡的女鬼。細(xì)細(xì)端詳她的動(dòng)作,會(huì)從她的一舉一動(dòng)中窺探到她內(nèi)心的寂寥與凄苦,混雜著悲傷和苦痛情感的六條讓人難以忘懷且心生悲憫。
從某種方面來看,六條的女妖形象背后折射的就是一種傳統(tǒng)的物哀美學(xué)。她的物哀美在于能夠愛己所愛,有自己的思戀、哀怨、憂愁等刻骨銘心的心理情緒,也有自己對世態(tài)炎涼的無奈慨嘆,進(jìn)而和觀眾形成了一種情感共鳴。她的物哀美也在于瞬間的綻放,愛情讓她獲得最執(zhí)著的力量和最痛苦的來源,為了能夠?yàn)樽约夯钜淮危龑幙沙翜S一次,也不愿默默一生。為心所動(dòng),同時(shí)也為心所感。她的物哀美還在于放逐,這種放逐是內(nèi)心情緒的一種傳遞。六條雖然變成惡鬼般若,但當(dāng)她的怨靈被法師驅(qū)散后,仍然對自己的惡行感到悔恨。這種放逐一邊驅(qū)使著她去報(bào)復(fù),一邊又在使她陷入自我怨恨情緒當(dāng)中。因?yàn)閻酆藿豢椝圆艜?huì)產(chǎn)生物哀美感,才會(huì)讓人從中得到一種世態(tài)炎涼的悲傷。
《葵之上》這部戲劇里的六條御息所是物哀美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身上所展現(xiàn)出來的愛與恨,就是外界的“物”與情感的“哀”達(dá)成一致的情趣世界,也是外部世界和人物內(nèi)心情感的高度契合的美感世界。
三、《葵之上》戲劇情節(jié)的物哀美
《葵之上》這部戲劇取材于物哀美代表作《源氏物語》中的一個(gè)故事。其文學(xué)內(nèi)涵本身就帶有一種濃厚的物哀美,在世阿彌的改編之下,這種物哀美由單純的文學(xué)故事變成了戲劇情節(jié)。它不僅僅體現(xiàn)在戲劇人物的關(guān)系的編排上,還體現(xiàn)在整個(gè)故事的發(fā)展脈絡(luò)上。
戲劇一開始,一個(gè)宮廷官員上場解釋了葵之上被鬼魂附體,訪遍高僧大德都無果,巫女瑛日被招來驅(qū)趕鬼魂。這時(shí)候帶著泥眼面的六條走上了舞臺(tái),她掩面哭泣,訴說自己的不公:
“世法無常意,生滅瞬息翻。風(fēng)吹芭蕉亂,川流浮沫幻。昨日花綻,今朝夢散。不驚覺,何癡暗。舊哀之上添新恨,此傷無刻難忘懷。心求稍寬轉(zhuǎn)。”
在巫女的詢問之下,她講述了在不久前一次節(jié)日聚會(huì)上,葵的車把六條的車擠到一邊,讓她受到了人格上的侮辱:
“不何時(shí)癡情一恨從心發(fā),就如個(gè)朝露掛上野蕨芽。但只求報(bào)得怨憎些,吾正應(yīng)現(xiàn)身到此家。……真?zhèn)€是恨怨心含。不將此婦打,吾意難甘。”
僧人的出現(xiàn)將整部劇帶入了高潮部分,六條的怨靈和僧人激烈交戰(zhàn)后,被佛經(jīng)打敗。她的怨靈得到了消散,佛法終究拯救了六條的靈魂。
整部劇沒有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和驚心動(dòng)魄的劇情設(shè)計(jì),也沒有聲嘶力竭的爭吵,有的只是六條在臺(tái)上反復(fù)卻又執(zhí)著地訴說著人生的世態(tài)炎涼和感情的善變。這種傳遞給觀眾的無奈和哀怨,也是日本獨(dú)特物哀美學(xué)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整部劇中有兩個(gè)情感高潮,一個(gè)是六條哀怨達(dá)到極點(diǎn)變成惡鬼般若,另外一個(gè)則是她與僧人斗法失敗,黯然離場。這兩個(gè)情感高潮是六條的兩次轉(zhuǎn)變,也能從中看出她“哀怨-妒恨-愧疚”的情感變化。當(dāng)六條登場,訴說自己的悲慘境遇,淚落如雨的時(shí)候,她沒有號(hào)啕大哭,而是掩面啜泣。將自己無限的情感都克制在有限的幾個(gè)動(dòng)作之中,從而為第一個(gè)情感高潮的來臨埋下伏筆。讓觀眾看完既為六條的命運(yùn)感到惋惜,又能從中她的命運(yùn)遭遇中感受到絲絲物哀之美。能劇中的情感都講究“恰到好處”,不會(huì)用力過猛也不會(huì)讓人覺得少了一點(diǎn)味道。這種恰到好處也正是能劇所講究的獨(dú)特物哀美學(xué)。
同樣地,在第二個(gè)情感高潮來臨的時(shí)候,僧人用佛經(jīng)對六條進(jìn)行加持,隨后她的怨念逐漸消散不見。舞臺(tái)上只留下了充滿悔恨的六條,她將自己的手放在太陽穴上,在凄切的伴奏中黯然離場。黯然離場中帶著余愁未盡和說不出的凄涼,這種情感是自然且真實(shí)地流露,也是此時(shí)此刻人與外在的一種和諧美的統(tǒng)一。它在觸動(dòng)日本人美感神經(jīng)的同時(shí),也讓人們的內(nèi)心深處產(chǎn)生了一種無法言喻的滿足感。[4]
所謂“物哀”是一種淡淡的且若有若無的離合之感,它像是兩種對立情感之間的過渡。在《葵之上》這部戲劇中,不論是人物形象還是戲劇情節(jié)都由內(nèi)向外透露著一種朦朧的物哀美學(xué)。
《葵之上》這部劇之所以充滿著物哀美,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椤皭邸薄_@種男女之情所生發(fā)出來的一種愛。這種愛讓六條瘋狂也使她嫉妒生恨,如果沒有這么強(qiáng)烈的愛也自然不會(huì)有如此強(qiáng)烈的恨。所以歸根到底,這種愛就是整部劇中物哀美的源頭。但凡為人,難抵情感之誘惑。不論是誰都難以坦然面對自己所愛之人,所以正是因?yàn)檫@種無法克制的愛才“物哀美”更加刻骨銘心。《葵之上》這部劇雖然最終以六條的悲劇結(jié)尾,但是其中蘊(yùn)涵著的是一種對于人生短暫無常之感的慨嘆。并在此基礎(chǔ)上,作者表達(dá)了對于美好事物凋落的一種無可奈何的物哀美感。《葵之上》這部能劇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成為一代傳奇,這和物哀美學(xué)對其影響是分不開的。換言之,是物哀美讓這個(gè)古老的傳說故事,在當(dāng)今時(shí)代有了更多種表達(d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