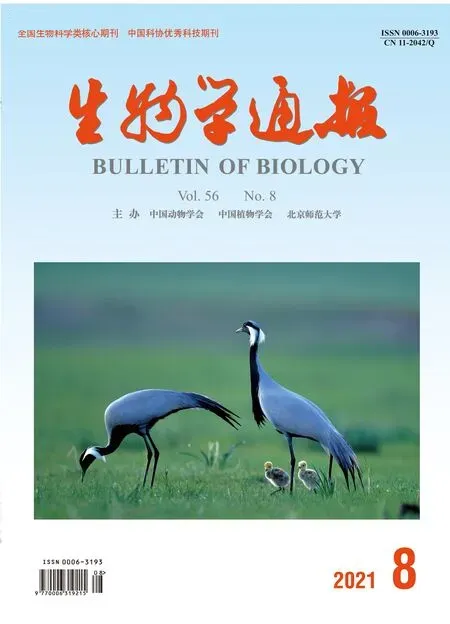熒光顯微技術(shù)與生命科學(xué)發(fā)現(xiàn)
衛(wèi)紅萍 任衍鋼
(陽泉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山西陽泉 045200)
顯微成像技術(shù)的發(fā)展是生命科學(xué)的重要驅(qū)動(dòng)力之一,其中,熒光顯微技術(shù)扮演著及其重要的角色[1]。依據(jù)2009 年《自然細(xì)胞生物學(xué)》(Nature Cell Biology)刊出《光學(xué)顯微鏡發(fā)展里程碑》的21項(xiàng)突破性進(jìn)展中,至少有一半與熒光顯微技術(shù)密切相關(guān)。
1 熒光顯微技術(shù)的發(fā)明
熒光現(xiàn)象最早的描述被認(rèn)為是16 世紀(jì)西班牙植物學(xué)家莫納德斯(Monardes)對(duì)軟質(zhì)木質(zhì)提取物熒光特性的報(bào)道。19 世紀(jì)早期研究發(fā)現(xiàn),許多標(biāo)本在紫外線照射下會(huì)發(fā)出熒光。1852 年,英國(guó)科學(xué)家斯托克斯(Stokes)在其出版的書中首創(chuàng)了“熒光”(fluorescence)一詞。1882 年,德國(guó)科學(xué)家埃爾利希(Ehrlich,1908 年諾貝爾生理學(xué)或醫(yī)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首先用熒光染料——熒光素鈉確定眼睛中體液分泌的途徑,開啟了動(dòng)物生理學(xué)使用熒光染料的先河。
早在19 世紀(jì)熒光方法就被應(yīng)用,熒光顯微技術(shù)的發(fā)明則在20 世紀(jì)后。德國(guó)物理學(xué)家科勒(K?hler)受阿貝(Abbe)發(fā)現(xiàn)波長(zhǎng)越短分辨率越高的啟發(fā),于1904 年在德國(guó)耶拿的蔡司光學(xué)工廠制造了第1 臺(tái)紫外(UV)顯微鏡。科勒注意到,在紫外線照射下某些物體會(huì)發(fā)出較長(zhǎng)波長(zhǎng)的光——熒光。依據(jù)這種現(xiàn)象,德國(guó)物理學(xué)家海姆施塔特(Heimst?dt)于1911 年建造了第1 臺(tái)熒光顯微鏡[2]。但是,因最初對(duì)成像物體自身熒光的依賴,以及對(duì)透射光和暗場(chǎng)聚光鏡的需要限制了該顯微鏡的使用。
20 年后,奧地利的研究員海廷格(Haitinger)和其他科學(xué)家一起開發(fā)了二次熒光顯微技術(shù)。與第1 次熒光顯微技術(shù)不同的是,這次可將外源熒光化學(xué)物質(zhì)應(yīng)用于樣品,并創(chuàng)造了“熒光色素”術(shù)語。1929 年,德國(guó)藥理學(xué)家埃林格(Ellinger)和解剖學(xué)家赫特(Hirt)設(shè)計(jì)了第1 臺(tái)以紫外線為光源,使之發(fā)出熒光的落射熒光顯微鏡,并對(duì)注射熒光素和色氨酸的嚙齒類動(dòng)物的腎臟和肝組織進(jìn)行了觀察。1942 年,庫恩斯(Coons)用異硫氰酸熒光素標(biāo)記抗體,標(biāo)志著免疫熒光標(biāo)記技術(shù)的誕生。1948 年,索爾茲曼(Saltzman)介紹了血液中水楊酸鹽的熒光分析方法[3],開啟了熒光分析方法的先河。
2 熒光顯微技術(shù)的發(fā)展
20 世紀(jì)30 年代雖已發(fā)明了比光學(xué)顯微鏡分辨能力更強(qiáng)大的電子顯微鏡,但其仍無法觀察到活細(xì)胞的生理變化特征。光學(xué)顯微鏡雖可觀察動(dòng)態(tài)生命,但會(huì)受到光學(xué)方面的限制。為此,科學(xué)家為克服光學(xué)顯微鏡中的難題進(jìn)行了不斷的技術(shù)突破。主要體現(xiàn)在2 個(gè)方面:一是GFP(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簡(jiǎn)稱GFP)的發(fā)現(xiàn)與應(yīng)用,二是熒光顯微鏡的改進(jìn)與應(yīng)用。
2.1 GFP 的發(fā)現(xiàn)與應(yīng)用
2.1.1 GFP 的發(fā)現(xiàn) 就生命科學(xué)而言,熒光顯微技術(shù)本身的意義在于提高顯微鏡的分辨能力,多年來科學(xué)家也從未間斷過尋找有效的熒光標(biāo)本。GFP 的發(fā)現(xiàn)正是這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突破。1962 年的某一天,日本科學(xué)家下村修(Shimomura)在下班回家臨出門前關(guān)燈后發(fā)現(xiàn):實(shí)驗(yàn)室含有水母提取物——水母素的水池出現(xiàn)發(fā)光現(xiàn)象。由于水池也接受養(yǎng)魚缸的水,他先懷疑是魚缸成分影響了水母素,好奇心促使他繼續(xù)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是鈣離子增強(qiáng)了水母素發(fā)光。1963 年,下村修和約翰森(Johnson)在《科學(xué)》雜志報(bào)道鈣和水母素發(fā)光的關(guān)系。其后,里奇韋(Ridgway)和阿什利(Ashley)提出可用水母素檢測(cè)鈣濃度的方法。由于鈣離子是生物體內(nèi)的重要信號(hào)分子,該方法對(duì)研究生命科學(xué)至關(guān)重要。
2.1.2 FRAP 和FRET 技術(shù) GFP 在應(yīng)用上需要解決的一個(gè)突出問題是,熒光圖像的衰減現(xiàn)象即光漂白影響了進(jìn)一步觀察。直至1976 年,阿克斯羅德(Axelrod)等才找到了解決方法——光脫色熒光恢復(fù)技術(shù)(fluorescence recovery after photobleaching,F(xiàn)RAP),這種技術(shù)首先被應(yīng)用到細(xì)胞膜蛋白質(zhì)的研究之中,它使研究人員能以微米級(jí)分辨率闡明細(xì)胞膜內(nèi)和細(xì)胞膜間蛋白質(zhì)的運(yùn)動(dòng)。隨著這些檢測(cè)技術(shù)的改進(jìn),使得單分子動(dòng)力學(xué)的量化成為可能[4]。同時(shí),GFP 應(yīng)用上又產(chǎn)生了一個(gè)重大進(jìn)展,費(fèi)爾南德斯(Fernandez)和柏林(Berlin)首次表明,20 世紀(jì)40 年代由福斯特(F?rster)提出的熒光共振能量轉(zhuǎn)移(fluorescence/forster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F(xiàn)RET)理論可用于研究細(xì)胞表面受體復(fù)合物的動(dòng)態(tài)分布。因?yàn)榕c標(biāo)準(zhǔn)熒光標(biāo)記相比,它促進(jìn)了更高空間分辨率的受體分布測(cè)定,并利用熒光顯微鏡繪制高分辨率活細(xì)胞中的蛋白質(zhì)分布和相互作用[5]。FRET 特別適合于細(xì)胞中蛋白質(zhì)-蛋白質(zhì)相互作用的成像,因?yàn)橐贔RET 信號(hào)中觀察到變化,2 個(gè)熒光團(tuán)必須非常接近。這些技術(shù)都為GFP 可視化探針的發(fā)現(xiàn)奠定了基礎(chǔ)。
2.1.3 GFP 可視化探針 隨著熒光顯微技術(shù)上的改進(jìn),1993 年,巴克斯凱(Bacskai)和華裔美籍科學(xué)家錢永健等應(yīng)用先進(jìn)的激光共聚焦熒光顯微鏡和FRET 等技術(shù),首先觀察到了海兔(Aplysia)感官神經(jīng)元在5-羥色胺刺激下環(huán)腺苷酸依賴性蛋白激酶催化亞基和調(diào)節(jié)亞基及游離cAMP 的變化。次年,錢永健又在實(shí)驗(yàn)室改良了多個(gè)GFP 變種,它們中有的熒光更強(qiáng)、更亮,有的呈黃色、藍(lán)色,有的可激活、可變色,有的更穩(wěn)定、更易激發(fā)。這使成像實(shí)驗(yàn)?zāi)芨櫦?xì)胞和生物體中的多個(gè)標(biāo)記蛋白成為可能。同時(shí),查爾菲(Chalfie)等在《科學(xué)》雜志發(fā)表的一篇報(bào)告中顯示,維多利亞水母的GFP 可作為蛋白質(zhì)定位和在活細(xì)菌及蠕蟲細(xì)胞中表達(dá)的標(biāo)記物,這樣可將GFP 用于研究體內(nèi)蛋白。GFP 作為體內(nèi)蛋白質(zhì)可視化探針的發(fā)現(xiàn),為更復(fù)雜的顯微技術(shù)奠定了基礎(chǔ)。2008 年,下村修、查爾菲和錢永健因這方面杰出的工作分享了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
2.1.4 熒光雙重標(biāo)記實(shí)驗(yàn) 隨著GFP 可視化探針的應(yīng)用,宮崎駿(Miyawaki)等意識(shí)到GFP 及其他顏色的熒光蛋白雖具有高亮度和極好的光穩(wěn)定性,但若能找到一些能變化和轉(zhuǎn)化的熒光蛋白才會(huì)更清晰地分辨不同蛋白的作用。為此,他們?cè)?997 年成功地構(gòu)建了一個(gè)編碼藍(lán)色GFP 的CaM 和肌球蛋白輕鏈激酶(M13)的CaM 結(jié)合肽與綠色GFP 的構(gòu)建體。這就如同不僅要給細(xì)胞內(nèi)不同的蛋白分子穿上不同顏色的“服裝”,而且還能觀察其在活動(dòng)中的相互結(jié)合及色彩或強(qiáng)度變化[6]。1999 年,馬茨(Matz)等則進(jìn)一步提出了類GFP 蛋白的熒光性質(zhì)不一定都與發(fā)光生物有關(guān)的解釋,并發(fā)現(xiàn)非生物發(fā)光的珊瑚礁同樣呈現(xiàn)明亮的熒光顏色。這導(dǎo)致了熒光技術(shù)的首次雙重標(biāo)記實(shí)驗(yàn),即將克隆的紅色熒光蛋白或綠色變異體注射到非洲爪蟾胚胎的胚泡中,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蝌蚪期標(biāo)記有單個(gè)蛋白質(zhì)(紅色或綠色)或2個(gè)蛋白質(zhì)(黃色)的區(qū)域。2000 年,扎科洛(Zaccolo)等發(fā)現(xiàn)FRET 可測(cè)量蛋白質(zhì)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發(fā)現(xiàn)對(duì)cAMP 的生理刺激可導(dǎo)致FRET 的丟失,用這種生物傳感器可檢測(cè)cAMP 水平的生理變化。正是這些不斷創(chuàng)新的方法,2003 年,美國(guó)科學(xué)家里德(Rieder)等觀察到了活細(xì)胞的有絲分裂過程[7]。
2.2 熒光顯微鏡的改進(jìn)與應(yīng)用
2.2.1 激光共聚焦熒光顯微成像 除了GFP 的發(fā)現(xiàn)和應(yīng)用外,激光顯微鏡的改進(jìn)及技術(shù)同樣功不可沒。首先是激光共聚焦顯微鏡的發(fā)明與應(yīng)用。普通熒光顯微鏡使用中存在的問題之一是:放大至一定倍數(shù)后,會(huì)因失焦信息干擾導(dǎo)致分辨率衰減。在20 世紀(jì)60 年代,為消除這種現(xiàn)象,美國(guó)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學(xué)家應(yīng)用1957 年由美國(guó)科學(xué)家即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Minsky)注冊(cè)的專利技術(shù)原理,制造出共聚焦顯微鏡。但20 世紀(jì)80年代前,觀察相對(duì)較厚標(biāo)本存在技術(shù)上的困難,共聚焦顯微鏡的應(yīng)用還十分有限[8]。1982 年,蔡司公司推出了能利用振蕩激光束和電子圖像處理進(jìn)行物體掃描的激光共聚焦掃描顯微鏡,可從多個(gè)光學(xué)視角拆解較厚、較大檢測(cè)樣本。這如同盲人摸象一樣,需要對(duì)多個(gè)掃面點(diǎn)綜合。1987 年發(fā)表的2 篇論文開啟了激光共聚焦顯微鏡在細(xì)胞生物學(xué)中的第1 個(gè)關(guān)鍵應(yīng)用。其中一篇是德國(guó)海德堡歐洲分子生物學(xué)凱西門(Kai Simon)實(shí)驗(yàn)室用熒光神經(jīng)酰胺標(biāo)記跟蹤新合成的鞘脂在上皮細(xì)胞中的轉(zhuǎn)運(yùn),清晰地觀察到該亞細(xì)胞過程[9]。到20 世紀(jì)80 年代末,激光共聚焦顯微成像成為標(biāo)準(zhǔn)的熒光顯微技術(shù)。1990 年,在激光掃描共聚焦顯微鏡的基礎(chǔ)上,又誕生了可進(jìn)行長(zhǎng)期的活體細(xì)胞成像(例如,腦)和深部組織成像的雙光子熒光顯微鏡。
2.2.2 反卷積算法 由于光通過某種介質(zhì)時(shí)會(huì)發(fā)生彎曲,導(dǎo)致光學(xué)顯微鏡圖像混濁和模糊。1983 年,科學(xué)家在使用瓊脂和鎮(zhèn)靜劑時(shí)找到了一種解決辦法——反卷積算法(deconvolution algorithms)。它利用顯微鏡光學(xué)特性的知識(shí)模擬成像過程,在幾輪迭代計(jì)算中,將對(duì)象的估計(jì)值輸入方程,并將計(jì)算結(jié)果與原始圖像進(jìn)行比較,以改進(jìn)估計(jì)值,直至確定對(duì)象的真實(shí)屬性。用這種方法首次獲得了用熒光標(biāo)記黑腹果蠅唾液腺細(xì)胞核內(nèi)染色質(zhì)結(jié)構(gòu)和組織的高分辨率圖像。1989年,費(fèi)伊(Fay)及其同事用熒光標(biāo)記平滑肌中蛋白質(zhì)的研究中又取得了另一個(gè)關(guān)鍵進(jìn)展,解決了反卷積算法可放大圖像中的噪聲使得很難縮小估計(jì)范圍以確定真實(shí)物體的問題。這樣產(chǎn)生的高分辨率圖像,能定量分析平滑肌細(xì)胞中α-肌動(dòng)蛋白的分布[10]。
2.2.3 超分辨率熒光顯微鏡 幾乎就在人們熱衷于研究GFP 技術(shù)的同時(shí),另一項(xiàng)與GFP 相關(guān)的技術(shù)也出現(xiàn)了重大突破。這就是突破了光學(xué)上的衍射極限屏障即傳統(tǒng)的光學(xué)顯微鏡(也稱為遠(yuǎn)場(chǎng)光學(xué)顯微鏡)無法分辨150~200 nm 以下的物體。由于許多細(xì)胞過程發(fā)生在這個(gè)長(zhǎng)度范圍為數(shù)十到數(shù)百納米的衍射極限距離內(nèi),傳統(tǒng)的光學(xué)顯微鏡在達(dá)到最大理論分辨率后,無法進(jìn)一步可視化。如何克服光學(xué)顯微鏡的衍射極限?
1990 年,正攻讀博士學(xué)位的羅馬尼亞出生的科學(xué)家黑爾(Hell)發(fā)現(xiàn),若不是像常規(guī)那樣使用1個(gè)透鏡聚焦,而是將2 個(gè)大孔徑的透鏡組合在一起聚焦可突破這個(gè)極限,從而提高光學(xué)顯微鏡的分辨率。1993 年某天早晨,黑爾正在看一本有關(guān)光學(xué)量子理論的書,忽然靈感在他的腦海里浮現(xiàn):用一束鐳射激發(fā)熒光分子發(fā)光,用另一束鐳射消除所有“大尺寸”物體的熒光。即通過運(yùn)用2束鐳射掃描樣品,就可呈現(xiàn)出尺寸小于0.2 μm 的分辨圖,突破權(quán)威認(rèn)定的衍射極限屏障。經(jīng)多次失敗后,他制作了受激發(fā)射損耗顯微鏡(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STED)。1994 年,黑爾在《光學(xué)快報(bào)》(Optics Letters)上發(fā)表了關(guān)于STED 的理論文章。但黑爾的工作曾經(jīng)受到質(zhì)疑,1999 年,他投給《自然》和《科學(xué)》雜志的研究成果均被退稿。直至2000 年,《美國(guó)國(guó)家科學(xué)院院刊》(PNAS)發(fā)表了黑爾的科研成果。黑爾被認(rèn)為是首次得到了納米級(jí)的熒光圖像并將顯微技術(shù)帶入“納米”領(lǐng)域的科學(xué)家。與此同時(shí),1993 年,貝茲(Betzig)和奇切斯特(Chichester)首次報(bào)道了在室溫下用近場(chǎng)掃描光學(xué)顯微鏡(NSOM)新技術(shù)對(duì)單個(gè)熒光團(tuán)進(jìn)行重復(fù)成像,并于1995年提出了單分子定位概念,開創(chuàng)了單分子成像的先河。1995 年,柳田(Yanagida)等使用優(yōu)化的全內(nèi)反射熒光顯微鏡實(shí)現(xiàn)了1個(gè)熒光團(tuán)標(biāo)記的ATP分子與肌球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實(shí)現(xiàn)了單分子技術(shù)在生物系統(tǒng)中的首次應(yīng)用,達(dá)到了能“親眼目睹”活細(xì)胞內(nèi)單個(gè)分子的動(dòng)態(tài)化[11]。1997 年,莫爾納(Moerner)在曾經(jīng)開創(chuàng)了單分子檢測(cè)及成像的基礎(chǔ)上,又發(fā)現(xiàn)了光調(diào)控綠色熒光蛋白發(fā)光的方法,該方法成為光激活成像(PALM)等超分辨熒光成像方法的基礎(chǔ)。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使貝茲等在2006年用熒光蛋白目睹了突破“阿貝分辨率”約10 倍(2~25 nm)的溶酶體和線粒體圖像[12]。這些杰出的貢獻(xiàn),使黑爾、貝茲和莫爾納共同分享了2014年的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
綜上所述,在細(xì)胞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中,熒光顯微技術(shù)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著名的物理學(xué)家弗里曼(Freeman)所言:每次我們引進(jìn)一種新的工具,總會(huì)帶來意想不到的新發(fā)現(xiàn),大自然的想象力比我們豐富。
- 生物學(xué)通報(bào)的其它文章
- 第29 屆國(guó)際生物學(xué)奧林匹克競(jìng)賽試題 實(shí)驗(yàn)3 動(dòng)物系統(tǒng)學(xué)、解剖學(xué)和生理學(xué)
- 種子萌發(fā)所需外界條件的拓展研究
- 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 線上學(xué)昆蟲*
- 諾貝爾獎(jiǎng)案例教學(xué)法在“核酸結(jié)構(gòu)”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與實(shí)踐*
- 通過多元表征進(jìn)行生物學(xué)概念教學(xué)
——以“血液”概念為例 - 例談初中生物學(xué)實(shí)驗(yàn)的優(yōu)化與創(chuàng)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