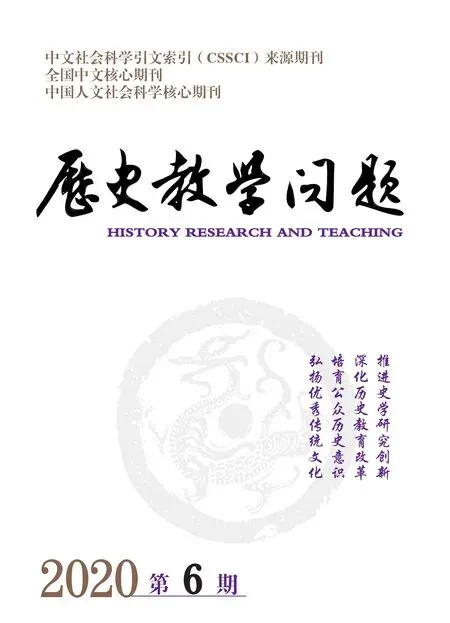上海考古新紀元:1948 年金山戚家墩遺址發掘
黃 阿 明
1935 年,上海金山縣發現戚家墩文化遺址。這是上海地區首次發現古文化遺址,它預示著上海地區現代田野考古揭開新篇章。戚家墩文化遺址發現后經過多次發掘,于1973 年公布發掘簡報,先后歷時30 余年。《發掘簡報》稱:
戚家墩遺址最初發現于1935 年,是上海地區最早發現的一處古代遺址。它位于市區西南金山縣山陽公社的海濱、杭州灣的東北部。
據調查和試掘,遺址的分布主要有兩個地點:……為了進一步了解該遺址的內涵以及采取保護措施,1963 年2 月8 日到28 日,和1964年5 月15 日到30 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曾兩次對他進行了發掘,先后開掘探方10 個,面積共140 平方米。另外,又在校場大隊前場地上發掘墓葬8 座,并在Ⅱ區清理古井一口和采集了一批文化遺物。①梁志成、黃宣佩:《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16 頁。
或許是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發掘簡報》只字未提1948 年的戚家墩遺址發掘史實,②實際上,在1973 年《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公開發表前,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曾有一份致上海市文化局的簡報,題名《松江縣戚家墩遺址試探工作簡報》,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5-696-90。在這份簡報中,亦無任何文字提及1948 年的發掘情況。而且參與遺址發掘的當事人楊寬、張天方等亦未提及此事,③1948年戚家墩遺址發掘,楊寬、張天方是領導者和參與者,他們的自傳和年譜卻無一字述及此事。參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張天方《張天方自撰履歷》(嘉善縣文史委員會:《文史大家張天方》,浙江攝影出版社,2005年,第220—230頁)、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218—219頁)。因此《發掘簡報》便成為學者研究戚家墩文化遺址最重要的文獻,甚至是唯一的文獻,④陳杰《實政上海史——考古學視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61 頁)稱:“發現于1935 年的戚家墩遺址,是上海地區發現最早的古代文化遺址。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剛剛起步的上海考古工作也把視野聚焦于戚家墩遺址上。為了確認遺址的內涵,1963 年和1964 年,當時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曾兩次對它進行了發掘,先后開掘探方10 個,面積共140 平方米。”據此,1948 年戚家墩遺址發掘似乎不存在。遂致1948 年的發掘史實湮沒不彰。筆者新近在上海市檔案館發現了1947 年《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的檔案,本文根據這份檔案,并結合其他材料對1948 年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事實進行考察,還原歷史真相,揭示其在上海現代考古文化上的歷史意義。
一、東南現代田野考古背景下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的發現
現代中國考古學自20 世紀20 年代建立以來,根本的問題是回答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重建中國古史系統。①沈頌金:《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以蘇秉琦為中心的考察》,氏著《考古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278—296 頁。在中國文化西來說和疑古思潮的內外夾擊之下,現代中國考古學勇猛前行。②西方學者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可追溯到17 世紀中期,代表性說法有埃及說、巴比倫說、印度說和中亞說。1929 年,何炳松先生在《東方雜志》26 卷2 號上刊發《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一文對中國文化西來說逐一進行分析和批判。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對此有全面論述。關于古史辨學派之于現代中國考古學關系,可參張學海《龍山文化》“引言”,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3—6 頁。龍山文化的廣泛發現,令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攻自破。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國文明是一元起源還是多元起源,成為考古學領域的重大命題。在以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山東半島、西北地區和華北地區的文化遺址考古事業蓬勃展開的同時,東南地區的考古似乎顯得有些黯淡、尷尬,甚至是帶著自卑的情緒。③在余姚河姆渡文化未發現,地下材料還是相對稀少的前提下,衛聚賢依靠文獻資料和有限的地下材料,于1937 年發表千余字的短文《中國古文化由東南傳播于黃河流域》雖說可視作衛氏一貫挑戰權威的品質,但亦未嘗不是上述心情的折射。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年,第154—160 頁。
晚清以降,人們長期受到傳統文獻特別是《史記》“吳世家”“越世家”、《吳越春秋》等記載的影響,普遍認為東南無石器文化。著名學者龔自珍慨嘆中原、北方地區的金石碑刻十倍于東南,曾發出“但恨金石南天貧”的悲鳴。④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457 頁。吳越史地研究會發起者在成立緣起中無奈地說道:“江浙古無文化的傳統思想,在人腦海中盤旋的久了。”又說:“書本子上告訴我們,江浙文化不如黃河流域之古。求其古物,僅有吳季子之劍、越王矛等十余種,這些古物不多而且是春秋戰國時物,沒有超過春秋以前的。”⑤《吳越史地研究會成立之經過》,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附錄,第384 頁。即使在杭州古蕩遺址、良渚文化遺址發現以后,東南文博界還有不少守舊的學者仍堅持舊的觀念和認識。譬如,西湖博物館的劉之遠說:“浙江的古代文化,考之歷史文獻,只能上推到春秋時代的吳越。”又說:“考之歷史,證明土壤,測其形狀及所藏地點,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認可殉葬物。絕不能作浙江古遠文化的證據。或作為石器之末期,而為金石并用時期,倘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遠文化,以此為新石器時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們,還要在那里發笑罷!”⑥劉之遠:《石器的形成與地層之探討:質衛聚賢先生》,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290、293—294 頁。胡行之更是直接以《浙江果有新石器時代之文化乎?》為標題予以質疑,胡氏說:“如古蕩及良渚一部分的石器,也頗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但就地層方面考察,江南一帶新石器時代未必有人類居住之可能,那末這些石器也只能著做是金石并用時期的特品,也是一種間接的殉葬品,而非直接的文化物產了。”他認為,這些出土之物只有玉器、刻紋陶片而無彩陶、土陶以及其他更古之物,在時代上最多只可推定到周末為止,“似不能再為提高了”。⑦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時代之文化乎?》,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288、289 頁。不難看出,東南無石器文化的觀念流播久遠,影響至深。
若以1921 年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遺址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確立標志的話,東南現代考古在時間上要晚10 年。衛聚賢、張天方、蔣大沂等先驅學者做出了杰出貢獻,居功洵偉。尤其是衛聚賢,不僅是當時東南地區一系列考古活動的領導者、參與者,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發揮著精神領袖的地位和作用。
1930 年,南京郊外棲霞山張家厙發現六朝古墓,由衛聚賢主持發掘工作,在當地人俗稱的焦尾巴洞發掘三國古墓時“無意中發現了石器”。1939 年衛氏追述:
當開此墓(三國古墓)道深約二尺時,發現了上為灰色(原處土為紅色),而且有木炭渣在內,知道這里曾為人類棲息過。再掘有紅色含砂質的粗陶片及鼎腿出土。這種陶器以我的經驗,在黃河流域只有新石器時代有;而且鼎腿長過一尺,是在未發明使用煤炭而用木柴作燃料時的現象。我就斷定這是新石器時代遺址。①衛聚賢:《吳越考古匯志》,《說文月刊》1939 年第1 卷合訂本,第365 頁。
衛聚賢將這一發現,告訴協助發掘工作的暨南大學歷史社會系教授張天方等,但是“他們以江南曾未發現過石器,據《史記·吳世家·越世家》所載,江浙在石器時代尚無人類”,認為這是后人使用的藥鏟。在發掘中,衛聚賢又發現一個完整的石斧,更加堅信了他的判斷。因此,衛聚賢“將這石器遺址封閉”,報告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蔡氏特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前來考察,李四光亦以江南不應有石器為詞,于是衛聚賢又電報中央研究院考古組主任李濟前來參觀遺址。李濟認為這是石器,但遺址只發現了一處,還是不足以證明東南地區有石器文化。所以,衛聚賢不得不再另尋其他石器遺址。②衛聚賢:《浙江石器年代的討論》,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307—308 頁。衛聚賢:《吳越考古匯志》,《說文月刊》1939 年第1 卷合訂本,第364—365 頁。
1935 年,江浙滬等地發現多處古文化遺址,上海金山縣戚家墩文化遺址即是其中之一。1935 年5月12 日,暨南大學教授張天方在常州奄城(建國后改作淹城)發現許多與南京棲霞山遺址相似的幾何形花紋陶片,他將此事告知衛聚賢。5 月16 日,衛聚賢從上海奔赴奄城進行考察。常州奄城遺址幾何形花紋陶片發現后,一起考察的衛聚賢、陳志良、張天方一致認為應該將“這種一向不為人所注意”的幾何形花紋陶片公諸于眾。③董大中:《衛聚賢傳》,三晉出版社,2017 年,第96、98 頁。張天方回到上海后,旋于《時報》發表《奄城考古記》一文,并配有若干幅幾何印紋陶拓片,開始引起世人注意。④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1935 年),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第207 頁。按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以張天方自撰履歷為基礎敷衍而成。
今人多謂張天方乃上海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發現第一人。事實上,是時任上海《時報》主編黃伯惠首先發現了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⑤董大中:《衛聚賢傳》,第98 頁。張天方發表《奄城考古記》以后,黃伯惠回故鄉金山戚家墩勘查田地,發現田中甚多與張天方公布的拓片印紋相同的陶片,遂攜帶幾片贈予張天方。張天方遂邀約黃伯惠赴金山戚家墩,撿回相同陶片一麻袋,藏匿家中,秘不告人。衛聚賢獲聞后,提出與張天方再訪戚家墩。⑥衛聚賢:《吳越考古匯志》,《說文月刊》1939 年第1 卷合訂本,第366 頁,第365 頁。1935 年9 月,衛聚賢、張天方、蔣大沂、金祖同等一行再赴金山戚家墩,在約20 余畝鹽田中俯拾兩大麻袋陶片。⑦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09 頁,第209 頁。1936 年10 月1 日,張天方率陳松茂、蔣大沂再赴金山嘴,進行考古活動。⑧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09 頁,第209 頁。不久,金祖同將衛聚賢、張天方等數次前往金山戚家墩探察考古之事撰成《金山訪古記》,予以發表。金氏說:“在海塘中發現灰跡,除了黃色土面層下含有鐵镕渣、宋元磁片的含砂礫炭炭土層外,再下去就是含有鼎足、鬲片、土器片、灰黑土層了,再往下去是沒有文化遺物發現,只黑色的淤土層了。我們在這里認為灰土層是近代文化層,黑土層為古代文化層的。”⑨松本信廣:《吳越史地研究會兩種報告之批評》,徒然譯,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369 頁。
1930 年代東南地區系列考古文化遺址發現,以1936 年杭縣良渚文化遺址發現最為重要。在良渚,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黑陶和大量的玉器。然而,當時中國現代考古學還處于初期階段,考古學理論和方法體系尚未建立健全,考古材料有限,無法對良渚文化做出準確判定。1939 年梁思永對龍山文化首次進行總結,根據6 處文化遺址將良渚文化納入龍山文化范疇,歸為龍山文化- 杭州灣類型,但梁氏還是敏銳地意識到良渚文化與龍山文化有所區別,因此特別指出:“它們的文化‘相’與在河南、山東的有顯著的分別,是很容易分辨的。”⑩梁思永:《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244 頁。
從南京棲霞山張家厙遺址、常州奄城遺址、金山戚家墩遺址,到蘇州吳城越城姑蘇臺、隨娃宮,澉浦、紹興、杭縣良渚等遺址,?衛聚賢:《吳越史地研究會成立紀》,《申報》1936 年9 月2 日,上海書店,1990 年。除了發現石錛、石鏟、石斧、石錐、石杵、石磨盤等石器外,還發現了鼎、鬲等大量陶器陶片,尤其引人矚目的是陶器陶片上的幾何形印紋。衛聚賢1930 年在南京棲霞山遺址發掘時就收集到陶片三百余片,“陶片上印有幾何形花紋,這些花紋共計有十四五種不同的形狀”。?衛聚賢:《吳越考古匯志》,《說文月刊》1939 年第1 卷合訂本,第366 頁,第365 頁。良渚文化遺址更是出土了大量的幾何形印紋陶片,花紋達到20 多種,包括早期的水浪紋、米字紋、回紋、重格紋、方格紋、回字紋、篾筐紋、麻皮紋、粗麻布紋、細麻布紋、繩形紋、蓆形紋、蘆菲紋、方格斜條紋等二十余種,晚期的五銖錢紋、蛇皮紋等五六種,①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浙江省教育廳,1938 年,第33 頁。施昕更說:“又有一種新事實引起我的注意,就是發見在地面上各處散布的印紋陶片極多……那時所蒐集的印紋陶片,具幾何形花紋,達二十余種,與江蘇金山、奄城所出是完全一致的。”②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第5 頁,第32 頁。
幾何形印紋陶的發現,令衛聚賢、陳志良、施昕更興奮不已。陳志良激動地說:“我們在常州奄城、松江的金山等地發現了大批的幾何形花紋的陶片而后,于是吳越民族的古文文化,略得曙光。”③陳志良:《南京考古記》,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233 頁。衛聚賢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江南)石器遺址中的陶器均為幾何形花紋,與黃河流域石器時代陶器上花紋完全不同。可證明江南自有文化,而不是受北方的傳播。”④衛聚賢:《吳越史地研究會成立紀》,《申報》1936 年9 月2 日,上海書店,1990 年。施昕更認為,從各方面來看,良渚發現的印紋陶片與江蘇金山、奄城、浙江平湖、吳興、海鹽等地陸續發現的遺址,“具同一典型,并且是同一時代的文化產物,也可無疑,亦暗示此項陶片分布于揚子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區域,為同一文化區域。是認為吳越民族本位文化,也是有相當的理由存在。”⑤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第5 頁,第32 頁。梁思永在判斷良渚文化時曾提示過:“杭州灣良渚附近的遺址也包含著兩個文化層。下層是龍山文化,上層是另一種文化,而這一種文化是以滿布著幾何形印紋的深色硬陶為特征的。這種硬陶廣泛分布在揚子江、錢塘江和珠江三處下流三角洲平原上。”⑥梁思永:《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第251 頁。
1930 年代東南地區在南京、常州、上海、杭州等地的一系列考古發現,特別是杭州古蕩、杭縣良渚文化遺址的發現,使得東南地區無石器文化遺址的局面大為改觀,直接推動了1936 年“吳越史地研究會”的成立。⑦《吳越史地研究會簡章》,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387 頁。為了破除東南無石器文化的陳見,在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一個月,吳越史地研究會借上海八仙橋青年大禮堂主辦了一次古代石陶器展覽,邀請胡樸安、呂思勉、何天行等蒞臨演講,主要展品就是自1930 年至1936 年東南考古界探訪、征集和考古所得成果,達數千件之多。⑧《申報》報訊,1937 年6 月12 日,第4 版。《申報》對此次展覽進行了簡要報導。無疑,這次展覽會對于宣傳和普及東南地區、江南地區也有石器文化的觀念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意義深遠。
二、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戚家墩遺址的計劃與發掘經費落實
20 世紀20—30 年代,中原考古、北方考古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語言與歷史研究所的考古組或考古所主持發掘的,而東南的考古發掘主要是由博物館主導的。比如,杭州古蕩遺址、杭縣良渚文化遺址是浙江省西湖博物館主持的,戚家墩文化遺址則是由上海市立博物館主持發掘的。
上海市立博物館(簡稱上海博物館)創建于1934 年,推葉恭綽為設計組主任,主持一切籌備事宜,直到1937 年籌備工作大體完成,“乃試行開放”,館暫設藝術、歷史二部。⑨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上海市立博物館,1948 年,第1 頁。藝術部“包括考古”,主要任務是“搜集古代藝術品及古器物,作有體系之陳列及說明研究,以供市民參觀”。⑩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3 頁。上海博物館自籌建伊始,就將戚家墩遺址發掘列為考古方面一項重要計劃:
此一古遺址(指戚家墩遺址)之發現,遠在十二年前,其時本館正當籌備之初,為準備開館后考古工作之推進起見,曾請本館特約研究員張天方博士并派現藝術部主任蔣大沂至東南各地調查古跡,當發現印陶系文化遺址十余處。此即其中之一處。至二十六年春,本館開幕,對各項業務,積極進行,在考古工作方面,選定安徽壽縣戰國末年楚都為第一工作目標,本遺址為第二工作目標,期以十年,擬將東南各地本館所發現之印陶文化遺址,盡作科學發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為東南歷史增一新頁。?《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擬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
據此可知,在上海博物館落成后,考古方面的工作計劃將戚家墩遺址考察、發掘置于第二工作目標的地位,雄心壯志,“期以十年,擬將東南各地本館所發現之印陶文化遺址,盡作科學發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為東南歷史增一新頁”。然而,上海博物館的考古計劃和抱負為戰爭中斷。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沿蘇州河南下久攻不下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主力部隊11 月5 日從金山嘴發動進攻。①金仲華:《敵由杭州灣進襲松江》,《抵抗》1937 年11 月9 日“戰局一覽”,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D2-0-622-1。日軍進攻方向正是戚家墩遺址所在地,這迫使上海博物館館務停頓,所有計劃被迫中輟。
抗戰勝利后,上海博物館發生了較大變化。首先,上海博物館的隸屬關系發生變化,由此前直屬市府改隸新成立的上海市教育局主管。其次,館址發生變更。上海博物館復館前,首要任務是尋回戰前寄存在震旦博物院、八年抗戰期間為奸偽劫奪的文物。②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168、171 頁,第173 頁。1945 年10 月,上海市教育局委派楊寬為接收委員,“追尋舊有文物”。11 月成立復館籌備委員會,聘請徐森玉、張鳳、徐蔚南、高君珊、楊寬等為委員,同時借實驗民眾學校成立辦事處,由楊寬出任主任,主持復館事宜。由于江灣的博物館舊樓在抗戰中屢被炮彈,損壞嚴重,“欲恢復原狀,需費甚巨”,并且由于行政與文化教育中心均已變遷,江灣市中心區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實施博物教育更多困難”,乃另撥四川北路橫浜橋1844 號一棟三層樓為博物館館舍,面積約一百英方丈。1946 年3 月,上海博物館復館,楊寬擔任館長,楊寬親自聘任蔣大沂、童書業,③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168、171 頁,第173 頁。分任藝術、歷史二部主任。④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2—3 頁,第4 頁,第5—6 頁,第3 頁。
上海博物館復館之初,原定設置五部,因條件有限,僅成立總務、歷史、藝術三部。歷史部工作目標是收集歷史文獻以及不屬于藝術、考古方面之文物,又因為博物館定位“為一地方博物館”,歷史部征集工作“著重于上海文獻方面”,搜集上海市及附近上海、松江、金山、青浦等十縣文獻;藝術部因兼包考古部門,范圍較廣,建館以來陳列品搜羅較富,有石器、銅器、陶瓷器、明器、書畫等珍品甚多,復館后繼續“竭力征集補充”。⑤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2—3 頁,第4 頁,第5—6 頁,第3 頁。在考古發掘方面,將戰前發現的金山縣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調整為首項工作,接緒戰前考古發掘計劃。
1947 年11 月,上海博物館在戰前掌握的相關信息基礎上組織考察團進行了最后一次周密調查工作。經確認確有發掘價值,上海博物館決心對戚家墩遺址進行發掘。首先,上海博物館按照政府規定的法定程序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轉請內政教育兩部發給采掘執照,經頒發執字第十號執照。⑥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2—3 頁,第4 頁,第5—6 頁,第3 頁。與此同時,為了獲得社會輿論支持,擴大社會影響,上海博物館藝術部主任蔣大沂親自撰寫了《松江戚家墩的文化遺址》一文刊于館辦《文物周刊》,介紹宣傳。蔣氏說戚家墩文化遺址的范圍相當寬大,但是“在沒有正式發掘以前,吾們不能說出它的詳細情形……,有待于吾們去發掘”。蔣氏進一步介紹說,“若然粗疏一點的說,便可把這個文化遺址算作上至新石器下迄鐵器時代先民居住之所,但是……真確的年代,在沒有正式發掘以前,吾們還不敢貿然的加以判斷”。不過,他特別指出戚家墩遺址發現的大量陶瓷碎片上面的各種幾何印紋與中原的陶器顯然不同。⑦蔣大沂:《松江戚家墩的文化遺址》,《文物周刊》1947 年第69 期,第7 版。今天已經無從知曉,此文究竟發揮了何種程度的社會影響效力,但就上海博物館方面來說,卻是為申請戚家墩文化遺址的發掘計劃與發掘工作做了比較充分周瞻的輿論準確,為即將開展的發掘工作造勢。
發掘戚家墩遺址,首先亟待解決的是經費問題。當時考古發掘經費或出于政府撥款,或來自社會資助。時值抗戰結束,中國很快深陷內戰泥淖,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物資匱乏,價格飛漲,特別是在社會對戚家墩文化遺址缺乏充分認知情況下,是不可能獲得社會經費資助的,而上海博物館在復館后又“經費奇窘”,⑧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2—3 頁,第4 頁,第5—6 頁,第3 頁。因此發掘經費只有仰賴政府撥款。
因此,上海博物館擬定了一份詳細的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計劃書《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下簡稱發掘計劃書),并向上海市政府遞交了申請戚家墩遺址發掘經費預算書。
《發掘計劃書》由正文和附件兩部分構成。正文約3000 字,包括(一)遺址之發現與調查,(二)論發掘此遺址之價值,(三)發掘方法。附件另裝一冊,包括(1)松江戚家墩附近印陶文化遺址略圖一幅,(2)戚家墩文化遺址照片五幀,(3)戚家墩文化遺址所出印陶紋樣拓片五十二種。⑨《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擬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
《發掘計劃書》雖以上海博物館名義提交上海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有關部門,但應是出自藝術部主任蔣大沂之手。楊寬雖是研治西周戰國史大家,但卻并不擅長史前考古。蔣大沂畢業于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1930 年參加南京棲霞山六朝墓發掘后興趣轉向考古,從1932 至1935 年在業余時間同張天方等在江浙滬地區從事田野考古調查,1935 年11 月任上海市立博物館籌備處干事,可以說蔣大沂是當時上海博物館館員中對東南地區文化遺址分布和戚家墩文化遺址情況最為熟悉的專家。蔣氏顯然是草擬《發掘計劃書》最合適的人選,何況考古本為藝術部主任職責所在。
《發掘計劃書》第一部分《遺址之發現與調查》,首先詳述上海博物館在30 年代東南考古事業中的參與工作,在中國現代考古方面的宏大抱負:期以十年擬將東南各地發現之印陶文化遺址“盡作科學發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為東南歷史增一新頁”,進而闡釋了發掘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的學術上的價值和意義。其次,詳陳上海博物館自成立以來征集、陳列、研究等方面工作情況,唯考古一項一直仍為空缺。因此,上海博物館復館后將此前考古發掘第二目標調整為第一目標首先進行。又松江為本市之鄰縣,本市地區與鄰近各縣之文化歷史“本有不可分之關系”,“故本館歷史部征集上海文物,向以上海市及附近十縣為對象”。而且,在此一文化區內,至今未有其他博物館之設立,研求此區之史跡與文物,上海博物館“責無旁貸”負有發掘此古遺址之責任。更為重要的是,此一遺址久已廢棄,附近之農民、鹽民又在利用,“而私掘之事已一再發現,設不及時用科學方法發掘,難免有被破壞之虞,是故此遺址之發掘實為本館當前急切之業務”。最后,簡要說明上海博物館為發掘計劃所做前期準備調查工作。
闡述戚家墩遺址發掘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是《發掘計劃書》第二部分的內容,也是《發掘計劃書》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關系到能否獲得政府經費撥款的結果。在論證戚家墩遺址“可斷定其本為一古人住宅區之遺址”的結論后,《論發掘此遺址之價值》著重闡述戚家墩文化遺址科學發掘在學術上的四點意義:
(一)可以探索東南地區之古代文化。《發掘計劃書》指出,我國近年考古發掘工作,僅注意黃河流域,而忽視長江流域,致使東南地區古代文化“尚多昧而未彰”,遺址發掘必定能使人們獲得對東南古文化有一深切了解。(二)可以探索東南各地印陶文化遺址間的關系。《發掘計劃書》分析,近代考古學家研究古代文化著重于探索陶器系統,如仰韶文化之彩陶文化、龍山文化之黑陶文化,皆是通過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使其文化明瞭于世,惟本館所發現之印陶文化因國難為輟,未能使其實際情況明瞭于眾。然而,印陶文化廣泛分布于安徽,東及于海,南及香港,地域甚廣,“實為我東南古代文化重要特征之一”,茍能于此遺址作科學發掘,必能使印陶文化實際情況及其時空關系大為明瞭。(三)可以探索我國瓷器之起源與發展進程。(四)可以探索東南金石并用時代之文化。正是深信金山戚家墩遺址的發掘在學術上所可能具有的貢獻,上海博物館“故雖在此經費極度拮據之時,亦擬排除萬難,從事此項工作”。
《發掘計劃書》第三部分說明戚家墩遺址發掘方法。根據戚家墩遺址存在上、下兩個文化層,《發掘計劃書》制訂了針對性的發掘方案,具體內容包括:第一,選擇一地點進行試掘,明其究竟,如有文化層留存,再用科學方法加以清理;第二,遺址上半部文化層,是此次準備發掘的中心。擬在遺址區內,依十字線挖等距離之長方形試探坑若干穴,探視遺址文化層之分布情況,再選各坑文化層蘊藏較富者,視地下情況,逐漸向外緣發掘,以期遺址蘊藏盡出;第三,整個遺址方位,先從事測繪。發掘時,由本館技術人員指導隨時制作坑位圖,記載坑內各文化層遺物情況。遇有重要遺物發現,由技術人員親自進行細作,以免損壞,并攝取照片,以便日后研究參考。各坑出土遺物,每日工作完畢后,編號登記,分別裝箱保管,待全部發掘工作完畢后運回館中保管。
發掘方案擬采用的發掘方法,無論是選取試掘點、長方形探方探道挖掘,還是遺址方位測繪、繪制坑位圖、記錄遺址文化層分布情況、坑內遺物拍攝、遺物編號登記等發掘技術、工序和注意事項,皆達到當時現代中國田野考古最先進的水平。
此外,《發掘方法》部分還提出海塘之內尚有若干其他遺址,在發掘工作之暇隨時考察此等古遺址情況,以備他日再行斟酌從事發掘的預設。《發掘計劃書》還指出遺址發掘工程規模大小,發掘后視遺址內蘊藏之豐富與否而定。若遺址蘊藏豐富者,可分年進行發掘。此次僅為初步發掘,發掘遺物運回館中加以整理研究,隨時編著發掘報告,以供并世學者研討。
根據計劃書落款時間,可知《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遞呈于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①《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擬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
同時,上海博物館還向上海市教育局遞交了一份發掘松江濱海古遺址支出的詳明《經費預算書》。《經費預算書》開列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的車旅費和膳宿費、發掘費、攝影費、繪制圖表費、包裝費以及運費6 項開支經費,每一大項下列分項。具體開支細目,參見下表:

表1 1947 年12 月上海博物館擬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經費預算表② (單位:法幣元)
《經費預算書》以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的名義遞呈上海市教育局,落款時間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這份《經費預算書》,應該是由藝術部主任、會計員和楊寬三方共同商量制訂的。當時上海博物館專設會計員一人,由上海市政府會計室核派。③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3 頁。
不過,上表之經費預算卻并非上海博物館遞呈教育局的原經費預算。上海博物館原《經費預算書》申請經費總金額為31,114,000元,而非27,114,000元。根據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市教育局代理局長李熙謀遞交上海市政府呈報,可知教育局對上海博物館申請的原預算經費,“照原送預算經本局核減為二七,一一四,000 元”,并特別說明“該款擬在歲出臨時門社教臨時費三款四項六目其他經費未領用數內支撥”,同時附呈預算書一式二份(經會計主任馬銘勛核算)、計劃書一份、計劃書附件一份。④《上海市教育局呈市政府為呈請撥發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代文化遺址所需經費》,上海市政府會計處秘四科分第一科卅六年12 月22 日滬36 字第30960 號收文,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上海市教育局削減了上海博物館原預算書中第二項“發掘費”第一分項“工資”,“工資”一欄原開列:“200 工,每工約需80,000 元,合計如上數。”按此,原工資合計16,000,000 元,核 減 了4,000,000 元,改 為12,000,000 元,因此上海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文化遺址的總經費最后變成了27,114,000 元。
根據這份《經費預算書》,可知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所需一切人力、物力、用工、設備和材料等具體名目,同時也對1947—1948 年的相關事項的物價和工資水平獲得一清晰認知。比如,上海至松江的二等火車票價每張21,000 元,松江至閔行的汽車票價每張35,500 元,閔行至金山嘴的汽車票每張35,500元,船費每人5,000 元;膳費30,000 元人/天,宿費10,000 元 人/ 天;草 鞋5,000 元/ 雙、竹 畚 箕30,000 元/只;三角板150,000 元/塊;棉花價格50,000 元/斤;工資80,000 元/工,等等。這對于了解和研究當時上海地區社會經濟尤其物價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經費預算書》經會計處秘四科黃熙珪主任簽章,遞呈上海市政府會計處。經會計處審核后,會計長閔湘帆簽字蓋章后于12 月24 日轉市政府秘書處,同時移文審計處、財政局(附預算書一份);市政府秘書處于27 日呈市長吳國楨,吳國楨29 日簽發,同意申請經費。⑤《上海市會計處關于上海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文化遺址經費案》(1947 年12 月22、24 日,筆者擬定題名),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根據上海市政府會計處呈市長吳國楨辦公室秘書處申批文,知道上海市政府1947 年歲出臨時門社教臨時費三款四項六目其他經費未支出費用總預算50,000,000 元,已支出15,380,000元,剩款34,620,000元,下撥上海博物館27,114,000元后,存余7,506,000元。①《上海市會計處關于上海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文化遺址經費案》(1947 年12 月24 日),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可知上海市將社教臨時費該項78.4%的經費撥給了上海博物館,用于發掘金山戚家墩遺址。1946—1949 年,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物資匱乏,法幣體系趨于解體,貨幣貶值,物價瘋漲。②潘連貴:《上海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98 頁。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博物館申請這筆發掘經費,一方面固然是上海博物館在申請發掘經費時已臨近年終結算上海市政府確實還剩有這么一筆經費,另一方面也頗可反映出當時上海市政府對于科教文化發展事業非常重視。
三、1948 年戚家墩遺址的發掘以及對遺址遺物的判讀
上海博物館組成的戚家墩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團,由楊寬任團長、蔣大沂任副團長,持經內政部、教育部核準辦法執字第十號執照,在江蘇省政府以及松江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謝承炳敕令當地駐軍協助、保護下,于1 月14 日抵達戚家墩,15日開工發掘。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3 編《上海市立博物館報送發掘戚家墩文化遺址綱要致電內政部代電》,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494—495 頁。
遺址發掘開始后,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對發掘工作進行全程跟蹤式報道,每月一報道。1948 年2 月15 日報訊:“上海市博物館在松江縣屬戚家墩一帶,從事科學發掘,已由內政、教育兩部會同核執字第十號許可執照。聞該館田野考古工作團,已于上月中旬由館長楊寬、藝術部主任蔣大沂率領前往,開始做有計劃之科學發掘,除發現石器刻文陶片、印紋陶器外,已發現古窯一所,預計發掘時期半載必有驚人收獲。”④報訊“滬博物館考古工作在松江墩開始”,《申報》1948 年2 月15 日,第2 版。從這篇通訊來看,《申報》應該并未派出前方記者,關于戚家墩遺址發掘的進展和遺物情況是通過聽聞途徑獲得的,因此才誤以為上海博物館此次發掘計劃時間為半載。3 月15 日《申報》以簡略的文字對發掘工作作了一次簡報,這次只說“發現了玉錛、刻文陶片、印紋陶器外,又發現古窯一所,預計發掘結果將有驚人收獲”。⑤報訊“市博物館人員在松發現古代窯”,《申報》1948 年3 月15 日,第2 版。4 月16 日《申報》對遺址發掘工作結束發表了簡訊,報訊陳:“滬市博物館楊寬正、蔣大沂由松江返滬,發掘戚家墩工作告一段落,刻正整理研究,編撰報告,定期展覽。”⑥報訊“文化界小新聞”,《申報》1948 年4 月16 日,第2 版。《申報》記者在經過較為詳細了解和采訪后,在戚家墩遺址發掘結束后一個月作了一次最為翔實的報道:
距離上海東百余里之戚家墩附近,曾發現漢代遺址,上海市博物館為發掘此項遺址,由楊寬正、蔣大沂領導組成之考古團,以考察工作暫告結束,已于日前返滬,擬于今秋晨忙期后,繼續進行次一步工作。據悉,此次在戚家墩與朱家勝兩鎮附近,復發掘近似窯基及三區域之古人住宅,同時發現有幾何印紋器與另一種陶器、灰陶器多件。⑦報訊“市博物館考古團已由戚家墩返滬”,《申報》1948 年5 月14 日,第1 版。
根據《申報》的連續報道,一般的普通讀者可以對戚家墩遺址的發掘工作進展、遺物獲得情況得到一概貌性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館方面的說法與《申報》的報道稍有出入。《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云,金山戚家墩遺址發掘時間從1948 年1 月15 日開始,由館長楊寬、藝術部主任蔣大沂、干事張子祺、助理干事張啟帆等組織田野考古工作團前往發掘,至4月20 日發掘工作告一段落。⑧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7 頁。然而,《東南日報》早在4 月13 日就已刊發了一篇具有簡報性質的報道——《戚家墩遺址的發掘》。⑨《戚家墩遺址的發掘》,《東南日報》1948 年4 月13 日,第3 版。綜而推論,戚家墩遺址發掘工作的時間不會遲于1948 年4 月13 日。《申報》當是在考古發掘工作團楊寬、蔣大沂等返滬之后再做出的報道。《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之所以著錄為4 月20 日,應是以遺物完全運輸到館時間作為最終結束時間。但是不管怎樣,發掘工作從1 月15 日開始,即使是以4 月13 日結束計算,戚家墩遺址發掘工作期也是89 天,近3 個月。這,已經大大超出上海博物館原訂為期15 天的發掘計劃,多出5 倍的工作日。按照1948 年物價和貨幣貶值水平,上海市政府撥給的27,114,000 元經費顯然不足以支持。至于這超出的74 天的發掘、食宿、用工等費用究竟是如何解決的,通過何種方式解決,尚未找到相關記載,仍有待進一步發現新的史料。
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工作結束后,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于4 月24 日給內政部發去一封電報,并附上《戚家墩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綱要》一份。根據這份《報告綱要》,可以知道發掘地點在海灘邊、海塘內和海灘邊高地。發掘地區分為A、B 和C 三個區:
(一)A 區,在戚家墩西里許海塘外之海邊附近海灘。因常年受到海潮沖刷,文化層遭到嚴重損壞。發掘工作團在此區先行試掘,共發3 個坑位,每坑長5 公尺、寬3 公尺,第一坑深1.6 公尺,第二坑深2.3公尺,第三坑深2.25 公尺。這3 個坑所獲遺物不多,僅發得少量繩紋瓦片瓷片灰陶幾何紋陶片并殘灰陶盆1 件。發掘工作團又在A 區地位沙灘處開一坑,南北長7 公尺,東西寬5 公尺,除陶瓷片外,發得殘瓷盂盆1 件、幾何紋陶罐2 件。
(二)B 區,在海塘內蘇南海濱民眾教育區第一教室東側荒地上。發掘后,判明為古代窯基,出土窯基磚和大量陶鼎足,略有甑底邊、豆座等,并發現鐵斤2 件。而后,發掘工作團在窯基東作放射線之試探坑二個,坑寬各1 公尺,南坑長11.5 公尺,北坑長11 公尺,又在兩坑東端開一聯絡長坑,寬1 公尺,長16.85 公尺,不過,因無任何遺物出土,故而挖至深0.47 公尺處即停工。
(三)C 區,在海灘內運石河北岸大木橋堍沈氏宅基前。先在東部高地發掘,挖一南北向長坑C1坑,寬1.5 公尺,長17.5 公尺,而后在C1 坑南端向西開一橫斜C2 坑,長4.4 公尺;又向南延伸開出C3坑,長5.9 公尺,寬1.5 公尺。又在C1 坑北端5 公尺處,向西開一橫坑C4,東西長5 公尺,寬2 公尺。再在C4 坑之南邊距西端0.5 公尺處向東開一坑C5,寬2 公尺,南北長4 公尺。又在沿河斜坑北邊距東端0.5 公尺處開一坑C6,貫通C1 坑,西邊距南端4公尺,坑西邊長4.5 公尺,坑北邊長2.5 公尺,寬均2公尺。又沿C3 坑西邊開一梭行坑,長5.9 公尺,寬7公尺。在C 區,發掘工作團前后共開出23 個坑。
C 區為此次發掘重點地區,是住宅區,出土文物較多。其中以C8 號坑出土文物最多,包括瓷杯6件,其中4 件完整,大小不同,2 件殘損;直邊碗2件,1 件完整;麻布紋陶罐1 件;殘斷銅刀1 件。其次C10 號坑,出土網紋陶甑、紅陶鼎、弦紋大瓷碗各1件。殘銅刀1 件。此外,C1 號坑出土直邊碗、帶蓋直邊碗以及殘銅刀各1 件。
此外,在C 區還發現石器3 件,石刀、石斧、石錛各1 件;灰陶紡輪2 件,全體圓形,中有一孔,中部厚,兩端薄。①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3 編《上海市立博物館報送發掘戚家墩文化遺址綱要致電內政部代電》,第495—496 頁,第496—497 頁。
戚家墩文化遺址的土層分布情況,1935 年衛聚賢、張天方、蔣大沂、金祖同等人考察時便已經發現戚家墩遺址的土層分布非常清晰,可以分作三層:地表層為黃土層,土層中含有鐵镕渣、宋元磁片的含砂炭土;第二層灰黑土層,含有鼎足、鬲片和土器片等;最下層黑土層,沒有發現文化遺物,僅有黑色淤土,因此衛聚賢等認為第二層灰土層為近代文化層,黑土層為古代文化層。②松本信廣:《吳越史地研究會兩種報告之批評》,徒然譯,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369 頁。黃宣佩、張明華:《上海地區古文化遺址綜述》,《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211 頁。在1948 年發掘后,《報告綱要》將戚家墩文化遺址土層明確分為四層:(1)農耕土,深度約三四公寸左右。(2)黃土層,厚者達1.3 公尺,薄者僅0.18 公尺。(3)文化層,存有大量農作物及堆積之垃圾,土色為青灰紫褐等色,深淺不同,厚者達1.6 公尺,薄者0.3 公尺。文化層,又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硬黃褐土;下冊為灰褐土,夾有軟灰土及黑灰。(4)底床,即生黃土層,質地極硬,為早期沖積而成,出土物多出于該層。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3 編《上海市立博物館報送發掘戚家墩文化遺址綱要致電內政部代電》,第495—496 頁,第496—497 頁。
據前所述,1948 年戚家墩遺址發掘面積,A 區80 平方米,B 區約40 平方米,C 區約120 平方米,總約240 平方米。而1963 年2 月8 日至28 日、1964年5 月15 至30 日兩次對戚家墩遺址進行發掘,先后開掘探方10 個,累計時間37 天、面積140 平方米;又在校場大隊前場發掘墓葬8 座,并在第二區清理古井一口和采集了一批文化遺物,發掘遺物數量約200 多件、五銖錢28 枚。④梁志成、黃宣佩執筆:《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2 年第1 期。兩相比較,無論是在發掘時間上,還是在發掘規模、獲得遺物方面,1948 年戚家墩遺址發掘都超過1963、1964 年兩次發掘規模和總量,發掘面積,前者是后者1.7 倍,時間是其2.5倍,遺物數量是其5 倍左右。這一發掘工作體量,也大大超出上海博物館原定發掘“遺址上半部文化層是此次準備發掘的中心”的計劃預設。①《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擬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
東南地區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現,給當時的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給考古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通過陶器系統判定考古文化遺址的性質和年代是現代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傳統,是現代中國考古學學科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因此,戚家墩遺址出土的大量的印紋陶器陶片也是判斷戚家墩文化遺址年代和文化性質最主要的依據。但是,戚家墩遺址出土的遺物的復雜多樣性給準確判斷這一文化性質帶來了不少困難,何況20 世紀30、40 年代中國考古學界關于印紋陶的性質和年代的判定存在很大分歧。印紋陶,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的東南沿海中國地區,北方則較罕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以中原和北方考古為“主戰場”的李濟、梁思永等著名考古學家在面對印紋陶時無法判斷或出現誤判。
況且,當時東南考古學界本身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930 年,在判斷南京棲霞山張家厙古文化遺址時,衛聚賢和張天方就已出現根本分歧。對于印紋陶器陶片和石器,張天方認為是漢代遺址,而衛聚賢則認為是更古的石器文化遺址。在東南考古遺物的判斷上,衛聚賢有他的見解和看法,他說:“發現古物,對于古物及遺址的年代,如有文字書明年號者,可知其絕對的年代,如有文字或花紋,就其文字花紋的語氣形式等,可以考知其相對的年代。故此,只能有推定的年代。推定的年代與其說得過晚,不如假定得早。”②衛聚賢:《浙江石器年代的討論》,吳越史地研究會:《吳越文化論叢》,第298 頁。如此,則可以引起社會與政府的重視,加強考古發掘,進而通過科學的研究做出精確判定。不過,衛聚賢的這一見解和認識傾向,遭到持不同意見的學者的暗諷。③張天方《欈李古址之初檢》一文謂:“夸大的考古學家,胃納很旺,動不動要從地底下搜集材料,說明某某地方,在歷史以前如何情形,當時的人民如何生活。依靠地質的年齡,憑仗古物的偶存,把他推論復推論,假設復假設,使勁使氣地,非把一地方的發現,一個人的見解,硬要拉長至數萬年以上不以為快。此種態度和心情,不知是在考古呢,還是在媚古或記古。”這段話頗似影射和暗諷衛聚賢的考古方法。參政協嘉善縣文史委員會編:《文史大家張天方》,浙江攝影出版社,2005 年,第78 頁。
張天方,是戚家墩文化遺址發現發掘過程中一位功不可沒的重要人物。張天方原名鳳,1930 年代曾幾次參加安陽殷墟遺址考古發掘,④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07 頁。是東南考古界最富田野考古工作經驗的一位考古學家。上海博物館籌備之初即聘其為特約研究員,受館方委托曾與弟子蔣大沂、陳松茂等赴東南各地調查古跡。⑤《上海市立博物館發掘松江海濱古遺址計劃書》,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擬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24-1-7157。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07 頁。1946 年,張天方自浙返滬,任職上海工業專科學校,并受聘上海博物館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⑥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18 頁。按楊越岷將張天方受聘上海博物館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的時間系于1944 年。張氏受聘在任職上海工業專科學校后之事,張天方自撰履歷謂1946 年任職上海工業專科學校,故本文將此事系于1946 年。可見張天方與上海博物館考古、東南考古事業的關系極為密切。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東南考古界另一重要人物衛聚賢1939 年離開上海,遠赴重慶,主編《說文月刊》,導致可能發出不同聲音的重要代表人的缺席。⑦董大中:《衛聚賢學術編年》,董大中:《衛聚賢傳》,第411 頁,第409 頁。而且頗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館復館首任館長楊寬與衛聚賢有著某些世人難以明瞭的恩怨。⑧董大中:《衛聚賢學術編年》,董大中:《衛聚賢傳》,第411 頁,第409 頁。因此,張天方關于東南考古遺址遺物的看法與判斷,會深刻影響甚至是左右他的弟子以及上海博物館的考古判斷立場和傾向性。
1935 年,張天方兄弟考察昆山陸家浜、上海西部,判斷發現的陶片是“漢代陶片”(按稍晚于良渚文化的馬橋文化即位于上海西部)。1936 年9 月衛聚賢、張天方等考察金山戚家墩遺址時,衛聚賢斷定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張天方認為是六朝遺物。衛聚賢后來追述:“我們兩方的意見,相距太遠,從此在江南考古上,各走了各的路線。”⑨衛聚賢:《吳越考古匯志》,《說文月刊》1939 年第1 卷合訂本,第366 頁。10 月,張天方再赴戚家墩,他在日記里說“再四探驗,撿得漢前后陶片”。①楊越岷:《張天方生平輯要》,楊越岷:《張天方文史補遺》,第209 頁。1947 年,上海博物館在發掘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前,藝術部主任蔣大沂在《文物周刊》上發文說戚家墩文化遺址范圍相當寬大,“在沒有正式發掘以前,吾們不能說出它的詳細情形”,綜合考慮調查所得陶器陶器、瓷器和銅器、鐵器,“若然粗疏一點的說,便可把這個文化遺址算作上至新石器下迄鐵器時代的先民居住之所”,蔣氏雖再三宣稱“真確的年代,在沒有正式發掘以前,吾們還不敢貿然的加以判斷”。但是,上海博物館卻是將從戚家墩遺址所得4個完整的陶器置于第二陳列室漢代陶器櫥窗陳列展出的。盡管蔣氏指出戚家墩遺址以及東南其他地區考古發現的印紋陶器陶片,“它和我國中原的陶器,顯然是不同的”,但蔣氏仍然強調這與河南信陽游河鎮擂鼓臺漢墓出土的漢代瓷器是同型的。②蔣大沂:《松江戚家墩的文化遺址》,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室輯《文物周刊》1947 年第69 期,第7 版。可以看出,蔣大沂關于戚家墩文化遺址年代的敘述比較客觀,但是傾向性也十分明顯。1948 年4 月13 日,《東南日報》上發表的《戚家墩遺址的發掘》一文宣稱:“由于這次的發掘,可以推尋漢代江南沿海一帶人民生活情況,同時連帶地還可以解決許多考古學上的問題。漢代各種的實用陶器的形勢,我們從這里可以多制度許多漢代的制陶工業,我們也可從這里獲得若干消息。”③《戚家墩遺址的發掘》,《東南日報》1948 年4 月13 日,第3 版。《戚家墩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綱要》也明確說:“幾何印紋陶器……實為我國東南古代文化遺址之特征,惟此類陶器均出鄉人偶然獲得,未經科學發掘,其時代頗不易定,昔年西湖博物館在杭州良渚發掘,于上層文化中亦有此類陶片發現,論者或斷為新石器時代之物,或斷為春秋戰國間物,惜因當時發掘之區域不大,同時出土之物不多,其時代終未能確切判定。由于此次出土文物之比較研究,此戚家墩遺址,當為漢代前后之文化,則此類幾何印紋陶器之時代當亦不出戰國六朝間。”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3 編《上海市立博物館報送發掘戚家墩文化遺址綱要致電內政部代電》,第501—502 頁。可見,以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蔣大沂為代表的考古學者認定了戚家墩遺址為漢代前后的文化遺址,而且還判定良渚遺址也當是此時期的文化遺址。此外,楊氏還在1949年6 月27 日答覆胡就明主任的信中也說“戚家墩在松江,這是個漢代居民住宅區的遺址”,⑤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書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33 頁。徹底坐實“漢代說”的斷論。因此,同年8 月上海博物館出版的《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以顯眼的段落文字徑稱松江戚家墩遺址是“漢代文化遺址”。⑥上海市立博物館:《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第7—8 頁。這樣,戚家墩文化遺址是漢代文化遺址似乎已成定讞,張天方“漢代文化遺址說”占據一邊倒的獲得勝利,當年衛聚賢所提醒的其他年代的可能性完全被過濾被擯棄。
1959 年,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調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⑦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256—259 頁。1963 年、1964 年兩次戚家墩遺址發掘,遺物經過科學的整理、分類和分析研究,1973 年發表了由梁志成、黃宣佩執筆的《發掘簡報》,公布結論:
(戚家墩)遺址包含有兩類文化遺存。早期文化遺存即所謂下層文化,包括和其性質相同的第一類墓葬以及采集的陶器和青銅器,其特征是有比較多的幾何印紋硬陶和一些釉陶。印紋硬陶的質料比較純凈,拍印的紋飾也富于變化,最常見的有方格紋、細方格紋、米篩紋、回字紋等……這些遺存的年代也大致在春秋戰國時期。……晚期是西漢文化遺存,包括第二類墓葬和一口水井……其年代應在西漢中期。……遺址中所出的幾何印紋硬陶,都疊壓在西漢文化層下面,而西漢文化層中未見這類陶器。⑧梁志成、黃宣佩執筆:《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24、29 頁。
逮至1980 年代初,考古學家對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已經能夠做出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準確的年代判斷,明確指出戚家墩遺址“早期文化為西周時代的幾何印紋陶遺存”。⑨黃宣佩、張明華:《上海地區古文化遺址綜述》,《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 年,第211 頁。經過半個世紀中國東南地區考古文化遺址的發掘和探索,我們知道東南地區的幾何形印紋陶的年代跨度很長,考古學界對于幾何印紋陶器已經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江南地區印紋陶產生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興盛于相當中原的商周時期,衰退于戰國至秦漢,他的發展鼎盛以至衰退,大體與商周青銅器工藝的盛衰一致。”⑩彭適凡:《中國南方考古與百越民族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52 頁。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1930 年代衛聚賢關于中國東南考古文化遺址判斷的前瞻性和卓越的預見性。當然,我們必須予以同情的理解,面對東南考古出現的新事物東南考古學界存在偏見甚至誤判也在情理之內,比如考古學家就曾經判斷良渚玉器是宋玉或是漢玉。①趙大川、施時英:《良渚文化發現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195、197 頁。詳見2019 年4 月22 日《光明日報》刊發的一組關于大眾閱讀的文章,分別是景德祥著《19 世紀德國的“閱讀革命”》、宮艷麗著《英國大眾科學閱讀的興起》和顧杭著《十九世紀法國的大眾閱讀場所》。
結 語
1935 年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的發現,構成20世紀30 年代東南考古鏈條上重要的一環。這一發現對研究杭州灣地區幾何印紋硬陶的發展序列及其下限年代,又增添了一批新資料,②梁志成、黃宣佩執筆:《上海市金山縣戚家墩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24、29 頁。高崢:《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干部蟬變(1949—1954)》,李國芳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年,“序言”第2 頁。不僅充分證明了東南有古文化遺址,而且還有不少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降至1980 年,上海境內陸續發現崧澤遺址、澱山湖遺址、馬橋遺址、亭林遺址等25 處古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分屬于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和戚家墩文化。其中戚家墩文化自成一類型,以戚家墩命名的文化遺址上海境內共有16處,系典型的春秋戰國考古文化遺址。③黃宣佩、張明華:《上海地區古文化遺址綜述》,第211—231 頁。戚家墩遺址作為現代上海地區最早發現的古代文化遺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和考古學史上的意義。抗戰結束后,上海博物館克服當時極其困難的物質條件策劃主持了1948 年金山戚家墩文化遺址發掘,為后來的發掘工作和上海境內其他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奠定了基礎。盡管金山戚家墩遺址不是上海境內最古老的文化遺址,即使當時對這一考古文化的性質和年代的判斷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卻開辟了上海現代考古的新紀元,對于推動上海考古文化體系的建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正如《戚家墩遺址的發掘》一文的作者所說:“這上海附近地區里,從事考古發掘工作,還是第一次,意義是何等重大!”④《戚家墩遺址的發掘》,《東南日報》1948 年4 月13 日,第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