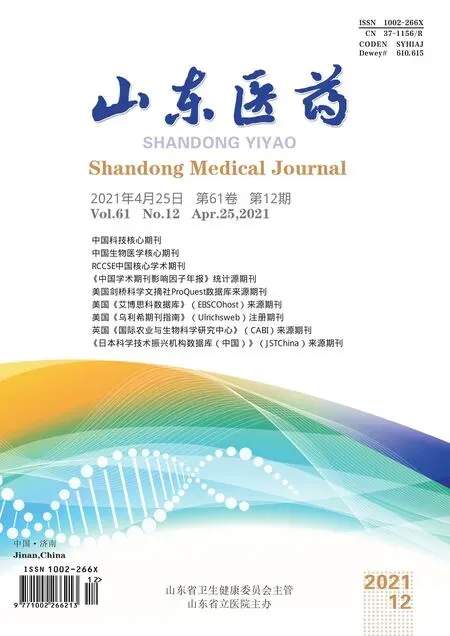供者特異性抗體對兒童肝移植預后的影響
肖艷麗,李西川,劉偉,劉純,康中玉,孫超,3,馬楠,3,李代紅
1天津醫科大學,天津300070;2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3天津市器官移植重點實驗室
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免疫特惠器官,有觀點認為較少發生排斥反應,原因可能是其具有豐富的血管床和雙重供血系統,Kupffur細胞能夠吸收游離狀態的免疫球蛋白,可分泌可溶性的HLA分子中和已產生的游離抗體,肝臟損傷后具有強大的再生能力[1-2]。供者特異性抗體(DSA)是指受者接受器官移植或者組織移植后,體內產生的針對供者組織抗原的特異性抗體,其產生增加腎移植、心臟移植和肺移植患者排斥風險,或導致同種異體移植失敗[3]。在實際的臨床工作中,一直忽視肝移植受體DSA的監測,以及DSA在肝移植后的損害作用。但隨著免疫學的不斷發展,DSA在肝移植中的意義已經被人們重新認識起來。近期國外研究表明,DSA與肝臟的損傷有一定的關聯[4]。而在肝移植方面,尤其是兒童肝移植術后DSA的產生對術后移植物存活的影響尚未見系統性報道。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50例接受肝移植并在肝穿刺活檢時檢測HLA抗體兒童的臨床資料,分析DSA的產生與肝臟生物化學指標和肝臟組織學以及移植術后并發癥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相關性,比較陰性組和陽性組的相關指標,研究供者特異性抗體在小兒肝臟移植中的臨床影響以及如何提高受者長期存活率。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擇期行肝移植的患兒50例,男28例,女22例;中位年齡1.0歲;先天性膽管閉鎖45例,進行性家族性肝內膽汁淤積癥2例,鳥氨酸代謝紊亂2例,Alagille綜合癥1例。納入標準:①在2013—2018年在我中心器官移植科接受親體器官捐獻或已故供體肝移植的兒童患者(18歲以下);②臨床資料完整,實驗室相關化驗完整;③進行肝穿刺活檢同時檢測HLA抗體;④均有供者的血清或者脾臟標本,進行HLA分型;⑤隨訪時間12個月以上。移植術前進行了HLA抗體檢測19例。患者隨訪時間(33.2±2.97)個月。
1.2 移植手術、免疫抑制方案和術后管理 所有患兒均行肝移植,其中親體部分肝移植29例,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肝移植21例。移植受者術中靜脈注射甲潑尼龍10 mg/kg,巴利昔單抗10 mg(體質量<30 kg),術后第4天給予巴利昔單抗10 mg,進行免疫誘導。肝移植術后第2天開始給予他克莫司,肝移植術后3個月內采用他克莫司聯合甲潑尼龍的免疫抑制方案,維持他克莫司血藥濃度谷值濃度在7~10 ng/mL,口服甲潑尼龍,劑量為4 mg/d,隨后逐漸減量,至術后3個月時撤除;術后3個月后僅單用他克莫司,血他克莫司濃度谷值維持4~6 ng/mL。
1.3 DSA檢測 兒童肝移植術后患者,在隨訪當天抽取肝移植受者的靜脈血3 mL(無添加劑),血液在無菌條件下收集,新鮮時進行分離操作,以避免因為不適當的存儲條件導致假陽性、假陰性反應或者樣本污染。全血及時進行分離操作,1 000 g離心10 min,分離血清于凍存管,血清在2~8℃不能超過48 h,如果需要存儲超過48 h,則應該在-20℃以下溫度保存或-80℃存儲兩年以上。應用Luminex液相芯片技術,依據試劑盒的說明書進行抗HLA抗體SAB檢測,LIFECODES LSA Single Antigen檢測試劑盒選自美國IMMUCOR公司。將待測血清與包被了特異性抗原的微珠加入到Millipore微孔板中,經過30 min孵育,若血清中存在HLA抗體則可與微珠上的抗原結合,利用抽真空方法洗滌除去沒有結合的抗體或其他雜質,再加入PE標記的二抗染色,孵育后,通過Luminex平臺獲取特異性結合微珠的熒光信號,再利用軟件分析得到特異性抗體類型。微球被紅綠染料設計成深淺不同的熒光編碼,在被激光掃描時測量目的熒光的平均強度(MFI)。我們通過分析軟件獲得MFI的大小,并根據MFI劃定陰陽性參考范圍。結果判讀標準:MFI<750陰性;750~4 000弱陽性;4 000~10 000中陽性;>10 000強陽性。如果多個位點陽性,以MFI值最高的為主,抗體特異性通過與供體配型比對,確定是否為DSA。
1.4 肝臟纖維化活檢 受者進行HLA抗體檢測同時進行肝穿刺活檢,經全身麻醉和局部消毒后,在超聲引導下進行肝活檢,在受者腋中線或腋前線第7~9肋間隙的肝濁音區穿刺獲取1條完整肝活檢組織,要求1條組織長度>1 cm最滿意,每例樣本觀察6個組織切面,所有病例通過免疫熒光或免疫組織化學方法進行常規蘇木素和伊紅、Masson三色和補體4d(C4d)染色。依據Banff ACR RAI標準對移植肝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T-Cell Mediated Rejection,TC?MR)進行評分,將門管區“三聯征”按其RAI各計3分,總分為9分。經Masson三色和網狀纖維染色評價肝臟纖維化及壞死程度,依照指南[5]對結果進行判定和強度分級。纖維化分級為半定量分級,具體分級:無纖維化記0分,致密周圍和脈絡膜纖維化記1分,周圍纖維化和非橋聯門靜脈纖維化記2分,橋聯纖維化顯示中心到中心橋聯記3分,廣泛的橋聯和脈絡膜纖維化顯示肝硬化記4分。
1.5 肝功能指標檢測 晨起空腹時采集受者靜脈血標本3~5 mL,標本采集送檢后1 000 g離心10 min,分離血清,采用羅氏Cobas c 311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清丙氨酸轉氨酶(ALT)、天冬氨酸轉氨酶(AST)、堿性磷酸酶(ALP)、谷氨酰轉肽酶(GGT)及總膽汁酸(TBA),通過HISS系統進行數據收集。
1.6 患兒產生DSA時的隨訪時間、存活、并發癥記錄 記錄產生抗體時的隨訪時間、存活、并發癥情況。
1.7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統計軟件。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四分位數間距(非正態分布)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Kaplan-Meier曲線用于事件發生時間的結果,并進行log-rank檢驗組間的生存率差異。肝纖維化評分使用單向有序定性資料的秩和檢驗(Kruskal-Wallis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50例肝移植患兒,DSA陽性者24例(陽性組),全部以抗HLA-Ⅱ類抗體為主,且抗HLA-DQ抗體是主要的抗體;DSA陰性者26例(陰性組)。
陽性組移植肝纖維化12例(50.0%),其中肝纖維化評分0分6例、1分2例、2分3例、3分1例;陰性組移植肝纖維化4例(15.4%),其中肝纖維化評分0分、1分各2例;兩組移植肝纖維化比較,P>0.05。
陽性組、陰性組血清ALT水平分別為24.40(18.45~73.73)、19.00(17.90~65.00)U/L,血清AST水 平 分 別 為46.50(31.00~54.00)、33.80(27.33~51.78)U/L,血清ALP水平分別為201.50(178.25~338.50)、232.10(136.67~338.42)U/L,血清GGT水平分別為14.50(11.25~26.25)、11.20(7.23~23.11)U/L,血 清TBA水 平 分 別 為8.00(7.08~10.50)、9.11(5.00~25.03)μmol/L,兩組血清AST水平比較,P<0.05。
陽性組、陰性組產生抗體時的隨訪時間分別為43、17個月,兩組比較,P<0.05。陽性組、陰性組術后1年的存活率分比為91.7%(22/24)和96.2%(25/26),兩組比較,P>0.05。陽性組2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為心功能衰竭和呼吸系統衰竭,分別隨訪43、27個月;陰性組1例患者死亡,隨訪13個月,受者抗HLA抗體顯示陰性,但是肝功能指標顯示異常增高,于是進行了二次肝移植術。陽性組并發癥為抗體介導的排斥反應1例,膽道并發癥2例,慢性排斥反應2例,TCMR 3例,藥物性肝損傷4例;陰性組并發癥為慢性排斥反應1例,TCMR 2例,藥物性肝損傷4例,血管并發癥5例,膽道并發癥5例,感染5例。
3 討論
肝移植已經成為治療終末期肝病的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幾十年來我國的成人肝移植手術技術已逐漸成熟,而對于兒童終末期肝病來說,可以通過活體肝移植或肝DCD移植手術獲得較理想的效果。隨著兒童肝移植手術的經驗積累和技術的提高,受者術后成功率和生存率有明顯的提高,但是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仍然較高。尤其對于肝移植受者早期檢測出DSA,避免排斥反應的發生,提高移植后的患者長期存活率,是肝移植長期存活的受體研究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腎臟移植和心臟移植受者的DSA與急性T細胞介導的排斥、抗體介導的排斥進展為慢性排斥、晚期移植物功能障礙、血管病變和同種異體移植物丟失有關[6-7]。而在肝移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DSA的存在與移植后的排斥、纖維化、炎癥有關。另文獻報道肝移植后DSA患者的比例在8%~67%[8-9],這些DSA陽性患者中的大多數是針對II類HLA抗原的抗體[10]。WOZNIAK等[11]報道DSA的患病率約為56%。GRABHORN等[12]報道稱,20例(47%)兒童患者在死亡或活體供體肝移植后有DSA,并且幾乎所有的兒童患者都有DSA。研究[13]顯示,在32例DSA陽性患者中,所有患者在各自的肝活檢中都有某種形式的纖維化,而35例DSA陰性患者中有24例患者存在某種形式的纖維化,并且DSA陽性患者的纖維化傾向于嚴重的分級。在兒童肝移植患者中,DSA的危險因素包括移植年齡較小,移植后生存時間長,爆發性肝炎病史等[14-16]。KANEKU等[17]發現,移植術后新生DSA可顯著降低肝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的長期存活率。與DSA陰性受者相比,術后新生DSA陽性的受者1年內死亡風險增加了1.99倍(P=0.005),移植物功能衰竭風險增加了1.85倍(P=0.01)。王永翠等[18]發現,DSA組與非DSA組術后1年、2年存活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本研究顯示,兒童移植受者的DSA患病率為48.0%,DSA的類型主要是具有高MFI值的二類HLA抗體。本研究結果與外文文獻陽性率大體一致。研究中DSA陽性患者中有一半患有纖維化,而DSA陰性患者中有15.4%(4/26)患有纖維化,且兩者無統計學差異,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納入的研究對象樣本量少,增加了Ⅱ型錯誤的風險。我們比較兩組的肝功生物化學指標,發現陽性組的AST數值表現比陰性組更高,說明DSA對肝移植受者的肝臟功能有一定的影響。只有19例病例在移植前進行了PRA的檢測,其他病例未在移植前進行抗體檢測,因此對于DSA無法判斷是術后新生還是術前預存,更無法比較新生DSA對于肝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率的影響。因此,根據我中心的臨床經驗,建議所有的肝移植等待者在評估時進行HLA抗體檢測,對于有致敏史的患者,更應多次檢測抗體水平。本研究缺少AMR的確診病例,原因可能為臨床上對于AMR的診斷具有一定難度,急性AMR的最終診斷需結合臨床表現、DSA檢測、組織病理學和C4d檢測結果等予以綜合判定,而AMR臨床表現的時間可能早于或晚于移植物損傷出現嚴重程度的時間。
隨著DSA繼發同種異體移植損傷的證據越來越多,在肝臟移植受者的長期管理中進行DSA監測的問題已經被重新認識。監測實體器官移植后DSA水平的中心指南,數據來源大多是基于腎和心臟移植[19]。最近,移植工作組會議報告[20]建議對肝移植受者進行常規DSA監測。雖然可能沒有必要對所有肝移植受者進行常規DSA監測和常規移植活檢,但可能有高危肝移植受者群體將受益于移植前和術后定期DSA篩查。臨床上應用血漿置換、利妥昔單抗、抗胸腺細胞球蛋白、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和類固醇治療循環DSA的受體。蛋白酶體抑制劑及其與下一代共刺激阻斷聯合使用已被證明在腎移植的臨床前模型中是有效的[21-24]。然而,這些新的治療方法在肝移植DSA介導的損傷中的適用性仍有待觀察。
總之,肝移植后DSA對于受者的預后有一定的影響,未來還需要利用更大規模的肝移植受體進行DSA與病理學結果的分析,并思考如何共同利用DSA和其他指標,早期預防排斥反應,或制定合理的干預措施,增加受者生存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