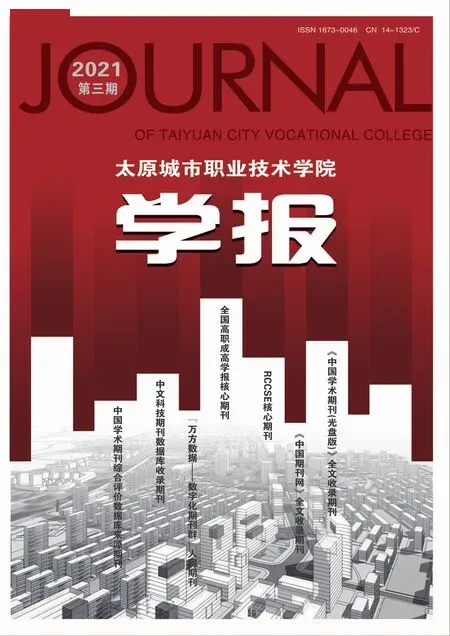群體訴訟制度后的法理及啟示
■葉文榜
(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一體化特征愈發明顯,大公司在更好地方便我們生活的同時,也會因為同一事實而引起眾多當事人受損,群體訴訟案件因此日益增多。我國在1991年修訂《民事訴訟法》時,在借鑒了美國集團訴訟、德國團體訴訟和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的基礎上,增加了代表人訴訟制度。但是,司法實踐并沒有像當初設想的那樣發展,運用代表人訴訟維護多數人權益的案例并不多見。正如章武生教授所說,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因證券欺詐、環境污染、產品責任等導致的大規模侵權行為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糾紛呈不斷上升趨勢,這些大規模侵權行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控制[1]。本文嘗試從法律合作主義的角度分析我國的群體訴訟制度,并對其完善提出一些建議。
一、我國群體訴訟制度的現狀及其困境
民事訴訟法上的群體訴訟制度是指:訴訟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人數眾多并且基于法律或事實上的關系而產生牽連。由于這個訴訟群體并不屬于某個固定的組織,因此無法將其作為一個法人實體進行訴訟,為了解決這種群體性糾紛,法律將其擬制成一實體的一種糾紛解決制度。在群體性訴訟涉及的范圍上,西方國家常見于公害、醫療訴訟、環境訴訟、消費者訴訟等方面,涉案利益呈現出群體性和擴散性的特征[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群體訴訟制度,前者是關于人數眾多且確定的共同訴訟的規定,即代表人訴訟制度;后者是對人數不確定的涉及多數人權益的共同訴訟的規定,即集團訴訟制度。
然而,群體訴訟制度在我國卻面臨許多困境。首先,群體訴訟制度確立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決日益增多的復雜群體性糾紛,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群體訴訟制度的適用卻并不多見。其中,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在各地司法實踐中有著少量適用,而各地法院對于人數不確定的集團訴訟制度的適用幾乎很難找到。也就是說,在集團訴訟制度頒布的近30年來,其基本屬于閑置狀態。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對代表訴訟的限制,這可以從一些司法文件中看出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訴訟案件問題的通知》第一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依法由基層人民法院受理。受理法院認為不宜作為共同訴訟受理的,可分別受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最高法對于群體性訴訟案件的司法策略是化整為零、分別受理,在必須面對群體性敏感案時最大程度上降低審判風險。這就從司法層面上限制了我國群體訴訟的開展。例如2004年的高爾寶事件,1300多名消費者共同狀告高爾寶南京經銷商和廣東高爾寶保健有限公司,受害者提起共同訴訟法院認為不適合,而1300多個消費者提起訴訟一個個來又不現實,消費者維權一時陷入了兩難境地。
其次,登記程序上不利于保護弱勢群體一方。我國代表人訴訟的登記程序是“選擇加入”機制,意思是說在法院決定適用代表訴訟制度,并且發布公告后,相關人員只有在公告期間內登記加入訴訟,才能具備代表訴訟的當事人資格。這種登記程序跟美國1938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中關于集團訴訟的程序類似。但是美國在1966年開始采用新的登記程序即“選擇退出”機制,即允許訴訟當事人在一定時期內,向法院明確表示退出集團訴訟。“選擇退出”比“選擇加入”機制更有利于保護訴訟集團成員的權利。根據有關調查,在“選擇加入”機制下,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受害人加入訴訟,只能解決百分之十五的糾紛;而在“選擇退出”機制下,有百分之十五的人退出,那就能解決百分之八十五的糾紛問題[3]。“選擇加入”機制加大了受害人一方的訴訟成本,尤其在“小額多數”的群體性糾紛中,當事人會覺得為了一點點損失而加入訴訟不值得,因此往往會選擇放棄訴訟,這樣無形中就損害了受害人一方的權利。
二、群體訴訟制度的法理分析
要更好地解決我國群體訴訟制度存在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溯源,找出我們為什么需要群體訴訟制度,它的意義在哪?然后以其目的出發,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本文嘗試從法律合作主義的視角解釋群體訴訟制度的法理基礎。
(一)法律合作主義——聯結孤立個人以減少組織歧視的技術
提到法律合作主義,我們不得不提到美國純粹法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唐·布萊克。布萊克提出了一種法律的新模式,即法律的社會學模式,它是相對于傳統的法理學模式而言。法理學模式認為,法律從根本上講就是規則,對案件的評估就是對法律條文的應用,是邏輯推導的結果,所以從一個案件到另一個案件法律本身是不變的,因此相同的事實會有相同的結論,即同案同判。但在社會學模式中,并不認為法律是邏輯的結果,而更多考慮案件的社會結構,法律會隨著各方社會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法律條文提供了法律的語言,而案件的社會結構提供了語言表達的語法”[3],所以法律是可變的,因此相同的事實并不一定導致相同的結論,即同案不同判。法理學模式視法律適用中的差別待遇為異常現象,是一種應被糾正的對道德的背離行為;而社會學模式認為對案件的處理總會反映出各方的社會特征,各方在種族、社會階層、性別和其他社會特征都會引起區別對待,所以差別待遇是無所不在的。
以社會學模式去分析法律適用中雙方社會特征我們會發現,一個組織比起無組織的民眾來說,在法律裁判中有著更優勢的地位,“孤立的個人是組織團體狀告的最好靶子,相反則不成立。而且個人通常不愿意同組織較量……組織是法律領域里的主要肇事者,與消費者權益或者環境相關的訴訟案件中,組織往往就是可以被狀告的一方,但遭受侵害的個人通常采取容忍的態度而不付諸法律行動,他們只是在忍氣吞聲”[4]。
可以看出,群體在打官司中是占據優勢地位的,他們更容易勝訴,甚至僅僅依靠組織的威懾力就讓個人不敢起訴。例如,在美國由組織(比如國家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發起的反歧視訴訟比起由個人發起的,勝訴的機會要大很多;無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當原告是組織團體,他們不服從原判而上訴的勝訴幾率會更大。所以布萊克指出,“現代法制中存在的社會偏見,最極端的形式之一就是這類組織歧視”[4]44。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法律糾紛很大程度上具有突出的個人化特點。絕大多數法律糾紛都是發生在個人身上的,他們沒有歸屬于某個組織,是完全孤立的,這就是“法律個人主義”。而在以往社會并沒有這么多不平等的組織,拿部落社會來說,部落社會的糾紛會被融入群體,如家庭、村落、種姓等其他聯盟,這就是“法律合作主義”。因為現代社會是個人參與法律,社會上不可避免出現了許多微妙差異,也就是我們說的歧視。例如,只要在訴訟中個人遇上了具有法人資格的團體,他的處境就很不利,這是因為個人是“無組織的”(組織性歧視)。所以布萊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法律上的個人主義使歧視得以長存,要減少法律生活中的歧視,就得減少法律事務中的個人參與”[4]45。
綜上所述,法律合作主義的本質就是將孤立的個人通過組織聯結起來,使案件雙方的社會地位趨于平等,目的在于平衡案件雙方的社會結構,從而減少司法中組織歧視現象的發生。正如布萊克所說,“法律合作社團的思想闡述了關于怎樣能夠把法社會學應用到現實中去的問題:改變案件涉及的社會結構,就改變了案件處理的過程。做到了主體的平等,就將得到司法的平等與公正”[4]48。
(二)法律合作主義視野下的群體訴訟制度——聯結孤立個人抗衡組織侵權
在法律合作主義的視角下,其實現代社會中的群體訴訟的起因多是占據優勢地位的組織一方對孤立個人一方的權利侵害。2013年《法制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澳法院開審史上最大消費者集體訴訟案》的報道,在澳大利亞,有大約18.5萬名消費者集體起訴澳大利亞的八家銀行,要求銀行歸還總額超過2.4億澳元(約合13億人民幣)的不合理收費。銀行這個組織利用其自身的絕對優勢地位,對用戶收取明顯不合理的非服務型費用,就像案件中的律師所說,銀行的這些收費與銀行的實際成本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如果要個人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發起訴訟是不太可能的:首先,每個銀行客戶的索賠數額不多,銀行的不合理收費每筆大概只有25澳元到35澳元,個人基于訴訟成本的考慮不太可能發起訴訟,但對于銀行來說是“積少成多”,有著很可觀的收入;其次,個人起訴銀行這種大組織,銀行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比如說銀行的法務團隊就絕對完勝個人,個人的勝率很小。所以,集體訴訟的意義在于,將孤立的個人聯結,最大程度上將銀行個人客戶與銀行這個組織拉到對等的訴訟地位,不至于遭受“組織性歧視”,從而維護個人的權益。
之前引發熱議的“流量清零”也是典型的組織基于優勢地位對個人的權益侵害。中國移動廣東公司董事長鐘天華說,“流量月底清零,好比你在肯德基買全家桶套餐,吃不完的雞腿總不能退回去吧”。一時間引起軒然大波,消費者們的憤慨溢于言表,連肯德基都忍不住調侃:“肯德基的雞腿肯定不會清零,吃不完可以打包、外帶、與他人分享,還可以回家燉湯燒菜,總之是你的,想咋用咋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指出,流量清零是典型的霸王條款。這種霸王條款是壟斷的產物,消費者頻頻吐槽,但又不得不接受,是因為在移動通訊上只有那么幾家公司,在服務上消費者沒什么選擇權。盡管法律明確規定霸王條款是違法的,但是要單個的消費者對抗霸王條款,就是以個人對抗一個行業,無異于螳臂當車。可以看到,當組織以其優勢地位對個人權益進行侵害時,因為雙方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個人的維權變得異常艱難。所以基于法律合作主義,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需要群體訴訟制度,因為這是賦予了個人與組織相抗衡的力量,從而使社會公正得以實現。
再如最近共享單車巨頭ofo的退押金事件,近1600萬小黃車用戶在排隊等候押金退還,涉及的金額接近15.84億元至31.84億元。小黃車用戶所交押金大多在99元到199元之間,由于數額不大,大多數用戶已經做好退不回押金的心理準備。在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個體的消費者面對作為組織的公司時維權的無力,金額不大,訴訟成本又高,如何才能維護好自己的權益?這讓消費者心里有種吃了啞巴虧的感覺。這是組織基于優勢地位對于個人的權利碾壓。
在現代社會,面對組織涉入非法行為時,尤其是當組織擁有絕對優勢地位給個人造成損害,社會批評家們給的建議大多是:對組織進行更嚴格的法律控制,從而達到保護個人權益的目的。例如,頒布更嚴格的法律條文規制公司等組織的行為,限制它們利用優勢地位侵犯個人權益。但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類建議是不可行的。“還沒有發現任何一種法律體系可以消解組織的優勢,建議鏟除這種優勢,簡單地、人為地用命令方式將其消滅,是和建議物體往上掉一樣不可思議”[4]56。所以,“法律合作社團”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提出的解決方案。“要么是一座大山,要么背靠一座大山。”它不要求通過強制性規定消解掉組織優勢,從而使組織變成跟個人同等的地位,合作社團要做的是通過某種社會技術,賦予個人同組織一樣的優勢。將個人融入組織之中,這樣就改變了案件的社會結構,雙方的組織力量就對等了。以組織對抗組織,這就從根本上減少了法律糾紛中組織歧視現象的發生。群體訴訟制度與合作社團有著類似的理論基礎,將單獨的個人融入法律所擬制的組織之中,這就改變了個人參與維權因力量弱小不足以與組織形成對抗之勢的局面。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關于維護消費者權益的群體訴訟,例如2014年央視3·15晚會上曝光的:顧客使用尼康D600拍攝出現黑點,尼康公司的售后服務人員認為是霧霾導致;大唐高鴻惡意預裝手機軟件偷窺顧客隱私;雅客等公司使用爛皮鞋加工明膠制作糖果等等。個體在面對這些侵權行為時都會感到對抗組織的無力,消費維權也就無從談起。只有把單獨的消費者聯合起來,加入法律擬制的組織,才能與侵權組織形成對抗之勢。
三、我國群體訴訟制度的完善
對于如何完善我國的群體訴訟制度,學者們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以章武生教授為代表,認為借鑒美國集團訴訟有利于遏制我國日益嚴重的大規模侵權行為,強制侵權方遵守公共政策,從而更好地保護我國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主張引進美國集團訴訟制度[4]55;一種以范愉教授為代表,認為完全引進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易引起水土不服,進而導致“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的局面,并且分析了美國集團訴訟制度的固有弊端,主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考慮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倡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5]。筆者認為,基于法律合作主義的視角,什么樣的制度是可行的需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把弱勢群體的一方組織起來,達到同強勢的組織一方有著相對平等的訴訟地位,只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那么這個建議就是可行的。
首先,我國群體訴訟制度的司法適用有其限制,但群體維權又日益增多,“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我們可以利用訴訟轉調解的方式,使群體訴訟向行政處理分流。從法律合作主義的角度來看,將群體訴訟轉化為行政協調處理是借助了政府這個組織,是把弱勢群體一方在某種意義上融入政府這個組織,使其在維權過程中擁有和侵權組織相對平等的地位。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政府主動介入,積極承擔責任,工商、衛生、質檢、公安等各個機構同時動員,召回問題產品、逮捕相關責任人,在尚未啟動訴訟程序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受害家長已經獲得企業的賠償。試想,要沒有政府這個組織與商家相抗衡,個體受害家長的維權之路肯定會漫長得多。
其次,適當擴大公益訴訟的應用范圍,以減少我國司法實踐中群體訴訟制度適用不多的局面。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群體訴訟為例,由于現代社會經濟一體化特征的不斷加強,商品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消費品的對象是一個群體而不是個人,消費糾紛已經涉及公共利益問題。2013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7條就規定了關于消費公益訴訟的內容,在面對眾多且不特定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害時,無直接利害關系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可以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而提起訴訟。在消費糾紛中,消費者屬于事實上的弱勢地位,消費者既沒有商家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沒辦法深刻了解商品本身的性質,這種不對等使個體的消費者在與商家的交往中難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消費公益訴訟賦予了個人享有同組織相對等的訴訟地位,從法律合作主義來說,它也是團結個人組成組織的制度,這樣一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就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因此,消費公益訴訟構成了對群體訴訟制度的有益補充,適當擴大消費公益訴訟的范圍可以更好地維護個體權益。
最后,在訴訟登記程序上借鑒美國的“選擇退出”機制。本質上來說,借鑒美國群體訴訟制度的登記程序,是為了讓弱勢的孤立個人更方便地加入法律擬制的組織里來,以抗衡組織侵權。如果登記程序的成本使當事人選擇放棄加入訴訟,那么群體訴訟制度的設立目的之一——聯結孤立個人就無法得到實現。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借鑒美國的登記機制。
從法律合作主義的視角出發,群體訴訟制度后的法理基礎就在于將孤立的個人通過組織聯結起來,使案件雙方的社會地位趨于平等,平衡案件雙方的社會結構,從而減少種種組織歧視現象的發生。所以,要完善我國群體訴訟制度,需把握的本質就在于將個人融入組織,賦予個人同組織一樣的地位,這樣就能減少組織歧視現象,更好地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實現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