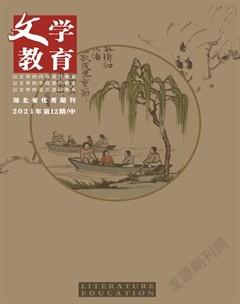試論卞之琳《斷章》的開放性結構
內容摘要:“空靈”是卞之琳《斷章》詩歌意境的特征,“因果”是《斷章》對生命狀態的解讀,而“靜觀”則是詩人對人生的領悟方式。基于《斷章》開放性語言結構,側重于詩歌具體詩句之間可能隱含的因果關系、假設關系、條件關系和遞進關系,對《斷章》“風景”進行別樣的解讀,領會詩人對人生哲理的智慧言說。
關鍵詞:空靈 因果 靜觀 人生 開放性結構
現代闡釋學提出了循環解釋的概念。所謂循環解釋指的是我們在閱讀文本的時候,并不是也不可能一次性解讀就意味著對文本意義解讀的完成和終結。
文本解讀的實質,用海德格爾本體論觀點來解釋,就是對文本的“去蔽”過程,就是讓文本中處于蒙蔽狀態的“真理”(意義)顯性化。文本的意義,固然包含作為創作主體的文本作者在構思創作文本的時候,所賦予文本作品本身的主觀思想情感。但文本作品一旦通過語言文字的固化,就成為讀者解讀闡釋的客體。在文本解讀環節,文本作者自然隱去,成為可有可無的一種存在,解讀者成為解讀闡釋的主體。解讀者對文本的闡釋過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本閱讀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闡釋主體更多的是基于解讀者自己已有的知識、經驗、人生閱歷、文化素養,甚至是解讀主體解讀文本時特定的心理、生理等諸種因素,通過解讀者自己的視角基于文本進行個性化解讀,使得被“遮蔽”的文本“意義”得以顯性化。這種顯性化的“意義”,有可能與文本作者最初賦予的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甚至相反。在闡釋性閱讀過程中,“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正常現象,也是闡釋性閱讀的價值所在。
就文學作品的解讀而言,越是經典越具有“哈姆萊特”效應,人們在不斷反復多次、甚至是無數次的循環解釋中,“發現”經典所蘊藏的豐富“意義”,讀者在這種循環解釋中,成就了經典的闡釋史,讓經典成為“經”、成為“典”,成為一種“永恒”。
一.空靈:詩歌意境的營造
卞之琳《斷章》意境的特點是空靈。詩歌中“你”和“看風景的人”構成了一個瞬間定格的畫面,實是詩人心造的虛相。它只是詩人對人生哲理性思考的符號而已。《斷章》空靈的意境,留給了讀者多元解讀的可能。《斷章》的藝術魅力,就在于似乎什么都沒說但又似乎什么都說透了。個中“意味”也只能靠讀者透過語言去領悟、去參透。
二.因果:生命存在的解讀
“風景”是本首詩的核心意象,是理解生命存在的形式、意義、過程和價值的關鍵詞。在文本中,“你”和“看風景的人”是互為主客體存在方式。兩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
辯證唯物主義觀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世界萬事萬物,多姿多彩,都有其個性化的獨立存在方式,但彼此之間又構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彼此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不可分割。在人世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在不經意間,貌似毫無關聯的人、事、物之間,卻存在著互為因果、相互依存的關系。“人說黛玉與寶玉是前世的相遇,百轉千回來到瀟湘館,雖然是為愛而來,卻因那瀟湘竹的斑斑淚痕,注定又是一段難以白首百年的恨緣。帶著滿滿的情而來,空空的心而去。”[1]人世間有許多動人的愛情故事,演繹的種種愛恨情仇,從唯心的角度而言,人們常歸因于“緣分”。茫茫人海之中,為什么“我偏偏遇見你”,仿佛“你”是因“我”而生,“我”是因“你”而存,這或許是《斷章》給我們提供的有關人生的另一種詩意解讀。一次邂逅、一次偶遇,貌似人生的偶然,實則必然,足以成為值得一生珍藏的美麗;有聚必有散,有散必有聚,聚散兩相依。人生個中的因果,猶如卞之琳筆下的《斷章》,你悟得是然,悟不得亦然。
《斷章》中站在橋上看風景的“你”和站在樓上“看風景的人”之間存在的這種互為因果關系,與語言表達中前后兩個句子之間存在的“因果”關聯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這是因為從語言表達角度而言,“你站在橋上看風景”與“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之間除了因果關系的復句可以解釋“因果”之外,還存在著并列關系、轉折關系、假設關系、條件關系、甚至是遞進關系,在句式上分別構成并列復句、轉折復句、假設復句、條件復句和遞進復句。人世間不同的人事物一旦產生了關聯、存在了某種關系,也就有了“因果”。
《斷章》一詩,我們可以把它解讀為基于“因果”揭示生命存在狀態的一首哲理詩,它巧妙通過詩句之間隱含的這種開放性結構,達到對生命存在狀態的詩性詮釋。詩句之間存在的轉折關系,我們可以同時品味出人生的悲劇性和喜劇性這兩種不同的生命存在狀態。而我們從詩句之間可能存在的并列關系中,又能夠領悟到人生既不是單純的悲劇、也不是單純的喜劇,而是一出亦悲亦喜、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悲喜劇的現實人生。[2]本文重點就另外存在的四種關系做一簡要分析。
1.因果關系。完整語言表述:“(之所以/因為)你站在橋上看風景,(是因為/所以)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你”與“看風景的人”在“有意”或“無意”當中,彼此都成為對方眼中的一道風景,在彼此的“有情”與“無情”之間更生濃濃的詩意。“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和“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兩詩句之間,我們雖然無法用合適的表達因果關系的關聯詞連接,但它們之間彼此存在的“因果”關系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這種因果關系闡釋的“因果”人生,就是因果雙方之間存在的彼此依賴,不分主客,渾然一體的生命存在形態。
2.假設關系。完整語言表述:“你(如果)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就)在樓上看你。(如果)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那么)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這種假設關系,從本質上來說揭示的主體與客體彼此之間的密切關系,只要有假設的“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就很有可能與其相關聯的“果”(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的存在。在這種假設關系中,“你”和“看風景的人”之間存在的“因果”,乍一看似乎是單向性的,“你站在橋上看風景”是因,“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是果,但我們何嘗不可以把“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的因也歸結于“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呢?這是因為從語言表達角度而言,“你(就)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如果)在樓上看你”也是一種合情合理又合乎語法規范的詩意表達,虛擬的場景中,雖然“我”和“看風景的人”都未出現在“現場”,但彼此之間存在隱性的“因”與“果”。
3.條件關系。完整語言表述:“(只要/一旦)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就)在樓上看你。”或者“你(就)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只要/一旦)在樓上看你。”這種條件關系,乍看很不合理性邏輯,因為從復句的前后兩個分句之間的關系而言,把“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視為“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充分條件有些牽強。但是你不能否認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合邏輯的邏輯性,在特定的情境當中,“(只要/一旦)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就)在樓上看你。”或者“你(就)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只要/一旦)在樓上看你。”就是一個十足的真命題,讀者可以作出“真”的藝術審美價值判斷。從言說人生“因果”哲理角度來分析,這樣的表述強調的是只要有“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的“因”,也一定有“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這樣的“果”,這“果”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隱性的,但它又是合乎情理的存在。
4.遞進關系。完整語言表述:“(不僅)你站在橋上看風景,(而且)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不僅)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而且)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你站在橋上看風景”這“風景”不就是“在樓上看你”的那位“看風景的人”嗎?而“你”不也就是那位“在樓上看你”的人眼中的那道“風景”嗎?“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已是令人神往,但“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更是一種心有靈犀的心動神搖。這種“因果”關系中,“你”和“看風景的人”均在“現場”,闡釋的是一種彼此欣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好人生體驗。
三.靜觀:領悟人生的真諦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我們把《斷章》視為一出獨幕劇,劇中共有三個角色。這三個角色在劇中的地位不同、出現的方式也不同。“你”和“看風景的人”是顯性角色,是臺前熱心的表演者。還有一個始終站在幕后的“我”,可以稱之為隱性角色,是戲劇冷靜的旁觀者。從角色主次角度而言,隱藏在幕后的恰恰是主角,而登臺表演亮相卻是配角。以闡釋學的觀點來理解,這主角既可以理解為詩人,但更可以理解為讀者自己。對人生的意義價值、對生命本真的存在狀態的領悟,只有讓“自己”成為“第三者”,以靜觀的態度冷靜觀照才能實現。以一種靜觀的心態“冷眼”人世間的蕓蕓眾生,才能望得遠、見得深、看得透。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參悟不透,其原因常常在于過于執迷于“自我”,視“自我”為主體,凌駕于“他人”、“它物”之上,最終導致迷失“自我”,始終無法看清“我是誰”,也無法覺解人生意義、生命存在的狀態及其價值。
“因果”是卞之琳《斷章》一詩對生命存在的解讀,詩句之間無論是轉折、并列還是因果、假設,抑或是條件、遞進,我們都能品味出人生百般滋味,個中的甜蜜美好、憂傷哀痛、惆悵失意、乃至有情人終不成眷屬的無奈,不同的讀者都能讀出屬于自己的味道。不悲不喜,“冷眼”靜觀一切人世界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都可以放下。這種境界就是“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境界。卞之琳在《斷章》中的這種人生境界,就是馮友蘭在《人生的境界》中所說的人生最高境界——哲學的境界。“靜觀”,這或許就是詩人卞之琳透過這首詩,想要告訴讀者的如何去領悟人生意義、生命存在的真諦吧。
參考文獻
[1]孔祥秋.納蘭容若詞傳[M].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16.
[2]孫國華.人生哲理的智慧言說[J].語文知識,2015(2):81-82.
(作者單位:無錫高等師范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