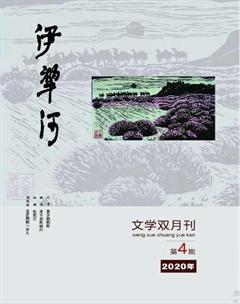邊疆的青春歲月
孫志宏
1968年初,我們北京政法學院66屆50多名畢業生從北京出發,到新疆烏魯木齊。大家唱起“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嘹亮的歌聲,歡樂載滿車廂。但是越往西走,滿眼是沙漠,不見人煙。同學們的心情一下子沉靜下來。我望著戈壁大漠,古道西風,突然想起王之煥的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經過四天四夜,火車終于到了烏魯木齊。按照分配方案,我們四名同學分到了塔城。又坐了三天汽車,到了塔城公安處。三名同學分到了沙灣、烏蘇縣公安局,我留到了地區公安處。第二天,公安處的領導向我介紹了有關情況。塔城是一個邊境小鎮,離蘇聯最近處僅為8公里,是地區所在地。由于文革的原因,沒有開展正常工作,每天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背“老三篇”,學習文件,開批斗會。有一天,領導跟我講,中央文件規定,凡是大學生,一律要求下去接受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再教育,我被分配到鐵廠溝煤礦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
第二天,我帶著行李,坐大卡車來到了鐵廠溝煤礦。這個煤礦是離塔城幾百公里的小煤礦。一片沙漠,沒有樹也沒有草,鳥兒也不飛。據老工人講,春秋是多風的季節,風把黃沙刮起來,使人睜不開眼睛。冬天,大風裹著大雪,漫天飛舞。煤礦四周有百來戶人家,有漢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等。工人大多數是內地到新疆找工作的農民、工人(當地統稱盲流)。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十幾名學生,有男有女,有北京的、河北的、遼寧的、烏魯木齊的、西安的,我們組織了一個知青小組。我和岳俊發、蘇志樸、杜海祥等人成了好朋友。
同學們來了以后,煤礦開了個歡迎會,會上貼出了一條大標語,很刺眼:“知識分子臭老九,老老實實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但是標語歸標語,工人們卻很熱情,介紹礦上的情況。第二天,我們下礦井挖煤。這個井是豎井,井深二百多米,工人上下班全靠爬上爬下。我們學生的任務是:女同學裝車,男同學拉車(兩個輪子的架子車),一次來回二百多米路程,一輛車裝有一百多公斤的煤。一天拉三四十趟。盡管當年年輕力壯,又經過了“四清”下鄉的考驗,但是勞動強度實在太大,很不適應,一天下來,渾身酸疼,連爬上井的力氣都沒有,我們自嘲說,確實要好好接受再教育。
時間長了,我們跟工人們慢慢熟悉了,說話多了,工人們也熱心地教我們如何干活,我們跟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很快打成一片。有一次煤層塌方,幸好我們幾個學生在工人的掩護下,轉移到安全的巷道里,避免了重大事故的發生。這使我們想到,當個煤礦工人真不易啊,拿生命創造了價值,煤礦工人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我們堅持每天出工,從不請假,得到工人們的好評。
一到冬天,下著鵝毛大雪,刮著大風,看不到一米遠的地方。工人們幫我們拴好繩子,拉著繩子一個緊跟著一個前進,不然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險。有時一早打開門時,大雪堆得跟門一樣高,就挖洞出去干活。礦上沒有澡堂,下班后滿臉黑呼呼的,回宿舍脫光衣服端臉盆洗洗就得了。礦上也沒有廁所,冬天冷,夏天蚊子咬。在大沙漠里,生活艱苦可想而知。在煤礦幾年的生活,既鍛煉了身體,又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在煤礦,每年過年過節,工人們對待我們像親人一樣,拉著我們到家里作客。還有一件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1970年1月,我準備結婚,當時要到塔城地區革委會登記,沒有車,礦上兩位老工人帶著我,央告司機,好說歹說坐上外單位拉煤的車到塔城,順利地開了結婚證明信。我帶著老工人的深情厚誼和美好祝福,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回到礦上不久,我們公安處軍管會主任到煤礦拉煤,無意中碰到了我,說咱們正缺人呢,你還呆在這兒干啥,讓我趕快回去上班。于是我與公安處聯系后,回到公安處上班了。
我回到了塔城,環視四周,遠處的雪山銀裝素裹,近處的草地一望無邊。繞著整個小城,有一條不寬不深的小河,清澈見底,是雪山流下的雪水,很干凈,家家戶戶用它做飯、洗衣服,活脫脫是一個地處西北邊陲的江南小鎮。
我到公安處上班后,先在辦公室搞文秘,后來調刑偵科工作。塔城是一個敵情和社情特別復雜的地區,斗爭形勢嚴峻,我多次參加了審訊特務工作。另外,案件也隨時有發生,深更半夜,突然響起鈴聲,我們就爬起來騎著馬執行任務。這樣的公安工作,對人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有時,我跟處、科領導,或坐車,或騎馬,或走路,從阿拉山口沿著邊境線巡邏行程好幾百公里。邊界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架起了鐵絲網,兩邊用拖拉機開了一片大約50米寬的松土帶,有沒有越境者一目了然。平時,老同志上課,講解刑事偵察案例,并帶著我們出現場,分析案情,指導我們收集指紋、腳印等。許多內容是我們在學校里書本上學不到的。看來光有書本知識那是不行的,還得結合實際才能真正學到真本領。實踐出真知,這是我參加工作中的一個深刻體會。
我們日常工作生活中,既有緊張嚴肅的一面,也有輕松愉快的一面。我們十幾個年輕的干警和大學畢業生,經常到草原訓練騎馬。我一開始不會騎馬,經過刻苦學習,總算有了收獲。那天我們十幾個小伙子在廣袤的草原上騎馬比賽,我騎在前面,后面有人說,不好了,有人摔下來了。原來前面有個大溝,一個干警不小心摔下來,腦袋碰著大石頭,幸好,沒有大事。回單位的路上,我們唱著歌,歡歌笑語洋溢在每個人的臉上。沒有任務時,晚上我們幾個年輕人一塊到塔城地區唯一的電影院看電影,放映的都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百看不厭,還經常學唱幾句,受到了革命傳統教育。
當時,我是單身漢,又是外地來的,單位領導和干警都熱情地照顧我的生活。每到星期天,食堂不開伙,干警們主動地挨個叫我吃飯,嘗遍了塔城各民族飯菜。我后來跟老婆說,塔城的飯菜味道好極了,至今想起來,我還念念不忘。那純真的年代里,友誼也是真誠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夏天,我老婆帶著一歲多的兒子來塔城探親,干警們十分關心,送這送那,問寒問暖,我心里充滿了感激之情。在回去的時候,機關唯一一輛吉普車一直送我們到烏魯木齊火車站。
每年夏天,我都買一百多公斤大西瓜,幾分錢一公斤,放在床底下,可以一直吃到冬天。塔城的夏天確實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冬天五塊錢買一只羊,賣了羊皮、羊腸,肉白吃。干警幫我宰好了掛在機關院子里,生活實在是“亞克西”。我們下去調查敵情和社情時,少數民族群眾對我們熱情招待,宰一只羊,在氈房里,大家圍在一起,吃著手抓肉,喝著馬奶子,民族團結氣氛濃濃的。有年冬天,我們到克拉瑪依辦案,塔城到克拉瑪依有幾百公里,我們坐在大卡車上面,氣溫零下40度,穿著羊皮大衣、氈筒,幾個人躺在一塊兒,還是冷得直哆嗦,但是我們堅持下來了。在艱苦環境中,經受鍛煉,吸取養分,在公安戰線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激情燃燒的日子里,深深刻上了塔城的印記。
二十五年后,我又去了塔城,舊貌換新顏。呈現在我面前的一排排高樓大廈,一條條寬廣的柏油馬路,一座座富于民族特色的建筑,富麗堂皇。環繞城市的那條小河,河水依然在流淌著,拍打著歡快的樂章,似乎在說:遠方的客人你回來了。在通往公安處的路上,一排排白楊樹高大挺拔,田野里向日葵一望無際,形成金黃色的海洋,微風吹來,似向我點頭致意。公安處的同志們、鐵廠溝的老工人、接受再教育的同學們更是熱情相擁,深情地訴說著當年美好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