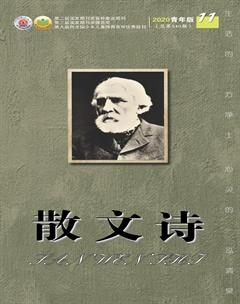象征的失落和詩的新生
2020-12-23 04:35:17
散文詩(青年版) 2020年11期
象征不僅是一個修辭問題和觀念問題,也是一個意義實踐問題。象征世界的法則與自然秩序密切關聯,它環環相扣、生生不息;這一法則不僅滿足了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意義需求,也解決了關于生產本身的困惑,甚至還化解了死亡難題。在古老而漫長的農業文明時期,生產與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更大時序輪回(天人合一)的顯現,死亡即是重生。
伴隨著理性的膨脹和現代性的發生,時間的線性神話被確立,革命的合法化和現代國家秩序的建立緊隨其后;其間伴隨著人的觀念的解放和失范——象征從宗教領域進入世俗領域,革命的象征敘事代替了宗教的象征敘事。而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為標志,象征實踐徹底從生產生活領域被擠壓至生產生活的終端——象征不再為人類的實踐賦義,而只為人類生產生活的結果提供解釋;一種基于等價交換而非象征交換的、外在光鮮陸離而內在支離破碎的商品拜物教產生了。
無疑,象征同時作為意義庇護和意義強制而存在。在個體對其所依存的象征秩序的接受中,存在一種張力;尤其是,當象征秩序衰落、動蕩、交替時,個人的感受性也愈加明顯。這也正是詩歌話語意義張力的基礎。在破碎的現代生存境遇中,詩歌借助象征的余威充當著現代世界的神話;正是在這一現代神話中,詩人的祭祀身份顯現,他們致力于建設一種新鮮的、個體的修辭經驗和知識體系,用以對抗成建制的話語秩序和基于其上的意識形態。只有在詩中,語言才是亙古如新的;只有在語言中,世界才是生生不息的。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2年9期)2022-09-17 07:10:5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6期)2020-12-16 02:56:41
小學科學(學生版)(2020年10期)2020-10-28 07:52:12
中國化肥信息(2020年7期)2020-03-19 01:54:02
中國軍轉民(2017年6期)2018-01-31 02:22:28
少年博覽·小學高年級(2016年12期)2017-01-16 12:48:35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
北極光(2014年8期)2015-03-30 0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