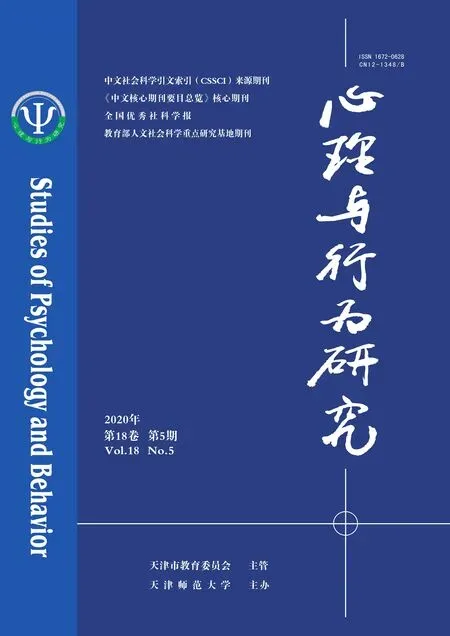術后乳腺癌患者體象對創傷后應激障礙和創傷后成長的影響:反芻的中介作用 *
孫小然 趙 悅 李文浩 安媛媛
(1 南京師范大 學心理學院,南京 210097) (2 蘇州 高新區第一中學,蘇州 215011)
1 引言
目前,我國每年因惡性腫瘤死亡的人數占死亡總人數的1/4(陳萬青等, 2015),其中,乳腺癌是最主要的惡性腫瘤之一,其發病率位居我國女性惡性腫瘤的首位(于莉, 孫麗美, 亓偉業, 李玉麗,2018)。同時,我國乳腺癌的發病率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乳腺癌已經成為威脅我國女性健康的重大隱患。我國罹患乳腺癌的患者數量龐大,預計到2021 年可達250 萬例(陳萬青等, 2015)。過往研究表明,乳腺癌癥患者往往會產生沮喪、痛苦、焦慮、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消極心理反應(張宗城, 葉樺, 岑建寧, 張艷玲, 劉麗, 2015)。PTSD 是在經歷了重大創傷的患者中最為突出的一種消極心理反應(Norris, 2006),指個體在受到非同尋常的、威脅到個體生命安全的創傷性事件后延遲出現的一種心理反應(鄧明昱, 2016),其核心癥狀分別是闖入性、回避性和警覺性增高(Angell, 1996)。雖然與其他惡性腫瘤相比,乳腺癌患者預后效果相對較好(陳萬青等, 2015),但是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仍然會因此承受極大的痛苦,因為患者的身體外觀、感覺和功能可能發生了一些暫時或永久的消極變化(Lewis-Smith, Diedrichs,Rumsey, & Harcourt, 2018)。因此,了解乳腺癌患者存在的創傷后心理反應是非常有必要的。有研究顯示,我國術后的乳腺癌患者PTSD 的檢出率為26.70%~58.00%,遠高于普通人群的檢出率(7.00%)(程玲靈, 楊芳, 趙立輝, 孫玉倩, 2017; 李玉香, 2018)。
在PTSD 的三個指標中,第一個重要的指標是闖入性癥狀,是指患者經歷創傷性事件后,常常會反復出現錯覺、幻想,患者會感受到自己彷佛又置身于創傷性事件發生時的情景中,從而產生十分痛苦的體驗等。第二個指標是回避性癥狀,是指患者不愿意提起和創傷事件有關的事件、盡量避免談及相關的話題等。第三個指標是警覺性增高,體現在患者難以集中注意力、易激怒、入睡困難或容易驚醒等(鄧明昱, 2016)。
但是,乳腺癌患者在與創傷性事件作斗爭的同時,并不是只會產生消極的心理反應,創傷性事件也會給他們帶來一些積極的改變(馬蘭, 李惠萍, 王德斌, 2013),如創傷后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PTG 是指個體在與威脅其安全的創傷性事件作斗爭時產生的積極心理反應,主要體現在自我覺知、人際體驗和生命價值這三個方面的改變(Tedeschi & Calhoun, 1996)。研究發現,在許多癌癥患者中都會出現PTG 這一積極變化與成長的現象(馬蘭等, 2013)。乳腺癌患者PTG 發生率高達73.01%(Schroevers & Teo, 2010)。PTG 能夠促使患者調動資源來有效應對創傷事件,達到身心健康的良好狀態。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關注PTSD 和PTG 的影響因素及其機制。研究表明,反芻、積極重評等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對創傷后心理反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Vranceanu, Hobfoll, & Johnson,2007)。除了上述一些與創傷相關的普遍性因素外,對于乳腺癌這一特殊群體來說,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體象是一個更重要的預測因子(Helms,O’Hea, & Corso, 2008)。體象是指個體對于自我身體構造和功能的感知,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當身體的形象和功能改變時,體象也會隨之改變。絕大多數乳腺癌患者在接受乳腺癌根治手術后會產生乳房缺失的情況,這會產生相應的體象問題(侯志瑾等, 2014)。乳腺癌患者經歷手術后可能導致乳房不對稱、瘢痕、感覺喪失和淋巴水腫,而輔助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能包括脫發、疲勞、體重波動、皮膚和指甲變色,以及更年期癥狀加劇等(Lewis-Smith et al., 2018)。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體象問題會帶來PTSD 等消極心理反應(洪曄, 王慧琳, 王建平, 2006; Janoff-Bulman,1989),甚至會影響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效果及康復(Paterson, Lengacher, Donovan, Kip, & Tofthagen,2016)。對于PTG 而言,對自己身體具有良好的體象也會有助于提高PTG 的水平(蘇怡, 方桂珍,2018)。但在體象問題比較嚴重的情況下,患者也有可能憑借積極的應對方式悅納自我,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更樂觀地面對生活,從而提高PTG 的水平。以往研究缺乏對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因此,體象問題的強弱如何影響PTG,這一點也是本研究所需要探討的。
那么,體象如何影響包括PTSD 和PTG 在內的創傷后身心反應呢?中間機制又是怎樣的呢?首先,破碎世界假設理論指出,個體在經歷生活中的負性事件時,之前穩固的核心信念系統會受到沖擊,這使得個體無法應對創傷性事件(Janoff-Bulman,1989)。負性事件之后,個體最常見的反應是一種強烈的脆弱感,因為他們從未想過如此糟糕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對于乳腺癌患者來說,手術帶來的身體形象上的改變會給身心帶來巨大的沖擊,因此患者會對之前的信念系統產生懷疑和否定,產生消極的認知信念,進而產生諸如PTSD 這樣的消極心理反應(Begovic-Juhant, Chmielewski,Iwuagwu, & Chapman, 2012)。其次,Tedeschi和Calhoun(1996)提出的PTG 整合模型認為,PTG 是與創傷事件斗爭的結果。癌癥使患者身體不再完整,其帶來的刺激會改變個體的自我認知,可能會促使個體對創傷事件、自我、世界等產生積極思考,從而引起PTG 的產生(周宵, 伍新春, 陳杰靈, 2015)。有許多實證研究發現,乳腺癌患者盡管身體完整性遭受破壞并飽受疾病帶來的身心折磨,但當他們利用反復思考、積極認知和情緒調節等諸多積極的應對方式去面對生活時,也會出現積極的成長和改變(馬蘭等, 2013; 蘇怡,方桂珍, 2018)。
由此可見,體象影響個體創傷后身心反應的機制可能通過患者自身的認知情緒調節來實現。其中,研究發現反芻這一認知情緒調節方式對于PTSD 和PTG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預測因素(Zhang,Xu, Yuan, & An, 2018)。反芻是指反復地思考與創傷性事件有關的想法和感受(Garnefski, Kraaij, &Spinhoven, 2001)。研究表明,反芻會加劇PTSD癥狀,產生更少的積極心理變化(Chan, Ho,Tedeschi, & Leung, 2011)。不過,也有研究者認為,個體采用表達抑制策略(如反芻)會減少對創傷事件所引起的消極情緒的感知,從而減輕消極情緒的影響,促進PTG 的產生(周宵, 伍新春,曾旻, 田雨馨, 2016)。可見,乳腺癌患者反芻與創傷后心理反應的關系尚不穩定。
綜上可知,體象對反芻有著一定的預測作用,而反芻又是PTSD 和PTG 的重要預測因子。因此,本研究假設反芻可能是體象影響PTSD 和PTG 的中介因素。為此,本研究以確診為乳腺癌并接受完手術的患者為研究對象,考察體象對PTSD和PTG 的影響,并考察反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根據以上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1)體象問題可以正向預測PTSD,也可以顯著預測PTG,但其對PTG 的影響方向有待證實;(2)反芻在體象與PTSD 和PTG 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于2018 年3 月,在江蘇省某三甲醫院選取已經確診并剛剛結束手術的乳腺癌患者為被試,全部為女性。入選標準如下:(1)診斷為0~Ⅳ期的乳腺癌患者并且意識清醒;(2)良好的口頭表達能力并且自愿參與本研究;(3)年齡大于或等于18 歲。排除標準包括:(1)病情危急、無法理解或清晰地回答問題;(2)其他生理或慢性疾病;(3)存在明顯心理障礙和精神疾病。本研究的樣本包括153 例術后乳腺癌患者,篩除無效問卷3 份,獲得有效問卷150 份,被試的年齡范圍為26~81 歲(平均年齡51.02±11.13 歲)。
2.2 研究過程
本研究在征得患者、患者家屬及醫院的同意下進行施測,由研究助手對指導語進行說明,大部分被試能夠獨立完成問卷內容,少數不能獨立完成問卷的被試由研究助手幫助其理解問題并完成問卷。問卷完成后,當場收回,整個施測過程大約需要20 分鐘左右,之后由訓練有素的研究助手對其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導,以消除問卷填寫過程中可能帶來的不適反應。本研究已通過南京師范大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2.3 研究工具
2.3.1 體象量表(Body Image Scale, BIS)
采用洪曄等(2006)修訂的體象量表,該量表共10 題,適用于患任何癌癥和接受任何癌癥治療的患者。采用4 點計分,0 代表“一點也不”,3代表“非常多”,分數越高,表示乳腺癌患者在體象上存在的問題越多。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5。
2.3.2 認知情緒調節問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C)
采用朱熊兆等(2007)修訂的中文版認知情緒調節問卷的反芻分問卷,用于評估個體遭遇負性生活事件后使用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該量表包括“我不斷地想這個事情是多么可怕”等4 個題目。該量表采用5 點計分,1 代表“幾乎從不”,5 代表“幾乎總是”,得分越高,表示個體越有可能在面臨負性事件時使用這一特定的認知策略。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9。
2.3.3 創傷后應激障礙量表(PTSD Symptom Scale,PSS)
采用中文版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量表(周宵,伍新春, 安媛媛, 林崇德, 2017),測查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該量表包含17 個條目,其三個維度分別是闖入性癥狀、回避性癥狀、警覺性增高癥狀。該量表采用4 點計分,0 代表“從未”,3 代表“總是”,分數越高,表示PTSD 癥狀越嚴重。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4。
2.3.4 創傷后成長問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
采用修訂后的中文版創傷后成長問卷(周宵,伍新春, 安媛媛, 陳杰靈, 2014),共有22 個項目。該量表采用6 點計分,1 代表“沒有變化”,6 代表“變化很大”,分數越高,表示個體經歷創傷后得到的積極成長越多。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6。
2.4 數據處理
采用SPSS23.0 對本研究中的描述性統計、皮爾遜相關分析等進行處理,采用AMOS24.0 檢驗假設模型和中介模型。模型擬合采用卡方自由比(χ2/df)、塔克劉易斯指數(TLI)、擬合優度(CFI)、近似的均方根誤差(RMSEA)。根據溫忠麟、侯杰泰和馬什赫伯特(2004)的建議,χ2/df小于5、TLI 和CFI 大于0.90、RMSEA 小于0.80 時,模型通常被認為擬合良好。為了評估中介,本研究對1000 個樣本進行了校正偏置引導估計,其置信區間為95%。在本研究中,如果區間置信度中不包含0,則認為存在中介效應(Mackinnon,Lockwood, & Williams, 2004)。
3 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及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對參加此次研究的150 名被試進行人口學信息和病情相關信息的調查,其中人口學信息包括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居住地、家庭類型、家庭收入水平。病情相關信息包括病程情況、病程分期、手術方式。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1所示。
3.2 反芻在體象與PTSD、PTG 關系中的中介檢驗分析
3.2.1 測量模型結果
首先建立一個包含兩個潛變量和一個顯變量的測量模型,潛變量為PTSD 和PTG,顯變量為體象。其中,PTSD 潛變量是由闖入性癥狀、回避性癥狀和警覺性增高癥狀三個維度抽取得來;PTG潛變量是由自我覺知的改變、人際體驗的改變、生命價值的改變三個維度抽取得來。分析體象對PTSD 和PTG 的直接效應模型圖和路徑,直接效應的模型擬合指數為:χ2/df=1.028,TLI=0.999,CFI=0.999,RMSEA=0.014。結果表明,該模型是正確的,并且適合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3.2.2 中介模型結果分析
在體象與PTSD、PTG 之間加入反芻作為中介變量后,模型結果見圖1,各項擬合指標如下:χ2/df=0.869,TLI=1.007,CFI=1.000,RMSEA=0.000。說明該模型為過度擬合狀態,經過調整,修改過后的模型結果見圖2,各項擬合指標如下:χ2/df=1.274,TLI=0.986,CFI=0.993,RMSEA=0.043。路徑分析結果發現,體象可以正向預測反芻、闖入性癥狀、回避性癥狀和PTG(β=0.28,p<0.001; β=0.53,p<0.001; β=0.49,p<0.001; β=0.18,p<0.05),反芻可以正向預測闖入性癥狀和回避性癥狀(β=0.21,p<0.01; β=0.16,p<0.05)。

表1 體象、反芻、PTSD 與PTG 之間的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圖1 反芻在體象與PTSD 和PTG 之間的中介作用

圖2 反芻在體象與PTSD 中的闖入性、回避性癥狀和PTG 之間的中介作用
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Preacher & Hayes, 2008)。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可以發現,體象經反芻至PTSD 中的闖入性癥狀、體象經反芻至PTSD 中的回避性癥狀的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說明上述中介效應成立。

表2 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的Bootstrap 分析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了體象對PTSD和PTG 的影響,并對反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接受手術后的乳腺癌患者的體象對PTSD 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也就是說乳腺癌患者術后身體意象問題越嚴重,創傷后的應激性癥狀越嚴重,這與以往的研究一致(Dyer,Bublatzky, & Alpers, 2015)。與此同時,乳腺癌患者的體象對PTG 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患者的身體意象問題可能會激發個體在完美意象喪失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現實,接納真正的自我,從而產生對“自我”以及“自身力量”的深沉反思和認識。所以,乳腺癌患者經歷手術后,盡管身體有一些不完美,但是相比于生命的重要性,他們反而更會產生一種“化繭成蝶”的體驗,從而更能夠獲得PTG 的體驗。
在進一步分析體象影響創傷后反應的機制時可以發現:一方面,體象通過反芻這一認知情緒調節方式對PTSD 中的闖入性癥狀和回避性癥狀起到正向預測作用。正如PTSD 的認知模型所指出,對于創傷性事件及其后果的反復思考和回憶會使個體更加痛苦,產生消極的心理反應(Szabo,Warnecke, Newton, & Valentine, 2017)。乳腺癌的治療,大部分采用根治切除的手術方式,這會對身體的外觀、感覺和功能產生重大影響。“切除”意味著“喪失”,喪失為個體帶來的身體形象上負面而持久的影響會給個體的身心帶來巨大的沖擊。個體對自己術后的“喪失”身體形象越不滿意,越會采用反芻認知情緒調節方式,個體越采用反芻的應對,越容易出現闖入性癥狀,仿佛自己仍然置身于創傷性事件發生時的情景中,從而產生痛苦的體驗。反芻還會產生回避性癥狀,這是指個體不愿意提起和創傷事件有關的事件、避免談及相關的話題。對于不滿意自己術后身體形象的患者來說,減少使用反芻思考來面對創傷經歷,可以減少PTSD 癥狀的發生。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體象通過反芻無法對PTG 起到預測的作用。這表明個體越不接納自己術后身體形象,就越會通過反芻這一消極認知情緒調節方式不斷思考、反復回想,這整個過程并不會促進PTG 的產生,這一結果與以往研究發現一致。以往結果表明,個體經歷創傷經歷后,一般采用積極的情緒認知方式會導致PTG 的產生(Chan et al., 2011)。PTG 整合模型指出,PTG 是與創傷事件斗爭的結果,創傷帶來的刺激會促進個體認知的改變,促使其對創傷事件、自我、世界等產生積極思考,從而引起PTG 的產生(周宵等, 2015)。剛剛經歷過切除手術的乳腺癌患者存在嚴重的體象問題,他們更傾向于使用抑制性情緒調節策略,會對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不斷回想,對人生感到悲觀失望,因此出現的積極性改變較少。
同時,本研究發現反芻這一消極的認知情緒應對可以中介體象到PTSD 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中介體象到PTG 的過程,這提示,PTSD 和PTG 的內部產生過程可能是有“雙通道模型”(安媛媛,伍新春, 劉春暉, 林崇德, 2013),即消極的應對方式(如逃避、反芻)正向預測PTSD,但是不能負向預測PTG,而積極的應對方式(如問題解決、尋求支持)可以正向預測PTG。由此可見,未來的研究應著重去探究體象與PTG 的中間機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于揭示體象對創傷后心理反應的作用及其內在機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一方面,體象是預測PTSD 的一個重要因素,乳腺癌患者對自己術后身體滿意度越低,并且越是采用消極認知情緒調節方式(如反芻),出現的創傷后應激反應越嚴重。建議在對患者的未來干預中,可以著重進行認知情緒方面的訓練,鼓勵患者更多地使用積極的、適應性的情緒調節方式,從而增加患者對自己身體變化的接納。另一方面,體象不僅能正向預測PTSD,也能正向預測PTG,換句話說,個體存在的身體形象問題越多,乳腺癌患者產生的消極心理后果越多,可能的積極成長也越豐富。盡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是橫斷研究,對于變量之間隨癌癥后恢復和發展的時間變化的關系無法進行探討,后續的研究可以設計縱向追蹤研究,更好地探討體象對PTSD 和PTG 的長期作用機制。其次,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均是自評量表,可能存在缺乏客觀性等問題,未來研究中可以通過他人報告或訪談等多種方法進行心理變量的考察。
5 結論
本研究發現,術后乳腺癌患者的體象既可以正向預測乳腺癌患者的PTSD 和PTG,也可以通過反芻這一認知情緒調節方式作為中介機制影響P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