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青春沒有點不單純的小美好
趙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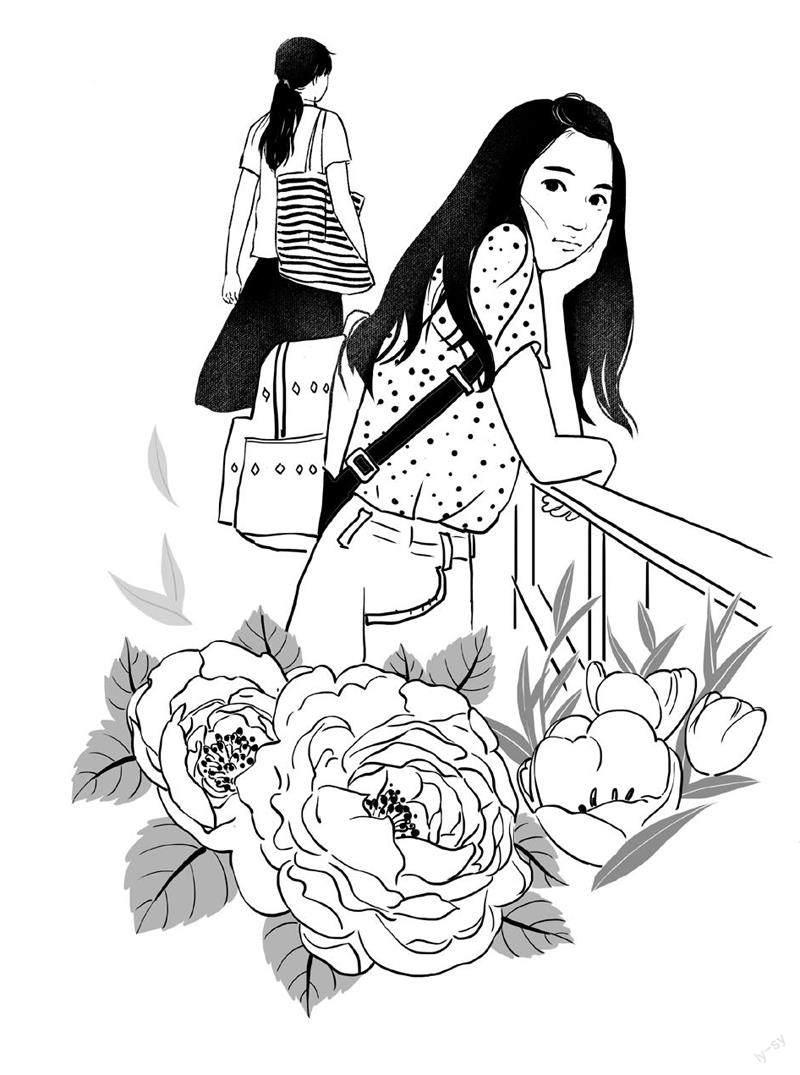
清涼的夜,一個女生跟我吐露真心:“我經常悄悄許愿,讓那個女孩越來越丑、越來越胖,考不上好高中。”停頓片刻,她問我,“我是不是很壞?”
我毫不猶豫地給出否定答案,可能是和她情誼深,心里的天平反而更傾向于她會這樣反省,感覺她善良又可愛,畢竟那個女孩——搶走了她曾經喜歡的少年。
她還在念叨對自己的不滿,而我滿心是她描繪過的畫面。
那個男生站在她宿舍樓下,大喊著她的名字表白;他們牽手繞著操場憧憬著明亮的未來,眉眼彎彎笑得合不攏嘴;他們驚動過老師和家長,終于熬過高考,卻以她被揭穿事情真相后掉不完的眼淚告終。
于是,她一邊告誡自己,真正錯的不是那個女孩,這樣的自己多不美好;一邊在午夜夢回時,狠狠地討厭她。
但其實, 她明明不是過錯的一方。誰的青春里,又沒有點不單純的小美好呢?如此鮮活又純凈。
前幾天和學姐聊天, 她突然發來一大串笑臉,然后用一些莫名的表情掩飾著,跟我說起高中時的事:“你不知道,其實一開始我很討厭你。”
“我嗎?”我有點蒙,一瞬間以為她在講故事。
沒等按下發送鍵, 她又補充道:“那大概是這種感覺——我穿著鎧甲,但你把它戳破扒開了。”我一臉茫然,她接著娓娓道來。
其實我和學姐的交集并不多。高二時我是學校文學社的社長,她不常寫,只是愛看書,甚至連社員都不是。
當時文學社太過冷清,我每天刷著貼吧發帖。她找到我,和我聊起天,說自己是一家著名兒童雜志社的小記者,采訪過也認識不少作家。我又驚又喜,還約她為我們的社刊寫稿。
如若不是她主動開口, 從始至終我都不會知曉她的這些情緒。她來找我時笑得溫暖熱情。后來某天在公交車站遇見,她沖過來給了我她最喜歡的作家姐姐的喜糖;又一個寒假時,還喊我一同去圖書館。那是為什么?
她三言兩語地說,因為當時采訪過作家姐姐,很開心很自豪,跑來跟我說喜歡溫暖的故事,我說我也是。
后來她才知道,我早已在那本兒童雜志上發表過文章。
算嫉妒嗎?準確說不是,但就是心里有點不舒服。但時隔幾年后提起,我們卻都覺得挺有趣的。我笑著說:“可當時,我覺得能做小記者的你,超厲害的!”
我不知道別人會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小心思。
不是鉤心斗角地爭名奪利,甚至你出現了困難,我一定會站出來幫你,我們可以全心全意分享難過、為對方著想,仿佛懷揣著一個溫暖的春天,實則心海又被寒冬冰封著。
叫她cream 吧,她是我少數朋友里一直很親近的姑娘。我不夠坦誠,從沒告訴過她,我曾悄悄因為她不開心過許多次。
而cream,正巧對我也有過相似的狀態。
當時是高一, 我格外迷戀寫信這件古樸文藝的事,于是迅速發展了十幾個筆友, 天南海北、五彩斑斕的信箋紛紛而至。我們互相交換秘密,有再多心事也不怕沒處傾吐。有一天,收到cream 的來信,她端端正正在第一頁寫了串Q 群號碼。
翻過這頁,她細膩的心事躍然紙上:“其實在知道這個兒童文學作家總群的號后,我就一直忐忑不安。因為我既想告訴你,但一想到你筆友很多,還能寫溫暖的故事,就又不想了。剛才終于寫下來,心里才舒坦了一些。你一定要原諒我這點不美好的小心思呀。”
我莞爾,心里一點都不在意。后來我羨慕過她寫下的故事,羨慕過她可愛的性格,以至于屏蔽掉她的動態,但還是很喜歡她。
甚至記得她的生日,精心挑選禮物送她,當她再有好事發生時,我也情不自禁一邊為她高興,一邊又悄悄討厭。
不能否認,時至今日我還是擁有數不清的“壞”心思。朋友許愿時,我哈哈大笑,告訴她,雖然喜歡過的少年早已成為過去式,也知道他新的彼岸單純可愛,但我還是不希望他們有好結局。
“我是不是更壞?”我認真地問她。她笑得格外開心。
其實原本我也有點討厭這樣的自己,但良知歸良知,現實里想做到極致的純凈善良,實在太難了,更何況那些所謂的灰色,其實沒有浸染過任何人的天空。
那個女孩不會因為好友的任何念頭而真的變差。這些小心思,只屬于我們自己,只會磨痛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那倒不如接受它,畢竟是我們對自己更好的期待滋生了它,也是我們的情緒、際遇和性格在滋養它。
沒錯,很久后我忽然發覺,我不甘、仰望、艷羨,是因為我也想擁有那些正照耀著別人的、在長路前方的美好事物。
可如若心海里總翻涌著對自己的不滿,又該怎樣奮力前行?
于是我只允許自己記住這是誰都有的心情,我并沒有多不好,我沒傷害到任何人,我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變得更好。
所以就當這些糾結、煩悶,是關于成長的一節必修課吧!是鮮活熱血和簡單心情的另一種體現;是青春里,或許不夠單純,但也足夠美好的存在。
(摘自《中學生博覽》2020年第3期,本刊有刪節,豆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