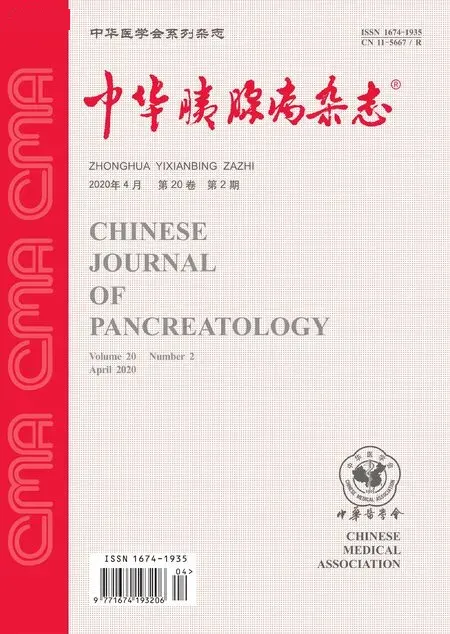胰腺腫瘤的基礎轉化研究模型
郭世偉
海軍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胰腺肝膽外科,上海 200433
【提要】 在多種癌癥治療取得突破的今天,胰腺癌治療藥物的研發仍舉步維艱,缺少能反映腫瘤細胞生物學特性和模擬其復雜微環境的模型是導致從基礎到臨床轉化研發失敗的重要原因。隨著類器官、人源腫瘤異種移植和人源化小鼠等技術的出現,使個體化精準研究腫瘤異質性、高度模擬包含間質細胞和免疫細胞的腫瘤微環境成為可能。利用這些新技術開展胰腺癌的基礎和轉化研究可以彌補既往研究手段的不足,有可能建立適用于胰腺癌研究的精準模型,推動胰腺癌治療藥物的研發,改善胰腺癌的療效。
2020年1月8日《C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1]發布了美國癌癥統計的最新數據,美國癌癥病死率出現歷史上大幅年度下降(2.2%),是自1930年以來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其中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結腸癌四大常見癌癥病死率穩步下降,黑色素瘤病死率下降幅度甚至達到了7%。究其原因,在危險因素防控的基礎上有效治療藥物的出現是其決定因素。黑色素瘤治療的突破要歸功于新獲批的多種療法,包括免疫檢查點抑制劑Yervoy (ipilimumab)、Opdivo (nivolumab)、Keytruda (pembrolizumab) ,靶向療法BRAF抑制劑Zelboraf(vemurafenib)等[2-4]。然而上述突破性療法,包括靶向治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細胞治療和質子重離子等在胰腺癌的臨床治療試驗中均以失敗告終[5];另一方面,大量通過傳統基礎研究模型篩選的藥物往往在臨床前動物模型驗證中即以失敗告終[6]。這些都導致了胰腺癌無藥可用,無法可醫,死亡人數接近發病人數,被認為是惡性程度最高的腫瘤。因此,探索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了目前治療的失敗成為胰腺腫瘤基礎和轉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一、胰腺腫瘤復雜的發病機制決定了現有研究策略的失效
目前研究認為,胰腺腫瘤的發病機制明顯區別于其他腫瘤,導致其惡性程度高的特性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1.腫瘤細胞來源多樣,惡變機制復雜:目前經典的胰腺癌發生模型認為腫瘤來源于導管上皮,早期病變為胰腺上皮內腫瘤(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PanIN),根據病變不典型增生程度可逐級分為扁平黏液上皮(PanIN-1A)到原位癌(PanIN-3)[7],即胰腺導管上皮細胞從正常演變到PanIN直至浸潤性癌的過程,同時伴隨K-ras、CDKN2A、SMAD4、TP53基因的突變。癌基因K-ras突變被認為是早期事件(PanIN-1A階段突變率35%, PanIN-1B 43% ,PanlN-3 100%),CDKN2A突變出現在PanIN-2,而SMAD4、TP53基因失活出現在后期[8-9]。然而臨床研究的結論卻與之不符。Guerra等[10]和Ji等[ 11]發現胰腺癌可來源于腺泡細胞,Ferreira等[12]證明通過癌基因AGR2可區分胰腺腫瘤的細胞來源,大部分胰腺癌來源于腺泡細胞發生導管組織轉化(acinar-ductal metaplasia, ADM)。而臨床上90%的PDAC患者可檢測出K-ras突變,只有60%的患者可檢出TP53突變[13]。Notta等[14]發現60%的胰腺癌細胞在有絲分裂過程中曾經出現過染色體碎裂(chromothripsis),導致腫瘤進展的基因突變不是依次發生而是同時產生,從而顛覆性認為胰腺癌的發生過程可能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量的基因變異可以通過一次或少數幾次有絲分裂過程中的錯誤而爆炸性地產生,從而造成胰腺癌高度惡性,最終導致不同胰腺腫瘤間存在極大的異質性,即生物行為差異明顯。以上假說使得胰腺癌分子分型研究在經歷多篇《Nature》文章論證后又回到了基于RNA表達分型的兩分法上[15-17],難以指導目前的臨床個體化治療。目前臨床獲益的只是具有遺傳BRCA突變,且鉑類化療無進展的近1%的患者[18]。因此,在針對K-ras和TP53突變的有效治療出現前,類似肺癌以針對單一驅動基因治療腫瘤的方案在胰腺癌上難以突破。
2.間質成分大量增生,作用因時而異:大量的間質增生是胰腺癌區別于其他實體腫瘤的另一大特征。在經典的胰腺癌病理形態中腫瘤細胞只占20%~50%,而剩余的由增生的間質細胞及其分泌的基質組成[19]。這些間質使得腫瘤局部壓力增高,缺血缺氧,導致腫瘤局部微環境復雜,化療藥物很難通過,是造成胰腺癌治療效果差的重要原因。臨床和基礎研究都證實間質作用復雜,盲目去除間質反而會促進腫瘤進展。2014年兩篇《Cancer Cell》雜志的研究分別證明間質成分可以限制而不是促進腫瘤細胞生長,刪除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 CAF,SMA+)會減輕纖維化導致的針對腫瘤細胞的免疫抑制,并加速腫瘤進展[20-21]。可有效抑制胰腺星狀細胞激活的Hedgehog通路抑制劑IPI-926(saridegib)的Ⅱ期臨床研究(NCTO1130142)結果顯示,IPI-926與吉西他濱聯用后患者生存期反而更短,不良反應發生率更高[22]。用KPGC模型小鼠進行的透明質酸酶(PEGPH20)研究在聯合AG化療方案取得陽性結果后[23],聯合FOLFIRINOX方案治療卻導致了患者更短的生存期[24]。相反,臨床取得成功的AG化療方案曾被歸因于可以和SPARC蛋白結合清除纖維間質并增加吉西他濱的灌注,然而最近的研究卻發現SPARC蛋白的表達并不能預測AG方案的療效,動物實驗也證明和SPARC蛋白表達無關,提示AG方案的有效與“去間質化”并不直接相關[25]。以上結果都說明胰腺腫瘤中CAF是一個復雜的、有多種細胞來源的混合體,部分成分(SMA+)可能主要起抑制腫瘤作用[26],部分成分(FAP+、FAK+、POSTN+)可能起促進腫瘤作用,在不同階段、不同藥物治療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27]。因此,在進一步明確各種來源的CAF在胰腺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具體作用之前,盲目針對間質的治療可能會產生臨床難以解釋的結論,干擾胰腺癌治療藥物的研究。
3.免疫逃逸機制不明,常規阻斷無效:雖然PDAC通常被研究者歸為“冷腫瘤”,但如果除去大量增生的間質區域,在腫瘤細胞周圍可以觀察到各種免疫細胞的大量浸潤[28],其中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比例偏少,而與免疫抑制相關的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調節性 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調節性 B 細胞(regulatory B cells,Bregs)較多[29]。這些細胞的免疫抑制機制主要包括上調抗腫瘤免疫細胞的免疫抑制受體,如細胞毒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a ntigen-4,CTLA-4)、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 1, PD-1)表達;分泌免疫抑制性可溶性介質,如 IL-10、TGF-β;抑制免疫細胞對必需代謝底物(如色氨酸、精氨酸)的利用等[30]。然而,最新研究發現這些免疫抑制細胞在胰腺癌中發揮的功能卻很復雜。《Cancer Discovery》的研究發現,單純Treg細胞的刪除會改變腫瘤微環境并加速胰腺癌變[31]。臨床研究也證實,可誘導Treg細胞凋亡并降低抑制性信號的CTLA-4單克隆抗體在胰腺癌患者中無效[32]。進一步研究發現,從癌前病變到晚期PDAC Treg水平逐步增加,癌旁小劑量 CTLA-4 單克隆抗體干預可有效減小腫瘤體積,而加大劑量后并未增加其抑瘤效果卻增加了次級淋巴節Treg細胞的浸潤,抵消了CTLA-4單克隆抗體抗腫瘤治療的作用[33]。PD-1治療只在微衛星不穩定的少數胰腺癌(<2%)中發揮作用[34]。同樣被寄予厚望的針對IL-10的SEQUOIA在胰腺癌三期臨床治療中以失敗告終[35]。這些結果都表明免疫微環境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單純抑制或拮抗某一類細胞無法解除整體免疫抑制。
因此,胰腺腫瘤需要一個復雜的三元n次方程來破解,腫瘤因素(a1,a2,a3……)+間質因素(b1,b2,b3……)+免疫因素(c1,c2,c3……)=高惡性生物學行為(Y)。
二、新研究模型的出現給腫瘤基礎轉化研究帶來希望
既往抗腫瘤藥物篩選模型已無法滿足目前個體化腫瘤治療的需要。2016年《Nature》雜志報道,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宣布,被研究人員使用達25年的抗癌藥物測試的癌細胞樣本群(NCI-60)即將“退休”[36]。主要是因為這些細胞系多來自惡性程度較高的腫瘤或者轉移灶,再加上歷經幾千代的培養,細胞的基因組和行為均發生了改變,難以反映臨床腫瘤真實特性[37]。而取而代之,條件重編程細胞(conditional reprogramming cell,CRC)、類器官(organoid)和人源腫瘤異種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用于基礎轉化研究的3種技術。目前類器官和PDX技術已初步證明可行。
類器官是指在體外由組織細胞或多潛能干細胞培養得來的3D細胞團,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組織的能力,且有與原組織相似的功能[38]。類器官最初應用于對體外正常組織器官的培養,是傳統體外2D培養與體內實驗模型之間的橋梁。相比于傳統的2D培養,類器官無論是在組成成分還是組織結構上都更貼近于來源組織;相比于體內實驗模型,類器官可以應用各類藥物和干預措施,研究組織器官發育及用于組織器官的移植和修復[39]。更重要的是,利用該技術構建的腫瘤細胞類器官可在體外真實立體模擬腫瘤和微環境中細胞的交互作用,真實反映藥物的作用方式,甚至可以應用體內實驗模型無法耐受的藥物[40]。同時還可以對類器官應用基因工程技術(CRISPR-Cas9等)改造某些目的基因,從而研究該類基因對腫瘤細胞的作用[41]。這些特點都決定了通過腫瘤類器官進行藥敏試驗篩選候選藥物,較細胞系等具有時間短、耗費低、結果準的優勢,為腫瘤的基礎和轉化研究提供重要工具。
PDX是將人的腫瘤組織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體內,依靠小鼠提供的腫瘤細胞生長所需活體環境而建成的動物模型[42]。該模型可以高度保留患者腫瘤的組織學特性、遺傳學特征以及腫瘤特異性,同時也保留了一部分腫瘤微環境信息,包括成纖維細胞、細胞外基質,但缺少免疫細胞,因此能較好地反映腫瘤細胞及其微環境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使其在模擬人體腫瘤組織生長、轉移、血管生成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43]。早期由于免疫缺陷小鼠構建的不完全,加上復雜的操作步驟及高昂的成本, 使PDX應用受到極大限制。而在NCI提出轉型后,全球已經加緊PDX庫建設,NCI初期目標是建立1 000個PDX模型,并將這些小鼠體內培養的人類腫瘤細胞提供給研究者,其中還包括每個腫瘤的基因組和表達譜數據。EurOPDX就是由16個歐洲機構聯合組成的PDX模型庫,旨在建立和發展臨床相關和標注的PDX網絡庫,據稱已經擁有1 500個PDX模型[44];美國的杰克遜實驗室已經擁有超過450個PDX模型。冠科生物科技(Crown Bioscienc)、諾華等國際制藥巨頭也紛紛采用PDX模型進行抗腫瘤藥物研究。目前很多不同腫瘤類型的臨床試驗已證明基于PDX模型與臨床患者的藥物反應相關性可達90%[45]。由于相同基因組特征的PDX模型可以被反復利用,使其在靶向藥物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再加上PDX模型是目前認為在體外最接近真實腫瘤環境的動物模型,已經成為目前化療和靶向藥物研發的不二選擇。
人源化腫瘤異種移植模型(humanized PDX cancer models, hu-PDX)是通過在NSG小鼠上重建人的免疫系統,然后再接種人的腫瘤,來評價腫瘤免疫治療效果的模型[46]。用于建立PDX模型的小鼠根據免疫缺陷程度可以分為BALB/c-Nude、SCID、NOD/SCID、NSG及NCG小鼠。其中NSG、NCG小鼠不但缺乏T細胞、B細胞和自然殺傷(natural killer, NK)細胞,而且細胞因子信號傳遞能力缺失,對人源細胞和組織幾乎沒有排斥反應,因此也可以重建人的血液和免疫系統[47]。通常在小鼠體內重建人類免疫系統的方法包括:(1)外周血單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人源化小鼠,即將人PBMC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體內,但PBMC小鼠只有T細胞功能,缺乏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 DC)功能,因此無法用于評價多肽及RNA類腫瘤個性化疫苗[48];(2)CD34人源化小鼠,即將人臍帶血來源的CD34+造血干細胞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體內,人造血干細胞在小鼠體內可分化為T細胞、B細胞、DC細胞、巨噬細胞等多種免疫細胞類型,因此CD34+人源化小鼠免疫系統功能更完全,目前已經被廣泛用于HIV等感染性病毒的機制研究及臨床評價中[49]。隨著腫瘤免疫療法研究熱度不斷提升,美國JAX實驗室及Crown Bio公司等也在CD34+人源化小鼠中移植人腫瘤細胞系,用于評價PD-1等免疫檢查點抗體藥物的藥效[50]。這一突破使得利用人源化小鼠評價免疫治療成為可能,彌補了PDX模型免疫治療評估的最大短板,成為目前少有的能在體外活體模擬評價人腫瘤免疫治療的模型,有望成為未來免疫治療個體化評估的模型。
以上3種模型最大的優點是腫瘤細胞來源于高度個體化的腫瘤患者,極大程度保證了腫瘤異質性的反應,同時盡可能保留了腫瘤微環境中的間質和免疫成分,無論對于胰腺腫瘤的基礎研究還是轉化研究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須的,也只有依賴這樣特殊的模型,胰腺癌的研究才有可能擺脫既往低效和無用的傳統,真正給胰腺癌的治療帶來希望。
三、新模型在胰腺癌研究中的應用
1.類器官:2013年,Clevers團隊率先利用來自小鼠胰腺的組織細胞在以RSPO1為基礎的培養基中培養出芽囊樣結構,并可以誘導其分化為導管細胞和內分泌細胞,被認為是最早的胰腺組織類器官[51]。2015年1月Clevers團隊在《Cell》雜志上率先報道胰腺腫瘤類器官可以從切除或活檢腫瘤組織中快速建立并長期保存,并表現出導管樣病變和腫瘤不同階段的特異性[52]。2015年10月 Muthuswamy團隊在《Nature Medicine》雜志首次報道在類器官上證實K-ras和TP53突變可以導致正常胰腺細胞癌變,并預測腫瘤類器官可用于藥物篩選和個體化治療[53]。2018年5月Tuveson團隊在《Cancer Discovery》首次報道構建了規模化的胰腺癌類器官庫,并系統評估了常用化療藥物在類器官和人群間反應的相關性,最終找出了可以用于臨床藥效預測的表達譜[54]。2019年11月 Clevers團隊再次在《PNAS》雜志報道了胰腺癌類器官庫用于臨床前潛在有效藥物庫篩選的研究,發現了一些目前臨床上尚未試用的敏感藥物,并強調了個體化方法對癌癥有效治療的重要性[55]。以上多個重量級的研究證實胰腺類器官體外培養的可行性,并證明了其在臨床轉化研究中的優勢。另外一些學者則在嘗試不斷完善胰腺類器官模型,以便應用于更多的研究。2018年3月Seino等[56]在《Cell Stem Cell》上報道了胰腺腫瘤類器官和不同間質細胞共培養的模型,應用該模型確定了兩種可逆的CAF亞型,成功揭示腫瘤和不同間質細胞的交互作用。2019年2月Tuveson團隊在《Cancer Discovery》上報道使用類器官和小鼠模型確定腫瘤分泌的TGF-β和IL-1是促進CAF異質性的重要配體,證明IL-1誘導LIF表達和下游JAK/STAT活化,產生炎癥性CAFs,TGF-β通過下調IL-1受體表達和促進向肌成纖維細胞分化來拮抗這一過程,為抗間質治療提供了策略[57]。而 James團隊在此基礎上加入了免疫細胞,形成了腫瘤細胞、CAF和免疫細胞共存的最接近活體情況的類器官模型,并在其中評價了免疫檢查點阻斷治療效果,為胰腺癌體外類器官模型做出了有意義的探索[58]。
2.PDX:腫瘤特性和所使用免疫缺陷小鼠的類型是影響PDX建模成功率的主要因素。2011年Garrido-Laguna團隊利用裸小鼠進行皮下移植的69例胰腺癌成功率為61%[59],2013年Mattie團隊利用SCID小鼠進行皮下移植的12例成功率為67%[60],2019年筆者所在課題組利用NSG小鼠進行皮下移植的121例成功率達71.1%[61]。進而,多個團隊利用胰腺癌PDX高成瘤率的特點進行了廣泛的臨床前藥物篩選和個體化治療研究。早在2006年Viqueira團隊就建立了一個胰腺腫瘤PDX平臺來測試一些具有轉化前景的藥物,并報道了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和磷酸化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的表達與某些藥物反應之間的關聯[62]。2008年Smith團隊使用了Freiburg PDX庫(由400個裸鼠皮下生長的人類腫瘤模型組成)測試吉西他濱和抗VEGF抗體(HuMV833)的藥效[63]。2015、2016年Lohse團隊利用PDX小鼠研究了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基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PARP)抑制劑olaparib(AXD-2281)對BRCA1/ BRCA2突變胰腺癌放化療敏感性影響的研究,證明其對鉑類更敏感[64-65]。另外一系列針對腫瘤干細胞的藥物drozitumab[66]和AZD7762(Chk1抑制劑)[67]先后在PDX模型上被證實可以抑制胰腺腫瘤生長。此外,腫瘤間質對藥效影響的評估也成為PDX的另一重要用途。2011年Von Hoff團隊利用裸鼠構建了一個被稱為PancXenoBank的PDX平臺,利用該平臺發現吉西他濱聯合白蛋白紫杉醇能顯著減少腫瘤組織中的間質含量,進而提高腫瘤組織中吉西他濱的濃度(2.8倍),該方案成為目前胰腺癌治療最有效的方案之一[68]。Valles團隊利用NOD/SCID小鼠PDX模型測試了Ibrutinib(PCI-32765,BTK抑制劑)抑制纖維炎癥反應的作用[69]。 Rajeshkumar等[70]甚至利用PDX模型研究了苯甲雙胍、二甲雙胍和丙酮酸脫氫酶抑制劑二氯乙酸對胰腺癌的抑制作用。在個體化治療方面,有包括絲裂霉素C和順鉑、替西莫司(mTOR抑制)和salirasib與吉西他濱等多個治療有效并長期生存的個例被報道[59,62],隨著PDX應用的更加廣泛,個體化治療的成效將更加明顯。
3.Hu-PDX:目前尚未有利用Hu-PDX研究胰腺癌免疫治療效果的報道,但其在其他實體瘤研究的經驗可以提供借鑒。將人外周血單個核細胞或成熟的免疫細胞亞群經靜脈注入受照射的NOG或NSG小鼠體內后,由循環中可檢測到人T細胞、B細胞、NK細胞和DC細胞,并被證明可以用于評價單克隆抗體、細胞因子治療(IL-2)、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CB)和DC疫苗的作用[48,71-72]。抗碳酸酐酶IX(carbonic anhydrase IX, CAIX)單克隆抗體與IL-2聯合應用可通過誘導人NK和T細胞反應抑制腎癌的進展。在PBMC人源化小鼠模型中也觀察到nivolumab、阿替唑單抗、彭布羅單抗和烏魯單抗的抗腫瘤活性[73]。在PBMC人源化小鼠模型中比較DC疫苗制劑效果,并評估黑色素瘤相關抗原特異性免疫應答和黑色素瘤抑制功能[74]。然而移植物抗宿主反應(graft versus host reaction, GVHR)的發展和小鼠存活率低限制了這些模型在評估癌癥免疫治療有效性方面的應用[75]。利用人CD34+造血干細胞建立人免疫系統可以克服GVHR的障礙。在小鼠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匹配的情況下,干細胞能夠適應小鼠的環境,發育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人免疫系統。在胎肝造血干細胞生成的人源化小鼠的循環中檢測到人輔助T細胞、細胞毒性T細胞、B細胞、單核細胞、NK細胞和DCs[76]。進而在肝細胞癌PDX培養過程中發現細胞毒性T細胞和NK細胞的數量和比例下降,而從腫瘤中分離出來的TIL顯示出受腫瘤改造的表型,包括免疫檢查點表達增加,細胞因子和細胞毒蛋白產生受損;同時在這個模型還觀察到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不良反應,這與臨床研究一致[76]。此外,在臍血造血干細胞生成的人源化小鼠模型中,nivolumab通過增強抗腫瘤T細胞反應、增加腫瘤中GrB+或IFN-γ+CD8+細胞和降低體內HLA-DRlow髓樣細胞的比率來抑制MDA-MB-231細胞和CRC172細胞的生長[77]。與單用nivolumab相比,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 HDAC)抑制劑OKI-179和nivolumab聯合應用進一步抑制腫瘤的生長,表明HDAC抑制劑可以改善體內的抗腫瘤免疫應答[77]。迄今為止,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抗PD-1和抗CTLA-4治療后,人源化小鼠體內的人PDX腫瘤發生了退行性改變[71],表明人源化免疫腫瘤模型可以作為腫瘤免疫治療或聯合免疫治療研究的新興平臺。
四、展望
研究模型的進步是推動腫瘤學發展的重要動力。2D細胞體外培養技術的成熟使腫瘤的基礎細胞分子研究成為可能,多種“基石”類的化療藥物得以發明。PDX模型的出現使研究腫瘤和機體間相互作用成為可能,為多種需要在體內代謝的抗腫瘤藥物評估提供了幫助。而新一代類器官和人源化PDX模型的出現,使研究者可以在高度保留組織學特性、遺傳學特征和異質性的同時,在體外重建腫瘤微環境信息,包括成纖維細胞、細胞外基質和免疫細胞,而這些特性的缺失正是既往胰腺腫瘤研究模型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雖然這些模型還有需要完善的技術細節,在胰腺癌中的應用還需進一步探索,但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研究者的應用,胰腺癌的基礎和轉化研究必將迎來突破。
利益沖突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