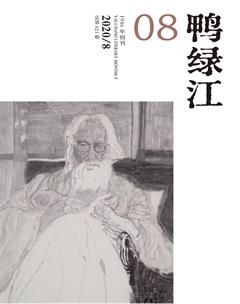農民敘事的主題擴展與批判焦點的位移
《尸功記》發表于《鴨綠江》1980年第11期,這是誕生于“高曉聲創作的旺盛時期” ①的一篇作品。1979年,“歸來者”高曉聲發表了《“漏斗戶”主》和《李順大造屋》兩篇小說,并憑借后者摘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0年,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發表于《人民文學》第2期,獲得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連續的獲獎給高曉聲帶來了巨大的文學聲譽,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深刻影響了此后文學史對于高曉聲敘述的走向,“陳奐生系列”成為高曉聲的代表作和標志性風格。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同一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尸功記》的被遮蔽似乎在情理之中,它不僅未能成為文學史關于高曉聲敘述的一個重要討論對象和組成部分,甚至在高曉聲本人的評價序列中也并不占據主要位置。1979年至1984年,高曉聲以年份為基準連續出版了年度性的短篇小說集,由此可見其在1980年代初期的創作量相當可觀,但這些作品大多被兩部獲獎作品所遮蔽了。高曉聲對此并不滿意,他曾在與葉兆言的對話中談及對于這一現象的個人思考,兩人有如下一段對話:
“我后悔一件事,《錢包》《山中》《魚釣》這三篇沒有一篇能得獎。”
“是啊,《陳奐生》影響太大了,”我說,“我看見學校的同學在寫評選單的時候,都寫它。”
“哎,可惜。”他嘆氣。②
在這段回憶性的以葉兆言視角復述和復原的對話中,高曉聲在為另外三篇同時期發表的作品打抱不平。從主題和敘事風格上看,這是游離于“陳奐生系列”之外的三篇作品,在敘事主題和方法上另辟蹊徑,與“陳奐生系列”并無關聯。相比較而言,《尸功記》與“陳奐生系列”的主題和風格更為接近,在彼時更有理由獲得關注,甚至好評。但在高曉聲個人的評價序列中,《尸功記》顯然并不占據靠前的位置,而在更為廣泛的讀者中間也未獲得太多的反響和認同。
然而,這的確是一部帶有典型高曉聲敘事風格,彰顯其機智和敏銳洞察力的作品。一方面,它延續了高曉聲一貫的對于農民與農村主題的書寫,并將《李順大造屋》《陳奐生進城》等作品中“吃”與“住”的主題擴展或上升至生與死的主題,并通過生死主題深刻反思批判社會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它延續了其批判性的寫作風格,并將批判的鋒芒更深地顯露出來。相較于《“漏斗戶”主》中終于分得糧食,擺脫“漏斗戶”窘境,《陳奐生進城》中阿Q式精神勝利的“光明的尾巴”,《尸功記》的批判性顯然更為徹底,且它的批判鋒芒不再聚焦于農民群體,而是位移到了公社領導這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體系的基層環節之上。換言之,這部作品既在創作題材和風格上與高曉聲一貫的創作具有延續性,同時又把這種風格強化和主題擴展了,是一篇不應該被忽視的重要作品。
1
考察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農民既是重要的考察對象,也是觀察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相比于以往歷史時段中農民作為被統治者/造反者的歷史定位和形象敘述,20世紀的中國農民無論是作為階級還是階層都有了巨大的內涵擴容和主體能動性。20世紀之初的前三十年,農民是作為被啟蒙者來定位和敘述的,這種敘述在魯迅等一批“五四”作家的筆下得到展現和強化。事實上,無論是晚清末期的軍閥混戰還是民主革命,農民對于社會歷史進程的參與度極低,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游離于主流的歷史進程之外,也因此成為被啟蒙者以及“國民劣根性”批判的重要對象之一。30年代之后,伴隨革命發展需要,農民作為革命主體的身份被逐步強調,并在毛澤東的一系列政治論著中得到理論上的確認。農民的身份地位由早期的被啟蒙者到革命主體,經歷了根本性的身份轉變、功能上升和意義負載。這種革命主體性的身份和地位此后延續下來,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段,這種身份的功能定位又有著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尸功記》中有著深刻體現。
《尸功記》的敘述起點是王老七之死,重點內容圍繞如何下葬的問題鋪展開來,是遵從傳統習俗土葬還是按照縣革委會的新政策火葬構成了小說的主要矛盾和敘事動力,二元對立的結構既簡潔明了又突出主題,這是高曉聲小說的一貫風格。王老七之死是典型的“農民之死”,不管是從出身、經歷、影響等各方面考察,王老七都歸屬于農民階層和農民隊伍,農民身份是王老七的本質性身份。王老七的死亡本是最常見亦非常普通的一個自然事件。“他離開這個世界,就像一片枯黃的樹葉從枝頭悄悄落下來,完全不該引起任何注意。”③然而,當王老七之死與關于火葬的新政策發生時間上的偶合,歷史的張力乃至殘酷就驟然顯現了出來。如果繼續遵循傳統進行土葬,則意味著傳統文化習俗對于新政策的抵抗。如果執行火葬,則意味著新政策的“時間開始了”。這樣,如何下葬的問題引發的矛盾和對峙就不再僅僅是個體生命的命運問題,而是不同歷史主體之間的對峙和對抗問題。從結果來看,作為傳統鄉村文化習俗代言人的王老七的被迫火葬預示著傳統鄉村文化力量的落敗。在此過程中,王老七成為改造對象和新政策執行的實踐者,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革命主體身份的降維,其在革命共同體內部的身份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轉換。
值得追問的是,發生身份轉換的原因何在?從外部來說,顯然與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密切相關,與不同時代的革命任務相關。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農民的革命主體地位最為重要的歷史時期,這顯然與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歷史形勢和緊迫任務直接相關,是黨領導下革命隊伍擴充力量的重要策略之一。無論從戰術還是戰略層面,這一時期的中國革命都帶有鮮明的“農村化”特征和農民化氣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下鄉”等口號的提出即是典型的表征之一。60年代同樣是農民革命主體地位得到強化的歷史時期之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分子勞動改造等等社會運動突出的均是農村和農民的重要地位和政治正確性。然而,隱形的變化在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面對的歷史形勢和任務是外御強敵、內爭解放,嚴峻的形勢迫使革命者空前強化革命共同體的團結協作關系,而占據多數人口的農民必然成為共同體中最堅固的基石,緊緊依靠農民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向農民學習、到農村“廣闊天地”中鍛煉改造要解決的是革命共同體內部的路線分歧和思想分歧,農村與農民是整頓思想和作風的舞臺和工具,是革命的一部分,但并不占據主導性位置。這是共同體內部力量之間的微妙變化,這種變化為身份轉換提供了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空間和可能。
另一方面,從農民群體的內部出發進行考察,不論在革命共同體內部扮演何種角色,占據何等地位,其始終未解決的一個遺留問題是啟蒙的未完成。在20世紀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結構中,啟蒙的未完成始終是一個懸置的歷史問題,而啟蒙的重要對象之一即是農民群體。雖然在革命進程的某個時段,啟蒙與被啟蒙的角色曾發生根本性的反轉,農民作為啟蒙者對知識分子展開啟蒙,但這只是特殊時期的革命策略,農民本身的啟蒙未完成反而因此成為一個被遮蔽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一問題在社會革命結束、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之后的歷史時期浮出水面。農村傳統文化習俗中落后、迷信、蒙昧的一面更多浮現出來。火葬政策即是對農村文化傳統習俗的一種革命性改造,它表面是針對人(農民)的下葬方式的改變,實際是對農民的思想認識和生活習俗的改造,也即對農民所依存的傳統鄉村文化習俗體系的改革和清理。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和農民是作為被改造對象而存在的,其身份的轉變根源即在于其內部那些未被現代化和啟蒙過的落后的文化和思想病灶,這個過程也可視為啟蒙的再繼續。
上述內外兩種因素構成了農民身份轉換和主體地位降維的主要原因。在小說中,作者是以王老七之死來打開這一歷史問題的,王老七之死不僅是個體生命的消失,同時將農民在革命共同體內部的身份轉換和位置變化映照出來,將革命共同體內部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關系張力凸顯出來。在這個意義上,王老七并未死亡,“王老七竟因此使熟悉他的人常常想起他”,盡管并非主動的選擇,但作為新政策落地生根的第一人,王老七在無意中成為新的政治實踐的“執行者”,成為一個顯著的歷史符號。命運在此既顯示出吊詭的一面,也顯示出辯證的一面。王老七生前的默默無聞、不為人所注意與死后的因火葬事件而使人“常常想起他”,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生與死在此完成了置換,他活著,但他是“死(無聲)”的;他死了,但他又長久地“活”(在人們的記憶中)。可以說,他是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向歷史的最大獻祭,也以死亡的儀式把自身存在的意義最大化地體現在歷史進程中,鑲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2
小說中“火葬事件”的矛盾具體體現在已經過世、不會開口的王老七身上,表現為執行縣革委會決定的公社書記與王老七的鄉親族人之間誰來挖墳的矛盾問題上。但這一事件在更深層意義上體現出的是鄉村傳統文化習俗與革命現代性之間的緊張關系。
長期以來,鄉村及其文化體系是作為被認可和學習的對象而存在的,新中國成立前的革命時期,鄉村作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重要戰略內容之一,被賦予了重要革命功能。新中國成立后,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體系的重要部分,鄉村承擔著基礎性的建設功能,農業、農村、農民構成了國家體系的重要環節和基礎。但問題在于,以傳統農耕文明為基礎的鄉村與力圖實現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目標是實現“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和鄉村社會向現代工業科技文明和城市社會的轉型。在這一巨變中,城市將高速擴張和發展,鄉村將在衰落中向城鄉交融推進而實現蛻變。”④ 換言之,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鄉村并不能長久承擔起國家建設的重任,即便它不是革命的對象,也要經過自身的改造才能適應未來的長遠建設,從而將自己更好地嵌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體系中去。“火葬事件”即可視為是這樣一種改造的方式和內容。但這種改造如何進行,由誰來承擔,以何種力度進行,又是充滿了疑問的新問題。
《尸功記》展現了這個過程的艱難性和暴力推進的后果。小說圍繞如何下葬構成了一個二元對立的結構性矛盾,矛盾的雙方是執行縣革委會決定的公社書記殷賽揚與王老六(事實上的死者王老七的代言人)。作為死者的哥哥,王老六“既怕得罪干部、得罪‘降大任于己的‘天,又怕得罪死者”,因此“用了兩面派手法”“一方面答應了干部,一方面卻在半夜里埋葬了弟弟”。王老六的做法是很容易理解和贏得同情的,這是在親情倫理的驅使之下,更傾向于照顧死者意愿的不得已的行為。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公社書記殷賽揚將矛盾激化,要堅決執行火葬規定。在王老六采用拖字訣避開挖棺任務之后,殷賽揚迅即招來生產隊長、民兵排長等人執行挖棺任務。令他意外的是,被他視為“專政力量”的生產隊長、民兵排長均意外地使其期望落空了。他們的拖字訣借口雖五花八門卻在本質上與王老六如出一轍,即拒絕執行這一違背鄉村文化習俗的任務,使得“殷書記心頭,一陣陣怒氣升騰”。在這里,一個鄉村文化的共同體顯現出來。從政治角度說,生產隊長、民兵排長同屬于政治體系的一部分,理應毫不遲疑地執行新的政治決定,這是革命干部的組織性、紀律性。但他們又同屬于鄉村文化意識形態哺養出的一類人,雖有政治身份,但精神層面卻有更多的鄉村文化屬性。在政治決定與鄉村習俗發生沖突的時刻,他們站到了鄉村的一邊,此刻,以鄉村傳統習俗文化為根基形成的一個共同體顯現出來。盡管作為改造的對象,這個共同體的命運結局早就注定,但這一過程充分顯示了改造的艱難。
殷書記在對專政力量失去信心之后,轉而求助于專政對象,利用專政對象來完成新的改造任務,這一行為既體現了他的機智,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令人玩味的是“四類分子”在挖棺中的表現。作為被專政對象和改造對象,“他們知道自己不會因破四舊立功,卻會因‘階級敵人挖了貧農的尸犯下彌天大罪”,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現實境遇決定了他們只能執行命令。不過他們“工作進展很慢”“縮手縮腳”并聲音低低地唱起了“雙推磨”,內心的抗拒展露無遺。作為專政對象,“四類分子”的大部分人也脫胎于鄉村文化意識形態,他們的態度既體現了一種個體性的道德判斷,同時也是傳統鄉村文化習俗影響下的結果。在這里,在傳統鄉村文化意識形態中生長起來的革命群眾、鄉村領導者和專政對象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情勢下再次結盟在一起,這是有別于階級話語的新的劃分方式。傳統鄉村內部被革命介入和區隔的不同力量再度實現了聯合,成為一個精神文化共同體。這一共同體的形成顯示了傳統文化意識形態所塑造的鄉村文化意識的強大和自足。
值得分析的另一個形象豐滿的人物是公社書記殷賽揚,他是一個具備文學典型性的人物。福斯特將小說人物分為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兩類,扁平人物是“基于某種單一觀念或品質塑造而成的”,其優勢在于“不論他們何時登場,都極易辨識”且“很容易被讀者記牢” ⑤。在一定意義上,殷賽揚具備了扁形人物的特質,在精神內涵上具有顯而易見的符號化和象征性功能,但他又超越了福斯特所謂扁平人物的單一向度,至少在兩個向度上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首先是政治身份的指代性。在小說中革命現代性與傳統文化習俗構成的二元對立結構中,他是前者的力量化身和執行者,是推動情節發展并突破對峙形態的主導性力量。作為革命意識形態的現實化身,殷賽揚具有符號化的非本我的功能指代性,即象征國家意志和意識形態的規訓力量。從這個角度講,其推動農村火葬工作、執行破四舊的規定命令并無道德性的對錯判斷,他只是革命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鏈條,火葬工作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細節。但作者顯然又賦予了這個人物以更多的象征意義和反思表達的功能,其處理方式和手段是把殷賽揚從革命工作體系中解放出來,還原為一個具體的、鮮活的、欲望化的個人,把他從一個符號化的敘事道具擴展為既能承擔意識形態的革命要求,同時又能代表一類基層公社干部的多面人。面對王老七之死和縣革委會火葬新政策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巧合,他迅速判斷出這“是天造地設給他們的一個立功機會,這具尸體比任何尸體都容易利用,他們付出的力氣可以‘最小、最小、最小,而成果肯定會‘最大、最大、最大。”殷賽揚在王老七火化事件中之所以破除一切困難,不惜與強大的傳統鄉村習俗力量為敵,其動力即源于此。落實新政策新要求是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也構成了此一事件的虛假表象,其實質乃是創造機會,做出政績的私欲追求,這正是革命隊伍內部投機者的典型心理和常見手段。值得玩味的是在火葬事件以暴力手段完成之后,殷賽揚對于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的“引而不發,躍如也”革命方法的思考,他不僅歪曲和背離了這一方法,同時也背離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體現的革命路線和精神。該報告是毛澤東關于農民革命主體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要點是要團結農民、引領農民,發動農民,凝聚革命共同體。殷賽揚的行為顯然是對這一歷史傳統的背離,在他嚴格執行縣革委會決定的虛偽外衣之下,隱藏的是他“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頂頭上司的屁才是真的”的偽革命者信念,是他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投機心理。他也果真如愿以償,“不久就升了官”。這一結果,將作者對于殷賽揚的批判性塑造上升為了對政治體制的反思和批判,他的升遷固然是個人投機性的勝利,但更是整個基層政治體制腐化墮落的表征,中國革命的力量體系在基部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由此,殷賽揚這一人物突破了福斯特意義上的扁平人物,具有了多向度的意義內涵,成為一個“極易辨識”且“很容易被讀者記牢”的典型性人物。
在這場現代性改造之中,新政策最終落地生根,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現代性在鄉村之中所遭遇的危機以及存在的種種難題。一方面是如何面對傳統鄉村及其主導下的共同體,如何安置作為革命主體的農民和農村,如何將其嵌入新語境下的革命體系之中。另一方面是如何面對異化了的革命投機者,如何選拔、委任政策的推行者和實踐者,革命的改造該以何種方式和力度進入和展開。這兩方面的問題共同構成了革命在鄉村領域的危機,這是新的革命問題和歷史難題。對于上述問題的表達和呈現體現出高曉聲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是他對于19世紀70年代社會歷史形勢的深入思考和洞察。
3
薩莫瓦約認為,“每一篇文本都聯系著若干篇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 ⑥。盡管在有關高曉聲的論述中,很難見到《尸功記》的影子,但這部時常游離于讀者和研究者視野之外的作品與高曉聲的其他作品之間存在著緊密而重要的互文性關系。這種關系一方面體現在這篇作品對農民、農村主題的擴展性書寫上,另一方面體現在更為深刻和徹底的批判性態度和立場上。
高曉聲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基點和目標是要為歷史留痕,這一動機決定了其作品必然會緊扣時代的脈搏和律動,與時代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高曉聲在文學創作中將這種緊密性從國家政策轉化為農民的日常生活問題,以生活化和個人化的敘事方式進行呈現表達。比如兩篇帶來巨大聲譽的作品《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進城》的突出主題分別是“住”和“吃”。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農民最關心的問題。高曉聲緊緊抓住這兩個核心問題,通過日常生活敘事實現了與國家宏大敘事的共振與共情,兩篇小說發表后所獲得的巨大認可,充分說明了由“吃”“住”等日常化問題連接時代核心命題的策略性成功。這種策略在《陳奐生包產》《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出國》等系列小說中均有使用。
盡管對于高曉聲與農民關系的情感理解和認同存在著分歧,但對于農民、農村的書寫構成了高曉聲文學創作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部分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將自己作為農民之一員來進行思考和寫作,還是將農民和農村對象化、他者化進行觀照和表現,農民與農村是高曉聲文學創作最重要的關鍵詞和內容。在《尸功記》這篇小說中,高曉聲同樣延續了其對于農民與農村的一貫關注與書寫。不同之處在于,這篇小說進入的切口并不是農民所熟悉和關心的衣食住行等基礎需求層面的問題,而是生與死這樣具有一定形而上色彩的文化性、哲學性問題。這或許也是造成這篇小說未能引起更廣大讀者反響的原因之一,即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感和介入性不足產生了間離效果。生與死的問題雖然也是農村農民生活的重大事件,但與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離,尤其是在傳統農村文化形態中,作為生命起點和終點的生與死更多被歸之于宿命,而宿命是不可更改的,只有被動接受。因此,相對而言它較少引起農民群體的深入思考。但高曉聲在這里不是要探討農民生與死本身的問題,而是要借生死問題談命運,確切地說,是由生死問題觸及農民在歷史浪潮中的命運之不確定性的問題。王老七之死是自然死亡,并無任何外力作用或內在復雜原因,但王老七之死構成了思考農民歷史命運以及傳統鄉土文化與革命現代性復雜關系的一個巧妙入口。生死問題是對于衣食住行問題的更高層次的延伸,也構成了與高曉聲其他小說的互文關系。在農民這個總主題和常見視角之下,高曉聲從各個角度展開他的思考和敘事,而生死問題、命運問題構成了對于這些問題的哲學化思考和意義延伸。這也使得高曉聲對于農民農村的書寫更加立體化和哲學化,豐富了他關于農民農村的思考和表達。
另一方面,批判性的深化。高曉聲的創作被譽為具有魯迅的風格,這主要是指其對于國民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在高曉聲筆下,農民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需要改造的一面,這是客觀化的存在,而不是經過文學美化修辭的塑造,對于農民問題的批判構成了他寫作的一個重要向度。比如在《“漏斗戶”主》中寫到陳奐生被隊長以他的需求具有普遍性而拒絕借糧的情形時,他“卻不想說出來,因為這太小算了,真是只有他這樣餓慌了的人才會這樣小算。而且這又不是欺他一個人。按照他歷來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個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會有比他強得多的人出來鳴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頭椽子呢。”陳奐生保守和順從忍受的心理性格被描繪出來。在《陳奐生進城》中,在被動交了五元錢的住宿費之后,陳奐生內心感到極為郁悶,他把這種郁悶通過破壞性行為發泄出來。他“推開房間,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猶豫:“脫不脫鞋?”一轉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塊錢呢!”再也不怕弄臟,大搖大擺走了進去,往彈簧太師椅上一坐:“管它,坐癟了不關我事,出了五元錢呢。”陳奐生的小農意識和幽暗心理被高曉聲敏銳地把握和生動呈現了出來。
斯賓格勒認為,“檢驗一個思想家的價值標準,是對他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發生重大事件的洞察力”。⑦文學家不能與思想家畫等號,但文學創作需要對所處時代與重大事件有敏銳的感知和深刻的洞察,否則就無以實現反映時代的文學使命和價值追求。高曉聲的創作與時代生活關系緊密,能夠與時代同頻共振,這里有一個重要前提是作者對于時代歷史走向的洞察與預判,這構成了高曉聲塑造典型人物的前提,也構成了反思意識和批判意識產生的基礎。高曉聲的批判意識并不僅僅局限于作為小說主角的農民,而是觀照整個社會場域,是對整體性的社會問題的思考和表達。《尸功記》典型地體現了他的這一批判性思維和問題意識。這篇小說盡管依然有著農民敘事的特征,但作為個體的農民并不是主要的書寫對象,而是借由農民視角揭示鄉村文化共同體與革命現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基層政治體系所存在的問題與裂隙。也即是說,高曉聲將批判和反思的對象由農民延伸到了基層政治乃至整體性的政治體系。以殷賽揚為代表的基層政治代言人如冰山一角,揭開了政治體系內部存在的隱患,其“不久就升了官”的結局將這種對隱患的思考輻射至整個政治體系,令人深感憂慮。這樣一個“反諷式”結尾,令問題擴大化和深化了,也讓批判的鋒芒不再遮遮掩掩,而直指問題的根源和深處。
可以說,《尸功記》更為徹底地深化和實踐了高曉聲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盡管小說整體上仍舊體現出其一貫的喜劇化風格,但反諷手法的巧妙運用讓這種喜劇風格具備了更強的諷刺力量。以“尸”立“功”,既體現出農民個體命運的悲劇性,也解構了農村基層政治的嚴肅性和崇高性,這是高曉聲批判意識在更寬闊社會層面的深度呈現和表達。因此,《尸功記》是高曉聲創作譜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篇應該被重視和重新審視、估量的重要作品。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崔慶蕾,男,1985年生,山東聊城人。文學博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副主編。有文章散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藝術評論》《創作與評論》《文藝報》等報刊,部分文章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