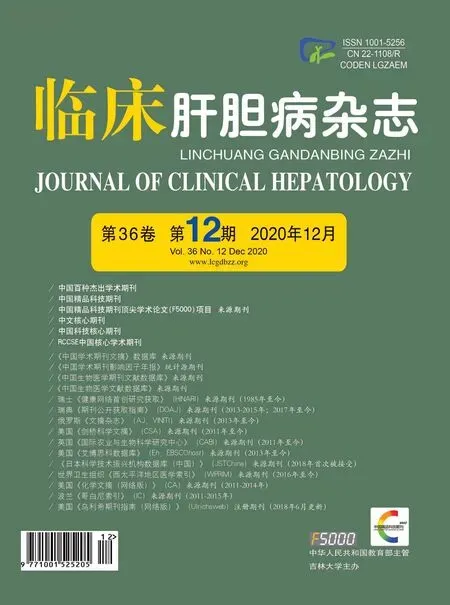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1例報(bào)告
吳 蓉, 冷愛(ài)民
中南大學(xué)湘雅醫(yī)院 消化內(nèi)科, 長(zhǎng)沙 410008
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PBC)是一種慢性肝內(nèi)膽汁淤積性疾病,其病理特點(diǎn)為進(jìn)行性、非化膿性、破壞性肝內(nèi)小膽管炎,最終可發(fā)展至肝硬化[1]。80%以上的PBC患者常合并至少1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干燥綜合征是較為常見(jiàn)的[2]。而PBC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的病例報(bào)告尚不多,現(xiàn)將中南大學(xué)湘雅醫(yī)院收治的1例PBC合并AIHA病例報(bào)告如下,并總結(jié)國(guó)內(nèi)外近10年報(bào)道的診斷為PBC伴AIHA的8例患者臨床資料,對(duì)以上9例患者的臨床特征、實(shí)驗(yàn)室檢查結(jié)果及治療轉(zhuǎn)歸等方面進(jìn)行分析,以提高臨床醫(yī)生對(duì)本病的認(rèn)識(shí),旨在為臨床診斷與治療提供更科學(xué)的理論依據(jù)。
1 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61歲,因“間斷腹脹12年余,乏力10 d”于2018年3月1日入住本院。患者2005年起開(kāi)始出現(xiàn)腹脹,輾轉(zhuǎn)多家醫(yī)院診斷為“隱源性肝硬化”,予護(hù)肝、護(hù)胃、利尿等對(duì)癥支持治療,2008年、2009年曾因嘔血在外院共行3次食管靜脈套扎術(shù)。個(gè)人史及家族史無(wú)特殊。2015年12月入院檢查:ALP 287.7 U/L,GGT 78.6 U/L,抗線粒體抗體M2亞型(AMA-M2)陽(yáng)性,抗核抗體(ANA) 1∶160(著絲點(diǎn)型),抗三聯(lián)體抗體陽(yáng)性,抗前髓白血病細(xì)胞抗體弱陽(yáng)性,抗核膜糖蛋白抗體(抗gp210)弱陽(yáng)性;腹部影像學(xué)示:肝硬化合并門(mén)靜脈高壓癥(脾大、側(cè)支循環(huán)開(kāi)放、腹水),膽囊大小形態(tài)正常、未見(jiàn)結(jié)石光團(tuán)聲像、膽總管內(nèi)徑5 mm、內(nèi)清;胃鏡示:食管靜脈顯露,慢性非萎縮性胃炎及球炎。診斷為PBC失代償期,予以對(duì)癥支持治療后病情好轉(zhuǎn),出院后患者以0.75 g/d劑量規(guī)律服用熊去氧膽酸(UDCA)膠囊,期間病情控制尚可。
2018年2月下旬患者出現(xiàn)明顯乏力,伴皮膚黃染及瘙癢,于2018年3月1日入院。體格檢查:體溫 36.7 ℃,脈搏 98次/min,呼吸 18次/min,血壓 87/46 mm Hg。慢性肝病面容,皮膚鞏膜黃染,口唇蒼白;右側(cè)語(yǔ)顫減弱,雙肺呼吸音粗,叩診清音;腹隆,肝臟肋下可捫及,脾可觸及中度腫大,移動(dòng)性濁音陽(yáng)性;雙下肢凹陷性水腫。血常規(guī):WBC 4.1×109/L,RBC 1.17×1012/L,Hb 57 g/L,PLT 78×109/L;肝功能:Alb 27.0 g/L,TBil 105.4 μmol/L,DBil 34.1 μmol/L,ALT 33.8 U/L,AST 91.1 U/L,ALP 128.2 U/L,GGT 30.2 U/L;免疫全套:補(bǔ)體C4 86.80 mg/L,補(bǔ)體C3 408.00 mg/L,IgG 19.30 g/L,IgA 2090 mg/L,IgM 1560 mg/L;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yàn)(DAT):抗lgG+抗C3(++++);網(wǎng)織紅細(xì)胞百分比 16.57%;乳酸脫氫酶(LDH) 685 U/L;綜合患者情況未行肝穿刺活檢,經(jīng)血液科會(huì)診考慮診斷PBC(失代償期)合并AIHA。2018年3月6日起予甲潑尼龍40 mg靜滴7 d后改口服甲潑尼龍片并逐漸減量,患者Hb穩(wěn)步上升,至2018年5月28日為102 g/L,因嚴(yán)重肺部感染甲潑尼龍片于2018年5月30日減停,之后患者Hb逐步下降,遂于2018年6月5日予人丙種球蛋白20 g治療5 d,Hb水平上升而后又呈下降趨勢(shì),2018年8月21日Hb降至21 g/L。由于溶血難以控制且抵抗力低下,患者于2018年9月中旬肺部感染加重并出現(xiàn)膽囊炎急性發(fā)作,血常規(guī):WBC 23.8×109/L,RBC 0.43×1012/L,Hb 24 g/L,中性粒細(xì)胞計(jì)數(shù) 21.2×109/L;降鈣素原 3.93 ng/ml;肝功能:Alb 21.6 g/L,TBil 507.6 μmol/L,DBil 271.4 μmol/L,ALP 113.6 U/L,GGT 28.8 U/L,ALT 30.8 U/L,AST 59.6 U/L;腹部彩超示:門(mén)靜脈內(nèi)栓子形成,膽囊泥沙樣結(jié)石,膽囊炎。積極予以合理抗感染、人丙種球蛋白及對(duì)癥支持治療仍無(wú)效而死亡。
2 討論
為進(jìn)一步探討PBC合并AIHA的臨床特征及治療轉(zhuǎn)歸情況, 筆者在Web of Science、PubMed和中國(guó)知網(wǎng)、萬(wàn)方、百度學(xué)術(shù)中對(duì)近10年(2010年1月1日-2020年1月1日)發(fā)表的PBC合并AIHA文獻(xiàn)進(jìn)行檢索,以2015年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PBC診斷標(biāo)準(zhǔn)[1]和2017年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AIHA診斷標(biāo)準(zhǔn)[3]為納入標(biāo)準(zhǔn),共檢索出8篇英文文獻(xiàn)[4-11],加上本例共9例患者,均為女性,其中年齡在44歲及以下者2例,45~59歲者4例,60歲及以上者3例。對(duì)所有病例進(jìn)行臨床及病理特征分析。(1)臨床特征:常見(jiàn)癥狀主要為黃疸、乏力,各7例;其次為皮膚瘙癢、氣促(或呼吸困難),各5例;尿色加深、心悸各1例。常見(jiàn)的陽(yáng)性體征主要為脾腫大、貧血(或面色、結(jié)膜蒼白),各7例;其次為肝腫大 5例,腹水3例。對(duì)其他的非特異性表現(xiàn)如納差、體質(zhì)量減輕等未進(jìn)行分析。此外,合并食管靜脈曲張2例;合并門(mén)靜脈高壓癥2例;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4例;PBC先于AIHA診斷5例。(2)血清學(xué)檢查:除1例提示肝功能惡化、部分?jǐn)?shù)據(jù)缺失外,9例患者血清學(xué)檢查中ALP陽(yáng)性率最高,為100%;其次為GGT和TBil升高,各8例;ALT和AST升高,分別為6例、5例。(3)免疫學(xué)檢查:2例未提供免疫學(xué)相關(guān)指標(biāo),其余7例患者AMA(或AMA-M2)和ANA均為陽(yáng)性;此外,抗gp210、抗SSA抗體、抗平滑肌抗體、抗Ro-52抗體和抗核小體抗體各2例;免疫球蛋白主要是IgM和IgG升高,各3例,IgA升高1例。(4)溶血相關(guān)檢查:9例患者中,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貧血分別為1例、3例、4例、1例;網(wǎng)織紅細(xì)胞、LDH升高各5例,結(jié)合珠蛋白降低4例;9例患者均行Coomb’s試驗(yàn),且均為陽(yáng)性;其中DAT陽(yáng)性8例,1例未具體分型。(5)肝臟病理檢查:4例患者行肝穿刺活檢,其中2例明確提示非化膿性破壞性膽管炎,符合PBC病理改變(其中1例提示合并界面性肝炎,符合自身免疫性肝炎特征性肝組織學(xué)表現(xiàn));1例提示符合自身免疫性肝病變異綜合征,屬PBC型,主要累及小膽管,而不累及肝細(xì)胞;1例提示符合PBC與自身免疫性肝炎的病理特征并伴有Ⅲ期纖維化。(6)治療及轉(zhuǎn)歸情況:① 6例患者接受UDCA(13~15 mg·kg-1·d-1)聯(lián)合糖皮質(zhì)激素(潑尼松或潑尼松龍,起始劑量1 mg·kg-1·d-1或60 mg/d)治療,其中1例輔以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及靜脈甲潑尼龍治療,另1例輔以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療。5例患者在2周~3個(gè)月后膽汁淤積指標(biāo)及Hb水平改善或正常,1例患者溶血無(wú)法控制而死亡;② 2例患者接受UDCA 1 g/d治療PBC,未提及AIHA后續(xù)具體治療。其中1例病程中輔以靜脈甲潑尼龍治療,隨訪10個(gè)月膽汁淤積指標(biāo)及Hb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另1例隨訪3周后Hb水平改善;③ 1例患者接受潑尼松龍60 mg/d單藥治療,3個(gè)月后臨床癥狀及生物化學(xué)指標(biāo)改善,患者自行停藥,2年后病情復(fù)發(fā),予以潑尼松龍60 mg/d及免疫抑制劑硫唑嘌呤50 mg/d治療,激素逐漸減量至停藥,硫唑嘌呤50 mg/d單藥維持,隨訪期間病情保持穩(wěn)定。
PBC是一種由免疫介導(dǎo)損傷的慢性膽汁淤積性肝病,其發(fā)病機(jī)制可能與遺傳、環(huán)境污染、膽道損傷、免疫耐受缺失等因素密切相關(guān)[12]。PBC以中老年女性多見(jiàn),疾病早期大多數(shù)患者無(wú)明顯特異性臨床癥狀,僅有AMA陽(yáng)性,隨著疾病進(jìn)展或當(dāng)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時(shí),可出現(xiàn)膽汁淤積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guān)的肝外臨床表現(xiàn)。國(guó)外一項(xiàng)研究[13]對(duì)1975年-2012年的361例美國(guó)PBC患者平均隨訪(8±6.9)年,結(jié)果顯示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達(dá)61.2%;而國(guó)內(nèi)研究[14]發(fā)現(xiàn)46.6%的PBC患者合并1種甚至多種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干燥綜合征是當(dāng)前報(bào)道較多的與PBC合并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其他還包括系統(tǒng)性硬化癥、CREST綜合征、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自身免疫性肝炎、類(lèi)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和甲狀腺功能亢進(jìn)或減退[15-17]。目前PBC合并AIHA病例的文獻(xiàn)報(bào)道并不多,后者為一種罕見(jiàn)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系自身抗體作用于紅細(xì)胞抗原致紅細(xì)胞加速破壞產(chǎn)生溶血,在兒童及成人中均可發(fā)病。國(guó)外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18]顯示AIHA年發(fā)病率約為8/100萬(wàn) ,患病率約為170/100萬(wàn)[19]。基于最佳的紅細(xì)胞自身抗體反應(yīng)溫度,AIHA可分為溫抗體型、冷抗體型和混合型[20],根據(jù)病因可進(jìn)一步劃分為特發(fā)性(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在溫抗體型AIHA患者中,51%可繼發(fā)于其他疾病[21]。首例PBC合并AIHA病例由Hume等[22]在1970年報(bào)道。
從上述報(bào)道的9例PBC合并AIHA患者中可以看出,5例患者AIHA在PBC診斷基礎(chǔ)上發(fā)生,這可能預(yù)示著二者之間存在某種關(guān)聯(lián),而并不是機(jī)緣巧合。相關(guān)研究[23]表明,不論肝硬化病因如何,50%的肝硬化患者會(huì)發(fā)生溶血。可能的機(jī)制包括膽鹽對(duì)紅細(xì)胞膜的直接毒性作用和膽鹽誘導(dǎo)機(jī)體免疫紊亂,導(dǎo)致新抗原暴露及紅細(xì)胞自身抗體產(chǎn)生[24]。同時(shí),從治療方案及療效來(lái)看,1例接受糖皮質(zhì)激素聯(lián)合免疫抑制劑方案的42歲患者獲得了良好預(yù)后;另2例患者接受UDCA治療PBC,但文獻(xiàn)中未提及溶血后續(xù)相關(guān)治療,在此不予贅述;在接受UDCA聯(lián)合糖皮質(zhì)激素方案的6例患者中,5例患者獲得滿意療效,而對(duì)于本例患者,2005年初診時(shí)診斷為“隱源性肝硬化”,3年后行3次食管靜脈套扎術(shù),已處于肝硬化失代償期。10年后患者再入院查膽汁淤積指標(biāo)ALP及GGT升高,血清AMA-M2陽(yáng)性,ANA陽(yáng)性,抗gp210弱陽(yáng)性,腹部B超已除外肝外膽道梗阻,無(wú)需做肝穿刺活檢即可診斷PBC。患者規(guī)律口服UDCA 0.75 g/d治療,其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膽汁合成及分泌、減少針對(duì)膽管的促炎因子分泌及調(diào)控細(xì)胞凋亡來(lái)改善臨床指標(biāo)、延緩肝組織學(xué)進(jìn)展及提高遠(yuǎn)期生存率。但隨著疾病進(jìn)展,在PBC診斷后不到3年時(shí)間,于2018年3月再次入院,發(fā)現(xiàn)該患者:(1)明顯乏力,出現(xiàn)皮膚黃染及瘙癢;(2)DBil 105.4 μmol/L,IgG升高,Hb 57 g/L提示重度貧血。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檢查示患者IgG升高,結(jié)合ANA滴度等結(jié)果尚不能排除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診斷,但入院時(shí)患者已處于嚴(yán)重肝硬化失代償期,貧血重,PLT低、出血風(fēng)險(xiǎn)大,且合并大量腹水,限制了肝穿刺活檢,評(píng)估利弊后未行此項(xiàng)有創(chuàng)操作。而患者無(wú)慢性失血表現(xiàn)且營(yíng)養(yǎng)性貧血證據(jù)不足,Coomb’s試驗(yàn)陽(yáng)性,網(wǎng)織紅細(xì)胞及LDH升高明顯,綜合以上臨床資料及疾病演變過(guò)程,患者最終被診斷為PBC合并AIHA。因患者一般情況差未行肝移植,予以UDCA聯(lián)合糖皮質(zhì)激素方案,急性期給予靜脈甲潑尼龍交替人丙種球蛋白沖擊治療,患者Hb逐漸上升,但因并發(fā)嚴(yán)重肺部感染逐漸減停了甲潑尼龍片劑治療,Hb水平低至極重度貧血標(biāo)準(zhǔn),溶血相關(guān)指標(biāo)居高不下,肺部感染難以控制,臨床療效不盡如人意。綜合上述治療方案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報(bào)道,在PBC合并AIHA病例中,往往需足夠劑量的糖皮質(zhì)激素來(lái)控制患者急性期的溶血,同時(shí)予以足夠劑量的UDCA或免疫抑制劑維持治療;對(duì)于嚴(yán)重危及生命的溶血,可以考慮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和大劑量糖皮質(zhì)激素沖擊治療。但也有相關(guān)研究[25]指出,應(yīng)盡可能避免對(duì)PBC患者長(zhǎng)時(shí)間激素治療,因該類(lèi)患者細(xì)胞介導(dǎo)的免疫功能低下,發(fā)生感染的風(fēng)險(xiǎn)更高,且骨量減少的相對(duì)風(fēng)險(xiǎn)增加4倍,更易發(fā)生代謝性骨病。目前,對(duì)于合并輕度AIHA的PBC患者予以UDCA單藥治療,并定期進(jìn)行患者血細(xì)胞計(jì)數(shù)評(píng)估療效已有成功報(bào)道[24];Kaibori等[26]證實(shí)肝移植和脾切除術(shù)是治療PBC合并AIHA的有效方法;但Retana等[27]報(bào)道肝移植后也會(huì)發(fā)生溶血,肝移植和脾切除術(shù)后應(yīng)用免疫抑制劑并不能避免機(jī)體進(jìn)一步產(chǎn)生抗紅細(xì)胞抗體。因此,需進(jìn)一步挖掘PBC發(fā)生發(fā)展的相關(guān)機(jī)制,以尋找新的特異性治療靶點(diǎn)來(lái)延長(zhǎng)患者的生存時(shí)間。
臨床上對(duì)于有黃疸、乏力、皮膚瘙癢及肝酶異常的中老年女性患者,應(yīng)進(jìn)一步完善血清相關(guān)抗體有助于PBC診斷,以免延誤該病的診斷及治療;其次,對(duì)于確診的PBC患者,若黃疸突然加重,除考慮疾病本身進(jìn)展外,還需要考慮溶血發(fā)生的可能;再者,對(duì)于確診的PBC合并AIHA病例,往往需足夠劑量糖皮質(zhì)激素治療,或者聯(lián)合免疫抑制劑及UDCA,根據(jù)病情緩解程度,及時(shí)、酌情撤減激素,以免并發(fā)嚴(yán)重感染,必要時(shí)行肝移植和脾切除術(shù)治療。本文旨在提高臨床醫(yī)生對(duì)PBC合并AIHA病例的認(rèn)識(shí),早期識(shí)別肝外疾病可改善PBC患者預(yù)后及生活質(zhì)量,因此臨床上對(duì)該類(lèi)患者早診早治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貢獻(xiàn)聲明:吳蓉負(fù)責(zé)擬定寫(xiě)作思路,收集數(shù)據(jù),資料分析,撰寫(xiě)論文;冷愛(ài)民參與課題設(shè)計(jì),指導(dǎo)撰寫(xiě)文章,修改論文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