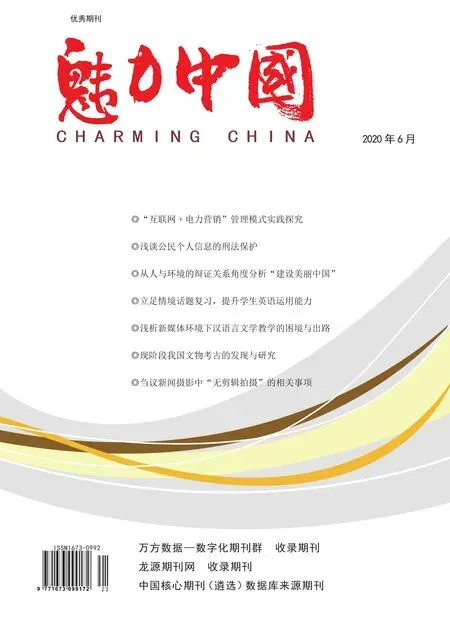從經濟角度看宋朝
(內鄉縣衙博物館,河南 南陽 474350)
宋朝建于公元960 年,亡于公元1279 年,因1127 年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被金兵攻破,皇帝、皇子、大臣等被俘虜,僅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宋高宗)逃脫,到臨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偏安一隅。因此今天很多人看來,宋朝雖然富庶,卻是歷史上最差的朝代之一,遠不如大漢與盛唐。讓我們回到真實的歷史中,看一下前因后果,就會發現,每個朝代都對中華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換個評價標準,無論人均經濟水平還是文化生活,宋代可謂中國歷代少見的斯文盛世。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的發達,在國家主義與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其燦爛的文明。
回看宋代,國人總是頗多腹誹,尤其感嘆“讀宋史長流淚”,宋代甚至被視為中國積弱的朝代。即使錢穆這樣的平和大家,一方面表示認可宋代經濟是近代經濟的開始,“中國在唐代以前可以稱為古代社會,自宋代起至現在可說是近代社會”。另一方面也認為漢唐宋明清五朝中,“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事實上,如果換個評價標準,無論人均經濟水平還是文化生活,宋代可謂中國歷代之中少見的斯文盛世。陳寅恪老先生曾經表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的成就,在海外評價甚高,其城市自由、商業生活與文教昌明彼此輝映。
宋代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國,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其燦爛的文明,因此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劇增加。宋徽宗時期人口即多達1 億,是漢唐的兩倍有余。“北宋十萬戶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豐年間為四十多個,宋徽宗崇寧年間為五十多個,而唐代僅有十多個。”
宋朝城市結構也逐步打破了商業和居住區的界限,從唐代的“坊市封閉”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導致了城市生活的迅速繁榮與空前自由。還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發展出后世認為的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這也意味著抑商政策開始向征商政策轉化,商稅的征收也變得更為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稅則例及其變動情況,各地州、縣、墟鎮廣置稅務機構,這些情況表明商稅征收到宋代首次進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時期”。
宋代的繁榮程度或許是中華文明在中古時期的高峰。北宋年間貿易繁榮已達到驚人的程度,隨著造船等技術發展,始于漢代從港口銜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公認在宋達到巔峰。宋與數十個國家開展貿易,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當年的貿易繁榮讓后人難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說宋、遼、金與西夏且戰且和數百年間連綿不絕的邊境貿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貿易(榷場)外,還有各類民間交易及走私。這些交易規模驚人,僅僅以當時交易較普遍的商品羊為例,宋代皇室御廚用羊每年就高達數萬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從河邊買入契丹羊的費用為40 余萬緡。
宋代財稅中與商業有關的稅種也空前豐富。宋之前對于商業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稅,唐朝雖也盡力征收商業稅,但還不成體系,而宋代則將各類商業稅收制度化。北宋時期的稅率保守估計已達到10%。當時的人如此記載,“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的發達,使得宋代的文明程度空前進化,在國家主義與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對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尤其紙幣的誕生,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在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產物與象征。
與此同時,宋代對于富人的態度也比較寬容。北宋年間,宋太宗即表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嘆之聲,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閭。外之租稅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
除了天子,當時的士大夫對于富人也相當寬容,如北宋文學家、詩人、宰相蘇轍即表示富人出現是情理之間,貧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南宋思想家葉適則更進一步,已經認識到有產階層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指出富人是維系社會上下階層的樞紐,甚至批評希望以打擊富人來救助貧人的想法雖然善良卻不應實行。“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宋朝最被后世詬病的是軍力,但如果宋朝軍事果真像被批判的那么孱弱,為何能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能與遼、金與蒙古這樣的軍事強大的政權對峙數百年?宋朝從開國到滅亡,三百多年間不是處于戰爭狀態就是處于備戰狀態,不得不長期奉行“守內虛外”(即禁軍多數駐防在京城,少數駐防在邊境)的政策理念,為發展爭取時間。實際上,宋朝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其常規軍數量最高達120 萬人,超過很多朝代,軍事開支需求龐大。以后勤為例,宋代的場庫務在各地都有設置,不僅需要儲存糧食與器械等軍需,主管官員也需費心經營以提供利潤,鹽、茶、酒等貿易及其征稅均獲得充分發展。能支撐如此龐大的軍事開支,離不開其制度管理與經濟實力,經濟思維滲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統,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正催生于這種競爭之中。
長期以來,人們關于宋代歷史的看法,一直隨著時代演進而變化。近代以來,國人痛感國力不強,備受外族欺凌,類比歷史,才使關于宋朝“積貧積弱”的看法逐漸定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人的文化自信心不斷強化,促使學界更改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軌跡也日益成為研究熱點。在國際上,這一學術趨勢還與學界試圖拋棄西方中心論的努力相輔相成。由于宋代在中國經濟史上的特殊地位,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場討論的中心。一些學者試圖估算宋代的經濟總量,集中體現的就是所謂“宋代GDP 的全球占比”論。目前已出現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更有所謂的占世界總量百分之八十的說法,使得宋代經濟之輝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現代中國為經濟發展在許多方面所付出的代價,也推動著專家學者更加冷靜地觀察歷史上的經濟現象。這在方法論省思與史實重構兩個方面都有所表現。前者的典型研究,是李伯重的《“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一文。李文在方法論層面上徹底否定了“宋代經濟革命說”,認為一些研究者用“選精”與“集粹”之法,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具體的和特殊的現象加以普遍化,從而使之喪失了真實性。也就是,將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個案性記載集中在一起,拼湊出一幅宋代經濟跳躍式發展的畫面。例如關于宋代糧食畝產量的估算,史籍中留有個別高達6 石的記載,不少學者往往將這種相當例外、僅反映局部地區個案性的現象普遍化,結果就大大高估了當時的平均糧食畝產量,其所給出的只是一個歷史的“虛像”,而非“實像”。
事實上,宋朝經濟顯著發展、超越中國古代平均水平的史實,不僅僅是GDP 總量增加、人口增多、大城市規模化涌出等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宋朝的文化高度進步:宋詞、唐宋八大家、三蘇等,科技發展迅速: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沈括寫出《夢溪筆談》這一專門的科學巨著,這些都是宋朝經濟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明顯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