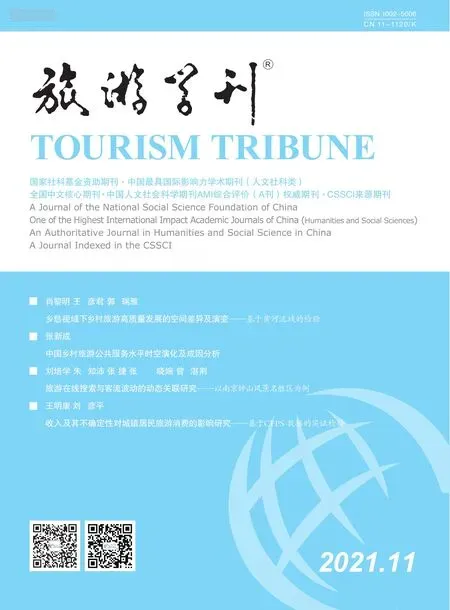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與認同
郭文 朱竑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旅游空間實踐大體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旅游資源勘查期、20世紀90年代后的旅游資源規劃期,以及21世紀以來旅游資源市場化導向與文化旅游深化發展期。在上述過程中,旅游空間生產作為特殊的空間生產行為,嵌套于不同時期的中國旅游空間實踐之中,不同階段均凸顯了旅游空間的社會化結構與社會空間關系的建構和協商2。與此同時,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與認同,也成為與中國旅游空間實踐相伴而生的時代性產物,受到了人們廣泛關注。黨的十九大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與認同更加成為人們繞不開的討論話題。作為一項重要的國民意識,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與認同不僅是一種社會經濟和文化實踐,也是調適和構筑未來理想生活的重要維度。關注此話題,是新時代重構旅游空間關系的理論切入點,也是優化國民意識、重塑生活環境的實踐指引。
一、空間生產的疊寫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研究中指出,構成其理論體系的“空間的實踐”“空間的再現”和“再現的空間”是一個不斷自我生產和膨脹的“三元空間辯證法”。這一辯證法的內涵及其過程,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談論生產概念時那樣的含糊其辭,也不是松散地使用從而使其失去規定性1。在新的理論體系中,空間生產是一連串動作相互建構和協商的過程,其結果既不是其他事物之中的一種物,也不是許多產品中的一種普通產品。三元空間辯證法的過程,雖然是由一系列看得見的客觀性活動構成,但其內在屬性具有非常強的社會意蘊,空間的疊寫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本文提出的空間的疊寫是指在空間實踐中生產出不同于原生空間的行為與過程。作為一種刻畫空間深層次內涵的生產維度,空間生產的疊寫是創新空間的重要要素。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角度看,空間生產把一切可能的要素納入其生產運作體系,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空間的資本化必然促使空間產生廣泛的社會交往,進而造就日益豐富的社會關系2。在此過程中,由于空間生產的內在特性,空間的疊寫還會進一步內嵌于深刻的社會文化生產中,這在使社會文化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之時3,也會改變原來的自然屬性,甚至出現難以認同的社會文化折損現象。關于這一點,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就將這種文化現象歸之為現代社會物品制造的“工業”4,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力操縱并通過符號生產和意義消費實現的。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敘事方式,空間的疊寫具有無可辯駁的雙面性和辯證性,在空間生產過程中,可能是創造空間興盛的基石,但那種內隱于空間生產中無意識或有意識的社會文化運作,也可能會帶來高風險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甚至成為空間倫理淪陷的媒介。
二、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與限度
旅游空間生產理論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生產思想在旅游研究領域的重要體現與延展,繼承了空間生產理論在認識問題、分析問題時表現出的整體性、徹底性和說服力,也成為中國學者重新認識改革開放以來旅游空間實踐及其在本體論上的重要轉折點。但是,中國學界對該理論的引介和實踐方式,基本上經歷了由外而內的消化過程,這導致人們使用該理論對旅游空間實踐和生產進行分析時,更多聚焦于結構主義式的范式和政治經濟學解析框架進行思辨,而對資本運作帶來的疊寫與話語建構的相關討論還比較薄弱。實踐證明,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及其帶來的流動性在不同地理空間的跨界滲透,中國旅游空間的實踐與生產也是引發社會關系重組、文化形態變遷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旅游空間要素交互辯證及其疊寫的過程。在此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例如,位于江南的甪直古鎮,長期以來由于旅游開發意識及其經濟形態對古鎮空間的滲透,高速的空間流動在使古鎮內部和外部建立密切關聯的同時,也改變了這些人的日常交往方式,甚至出現了內外部日常生活空間關系的重組。但是,通過深入調研發現,流動中的地方人在新空間中的社會文化實踐,并沒有揚棄原鄉空間的地方性,不同空間的基因融合反而成為了新的日常實踐。這說明,這種重組后的社會文化裁決,不是兩種空間的“一刀兩斷”,更不是“劃清界限”,而是凸顯了古鎮新特質與舊個性的延續性繼承與創新。這類現象并非孤案,在我國新疆哈薩克族的高山牧場,由于草場隨海拔高低不同而具有地理分帶性,牧民隨季節變化而轉移牧場的現象被稱為“轉場”。這原本是一項自然而然的傳統生活方式,但隨著旅游業的融入與深化,傳統牧民的生活空間和軌跡也會隨之改變,甚至反季節停留牧場成為新的空間活動形態,牧民們不但沒有反對,還樂在其中。這說明旅游塑造了不斷變遷的日常文化體系,基于旅游的空間實踐也是空間生產和地方性疊寫的重要推動因素,社會文化本身內在于活動的固有訴求,決定了社會文化的生產總會表現出一定的協商性和創新性。
旅游空間生產的疊寫也會遭遇疊寫的限度,出現空間生產違反原空間社會文化基因的生產過程。例如,在云南哈尼族箐口社區旅游開發中,資本對地方的滲透成了村寨新近開發的重要路徑,在強勢利益主導下資本帶動日常空間更迭并使地方空間發生轉向,甚至帶來社區共同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層面的分化與隔離5。旅游空間生產使作為弱勢主體的村民和空間生產主導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但無法形成協同價值和互容利益,而且還帶來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空間行為和心理的“雙抵抗”。這一現象其實是空間疊寫遭遇的限度,凸顯了地方與空間困難地并存的現實。大衛·哈維認為,資本自身通過空間延伸來面對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意義時,常常會加劇不平衡地理的發展1,這必然需要引起重視。但面對諸如此類實踐,也有研究者認為,保持空間的開放性和動態性是必要的2。不同學者基于不同視角闡述了差異化的空間生產觀點,這也被很多解讀者用作厘定空間性質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生產的重要指引。回到實際案例地中,甪直案例、哈薩克案例、箐口案例,哪一種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更符合對他們今日的關照和對未來的預期?那些基于地方空間和文化的創造者,“生于斯,長于斯,奮斗于斯,充盈于斯”的當地人的認同立場,或許可以成為空間優化的重要參證。
三、旅游空間生產疊寫的認同
認同是群體中成員束縛在一起的集體聯系。進一步深度解讀可以認為,空間疊寫的認同是社會發展中人們基于價值觀取向和行為規范形成的一種國民意識。積極的認同不僅能強化個體對地方的認同感,也能強化人們對地方的積極參與和融入。例如,廣東汕頭澄海上社村“拖神”活動的身體展演,憑借地方性的共同文化信仰,被實踐為聯結人和地方的紐帶,這一活動提升了上社人的文化自豪感與榮譽感3。與此同時,各大宗族通過“拖神”活動的組織,將社區建構為緊密團結且具有強悍堅毅道德氣質的村落,并以此維持著村民相互間的社會關系4。這實質上指向了關于“我是誰”的或明或暗的回答,體現了空間實踐意義之“我”,而非“他”的規定性。
但是,單一的空間疊寫認同也必將導致地理空間的認同分異,并重構消極的人地關系。例如,我國仡佬族祭祖本應是一種族群行為,但在以旅游為媒介的流動性背景下,政府與地方主導的祭祖活動成為懸置于族群之上的社會和文化重構活動。在面對政府主導的仡佬祭祖神圣活動身份認同時,仡佬族人不僅參與者寥寥,而且以一種局外人的態度來看待官方的祭祖活動,在仡佬族代表和被代表之間,無形中形成一種不對等的階層身份和沖突關系。這一不對等的關系導致的隔膜,使官方建構了“自上而下”的認同,但卻難以得到“自下而上”的認同5。事實上,較多類似的案例都表明了一個樸實的道理,那些尋求在地方性基礎之上獲得控制和權力的行為,必然受到其他社會群體的抵抗。
四、理想空間的意義塑造之維
旅游空間生產及其疊寫是一個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實踐活動,這一活動引發的空間認同也是新時代社會矛盾轉化后,重塑國民意識,創造人們美好生活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旅游空間實踐和生產層面上,意義是需要直接面對且不斷探索的命題。意義是指引真理觀和真實觀的路徑所在,也應該是旅游空間實踐中日常生活空間的內涵所在。在以往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理想空間的塑造雖然各有不同,甚至存在爭議,但在本質上的共同追求,均應該反對具體空間實踐中的非人化導向,因為基于空間結構深處的探索,總是建立在實際環境塑造的空間間性之中,這也將指向地方及其認同的忠誠和安全。未來需要什么樣的旅游空間實踐,這個問題和我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想塑造什么樣的社會形態,想珍惜什么樣的人與自然關系,想抱持什么樣的空間價值觀一樣,是永遠分不開的。在旅游空間實踐和生產中,探索理想空間的意義塑造之維,或許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爭論的議題,但最終絕不會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命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意義的理想空間實踐的構想。
(第一作者系該院副教授、博士,第二作者系該院教授、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收稿日期:202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