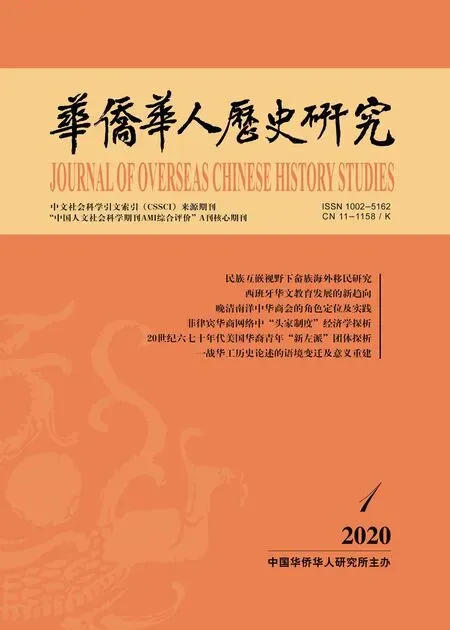美國1882 年排華法的前奏: 1875 年《佩奇法》實施的背景及影響
顧國平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英語學院,北京 100024)
1875 年,美國國會繞開中美兩國《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中“自由移民”的條款,通過了以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賀拉斯·佩奇(Horace F. Page)的名字命名的《佩奇法》。該法實施后,限制了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苦力和女性移民美國,成為七年之后1882 年美國全面排華的前奏。對于《佩奇法》的背景及其影響,美國學者喬治·佩弗爾(George A. Peffer)通過對史料的挖掘,矯正了學界先前對《佩奇法》的漠視,指出該法極為有效地將中國女性阻擋在美國國門之外;[1]凱利·亞布拉姆斯(Kerry Abrams)則將該法置于當時美國國內掃黃運動和反對一夫多妻制的背景下,從文化的角度解讀了《佩奇法》出臺的背景與過程;[2]另有學者追溯了《佩奇法》出臺前美國加州通過立法限制華人婦女入境的嘗試。[3]
國內學界對美國移民研究中排華主題的研究,多集中于1882 年《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出臺的原因和影響[4]以及美國排華期間的華人處境[5]等,具體到早年華人女性赴美的研究,數量還不是很多,已有的研究包括對華人女性早期赴美動機的論述,[6]對華人女性在美國的處境和地位變化的探討等。[7]關于中美1868 年《蒲安臣條約》,由于其中“自由移民”的條款,梁啟超遠在百年前就稱其為中國“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8]徐國琦在2019 年初出版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中,也稱該條約是“中美兩國之間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這或許是清朝在19 世紀唯一的平等條約”。[9]關于該條約如何客觀抑制了美國國內對華工的排斥,[10]保護了出國華工和華僑等,[11]學者們都已有論述。相比而言,國內對于《佩奇法》及其對華人赴美影響的研究幾乎尚未觸及。無怪乎學者韓玲在梳理了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內美國移民政策史研究的文獻后,認為國內對“重要轉折階段的政策研究欠缺”。[12]
《佩奇法》作為美國第一部聯邦層面限制移民的法律,既是美國排華立法過程中從加州立法向聯邦立法的過渡,也是中美移民史上美國聯邦政府層面從拋棄《蒲安臣條約》轉向擁抱《排華法案》的一個重要過渡性法律和政策。《佩奇法》中對華人赴美的部分限制,是美國在華人移民問題上從自由移民向全面限制的一個中間站和重要轉折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性別失衡的早期美國華人社區
在19 世紀中期前往美國西海岸加入淘金浪潮(Gold Rush)的華工中,男性占絕大多數,性別失衡嚴重。當時的美國西海岸尚未完全開發,屬于邊疆性質,性別失衡并非華人社區獨有,但是華人人口的性別失衡問題尤為突出。1850 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平均男女性別比例是12︰1,而華人中的男女比例則是39︰1。在加州的舊金山,當時的華工主要還在金礦從事苦力活,尚未定居城市,其性別失衡問題更為嚴重。以1852 年為例,生活在舊金山的華人中有男性2954 人,女性19 人,男女比例高達155︰1;而到1860 年,這一比例進一步失衡,達到186︰1。[13]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1860 年、1870 年和1880 年,在美國的每1000 名華人男性對應的華人女性人數分別是54 人、78 人和47 人。[14]
美國華人中當時如此嚴重的性別失衡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既有中國傳統社會習俗的制約,也有經濟因素的影響,更有美國當時排華環境的作用。首先,在傳統的中國家庭權力結構中,父母占據主導地位,夫妻關系從屬于父子/母子關系,兒子結婚后有義務將其妻子帶回家服侍父母。因此對已婚女子來說,對公婆的責任在其所有家庭責任中處于第一位,她需要服從婆婆的指揮,承擔家中各種不同的職責。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中寫道:“當中國男性外出謀生時,他們的妻子被要求留在家中撫養孩子,照顧公婆。直到20 世紀之前,這樣一種社會規范一直制約著從中國南方向海外的移民,在東南亞的華人移民是如此,在北美和澳洲的華人移民也是如此。”[15]
第二,早期前往美國的中國男性華工的“旅居者心態”(sojourner mentality)是另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的男性華工與來自歐洲的移民不同,他們赴美務工只是一個短期打算,掙到錢后最終要回到中國。這一旅居者心態讓大多數華工的妻子選擇留在了國內,照顧家小,等待丈夫歸來。實際情況也表明,早期前往美國的男性華工中有一半左右最后都回國了。[16]
第三,橫跨太平洋的高昂旅費以及美國較高的生活成本,也是阻擋女性前往美國的重要原因。[17]
第四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當地社會對華人尤其是對華人女性的敵視態度,以及美國法律缺乏對華人的保護。在美國學者佩弗爾看來,中國傳統習俗、華工的旅居者心態和經濟因素等固然重要,但不足以解釋“美國華人性別失衡問題如此嚴重,而且持續時間如此之長”,中國的家庭傳統雖然要求女性恪守各種規范,但也并非一成不變,隨著地方經濟狀況的變化,中國家庭一直在為適應變化而做出調整。此外,通過比較早期美國華人社區與其他諸如新加坡和夏威夷等海外早期華人社區可以發現,其他海外華人社區的華人較早地經歷了從旅居者向定居者的轉變,其地方當局很早就意識到鼓勵華人女性移民可以緩和男性占絕大多數的華人社區的多種矛盾和問題。因此,美國華人社區性別比例長期嚴重失衡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當地敵視華裔婦女的環境。[18]
二、早期美國華人女性:賣淫業與一夫多妻制
在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華工旅居者心態以及美國當地社會敵視態度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美國華工人口中的女性一直很少,華人聚居的地方形成了所謂的“單身漢社區”。餐館、賭場、鴉片館和妓院等場所構成了當地華人社會的活動中心,基本都以男性華人為服務對象。在為數不多的華人女性中,除了極少數包括外交人員、商人和學生等屬于特殊階層的女性配偶外,大部分從事賣淫業,另外一部分是條件較好的華人男士的妻妾,其余的從事著洗衣、挖礦、裁縫、廚師和女傭之類的工作。根據不同學者對當時舊金山華人人口構成的統計,1860 年華人女性中妓女的比例在85%至97%之間,1870 年這一比例是63%至72%,1880 年大約是18%至50%。[19]
(一)賣淫業
19 世紀中期的加利福尼亞州尚屬美國西部邊疆的一部分,人口構成以年輕男性為主。西部艱苦的條件造就了他們敢于冒險勇于闖蕩的性格,而邊疆社會也缺乏文明社會的各種約束。各種專門針對單身男性的活動和消遣應運而生,賣淫業即為其中之一。當時,加州有來自世界各地各個種族的妓女,本地出生的白人女性、新來的歐洲和拉美女性以及黑人女性和印第安女性都有從事賣淫業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華人妓女的人數最多,超過其他妓女人數的總和。[20]究其原因,當時加州華人人口性別嚴重失衡、中國南方當時貧苦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華人幫會對賣淫業的操控等,都是重要因素。
19 世紀上半期,中國清朝與西方相比正經歷著不可逆轉的國勢衰退,而人口卻從18 世紀末的3億左右增長到了1850 年前后的4.3 億,人口壓力與日俱增,而廣東省則是其中人口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與此同時,內憂外患不斷困擾清朝政府,尤其是南方省份。19 世紀40 年代的鴉片戰爭帶來的是巨額賠款以及廣州等口岸的被迫開放,為了償還賠款,政府加重了稅收。而西方經濟帝國主義的入侵,則使得廣東市場上充斥西方的廉價商品,民間落后低效的手工業受到擠壓,難以為繼。外患之后是內憂,19 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起義(1851—1864)、廣東紅巾軍起義、土客沖突,再加上各種自然災害,加劇了廣東民間的貧苦程度。在這樣的內外背景之下,為了生計,售賣子女甚至棄嬰殺嬰等做法都成為不少家庭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由于男尊女卑的傳統,與兒子相比女兒更容易成為出售的對象。[21]
當然,即使家庭條件再艱苦,也很少有父母會同意將女兒賣給妓院,但這在人口販子眼里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在買賣過程中,他們保證說什么這些女孩絕對不會被賣到妓院,而是去美國當家傭或者是嫁給美國華工當妻子。這類信誓旦旦的保證確實起到了緩減買賣女兒時情感上的痛苦,因此也讓交易變得更為順暢。除去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買賣外,一些蛇頭還通過坑蒙拐騙來誘騙年輕女性,甚至直接綁架。這些女性一般都被許以到美國去結婚或務工之類的承諾,待到在美國登岸才發現自己被賣給了妓院。更有甚者,一些女性直接被綁架。不少關于美國早期華裔女性的著作都有此類記載和論述。[22]有一位廣東少女受邀參觀一艘泊在港口的美國汽船,然而當她正在船上參觀之際,那艘船卻起錨發動,揚帆駛向舊金山。[23]在華裔女性作家嚴歌苓那本基于充足的史料寫成的小說《扶桑》中,主人公扶桑也是同樣遭遇了綁架后被賣到美國從妓。
就當時華人女性賣淫業的運營而言,1854 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華人妓女同來自其他國家的妓女一樣,處在“自由放任”的狀態,相當于從事一種自由職業,有基本的人身自由。但1854年以后,華人幫派開始接手賣淫業,妓女的境遇變得更為慘淡。她們終日生活在妓院,與外面的世界基本隔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難以跳出服務契約。一般的妓女契約在4 年到6 年之間,其間沒有工資,而且規定如果妓女發生生病或懷孕等情況,都需要相應延長契約時限。陷于賣身契的妓女都受到嚴厲的剝削,很多妓女活不到賣身契到期之日。當然,就像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妓女的生活也有其幸運的一面。首先,妓女身上的商業價值使得幫會和妓院老板在對妓女實施嚴重的人身傷害時會有所顧忌,而且,顧客們也因為不想身份曝光一般不會對妓女施加傷害。還有一些妓女更為幸運,或因自身的堅持或因中意顧客的介入獲得贖身,此外,也有的和情人私奔或在當地教會尋求庇護逃出妓院。[24]
(二)一夫多妻制
除了占比最大的妓女之外,當時美國華人女性中人數上占第二位的群體是一些條件較好的華人男性所納的妾。這里涉及美國與傳統中國在家庭和婚姻制度上的巨大不同。在美國,歷史上除了摩門教所在的猶他州外,在婚姻制度上歷來實行一夫一妻制,而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允許一夫多妻。在19 世紀以前,中國的男性只要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就可以納妾,三妻四妾是男士能力和地位的象征。如果這些有妻妾的男士短期或長期外出,一般的安排是妻子留在老家,負責照顧全家老少,妾跟隨外出。這種情況在赴美務工的華人中間也相當普遍,當時美國西海岸與條件較好的華人男士生活在一起的女性一般也都是妾。[25]
綜上所述,19 世紀中期美國西部的華人社區中,男性多為單身漢,或者雖已成家但妻子留在國內,因此也形同單身;女性主要是妓女或一夫多妻制中的妾,符合美國一夫一妻制傳統的家庭和婚姻關系在華人社會中較為少見。這些占大多數的華人男性和女性在當時美國社會中非常規的從業和生活狀況,逐漸引發了當地白人社會的不解與擔憂,并成為后來美國白人排華反華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排斥華人女性:種族仇視與傳統差異
華人女性在美國西部的職業和生活狀況,給當地社會制造了不少或真實或想象的問題。如果說在經濟領域白人社會關注和擔憂的是華工帶來的經濟威脅的話,[26]那么華人女性則是當地社會道德擔憂的主要對象。白人社會對華人女性的擔憂和排斥一方面源于種族偏見,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國和傳統中國巨大的文化和制度差異所致。由于絕大部分的華人女性在美國不是從事賣淫業,就是一夫多妻制中的小妾,因此在美國當地社會眼中成為“異類”,違背美國傳統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華人妓女和小妾的存在,不僅被認為沖擊到了美國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而且還被認為與當時美國剛剛廢除的奴隸制相似,威脅到了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行。
(一)種族偏見與仇視
美國當地白人社會對華人女性的歧視和排斥,首先源于種族主義偏見,認為華人女性由于其種族屬性,屬于落后與墮落的階層,而華人女性中妓女的比例如此之高,則是該種族墮落的證明。這一種族偏見與當時流行西方的有關人種分類的“偽科學”有關,即認為人類由不同人種構成,且不同人種天資與能力各異,形成一個種族的等級格局。鑒于白種人當時相對于其他種族技術上更為領先,他們普遍被認為處于人種等級格局的頂端,是凌駕于其他種族之上的“高等”種族。這一人種偽科學還認為,不同種族和民族之間的通婚會導致“高等”種族或民族的墮落和退化,因此,白人在與其他人種交往的過程中,需要防范相互通婚,防止自身的退化。這些觀念當時雖然也有爭議,但在整個西方相當流行。以1862 年在美國出版的《華人移民與一個國家墮落的生理原因》(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a Nation)為例,作者亞瑟·斯塔特(Arthur B. Stout)充滿種族偏見與對黃種人的仇視,在書中宣揚排華立場。作者寫道:“自然界的第一法則是保衛種族的純潔性……種族自衛的法則要求我們制定國家的第一部保護性立法。”為了說服讀者,他還引用種族偽科學,挑撥讀者對異族的恐懼心理:“如果我們與東亞人(Eastern Asiatics)混居通婚,我們會生下墮落的雜種。”[27]
除了基于當時流行的人種理論而引發的一般性的道德恐懼之外,華人妓女還在當地白人社會造成一種切實的道德憂慮。在白人眼中,華人妓女離經叛道,嚴重偏離了維多利亞時代要求女性矜持端莊的道德正統。[28]此外,正如小說《扶桑》中描述的,相對于來自其他國家的妓女,華人妓女收費更為低廉,而東方女性在白人男性眼中又充滿神秘感。獵奇心理加上廉價服務,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十幾歲的白人少年用他們的零花錢時常光顧華人妓院。這一現象造成了白人家長的擔心,他們大力譴責華人妓女導致了當地傳統道德的崩壞。
當時的醫學知識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當時的醫療知識體系中,華人妓女被認為威脅到了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的存續。當時的醫生們“診斷”出了一種所謂的“反常”(deviant)行為,源于先天的生理缺陷,是智力低下與落后的“癥狀”。其中,性病就與這些先天的缺陷相關。而妓女相對于其他人群來說,確實是一個更容易患上各類性病的群體。這種針對華人妓女的醫學偏見很快傳遍社會,華人妓女很快就被貼上了“不道德”、“異族”、“淫蕩”等標簽,被認為是性病尤其是梅毒的傳染之源。另一種當時流行的有關疾病的所謂“瘴氣理論”(miasmatic theory)認為,流行病的爆發與該地的環境或衛生條件相關。舊金山的衛生官員與醫療人員將矛頭指向唐人街,認為唐人街到處管道漏水,水溝破爛,垃圾遍布,臟亂環境正是該市大氣污染、“烏煙瘴氣”的根源所在。在這樣的背景下,華人妓女連同其他華人一起被指控犯下了“衛生罪”(sanitary evils),嚴重威脅到了當地白人的生存環境。[29]
關于華人妓女會帶來道德敗壞與身體疾病的看法,在加州上到官員下至普通白人,十分流行。加州聯邦參議員科爾(Cornelius Cole)1870 年接受《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采訪時說:“在那些來到我國的華人中有一類最不受歡迎的人——我指的是華人女性,因為她們在我們白人中傳播疾病和道德敗壞的種子。每當我看到這類人,我就問自己要不要對她們的入境進行限制。”[30]在1875 年美國國會通過《佩奇法》之前的發言中,議員佩奇所引用的加州移民官員(Commissioner of Immigration)的一封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恐慌:“眾所周知,加州的每個城鎮都有華人妓院,數量之多足以將疾病傳播給我們那些少不更事的白人青年。”[31]
(二)文化傳統的差異
其次,19 世紀中后期的美國當地白人社會對華人女性的排斥,也源于兩國當時不同的家庭和婚姻制度。華人女性中占絕大多數的妓女和妾的生活狀況和地位,使得白人將其與奴隸制聯系起來。如上文所述,傳統的中國家庭允許一夫多妻制,這一傳統習俗也被華工帶到了海外。華工一旦通過自身的打拼條件轉好,多會選擇納妾,原配妻子留在國內照顧家小,妾則陪伴在身邊。華工的這一做法即是對傳統一夫多妻制習俗的傳承,也是其在海外成功地位的證明。華人社會不僅認可一夫多妻制,對于妓女也表現出較大的寬容。海外華人社區中的“妓女”與“妻子”之間的界限并非一成不變,妓女中有不小的比例在從事一段時間的賣淫業后又嫁給男性華工成為其妻子。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底層并不給妓女貼上“墮落”或“無可救藥”之類的道德標簽,這些“失足婦女”只是聽從父母之命,為了幫助貧困的家庭而犧牲自己。因此,底層貧苦家庭的男子并不排斥從良的“失足婦女”。這一文化上的差異,再加上嚴重失衡的男女比例,使得加州華人社區的男性華工娶妓女為妻的現象更為普遍。[32]
與傳統華人社會不同的是,在美國社會中,妓女與普通女性之間的界限涇渭分明,一夫多妻制與一夫一妻制也是無法兼容。如上文所言,大量華人妓女的存在已經造成了白人眼中的道德與衛生方面的威脅,而華人社區所允許的一夫多妻制,嚴重挑戰了美國正統的婚姻制度。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社會將妓女制度和一夫多妻制與奴隸制度聯系起來,認為絕大部分華人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妾,處于一種類似奴隸的狀態。
賣淫業與奴隸制的關聯,建立在白人社會對華人妓女受幫會控制沒有人身自由的認識基礎之上。與賣淫業相似,一夫多妻制也被美國白人社會認為與奴隸制有緊密關聯。在1856 年美國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確定的競選綱領中,就明確指出要在美國的西部領地上同時廢除奴隸制和一夫多妻制,認為這兩種制度都是“野蠻時代的殘余”。[33]而且,對于內戰前的美國來說,這兩種制度在美國南方種植園得到了結合,因為當時南方種植園實施的奴隸制度同時也是一種一夫多妻制,白人男性種植園主對種植園的全部黑人女性擁有性特權。[34]美國社會對一夫多妻制的抵制還表現在對西部摩門教徒的立法打擊。1862 年7 月1 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反一夫多妻制法》(Anti-Polygamy Act,全稱The Morrill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olygamy),立法對象是生活在當時還是猶他領地的摩門教徒。在主流白人社會眼中,實行一夫多妻制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一種變態的行為,不僅使社會風氣敗壞,道德墮落,更是一種政治暴政,給深陷該制度的男男女女套上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枷鎖。[35]白人主流社會對一夫多妻制與奴隸制的這一關聯,確實給摩門教徒施加了強大的壓力,使其于19 世紀90 年代早期宣布廢除一夫多妻制。猶他州于1894 年被接納為美國一個州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禁止一夫多妻制。
鑒于美國主流社會對一夫多妻制和奴隸制的關聯,孔飛力做出了如下論斷:“在美國,當地人對于奴隸制度的深惡痛絕,卻在對待中國移民的問題上起著奇怪的、具有諷刺意義的作用。”[36]當華人男性引以為傲的一夫多妻制遇上美國的婚姻傳統,不僅被認為是一個異類,而且還是一種罪惡的制度。文化傳統的差異難以調和。
綜上所述,美國當地社會戴著種族主義的有色眼鏡,認為占華人女性多數的華人妓女不僅構成了人種上的威脅,直接危害到了白人文明的存續,而且還是一種道德污染源,威脅著美國傳統的性道德。而美國與中國傳統社會在婚姻制度與家庭習俗上的差異,再加上美國當時反奴隸制、反一夫多妻制的歷史背景,使得美國白人社會認為,大部分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女性(還有男性苦力華工)無異于奴隸,無法成為美國參與式民主制度中合格的公民,是不受歡迎、需要排斥的。
四、1875 年《佩奇法》及其實施
在美國當時機會主義盛行的政治環境中,彌漫于白人社會的對華人的歧視和排斥,是不會被政客們放過的,加州議員們很快便開始在華人問題上大做文章。為了贏取選民支持,他們不僅利用了當地社會普遍存在的排華情緒,還夸大華人帶來的各種威脅。華人妓女和妻妾帶來的道德、種族和醫學等挑戰與華工的經濟威脅被打包組裝,成為一系列加州當地排華法案的主要內容。[37]但這些地方法案都被美國最高法院宣布無效,原因是它們違背了1868 年中美兩國《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中允許“自由移民”的條約精神。[38]在地方上不斷受挫后,加州議員便將立法努力轉向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國會。
(一)《佩奇法》的制定
相比于法案中的“華工經濟威脅”條款,華人妓女帶來“道德威脅”條款在全國政治舞臺上獲得了更多的呼應與支持。在19 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西部邊疆地區的賣淫與道德腐敗等是許多人關注的政治議題,像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總統和海耶斯(Rutherford B. Hayes)總統等政治人物,雖然從經濟角度尚不支持禁止華工入境,但他們認同妓女造成的道德沖擊,也加入了加州政客的行列,一道譴責華人妓女。[39]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加州聯邦眾議員賀拉斯·佩奇,1875 年的《佩奇法》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佩奇是共和黨人,因其排華立場而聞名,1873 年當選聯邦眾議員后,他便在眾議院大力推動排華立法。當時除了華人較多的西部各州之外,排華議題還不是其他地區議員們關心的話題,佩奇推出的多項排華議案均無疾而終。在競選連任的過程中,由于第一任期內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他擔心選民棄他而去,因此更是信誓旦旦,誓言將排華立法努力進行到底。獲得連任后,佩奇馬不停蹄,為了議案獲得通過,他采取了新的策略,對原來完全排華的目標做了妥協,小心繞開了《蒲安臣條約》中“自由移民”的條款。1875 年2 月10 日,新一屆國會開始不久,佩奇便提出新的法案,指出華人移民中大多不是自由移民,而是沒有人身自由的苦力和妓女,應當禁止入境。他堅持認為聯邦國會必須就此立法,一勞永逸地解決“黃禍”威脅和從中國輸入的道德淪喪的問題。[40]
為了通過《佩奇法》,佩奇在國會發表演講,長篇大論為何大部分赴美華人不是自由移民這一主題。他特別強調的是華人女性對美國的家庭和婚姻傳統造成的沖擊和對白人種族純潔性的威脅。他無中生有,煽動美國人的恐懼,說什么中國把美國當成一個“糞池”(cesspool),把臣民中最墮落的、受奴役的人群——包括苦力和妓女或小妾——派往美國。佩奇進而指責中國破壞了《蒲安臣條約》,沒有遵守其中“自由移民”的條款。而美國只是通過法律禁止苦力和妓女赴美,并沒有限制兩國之間受《蒲安臣條約》保護的“自由移民”。[41]此外,為了掩飾其中限制移民的本質,佩奇等人對法案的名稱句斟字酌,最終以《現有相關移民法律的增補法案》(An Act Supplementary to the Ac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為名提交,巧妙掩蓋了該法對原有移民法律的巨大改變。[42]《佩奇法》沒有遭到太多的反對便在國會獲得通過。該法抓住了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反對奴隸制和一夫一妻制的情緒,以保衛美國傳統的婚姻制度和民主制度為名,成功地對被當地人等同于奴隸的東亞尤其是中國苦工和女性關上了大門。
《佩奇法》最終限制的對象是華工苦力和華人妓女,在國會開創了針對某一種族和民族的特定群體立法進行移民限制的先例。就該法規定的懲罰措施而言,妓女買賣與苦力貿易相比受到的處罰更為嚴厲。法律對從事苦力貿易的違法者施加最高1 年監禁和最高2000 美元的罰款。而從事華人妓女買賣被認定為“重罪”(felony),一旦定罪,最高刑期為5 年,最高罰金是5000 美元。[43]除去之前被最高法院否決的加州地方排華法案,《佩奇法》成為當時最為嚴厲的限制部分華人移民的美國聯邦法律。
(二)《佩奇法》的實施與影響
與法律條文相比,更為重要的是法律的執行。《佩奇法》沒有達到阻止苦力華工赴美的目的。從法律出臺到1882 年《排華法案》之間的七年間,移民美國的華人超過了之前的任何一個以七年劃分的時間段。但是在阻止華人女性移民美國方面,該法相當成功。法律實施后的七年間,到達美國的華人女性與之前的七年相比下降了68%。七年間美國的華人人口總共增長了超過32,000 人,但是華人女性占美國華人人口的比例卻從1870 年的6.4%跌落到了1880 年的4.6%。[44]該法實施后,不僅禁絕了華人妓女赴美,而且連其他普通華人女性也受到牽連與打擊,她們前往美國的正式渠道基本被切斷。正如孔飛力指出,“雖然該法令只是限制娼妓入境,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使移民當局得以以此為借口,將華人婦女都當成娼妓而拒絕其入境。”[45]
鑒于當時華人前往美國主要經由香港與舊金山,該法的執行實際落在了香港和舊金山兩地的移民官員手中。就香港方面而言,美國駐港領事館官員在華人赴美的程序環節中負責把第一道關。他們與港英當局以及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等機構合作,開展申請資料審核、離港前體檢和面對面盤問等工作。以《佩奇法》剛實施時在任的美國駐香港領事大衛·貝利(David H. Bailey)為例,當他得知該法獲得通過后,對其上級說希望借此能夠阻止那些出于下流和不道德的目的前往美國的華人女性。他為此專門設計了一系列用于篩查妓女的問題,對每位女性申請者進行盤問。問題包括“你是已婚還是單身?”“你是自愿去美國的嗎?”“你去美國做什么工作?”“你是去美國從事賣淫業嗎?”“你在香港、澳門或中國大陸的妓院生活過嗎?”“你曾經從事過賣淫業嗎?”“你是一位有德行的貞潔女子嗎?”,等等,其中有不少都是華人女性申請者在日常生活中聞所未聞、難以啟齒的問題。[46]這些盤問環節之后,領事官便下結論寫報告,并上報美國國務院申請批復。由于國務院距離遠,缺少其他的信息渠道,對駐港領事官的報告一般都會例行公事,程序性地簽署批準。因此,對于出境審核,香港領事館擁有事實上的最后決定權。當然,由于領事官員玩忽職守、腐敗受賄以及從事妓女買賣的蛇頭繞開出港手續的各種伎倆,《佩奇法》頒布后并未完全阻斷華人女性赴美的渠道,但確實有很多華人女性申請者因為新法律要求的各種嚴厲手續而被拒之門外。而每一位被拒的申請者都會產生示范效應。她們受挫的經歷在當地傳開后,不少其他原本有意申請的女性也就打消了申請的念頭。
就舊金山港而言,考慮到加州此前在排華反華方面不斷立法不斷受挫的經歷,《佩奇法》的通過對其是一大鼓舞,他們在法律的實施方面尤為賣力。舊金山的移民官員同樣心懷前述針對華人女性的種族和道德偏見,在執法過程中打擊范圍擴大的現象經常發生。很多華人女性通過了香港的層層檢查與盤問,又經過了遠洋航行到達舊金山后,卻發現自己又被舊金山港口移民官扣留,而申請解除扣留的法律手續極為復雜,港口的法官又敷衍塞責,結果是不少華人女性因被懷疑與賣淫業有牽連而又被長途遣返回中國。[47]
從1875 年《佩奇法》實施到1882 年《排華法案》之間的七年時間,美國駐香港領事官員與舊金山移民官員共同嚴格執法,不僅將華人妓女成功排除在赴美的官方渠道之外,還將法律的打擊對象擴大到所有正常赴美的華人女性,成為華人女性前往美國的一道難以逾越的法律障礙。該法實施一年后,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聯合委員會調查華人移民的情況,參與聽證的舊金山港檢查員格雷(Giles H. Gray)作證說,在《佩奇法》實施前,每月有兩艘華人移民船抵達舊金山港,每艘船平均載有200 至400 名華人女性。法律實施后,抵美的華人女性人數急劇減少。實施后的前4 個月(1875年7 月—10 月),抵達舊金山的華人女性減少至161 人,而到了1876 年的第一季度,總共只有15 位華人女性登岸,[48]這足見該法在限制女性入境時的執行力度。
五、結語
《佩奇法》實施后,來到美國的華人女性越來越少,華人社區中女性比例愈發降低。前文提到的美國人口統計數字顯示,從1860 年到1870 年,在美國的每1000 名華人男性對應的華人女性人數從54 人上升到了78 人,但到1880 年,即《佩奇法》實施后的第5 年,這一數字又下降到了47 人,不僅大大低于1870 年的水平,與1860 年相比也有較大的回落。鑒于該法基本阻止了華人女性移民美國,有學者將這七年時間命名為“限制華人女性入境期”(female exclusion)。[49]
《佩奇法》與中國文化傳統、華工的旅居者心態等因素一起,有效阻止了華人女性前往美國,而相比于其他因素,《佩奇法》帶來的更大的不良后果是使這一現象長期化。華人女性赴美受限,反過來加劇了北美華人社區性別嚴重失衡的問題,正常的以婚姻為基礎的華人社區長期難以出現和發展,而賣淫業等與單身漢社會相關的產業得以繼續興盛。此外,這一法律還在聯邦層面開創了針對某一特定群體排外立法的先例。加州議員繼續推動更徹底更全面的排華法案,并得到其他地區議員越來越多的響應,最終導致1882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歷史上的第一個限禁外來移民法案,即通常所謂的1882 年美國排華法案。
[注釋]
[1]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6, No. 1,Fall, 1986;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2]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3] Sucheng Chan,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n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 曹雨:《美國〈1882 年排華法案〉的立法過程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5 年第2 期;李曉靜:《19 世紀中期到20 世紀初美國排華政策對華人社區的影響》,《山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 年第4 期;梁茂信:《論19 世紀后期美國對華移民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98 年第6 期。
[5] 楊國標等:《美國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陳堯光:《美國華人境況的變遷》,《美國研究》1987 年第2 期。
[6] 令狐萍:《十九世紀中國婦女移民美國動機初探》,《美國研究》1999 年第1 期。
[7] 劉卓、楊大偉:《從邊緣到主流:華裔美國婦女社會地位的上升歷程》,《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6 期;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版。
[8]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1200 頁。
[9] 徐國琦:《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59 頁。
[10][38] 謝青、羅超:《蒲安臣條約對美國排斥華工的客觀抑制作用》,《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3 期。
[11] 劉華:《評1868 年中美〈蒲安臣條約〉——以華工出國及華僑保護問題為視角》,《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年第1 期。
[12] 韓玲:《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內的美國移民政策史研究》,《世界民族》2016 年第6 期。
[13] Benson Tong,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p.25; Judy Yung,Unbound Voic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99.
[14][43][49]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24、p.115、p.8.
[15][36][45] 孔飛力著、李明歡譯:《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23、200、236 頁。
[16] Thomas Sowell,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BasicBooks, 1981, p.136.
[17] Benson Tong, 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p.25.
[18] George Anthony P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5-6, 11-27.
[19] Elmer Clarence 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1939,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1, p.9;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4, 15, 94;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31.
[20][31][33][34][35]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21] Susie Lan Cassel,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Alta Mira Press, 2002, p.24; 令狐萍:《十九世紀中國婦女移民美國動機初探》,《美國研究》1999 年第1 期;Shih-Shan Herny Tsai,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
[22] 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4 輯》,中華書局,1984 年。
[23] 類似的綁架故事參見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40; Judy Yung,Unbound Voices: A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pp.125, 130-131, 148-149.
[24] 參見Judy Yung, Unbound Voices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pp.125, 141;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p.75, 101-105, 144-145, 201.
[25] Yung,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p.19, 320.
[26] 對于美國排華因素的經濟解讀,可參見Elmer C. Sandmeyer,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7] Arthur B. Stout,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a Nation, 1862, Xerographic Reprints, UMI, 2001, pp.6, 8.
[28] Benson Tong, 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27-28, 131;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pp.73-86.
[29][39]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pp.129-132、pp.132-133.
[30]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5, No. 3, April, 2005.
[32] Yung,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1.
[37] Sucheng Chan(ed.),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6.
[40]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34-36; 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p.71.
[41] 關于議員佩奇在法案通過前的國會演講及聽證證人證詞等內容,參見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 pp.692-694.
[42]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 105, No. 3, April, 2005.
[44]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6, No. 1,Fall, 1986.
[46] 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pp. 31-32.
[47] George Anthony Peffer,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pp.57-72; Benson Tong,Unsubmis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p.47-50.
[48] Kerry Abrams, “Polygamy, Pro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 105, No. 3, April,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