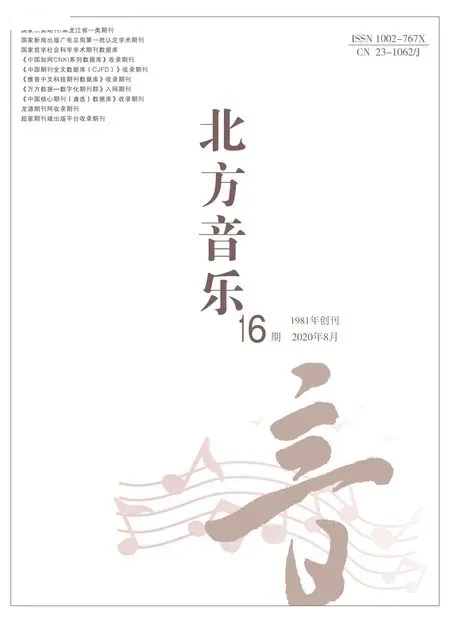房曉敏論著《五行作曲法》評述
賴海忠
(廣州工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五行作曲法》是中國近現代民族作曲技術理論探索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與上海音樂學院趙曉生的《太極作曲技法》、中央民族樂團吳少雄的《干支和樂論》、上海音樂學院何訓田的《R·D(任意律和對位法)作曲法》等音樂作曲技術理論論著,共同組成了中國近現代民族作曲技術理論探索方面的重要成果。
該作曲技法以中國古老的《周易》陰陽哲學為依據。《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哲學,是群經之始,是諸子百家的開始,是中華文化的總源頭。臺灣大學曾仕強教授說:“《易經》是解開宇宙人生密碼的一部寶典。”其中的“宇宙人生”包括了宇宙萬物和人生萬事——醫學、建筑、科學、天文、體育、教育……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音樂。因此,也可以說《周易》是解開音樂密碼的一部寶典。然而,《周易》與音樂的關系怎樣?《周易》里包含的音樂密碼到底是什么?成為房曉敏多年研究和探尋的最核心的問題。帶著這些問題,他嘗試從音樂的節拍、節奏、曲調、調式、和聲、音高等多種要素上進行探索,最終尋找到音樂與《周易》的對應關系,創立了《五行作曲法》。通過整理,該作曲技法大致有以下特點:
一、包容性
筆者曾做過一項調查研究,在與同行友人交談之間問詢其對《五行作曲法》的認知和理解,其中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是:《五行作曲法》較適用于中國民族音樂,或者是房曉敏個人創作的音樂。《五行作曲法》的理念來源于《周易》,《周易》認為,“陰陽”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元素,用符號“—”“— —”來表示世界萬物。“陰陽”在音樂中的表現形式是無處不在的,比如說,速度的快與慢、力度強與弱、音高高與低、節奏的密與疏、和聲的松與馳、色彩的暗與亮,等等。這些音樂的“陰陽”不管是在什么時期、什么風格、什么區域的音樂,都是具有適用性的。而實際上來說,音樂元素的“陰陽”在任何音樂中都是存在的,只不過我們不用“陰陽”這個詞匯去表達,而是用“強弱”去表達音樂的力度,用“長短”表達音樂的節奏,用“剛柔”表達音樂的調性色彩,用“高低”表達音樂的音高關系等,而這些相對關系,在《周易》音樂哲學理念以及《五行作曲法》中,這種相對應的關系都表達為“陰陽”,音樂中的陰陽關系,同樣的道理,會延伸和細化到音樂的其他方面。也許就是想說明這個問題,房曉敏用《五行作曲法》的相關作曲技術理論分析了洗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的調式——《<黃河大合唱>調式風格研究》;分析了梅州客家山歌調式——《梅州客家山歌調式結構比較》等。在五行作曲技法的第四章節——“三才調式”中,房曉敏撰寫了“傳統調式與近現代調式比較、東方與西方調式比較、東西方音程調式比較”等內容,意為在《五行作曲法》的“三才調式”中探尋中西方調式、古今調式的同異之處。這些都體現了該作曲技法的包容性問題。
二、創新性
在《周易》的陰陽思維的指導下,在音樂的“陰陽世界”里,《五行作曲法》在節拍、節奏、結構、調式、和聲、音高系統等方面存在著多方面的創新。首先是對每種音樂元素使用的邏輯上;其次是每種音樂元素形態在思維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新的形態;再次是音樂元素的形態對音樂的意義。比如說,在音樂的節拍方面,《五行作曲法》的“太極節拍”中,節拍的觀念改變了,這就直接影響到創作者對節拍運用的思維和對節拍的認識;拍強思維改變了,這就導致了出現很多與傳統不一樣的節拍拍強形態,如三拍子,三個連續的強拍、六拍子的相隔強拍等,這些拍強形態,不管從拍強形態上還是在運用拍強的思維上,都是與傳統不一樣的;還有一些專業音樂概念的創新,如太極節拍、陰陽節奏、兩儀結構、三才調式、四象和聲、五行音高等,從音樂與音樂理論發展的角度上看,這些創新是不同程度上對傳統的音樂概念的擴充和發展。
三、現代性
20世紀的音樂走進了我們所謂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就是上海音樂學院趙曉生教授所說的“合力論”。[1]“合力論”風格是指20世紀作曲可在理論與情感、控制與反控制、中心與無中心、協和與不協和、民族性與世界性等互相對立的諸范疇中,以一特定基點為出發點,綜合應用其他各種與之對立的因素,為作品尋找恰當的“綜合點”或“凝聚中心”;圍繞這一中心,將多因素同時復合,從而形成新的風格特征。在房曉敏的《五行作曲法》中,通過對《周易》陰陽哲學的感悟與運用,借助周易陰陽五行的生克理論對音樂的“節拍、節奏、曲調、調式、和聲、音高”進行調控,而作為一種作曲技法,作曲技法本身與音樂的具體風格是沒有絕對關系的,《五行作曲法》是一種音樂元素與音樂周易陰陽理念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戲可以做現代性的表達,也可以做傳統性的表達。而作品風格的取向則在于作曲家本身的選擇上,如房曉敏的創作,其作品中有很現代的——三重奏《悟》,也有很多很傳統的音樂作品。筆者曾就這個問題采訪過房曉敏:“現代音樂的風格的現代性與傳統性對于作曲家來說是一種選擇,看作曲家自己的角度和追求,在我看來,現代性的詮釋體現在其‘綜合與多元’方面,在我的作品中,總喜歡在現代與傳統中尋找平衡,在繁復與簡單中尋找‘折中’,讓聽眾在現代中不致于迷于方向,在傳統中又不至于‘陳腔舊調’。”他重視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新的美學潮流相結合,重視人文精神,考慮聽眾的接受能力,而這一切選擇與作曲技法是沒有關系的。在《五行作曲法》的運用下,可以寫出很傳統的作品,也可以寫出很現代的作品。
四、文化性
《五行作曲法》最大的特點之一就在其文化性,這與其產生的背景有密切關系。縱觀西方的作曲技法論著,很少作曲技法是來自于一部哲學論著,而《五行作曲法》卻是這樣,它來源于《周易》陰陽哲學,這就導致了其“文化性”的特點。在五行作曲技法中,每一種現象里面都有一些含義。比如音樂的節奏,每一種節奏都存在一種文化含義,它跟單純的節奏作為文化符號不盡相同。比如說,在房曉敏的作品《悟》中出現了唯獨的一個全音符,這個全音符是有文化含義的,在《五行作曲法》中稱其為“太極音符”,這個“太極音符”是生成其他音樂的本源,是音樂音符的“太極音”,因此,這個音符的意義就變化了,它不代表簡單意義的音符,其存在一種文化含義;比如說音樂的結構,每一種結構(包括一些新派生的結構),就拿三部曲式來說吧,三部曲式在《五行作曲法》中被稱為“離”結構,“離”來自于《周易》的“八卦”,而“離”這種結構的布局思維又來自“八卦”的卦象,因此,它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三部曲式。
五、變易性
“變”是《周易》哲學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乾”卦就講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中就包含了“變化發展不息”的含義。以《周易》為哲學基礎發展而來的“五行作曲法”,“變”在音樂中被高度強調。其認為,音樂的發展過程就如人一生的發展過程、植物的生長過程一樣,在每個階段、每個季節存在變化,音樂在不同的結構位置、不同的空間位置也需有不同形式的變化,要做出階段性的調整。然而,不管是傳統音樂,還是用“五行作曲技法”所寫成的音樂,變化都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變化的思維和方式是不一樣的。在五行作曲技法中的“變化”依據于《周易》陰陽、五行理論,在音樂中,不同音樂元素的變化發展,具有了五行“生克”等理論的支撐,建立了獨特的變化思維,產生了不同的變化方式與不同的音響效果。
六、延伸性
《五行作曲法》是房曉敏首創的一種與傳統不同的作曲技法,這套作曲技法,不管從觀念層面還是技術層面,不管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運用層面,它都是與眾不同且值得參考借鑒的。因此,我認為《五行作曲法》具有了被弘揚和發展的需要。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困難——技法的深奧性。作為一部學術論著,總需要被實踐檢驗,被大眾認知,甚至于被大眾付諸創作實踐,然后對后人產生影響。我相信,這是每一位熱心于寫作論著的人的共同追求之一。然而,這種追求是不會停止的,因為世界萬物在變化、在發展;音樂在變化、在發展;理論也需要不斷地完善與發展。在跟房曉敏的談話中,房曉敏曾經說:“對于《五行作曲法》,這是一部寫不完的書,實際上,自2003年其第一次出版后,之后也在不斷地往里面增添內容,以達到不斷完善的目的。這需要很多熱心人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斷地努力。”我認為,努力的方向大致在技法的寬度與深度以及技法的通俗性、普及性等方面。
七、結語
20世紀的音樂,我們不敢應望所有的音樂作品都用同一種技法寫成,用同一種分析方法對所有作品進行分析,我們也不希望音樂分析者單純進入作曲家設定好的范疇作看似繁復的技術分析,我們渴望從多層面、多視角去創作作品、認識作品。通過對《周易》文化的學習以及對《五行作曲法》的學習和研究,作曲者可以更好地處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問題——如何在傳統中發展現代、如何在現代中保留傳統;現代音樂的文化內涵問題——如何在現代音樂創作中把握自己的音樂理念與哲學取向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