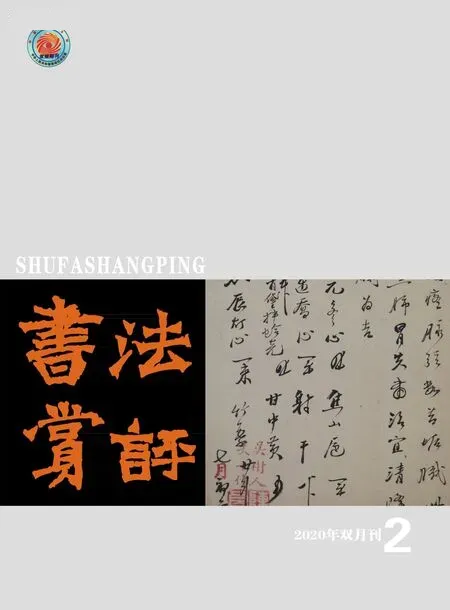李瑞清“蘭亭觀”的轉變及緣由探析
朱 琳
導師評述:
朱琳目前是杭師大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書法篆刻史論研究方向)的二年級學術碩士生,她在研二上學期完成的這篇論文經過多次修改得以刊發,是對她前一階段學習和思考的一個肯定。雖然論文尚有不足,偏于稚嫩,但我非常樂意就此做出評述和推介。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一、該研究基于作者的學術興趣點,有較明確的問題引領。二、有較扎實的文獻梳理和解讀,前期的學術訓練和研究鋪墊起到了支撐作用。三、研究具有較好的持續性,由點至面再至立體,逐步深入。這三方面的看法,當然并非只建立在這單篇論文的基礎上。朱琳自入學不久,即顯現出格外勤奮好學和善于思考的品質,課外我經常被她“攔截”追問,并不時收到她“塞”過來的額外論文,因此交流更為頻繁。
作者對于晚清民國時期的書法教育一直存有濃厚的興趣,試圖梳理此期有代表性的書法教育者及其教育理念、書學思想。前期她在撰寫另一論文《李健<金石篆刻研究>中的“古器物圖”探析》時,對李健與李瑞清的師承、淵源關系已有一定的認知。李瑞清身為兩江優級師范學堂督學,是晚清民國書法教育史上的關鍵人物,其門人胡小石、姜丹書、李健后來也都身肩上海、南京、杭州等各地教職,因此追索李瑞清的教育理念及書學思想成為下一個目標。作者認為,李瑞清的“蘭亭觀”雖是其書學思想的一個局部,但先聚焦于這個“點”,進而將視野擴展,探究李瑞清對古代碑帖經典的觀念及促成因素,是一個可行的研究路徑,有助于全面、系統地把握李瑞清的書學思想,乃至更大范圍的晚清民國時期書家的思考和選擇。因此,她對《清道人遺集》中的碑帖題跋進行了較細致的解讀,又對李瑞清與同時代書家的交游和學術大環境加以考察,最后得出的觀點便聚結為這篇論文。朱琳在撰寫這篇論文期間,正是學位論文的開題階段,經過反復驗證,她將選題和研究方向仍鎖定于“晚清民國書法教育”,因此前期的這些點滴或片段思考,與后期的研究必然有緊密的聯系,我期待她能夠不斷推進,對這一時期的書法史、書法教育史逐步建立起更為立體、深厚的學術認知。
研究生的教學和培養,涉及很多層面的問題。從長遠來看,碩士生階段是進入專業領域、從事學術研究的“起點”,而學術論文的寫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這一環節中,尤其需要培養的,一是問題意識(學術敏銳度和思辨能力),二是文獻能力(對文獻史料的收集、解讀和運用能力)。我作為導師,理當與學生共同努力、不斷錘煉。
導師:徐清(杭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20世紀初,新、舊學術思想相互交匯,書家、學者的書學觀念亦體現出這一時代的印記。李瑞清(1867-1920)作為晚清民國書法史上“金石派”的代表人物,[1]其獨特的書畫造詣早已為書法界、美術界所關注,其作為金石學家、書學教育者的身份及與此緊密相關的學術思想也受到了學界的重視。以往研究者對李瑞清及晚清民國書家的探究已取得諸多成果,但是仍有值得繼續推進的空間。筆者試以李瑞清有關《蘭亭序》的題跋為基礎資料,對其“蘭亭觀”加以分析,借此梳理其帖學觀念及促成因素,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李瑞清的書學思想和書學教育理念,進而窺知晚晴民國時期書學發展的特質。
一、李瑞清“蘭亭觀”的轉變
李瑞清早年受翁方綱、阮元、何紹基等前輩金石學家的影響,從事金石拓本的搜集與考訂,并據拓本觀察古代書體與風格的歷史變遷,尤其青年科考時期,對阮元的碑學思想較為推崇。[2]根據夏壽田的記述:
“歲戊戌復相遇京師。余賃廡晉陽寺,髯與清道人同居臨川館。髯與清道人至相得,約為兄弟,朝夕龂龂論書家南北宗,又各出唐宋人畫相夸詫,髯得意時,輒聲震屋瓦。”[3]
可知,李瑞清在赴京師科考(1898-1899)期間,曾與曾熙反復討論阮氏的南帖北碑論。李瑞清的《玉梅花庵書斷》中,也有與阮元南帖北碑論相近似的言論:“書學分帖學、碑學兩大派,阮云臺相國元以禪學南北宗分之,帖學為南派,碑學為北派。何謂帖學?簡札之類是也。何謂碑學?摩崖碑銘是也......碑學之中興,自阮相國始,以南北分宗,其論甚辯,然究不確。阮既倡碑學,至鄧石如、包慎伯是其后勁,今之書家,莫不人人言碑矣。鄧書全從碑入,包則手寫帖而口言碑,然著有《藝舟雙楫》,于碑學頗多發明,不能謂為無功也。”[4]他又論說道:“南朝士大夫雅尚清淡,揮塵風流,形諸簡札,此帖學之萌芽也。唐太宗好《蘭亭》,于是又唐一代書家,無不學王者。蘇靈芝欲展《蘭亭》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書實傷婉麗,所謂俗書之祖也。”[5]這表明李瑞清早年頗受阮元書論及碑帖發展觀的影響。而對于《蘭亭序》,李瑞清在閱讀了阮元以及光緒學人李文田(1834-1895,字仲約)的考證、著述后也深有感觸,《蘭亭序》文本內容和文字書寫的真實性一度成為他關注的重點。
李瑞清《跋自臨蘭亭序》(1912年后)云:
“余生平不解《蘭亭》,頗為沈乙盦先生所訶。然不能違心隨聲雷同以阿世。順德李仲約侍郎,有三可疑之說,如道人胸中所欲語。今世所傳《蘭亭》與《世說新語》所載多異,‘莫春’作‘暮’,‘禔’作‘禊’,‘畼’作‘暢’,唐以來俗書也,晉代安得有此?此余所大惑也。”[6]
李文田曾在《蘭亭序跋》中,從文本角度指出《蘭亭序》有三個可疑之處:一是《蘭亭》用筆與現存的晉碑不同,唐以后《蘭亭》并非是梁以前的《蘭亭》;二是《蘭亭》的篇幅比《金谷序》的較長,應是隋唐人根據晉人偏好而任意添加;三是《蘭亭》與《世說新語》的注所引不同,且與王羲之文集不相應。[7]李瑞清不僅對李文田的質疑表示認同,還進一步舉證了“暮”“禊”“暢”三字,認為它們是唐代以后出現的俗字,不符合東晉的字形寫法,因此《蘭亭序》的真實與否令人疑惑。
然而,李瑞清在鬻書滬濱期間(1912-1920)對《蘭亭序》的態度已開始產生變化,他并不一味地糾結于《蘭亭序》的真或偽,而是逐漸傾向于從更宏觀的書法史層面,對其書學地位和價值加以認知,并以自己的理解來臨寫《蘭亭序》。
這種變化是逐漸產生和深化的,在上文引述的這段李瑞清《跋自臨蘭亭序》中,他還說道:“頃見曾季子、鄭蘇戡所臨《蘭亭》,鄭則自運,盡變其面,曾則以率更法為之,‘定武’嫡派也。余則略參以篆隸筆作此。”[8]李瑞清看到曾熙臨《蘭亭》得歐本筆法之精妙,而鄭孝胥則完全改變了《蘭亭》原貌、純出自運,因此他也嘗試以另樣的方式來寫蘭亭,即參用篆隸筆法。1914年,李瑞清在跋《定武蘭亭肥本》時,強調了《蘭亭序》的筆意古法:
“自來言帖者莫不首推《蘭亭》,宋時士大夫家刻一石,游丞相一人刻五百之多,故以定武石刻為第一,以為不失古法,而肥本最為難得。此本墨色黝古,用筆渾厚,猶有鐘元常風度,如‘欣’字末畫翻落,章草筆也。‘向’‘因’‘固’諸字,汪容甫先生謂似《始平公》,非得此本,何以證其言之非誣。”[9]
李瑞清稱賞《定武蘭亭肥本》保留了鐘繇的筆法風貌,收筆的翻出體現了章草筆法。此后,李瑞清在1915年《跋蘭亭六種影印本》中,又對《蘭亭序》存世版本有所梳理和探討:
“《蘭亭》為書道一大關捩,繭紙既入昭陵,‘定武’歐模耳,只能以之求《化度》,右軍真面不可復見,仍當于唐賢中求之。唐人摹《蘭亭》者以歐、褚最稱于世。余曾見虞摹于徐叔鴻丈齋中,薛摹素未之見。薛本自褚出,而此本獨凝靜絕,無褚法,于此或反可以想象右軍‘玉枕本’實從‘定武已損本’出。‘穎上本’世傳為褚書,與‘神龍本’殊,然有煙霏霧結之妙,可寶也。”[10]
李氏認為:學書者可從唐代書家的模本中,窺探右軍書法面貌,其中尤以歐陽詢和褚遂良的臨本最為著稱;“玉枕本”雖然沒有體現褚遂良的筆法,但體現出筆法的凝靜,應是出自“定武已損本”。
1915年,曾熙在題跋中提及:他與李瑞清“共幾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見,今則服膺予論”。[11]曾熙認為書學應溝通南帖北碑,他的書法善用漢隸圓筆、融合方圓,故自稱南宗。這條記錄也佐證了這一時期的李瑞清已由服膺阮氏的南帖北碑論,轉為認同曾熙的觀點。曾熙在《跋清道人節臨六朝碑帖》中,也針對阮元南帖北碑論提出過自己的見解:
“《晉書》《南北史》皆唐人所修,阮于《北史》所稱崔悅、盧諶等善隸工草,則信為有家法,右軍傳中善篆隸書為古今之冠則疑,援史品題,謂世不傳右軍隸法則可。至疑右軍不能為隸,大令不解榜書,所謂非惑也,乃謬也......阮氏執南宋以來輾轉勾撫,真偽混雜之閣帖,幾疑江左風流,盡出渡江衣帶一帖,何異見今日僧子誦經,即奉為如來法耶......近敦煌石室經卷,見有北朝書章草,以證沙簡中晉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見也。”[12]
曾熙指出:阮元因時代局限,未能對新材料進行研究,對王羲之認識存在缺憾,南北碑帖論也多有偏頗。這樣的見解和認識,對李瑞清原有的碑學觀念有所撼動。
李瑞清在《跋裴伯謙藏定武蘭亭序》中,更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對《蘭亭序》的肯定:
“有唐書家無不宗右軍者,猶宋書家之無不學顏,國朝書家之無不學董,其風尚然也。雖時代遞嬗,所師各殊,然無不推右軍為不祧之祖。右軍行書于世者,無豐碑巨碣,但有箋簡、尺牘之屬。其最著者,世稱《蘭亭修禊帖》,其時歐、褚諸家均有模本。歐模極近右軍,今所謂‘定武本’是也,歷代書家無不寶之,奉為模范。余學北碑二十年,偶為箋啟,每苦滯頓。曾季嘗笑余曰:‘以碑筆為箋啟,如載磨而舞,所謂勞而寡功也。’比年以來,稍稍留意法帖,以為南北雖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論古今書法之源流變遷,使知此帖為古今書學一大關鍵,要非阮蕓臺奮其私說所能革命也。”[13]
李瑞清認識到:雖然時代遞嬗,但王羲之書法依舊是書家學習和繼承的“不祧之祖”;結合自身二十年的學碑經驗來看,純以碑派筆法書寫簡札,容易板滯,因此臨習法帖、碑帖兼涉,方是通途;《蘭亭》是書法發展史的關鍵節點之一,其價值絕不是阮元北碑南帖論可以抹殺的。這段題跋也印證了曾熙所說,李瑞清對阮元北碑南帖論的前后態度發生了轉變,由服膺轉為質疑和反思,對帖學標桿《蘭亭序》的態度也因此隨之轉變。
綜上,李瑞清在1912年鬻書滬濱后,沒有將《蘭亭序》的研究內容局限在單一的考證層面,對《蘭亭序》的態度也不再是單純的質疑真偽,而是轉從書法源流發展史的研究角度出發,以書法史觀念重新看待《蘭亭序》的傳承脈絡,肯定《蘭亭序》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并提出要以篆隸筆法臨寫《蘭亭序》的見解。
二、內因:李瑞清對書學源流發展的再認識
在阮元、何紹基南北書派論的影響下,李瑞清與其他的金石學家前輩一樣,在研究中注重字義的考證、名物的解釋,以及拓本校對、考證;與前人不同的是李瑞清更為注重對書法史源流的考述,[14]這也成為促使他日后能夠反思、修正碑帖觀念的契機。且李瑞清在南京任兩江師范學堂監督時(1903-1911),與端方交游圈中的金石學家、碑帖收藏家頗多交游,有機會寓目并參與校對大量的拓本,飽覽端方、楊守敬、王孝禹等人豐富的收藏,[15]為其書法史源流的考述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拓寬了其學術視野。
自19世紀末起,甲骨文、西北簡牘等新材料的陸續出現,引發學界的髙度關注,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收藏家、學者的圖錄、研究著作相繼出版,這些成果同樣引起李瑞清的關注。[16]
出于梳理書學發展史的契機,以及樸學家整理古代文獻的促動,李瑞清對所見到的古代文字、圖像材料進行整理比對,即:對商周甲骨文、金文,秦漢篆隸、六朝隋唐楷書進行追本溯源、劃分流派;并將研究范圍拓展到錢幣、磚瓦、鏡銘、度量、權衡、陶器等器物上,對阮元的關于古代書體、風格考據式的研究范圍進行拓展,至尚未得到充分關注的商周青銅銘文也成為書法研究的內容,尤其是新發現的文字材料如甲骨文、西北簡牘也被他及時納入到觀照的系統中,這為李氏在阮元的研究基礎上進行推進和反思,提供了新的佐證材料。此后,李瑞清對商周迄于隋唐的書體與書法風格,進行大量深入的分析,并將此研究方式延伸至唐宋以至于清代的書法墨跡中,使其在研究的范圍和方法深度上,都對于阮元的相關論述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入,[17]為自身客觀認識《蘭亭序》的書學地位和價值,提供了可能性。
李瑞清在進行書法史源流考述的過程中,對商周迄于清代的書體與書法風格,進行分析和梳理派別,注重對鐘繇和“二王”書跡的推研,提出:“《宣示》《力命》平實微帶隸意,皆右軍所臨也,無從窺太傅筆意。”[18]并在1918年李瑞清《跋曾農髯夏承碑臨本》時言:“有晉王逸少世所號書圣者也,王師鐘繇,鐘實出中郎,是中郎為學書祖。”[19]可知李氏認為:鐘繇下啟王羲之,而師承蔡邕,王羲之楷法師法鐘繇,實則是學習蔡邕筆法,王羲之書法師承蔡邕傳襲隸法。在李瑞清《匡喆刻經頌九跋》中,也曾提及:“‘字似欹而實正’,此唐太宗贊右軍書也。其實亦從商、周鐘鼎中來,此秘惟《鶴銘》《龍顏》、鄭道昭、《張黑女》及此石傳之,其要在得書之重心點也。”[20]李氏將王羲之書法可得唐太宗稱贊,歸因為字的欹正關系處理取法于商、周鐘鼎,得書之重心點的正確方法,再證王羲之楷法上承篆隸的主張。王羲之作為“二王”書法群體的開派者,李瑞清對其楷法溯源,實源于對整個“二王”帖學系統梳理的需要。《臨右軍帖》言:“世之言草書者稱二王,實大令支流耳。大王法孫過庭,后惟趙子昂略涉其藩,世傳但素師派也。”[21]并在《臨大令送梨帖》中補充:“大令草出于篆,然其縱者已開唐派,余獨憙此。”[22]由此可證,王獻之草書出于篆,取其變化縱式的懷素開唐派草書。這一觀念的產生,促使李瑞清將“二王”帖學取法上溯篆隸,置于書法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李瑞清在1912年后,以遺老身份蟄居海上,鬻字賣畫為生。初至上海時生活頻遇窘境,[23]為鬻書糊口滿足時人的購書需求,多取法“二王”書跡。[24]此時期對“二王”書跡的大量臨摹,對其客觀定位《蘭亭序》有一定促動性。
三、外因:時代觀念促使與交游學者影響
李瑞清“蘭亭觀”轉變的緣由,與其對新材料的關注有密切關系,[25]同時也因受到沈曾植、曾熙和鄭孝胥等人碑帖觀念的影響。20世紀初期,隨著甲骨文和《流沙墜簡》等書法新材料的出土,使得書家對書法史發展研究進入更深層的領域。鄭孝胥曾言:“自《流沙墜簡》出,書法之秘盡泄,使有人發明標舉,碑學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徑轍,則書學之復古,可操卷而待也。其文隸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細勘之,楷即隸也,草亦隸也。”[26]并題唐臨絹本《蘭亭序》曰:“米老所稱‘轉折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或指此本。唐人一代筆法不能越此。若更欲向上,需從隸草中求之矣。”[27]可見《流沙墜簡》的出現佐證了鄭孝胥楷、草書溯源隸法,于隸草中求古法臨《蘭亭》的觀點。李瑞清在《跋自臨蘭亭》中,也提及觀看鄭孝胥所書《蘭亭序》,故其參篆隸筆法臨《蘭亭序》,且此時期,鄭孝胥與李瑞清的交游較為頻繁,嘗共宴、論書畫文字源流發展,[28]可見二人在《蘭亭序》的研究方面互有參照。
沈曾植較李瑞清年長,對碑帖皆有研究,處于清末書壇,深受阮元重碑抑帖,以及康有為貶卑唐碑的思想影響。1913年底或1914年初,沈曾植曾寫給羅振玉的信中提及:“漢竹簡書,近似唐人,鄙向日論南北書派,早有此疑,今得確證,助我張目。”[29]新材料的出現,引發沈曾植對阮元南北書派論的反思和研究,促其開始重新審視書法源流和傳統書學理念,嘗試將碑與帖進行融合,成為這一時期“碑帖融合”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30]李瑞清在《跋自臨蘭亭》曾言:“余生平不解《蘭亭》,頗為沈乙盦先生所訶。”[31]從沈曾植對于李氏的批評,及沈增植不采用南北書派論的明顯界定和尊卑態度來評價鑒賞蘭亭,并認為《蘭亭序》有風骨神采,可借《蘭亭序》從唐人模帖中追溯晉人書風等觀念,皆佐證沈增植對《蘭亭序》的認同。[32]李氏曾言:“年來避亂滬上,鬻書作業,沈子培先生勖余納碑入帖......酷暑謝客,乃選臨淳化秘閣、大觀、絳州諸帖,不能得其筆法者,則以碑筆書之,不知他日沈、秦兩先生見此,如何論之?必有以啟余。”[33]故在李氏居于上海期間,沈曾植作為書學前輩對李氏給予相應指導,其碑帖融合的觀念對李氏產生了一定影響。
曾熙是促使李瑞清“蘭亭觀”轉變的重要推手,除前文中有關阮元南帖北碑論偏頗的論述外,曾熙嘗與李瑞清、譚延闿等書家學者共同賞定《蘭亭》諸本,曾熙善比較不同版本之優劣,論其存本源流。[34]據李瑞清1915年《跋蘭亭六種影印本》中,版本分析的詳盡程度可知,此期間與曾熙的探討,使李氏對《蘭亭序》的認知逐步深化。同年十一月,曾熙云:“共幾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見,今則服膺予論,因書其后。”[35]在此后李瑞清的論帖題跋中,也流露出與曾熙相近的學術思想。種種皆表明,在曾熙對于阮元南北碑派論的否定下,李瑞清形成了新的碑帖觀念,也使其對《蘭亭序》的書學地位給予肯定。
在20世紀初新、舊學術思想相交匯的特殊歷史時期,新材料與新視角的出現打破了碑帖間的界限,從而將研究者從碑與帖何為上的糾結掙扎中解放出來。客觀而言,李瑞清受所處時代對《蘭亭序》研究材料和方法的局限,其“蘭亭觀”也并非完美,但體現出李瑞清對書法史源流研究的高度重視;代表了同時代書家對于《蘭亭序》的認識變化,暗含著書學者對碑帖關系的新審視,以及關注新材料所帶來的書學研究群體性變化。李瑞清的“蘭亭觀”雖只是其書學思想的一部分,但作為一個重要的聚焦點,有助于我們更系統、深入地把握李瑞清的書學思想,乃至更大范圍的晚清民國時期書家的思考和選擇。
注釋
[1] 《<清道人遺集>前言》,(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6頁。
[2] 王東民:《以古為新—金石學傳統下的李瑞清書畫研究、創作與教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第56頁。
[3] 夏壽田:《題曾熙山水冊十二幀》,王中秀、曾迎三編著:《曾熙年譜長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頁。
[4](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6-157頁。
[5] 同上,第157頁。
[6] 同上,第150頁。
[7] 李文田:《蘭亭序跋》,水賚佑編:《<蘭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頁。
[8](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0頁。
[9] 李瑞清:《題定武蘭亭肥本》,水賚佑編:《<蘭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版,第824頁。
[10] (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49頁。
[11] 王中秀、曾迎三編著:《曾熙年譜長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頁。
[12] 同上。
[13] (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73-74頁。
[14] 王東民:《以古為新—金石學傳統下的李瑞清書畫研究、創作與教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第52頁。
[15] 同上,第54頁。
[16] 李瑞清《題跋》中對石室經書及《流沙墜簡》等有所論述,詳見(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33-165頁。
[17] 王東民:《以古為新—金石學傳統下的李瑞清書畫研究、創作與教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第62頁。
[18] (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2頁。
[19] 同上,第146頁。
[20] 同上,第142頁。
[21] 同上,第153頁。
[22] 同上,第153頁。
[23] 同上,第38頁。
[24] 同上,第126頁。
[25] 《玉梅花庵書斷》:“近出龜版牛骨,實為殷墟文字,至可寶貴,睹之其派,最為明顯。從前殷代文字,但于殷器中見一二象形字,不足成立,今殷墟之龜版牛骨,其文字雖不全,可以灼然知其一代文字之派矣。”(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9頁。
[26] 鄭孝胥:《題莊繁詩書陶詩序》,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印刷,第944頁。
[27] 鄭孝胥:《題唐臨絹本<蘭亭序>》,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印刷,第1004頁。
[28] 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印刷,第958頁。
[29] 沈曾植:《海日樓遺札》,《同聲月戶》,1944年第四卷第二號,第94頁。
[30] 劉星振:《清代書家對<蘭亭序>解讀立場分析,《書法》,2018(06),第61頁。
[31] (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0頁。
[32] 沈曾植有關《蘭亭序》題跋,詳見水賚佑編:《<蘭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644頁。
[33] (清)李瑞清著,段曉華點校整理:《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第155-156頁。
[34] 《譚延闿日記》中,多次談及與曾熙、李瑞清等人共同賞定《蘭亭》諸本,探討書畫文字源流。詳見王中秀、曾迎三編著:《曾熙年譜長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版。
[35] 王中秀、曾迎三編著:《曾熙年譜長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