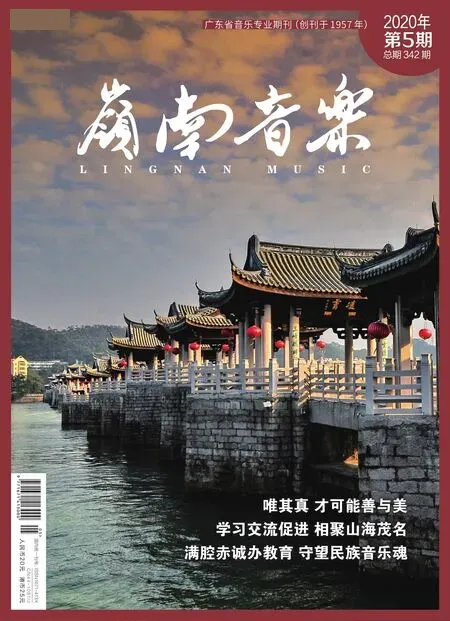生命體驗(yàn)與音樂(lè)藝術(shù)(上)
——曾健音樂(lè)創(chuàng)造本體論
文|
生命體驗(yàn),顯示出生命之嚴(yán)峻性與可能性。體驗(yàn)?zāi)松饬x之不斷感悟,在此不斷感悟之中,本體之思考,撕裂時(shí)間母胎而把握到永恒。思考是從虛無(wú)中透射進(jìn)來(lái)的澄明之光,它照亮了人生之現(xiàn)實(shí)世界。藝術(shù)創(chuàng)造,即對(duì)自己存在體驗(yàn)之反思與領(lǐng)悟。
對(duì)于從事一生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曾健先生(為敘述之便,下文均略去先生之稱謂)來(lái)說(shuō),體驗(yàn)就是一種人生境界,身處其中,人因秉持回憶、想象、激情、溫愛(ài)而將有限之生命,帶入出神狀態(tài)之中。曾健的此種本我體驗(yàn)性或體驗(yàn)的本我性,標(biāo)明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人生是一個(gè)永遠(yuǎn)體驗(yàn)與探索之過(guò)程,知識(shí)與理性乃至邏輯推理,并給我們提供現(xiàn)成的人生答案,答案只在每個(gè)人的尋找與探索之中,在于把握那震撼我們靈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對(duì)生存處境的深切洞悉本真之揭示中。我們只是人生最高問(wèn)題的提問(wèn)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體驗(yàn)中,在親身之經(jīng)歷、直接之感受、心靈之慰藉與喚醒之中,體驗(yàn)給予我們?nèi)松伎贾瘘c(diǎn),同時(shí)又使我們關(guān)心生命意義超過(guò)關(guān)心生命狀態(tài)本身。
曾健的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體驗(yàn),就是他的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造本身之呈現(xiàn)。曾健的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因體驗(yàn)的激情性而顯示出他的悲、歡、苦、樂(lè),因體驗(yàn)的原生性而無(wú)保留地坦露出創(chuàng)造者心中的每一絲波瀾、每一陣顫栗、每一分虔誠(chéng)。音樂(lè)關(guān)乎人生,這是曾健生命之表現(xiàn)與傳達(dá),它表達(dá)了音樂(lè)創(chuàng)造者曾健的本我體驗(yàn),而且表達(dá)了他生命之本真。只有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體驗(yàn),才使曾健不斷擺脫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之平庸、虛偽與成見(jiàn),曾健是帶著淚和微笑去體驗(yàn)生命與思考人生的。
體驗(yàn)即本我反思與探索,體驗(yàn)蘊(yùn)含的是他面對(duì)人生終極價(jià)值關(guān)懷的問(wèn)題與痛苦追問(wèn)。人生經(jīng)歷曲折,然而音樂(lè)藝術(shù)家曾健受同一根本痛苦的驅(qū)迫而追尋著同一個(gè)大謎底,并窺見(jiàn)同一本真之境。體驗(yàn)是開(kāi)啟曾健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本我論之鑰匙,是音樂(lè)美學(xué)本我論之根基。體驗(yàn)關(guān)乎音樂(lè)家曾健人生之意義與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之意義。因此,我們將曾健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體驗(yàn)作為美學(xué)本我論之重要之維加以研究,并藉此追問(wèn)體驗(yàn)與生命、體驗(yàn)與音樂(lè)藝術(shù)、體驗(yàn)與意義、體驗(yàn)與世界之同一關(guān)系的問(wèn)題。無(wú)疑,此已構(gòu)成曾健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本我之軸心。
一、體驗(yàn)與生命:同構(gòu)同質(zhì)之共生性
體驗(yàn)作為曾健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本我論范疇,是筆者在此獨(dú)立使用之概念,其主要目的是考慮主體與對(duì)象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是體驗(yàn)者與其對(duì)象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主體全身心地進(jìn)入客體之中,客體也以全新之意義與主體構(gòu)成新的關(guān)系。此時(shí),無(wú)所謂客體也無(wú)所謂主體,主客體之此種活生生的關(guān)系成為體驗(yàn)之關(guān)鍵。對(duì)象對(duì)主體之意義不在于是否可認(rèn)之物,而在于對(duì)象上面凝聚了主體的客觀化了的生活與精神。對(duì)象的重要正在于其對(duì)主體有意義,這就使主客體關(guān)系成了“曾健個(gè)體自己的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世界”了。
體驗(yàn)關(guān)涉曾健的有限生命之超越與現(xiàn)實(shí)世界價(jià)值之探索。體驗(yàn)打開(kāi)了人類與曾健,曾健與世界之障礙,使曾健的當(dāng)下存在與人類歷史相遇。在體驗(yàn)過(guò)程中,個(gè)體絕非一個(gè)超然物外、面對(duì)客體的純粹“主體”,同樣,對(duì)象也非外在于個(gè)體之純?nèi)弧翱腕w”。處在體驗(yàn)之中的個(gè)體所體驗(yàn)到的是:我在世界中,世界也在我中。體驗(yàn)表明了有限生命世界關(guān)聯(lián)中之存在性,從而具有了本我之意義。
體驗(yàn)關(guān)乎人的生存方式,即人生詩(shī)意化問(wèn)題,深層體驗(yàn)總是關(guān)乎人本體屬性之命運(yùn)、搏斗與愛(ài)憎。體驗(yàn)就是曾健感性個(gè)體本身之規(guī)定性,就是要使自己直面人生之真,去解人生之謎。通過(guò)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體驗(yàn),去把握生命之價(jià)值,通過(guò)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dòng),去穿越世界晦暗不明之現(xiàn)象,揭示生命之超越性意義。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體驗(yàn)與生命之詩(shī)意化,有著非此不可之聯(lián)系。音樂(lè)審美藝術(shù)把心靈從現(xiàn)實(shí)之重負(fù)下解放出來(lái),激發(fā)起心靈對(duì)自身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通過(guò)音樂(lè)美學(xué)的詩(shī)意化媒介,從意志的關(guān)聯(lián)中提取出審美價(jià)值內(nèi)核,從而在此一現(xiàn)象世界中,詩(shī)意地創(chuàng)造出反映現(xiàn)實(shí)世界本質(zhì)的音樂(lè)藝術(shù)作品。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造擴(kuò)展了對(duì)創(chuàng)造者個(gè)體釋放之效果,以及個(gè)體世界體驗(yàn)之視界,從而滿足了個(gè)體者的內(nèi)在之精神需求:當(dāng)命運(yùn)以及個(gè)體自己的選擇,仍然將自己束縛在既定的世界秩序中時(shí),創(chuàng)造者的想象使個(gè)體自己臻達(dá)他永不能實(shí)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境界。音樂(lè)藝術(shù)開(kāi)啟了一個(gè)更高更強(qiáng)大的審美世界,展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審美遠(yuǎn)景。
現(xiàn)實(shí)世界不是曾健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它是由命運(yùn)帶來(lái)的直接性,由命運(yùn)、愛(ài)憎、遭際、誕生、重負(fù)、祝福、悲憫等組成,只有擔(dān)當(dāng)實(shí)名之歡樂(lè)與痛苦,才能深諳現(xiàn)實(shí)世界之謎,而音樂(lè)人生者必被人生音樂(lè)藝術(shù)所籠罩。體驗(yàn)與生命,在曾健本我論上具有一種同構(gòu)同質(zhì)之共生性。
了解一個(gè)音樂(lè)家的創(chuàng)作與個(gè)性,先得知其人,了解他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之大體過(guò)程與決定性因素。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說(shuō):“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其個(gè)性就是這“成心”之主要方面,它會(huì)極大地影響一個(gè)音樂(lè)家的生活態(tài)度、行事方式與創(chuàng)作特性。
曾健的個(gè)性如果用樹(shù)木來(lái)作比,那么就是說(shuō),他既有像春天的垂柳,婀娜披拂,給人一種柔和而溫順之感覺(jué),又有像秋天之國(guó)槐,堅(jiān)剛挺拔,望之森然,顯示出一種嚴(yán)正而凜然之氣象。
一個(gè)民族,只有擺脫了外在羈絆,并吸取人類文明之精粹,創(chuàng)造出自己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這個(gè)民族才能屹立在世界之巔;一個(gè)人,只有當(dāng)他成為人格獨(dú)立之人,精神自由之人,他才能成為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音樂(lè)家。在音樂(lè)藝術(shù)的精神王國(guó)里,音樂(lè)家就是自己靈魂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絕對(duì)主宰。
曾健出生于1936年的江西南康。自古以來(lái),南康就是溝通中原與南粵的必經(jīng)之地,商賈云集,人文薈萃。在童年與少年時(shí)代之人生境遇中,顯然埋藏著曾健的精神密碼,也微妙地影響著他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深度。所以,現(xiàn)實(shí)中的曾健,常常在微笑的表情中帶著凝重,使人隱約看見(jiàn)他童年生活留下之影子。1950年,曾健在部隊(duì)開(kāi)始了他的文藝工作。他說(shuō):“堅(jiān)守中國(guó)魂,講好中國(guó)故事,說(shuō)好中國(guó)話,樹(shù)立中國(guó)手風(fēng)琴學(xué)派,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抵制洋垃圾,不被異化、矮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是我終生的目標(biāo)!當(dāng)然更需要年輕人傳承下去,把這面大旗舉的高高的。共同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引自曾健微信聊天記錄,以下相同者不再注明。)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音樂(lè)言論,是一個(gè)自信的音樂(lè)家的音樂(lè)藝術(shù)言論。這是一個(gè)音樂(lè)家徹底擺脫了外在羈絆之后的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者的宣言。它顯示著曾健卓爾不群的個(gè)性與充分成熟的音樂(lè)意識(shí)。它表達(dá)著這樣的一種音樂(lè)美學(xué)認(rèn)知:一個(gè)民族,只有擺脫了外在羈絆,并吸取人類文明之精粹,創(chuàng)造出自己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這個(gè)民族才能屹立在世界之巔;一個(gè)人,只有當(dāng)他成為人格獨(dú)立之人,精神自由之人,他才能成為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音樂(lè)家。在音樂(lè)藝術(shù)的精神王國(guó)里,音樂(lè)家就是自己靈魂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絕對(duì)主宰。曾健拒絕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擾與控制,既拒絕過(guò)去舊的藝術(shù)教條之束縛,也拒絕現(xiàn)在新的“現(xiàn)代主義”的拜物教束縛。他揚(yáng)棄盲目沖動(dòng)之意志,而使具有歷史性(即體驗(yàn)著的)生命獲得了本我論之優(yōu)先地位。生命不僅僅是生物進(jìn)化中之一環(huán),生物性之規(guī)定不能解放出人的生命之謎。生命非他,是有限個(gè)體從生至死之體驗(yàn)之總和,是以身體之,以心驗(yàn)之,以思悟之的解謎過(guò)程。所以說(shuō),不是任何一個(gè)音樂(lè)家都有曾健這樣的強(qiáng)大性格,都能像他這樣,敢于以“獨(dú)立”之姿態(tài),對(duì)音樂(lè)創(chuàng)造提出挑戰(zhàn),敢于以自信之態(tài)度,與一個(gè)時(shí)代流行的音樂(lè)風(fēng)氣相抗衡。
如果說(shuō),我們的藝術(shù)曾經(jīng)被外在力量之束縛與壓抑喪失了活潑的個(gè)性與內(nèi)在的激情的話,那么,曾健就是掙脫了此種束縛與壓抑,顯示出了一種強(qiáng)大的個(gè)性力量與藝術(shù)生命之能量。本我論問(wèn)題即曾健生命底蘊(yùn)之問(wèn)題,生命底蘊(yùn)問(wèn)題即曾健體驗(yàn)之向度問(wèn)題。他與世界迎面走去,因?yàn)槭澜缡撬氖澜纾凰忉屢魳?lè)文本意義,因?yàn)樗且魳?lè)意義之給出者;他了解他人之表現(xiàn),因?yàn)樗约壕褪且粋€(gè)深切的表達(dá)者。感性個(gè)性個(gè)體之總體世界構(gòu)成了他個(gè)體之生命世界。在此意義上,曾健的生命體驗(yàn)即意味著超越有限性之僵硬界面之全新過(guò)程。
因此,曾健非同凡響的音樂(lè)“宣言”,使人聯(lián)想到普希金的那個(gè)振聾發(fā)聵的藝術(shù)宣言。曾健致力于讓音樂(lè)“堅(jiān)持中國(guó)魂,講好中國(guó)故事,樹(shù)立中國(guó)手風(fēng)琴學(xué)派”,并視為自己“終生奮斗之目標(biāo)”。普希金則認(rèn)為,詩(shī)人自己就是藝術(shù)世界的最高主宰。普希金在《致詩(shī)人》中說(shuō):“你是帝王:你要獨(dú)立生活下去/你要隨著自由的心靈的引導(dǎo),沿著自由之路奔向前方/致力于結(jié)成那可愛(ài)的思想的果實(shí),不要為你高貴的功績(jī)索取任何褒賞/它們都存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法官/你善于比誰(shuí)都嚴(yán)格地評(píng)價(jià)你的勞作/嚴(yán)厲的藝術(shù)家啊,你對(duì)它們滿意嗎?”(沈念駒、吳笛主編:《普希金全集》第2卷.抒情詩(shī),烏蘭汗、丘琴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50頁(yè)。)在普希金看來(lái),詩(shī)人自己就是藝術(shù)世界的最高主宰,而獨(dú)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則意味著一切。也就是說(shuō),音樂(lè)藝術(shù)是一種高度自律的精神活動(dòng),是心靈翅羽最自由、最自在之飛翔。沒(méi)有此種最高意義上的自由與尊嚴(yán),任何藝術(shù)家都不會(huì)創(chuàng)作出偉大的作品。
然而,這樣的獨(dú)立而自由的音樂(lè)意識(shí),曾健終其一生,至少在他創(chuàng)作生涯之絕大部分時(shí)間里,殆未嘗有一念及之。曾健的主要音樂(lè)藝術(shù)理念,庶幾都是從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來(lái)。曾健既是音樂(lè)的設(shè)計(jì)師,也是音樂(lè)創(chuàng)造的踐行者。曾健既是音樂(lè)藝術(shù)戰(zhàn)場(chǎng)上的拿破侖,也是士兵,是一個(gè)像拿破侖身后的名叫阿爾芒與巴蒂斯特的法國(guó)士兵一樣的士兵。曾健的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造是服從自我意志的創(chuàng)造,是有“我”的創(chuàng)造,是“我”的情感、思想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經(jīng)驗(yàn)滲透到整個(gè)作品中的創(chuàng)造。很多時(shí)候,在對(duì)應(yīng)性很強(qiáng)的音樂(lè)作品中,音樂(lè)造型就是作者的精神之子,就是他的人格鏡像與精神投影。20世紀(jì)70年代,曾健改編創(chuàng)作的手風(fēng)琴獨(dú)奏曲《我為祖國(guó)守大橋》,就體現(xiàn)著他自己的態(tài)度與性格。這首著名的經(jīng)典音樂(lè)作品,是人類普遍性大于時(shí)代特殊性的創(chuàng)作,是開(kāi)放的、包容的、多樣化表達(dá)的創(chuàng)作,也是指向普遍性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因而是個(gè)性大于整體化的創(chuàng)作,是個(gè)性與普遍性相互融合的創(chuàng)作。在曾健的這首獨(dú)特性很強(qiáng)的獨(dú)奏音樂(lè)作品里,作曲家的造型是大于至少是等于時(shí)代的,而精神視野則是高于時(shí)代的。在這首音樂(lè)作品里,曾健的視野和思想,是超越了時(shí)代之精神邊界,也是高于時(shí)代的平均值的,甚至顯示出一種超越性與超前性。因此,曾健將音樂(lè)藝術(shù)的邊界,拓展到了普遍性的人性之領(lǐng)域,又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切實(shí)地提升到了現(xiàn)實(shí)主義與藝術(shù)之高度。曾健賦予此作品以巨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任何一個(gè)演奏者,只要他有正常的音樂(lè)藝術(shù)的體驗(yàn)?zāi)芰Γ灰释私庹鎸?shí)的士兵和真實(shí)的士兵生活,他就會(huì)對(duì)《我為祖國(guó)守大橋》這部作品的曲作者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興趣,就會(huì)對(duì)這首作品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演奏沖動(dòng)。就此而言,流傳近半個(gè)世紀(jì)的此首獨(dú)奏曲,將會(huì)在人類音樂(lè)歷史的長(zhǎng)河里,吸引無(wú)數(shù)的演奏者,并贏得他們的信任、認(rèn)同與高度評(píng)價(jià)。可見(jiàn),曾健的音樂(lè)藝術(shù)與人類的關(guān)系是多么的緊密,以致于我們認(rèn)為音樂(lè)藝術(shù)本體與人的本體同構(gòu),音樂(lè)藝術(shù)就是人的生存世界。由曾健這首經(jīng)典音樂(lè)作品的創(chuàng)造與流傳,可以欣慰地告訴我們,那就是:音樂(lè)藝術(shù)是由人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并為了人而存在,音樂(lè)藝術(shù)的中心是人的生命形式,音樂(lè)藝術(shù)是人超越生命有限性而獲得無(wú)限性之中介。人通過(guò)音樂(lè)藝術(shù)體驗(yàn)為中介向無(wú)限超越之時(shí),時(shí)間之流向即發(fā)生了變化。在體驗(yàn)之中的時(shí)間,不再像日常生活時(shí)間是由過(guò)去走向未來(lái),而是以未來(lái)朗照現(xiàn)在。人攜帶生命之全部過(guò)去與現(xiàn)在進(jìn)入未來(lái)之中,并以未來(lái)消融全部時(shí)間,根據(jù)自我內(nèi)心所體驗(yàn)過(guò)的內(nèi)在時(shí)間重新構(gòu)筑出一個(gè)新的時(shí)空境界。此種通過(guò)音樂(lè)藝術(shù)審美所把握到的無(wú)限境界,把感性個(gè)體引出有限性之規(guī)定與局限性之存在,使之與大同覿面。這是一個(gè)絕對(duì)超越時(shí)間的世界,剎那凝聚為永恒。曾健的奧秘即在于此達(dá)到時(shí)間之超越、頓悟的同一心境。而真正的音樂(lè)、真正的藝術(shù)就能將人導(dǎo)入此一全新之超驗(yàn)世界。
二、體驗(yàn)與人格:主客體之互動(dòng)性
每一個(gè)音樂(lè)藝術(shù)家都有自己喜愛(ài)的音樂(lè)家。這些最受喜愛(ài)的音樂(lè)藝術(shù)家,通常就是對(duì)他們的創(chuàng)作影響最大的人。曾健最喜愛(ài)的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中外音樂(lè)家,中國(guó)的音樂(lè)家有蕭友梅、王光祁、華彥鈞、劉天華、黎錦暉、張寒輝、黃自、冼星海、聶耳、馬可、鄭律成、賀綠汀、丁善德等;外國(guó)音樂(lè)家?guī)缀跄依藲W美所有古典音樂(lè)藝術(shù)家,諸如貝多芬、莫扎特、海頓、巴赫、勃拉姆斯、大小約翰·施特勞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德彪西等,以及現(xiàn)當(dāng)代的一些中外音樂(lè)藝術(shù)家,不論地域性或空間距離,就音樂(lè)藝術(shù)的美學(xué)精神講,它們是沒(méi)有距離的,他們都具有崇高的音樂(lè)精神和嚴(yán)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從某種程度上講,曾健幫助國(guó)人音樂(lè)愛(ài)好者克服了音樂(lè)藝術(shù)上的某種神秘感、距離感與自卑感。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人來(lái)講,曾健意味著光榮和驕傲,也意味著信心和力量:咱們也有了一個(gè)曾健。在曾健七十多年來(lái)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時(shí)間里,他既屬于自己的時(shí)代,也屬于個(gè)人與自己的故鄉(xiāng)。當(dāng)然,健全而自然的個(gè)性化創(chuàng)作,到改革開(kāi)放以后才使他獲得了自己的生長(zhǎng)契機(jī)與生存空間。
一個(gè)音樂(lè)家崇拜和熱愛(ài)古今中外的大師,就會(huì)接受他們的影響。中外歷代大音樂(lè)家對(duì)曾健的影響,毫無(wú)疑問(wèn)是巨大的,這從他改編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音樂(lè)演奏作品即可見(jiàn)出。可以說(shuō),音樂(lè)前賢對(duì)曾健的“精神素質(zhì)”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是音樂(lè)家的人格修養(yǎng)與自我人格,一個(gè)是音樂(lè)藝術(shù)修養(yǎng)與創(chuàng)作技巧。對(duì)音樂(lè)創(chuàng)作來(lái)講,音樂(lè)家的人格有著根本性和決定性的意義。人格境界之高下,決定了其創(chuàng)作境界之高下。因?yàn)椋烁褚馕吨煽康姆较蚋校馕吨∪膫惱砭瘢馕吨己玫纳茞好栏校踔烈馕吨耪拿缹W(xué)情趣。自古及今,沒(méi)有一首經(jīng)典的音樂(lè)篇章,沒(méi)有一部偉大的音樂(lè)史詩(shī)作品,是人格卑劣的音樂(lè)家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就人格修養(yǎng)與精神境界來(lái)看,曾健實(shí)實(shí)在在是一個(gè)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當(dāng)代音樂(lè)大家。他在部隊(duì)從事文化藝術(shù)工作七十余年,他的業(yè)績(jī)被編入1988年由鄧小平親自題字的最具權(quán)威性、代表性的《中國(guó)音樂(lè)家名錄》一書(shū)中。1997年,第九期 《中華手風(fēng)琴之最》中說(shuō),曾健是我國(guó)手風(fēng)琴界“資深、業(yè)績(jī)突出者”;曾健是“我國(guó)從事手風(fēng)琴專職演奏時(shí)間最長(zhǎng)(47年)、年齡最大(60歲)、演出場(chǎng)次最多(約4600多場(chǎng))”的著名音樂(lè)家;曾健改編和創(chuàng)作了大量手風(fēng)琴演奏音樂(lè)作品,其中《我為祖國(guó)守大橋》《吹起蘆笙跳起舞》《飛速前進(jìn)》《歡迎叔叔凱旋歸》等已成為國(guó)內(nèi)外業(yè)界經(jīng)典作品。他自1996年60壽辰,開(kāi)始用作曲軟件在電腦上撰寫(xiě)了三百余首音樂(lè)作品。這些作品,滲透了他70余載的軍旅生活體驗(yàn),此乃真正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唐李商隱詩(shī)句)啊!其中,為少年兒童也編創(chuàng)了大量的音樂(lè)作品,電子琴獨(dú)奏曲《醒獅之舞》曾在全國(guó)獲得金獎(jiǎng),在我國(guó)少兒藝術(shù)教育事業(yè)中作出卓著貢獻(xiàn)。這是音樂(lè)家曾健最具智慧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這些輝煌藝術(shù)成果,并不是哪一個(gè)音樂(lè)家都可以做得出的。曾健還舉辦了各種形式不同的青少年手風(fēng)琴音樂(lè)培訓(xùn)班,親自為學(xué)員上課與演奏示范,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他曾說(shuō):“藝術(shù)的傳授首先是做人,要梳理正確的人生觀。遵循前人教誨,在我的演奏、創(chuàng)作、教學(xué)工作中,著力以人為本:演奏接地氣,創(chuàng)作雅俗共賞,教學(xué)先教做人。以此鞭策自己,拿起手風(fēng)琴這個(gè)文藝武器,作為全身心投入到為人民服務(wù)的動(dòng)力,這是責(zé)無(wú)旁貸的使命!”這就是說(shuō),追求生命意義之明晰性必然遇到一個(gè)困境:音樂(lè)家必須思考別人無(wú)法思考的東西,即為了意義,他必須對(duì)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種界限之兩邊皆加以思考。曾健也意識(shí)到了此種困境。故他不談此種劃界,而是讓音樂(lè)藝術(shù)本身來(lái)“說(shuō)話”,以音樂(lè)的審美造型來(lái)表達(dá)此種“界限”。這就是體驗(yàn)的一種指向意義之活動(dòng),堅(jiān)持體驗(yàn)中主體客體相互融合之立場(chǎng),指向主客體互動(dòng)所產(chǎn)生之意義。此種意義絕不是外在于體驗(yàn)活動(dòng)之超驗(yàn)之物,而是主體在體驗(yàn)中通過(guò)對(duì)主客體關(guān)系之自覺(jué)與自由之呈現(xiàn),在主體總體精神活動(dòng)中建構(gòu)起來(lái)的。主體在音樂(lè)造型(對(duì)象)之全面占有之中,將造型加以生命化,從而保證其具有完滿的充實(shí)性,并反證主體給出意義之深度。可以確認(rèn),體驗(yàn)主體確立自身意義之世界,是獲得主體性地位之保證。這就是曾健的音樂(lè)思想,也是他觸及情操、靈魂體驗(yàn)的音樂(lè)藝術(shù)世界。此種體驗(yàn)是曾健將自己的知、情、意與音樂(lè)世界及其命運(yùn)之遭際融為一體,在主客體互動(dòng)中返身透視自己精神之內(nèi)海。這是曾健內(nèi)在音樂(lè)審美意義之體驗(yàn),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種生命體驗(yàn)。
音樂(lè)是一種和榮譽(yù)關(guān)系密切的事業(yè)。追求榮譽(yù)是創(chuàng)造之動(dòng)力之一。完全沒(méi)有榮譽(yù)感的人不可能持久地?zé)釔?ài)藝術(shù)創(chuàng)作。但是,追求真正的榮譽(yù)與追求虛名浮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曾健雖然在國(guó)際國(guó)內(nèi)獲得過(guò)數(shù)十次的各類音樂(lè)藝術(shù)大獎(jiǎng),但他的“成功”與“成名”,并不在言說(shuō)中,而是重在創(chuàng)造實(shí)踐中。無(wú)論怎樣說(shuō),只要?jiǎng)?chuàng)作出劃時(shí)代的經(jīng)典作品,那就一切均在不言中了。如他的手風(fēng)琴獨(dú)奏曲《我為祖國(guó)守大橋》,被世界音樂(lè)界權(quán)威人士評(píng)價(jià)是“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是中國(guó)手風(fēng)琴一張閃亮的名片!具有里程碑意義與劃時(shí)代意義的經(jīng)典作品”。在國(guó)際手風(fēng)琴大賽現(xiàn)場(chǎng)演奏時(shí),世界一流的手風(fēng)琴大師們激動(dòng)地舉起手臂高呼:“中國(guó)!中國(guó)。”這些權(quán)威人士發(fā)出的贊譽(yù)之聲,此皆實(shí)話,絕非虛語(yǔ)。曾健對(duì)于榮譽(yù)與經(jīng)典的理解,是他生命體驗(yàn)和美學(xué)表達(dá)的基本方法,他不是借助邏輯推理,而是由個(gè)體生命體驗(yàn)進(jìn)入藝術(shù)生命之中,讓整體生命意識(shí)融合在一起。他與生命相關(guān)的音樂(lè)藝術(shù)現(xiàn)象,皆是借助于音樂(lè)的節(jié)奏、符號(hào)、語(yǔ)言滲透在一起的生命表達(dá)。因此,理解榮譽(yù)與經(jīng)典之傳達(dá)就是理解了生命,為了達(dá)到此種深層理解,曾健是通過(guò)他的音樂(lè)符號(hào)與音樂(lè)語(yǔ)言中介而感受其所表達(dá)的生命本體。是的,任何一位踏實(shí)的音樂(lè)家,尤其是集作曲家、演奏家、音樂(lè)教育家于一身的音樂(lè)家,皆不能心浮氣躁,急于求成,而是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視為一個(gè)漫長(zhǎng)而艱辛的生命體驗(yàn)過(guò)程。雖然曾健的“七十年一個(gè)單元”,似乎有點(diǎn)過(guò)長(zhǎng),但將他的創(chuàng)作豐收期設(shè)定在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應(yīng)該是符合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生命成熟與成功規(guī)律的。
音樂(lè)是一種和榮譽(yù)關(guān)系密切的事業(yè)。追求榮譽(yù)是創(chuàng)造之動(dòng)力之一。完全沒(méi)有榮譽(yù)感的人不可能持久地?zé)釔?ài)藝術(shù)創(chuàng)作。但是,追求真正的榮譽(yù)與追求虛名浮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在人格修養(yǎng)與倫理精神上,曾健受到歷代前賢大師之巨大影響。接受影響之程度,決定于對(duì)影響者認(rèn)知之深度。曾健有自己的心靈世界,有自己的體驗(yàn)歷程。體驗(yàn)、理解與傳承乃是進(jìn)入人類精神世界之過(guò)程,音樂(lè)歷史也由通過(guò)體驗(yàn)、理解、傳承才成為自己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之一部分。如果沒(méi)有理解,便不能構(gòu)成音樂(lè)的歷史,精神世界便是平庸與荒蕪的,就談不上生命之可能性,表達(dá)與意義都將不復(fù)存在。因此,體驗(yàn)與理解活動(dòng)是曾健音樂(lè)審美活動(dòng)質(zhì)的規(guī)定性。他的音樂(lè)藝術(shù)作品作為審美對(duì)象,集中體現(xiàn)了人類體驗(yàn)及其理解的本質(zhì)。他對(duì)中外歷代前賢的人格與德性有著深刻的理解。他曾在《敬幕孔子的音樂(lè)思想》一文中說(shu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孔子的音樂(lè)觀點(diǎn)有許多論述,如:‘移風(fēng)易俗莫善于樂(lè)’,是指社會(huì)風(fēng)氣的改變與人們心靈的凈化,在此方面,什么東西都比不上音樂(lè)。圣人的音樂(lè)美學(xué)觀,在歷史長(zhǎng)河中閃爍著耀眼熾熱的智慧與光芒。讓人敬佩與仰慕!孔子是從道德品格層面上來(lái)論述,印證著音樂(lè)對(duì)社會(huì)的推動(dòng)發(fā)展所起的巨大作用。這是一位真真確確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國(guó)人感到無(wú)比驕傲與自豪。”曾健對(duì)這些貼近音樂(lè)人格和精神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揭示是深刻的。亦由此才使他的體驗(yàn)與音樂(lè)藝術(shù)作品得以流傳與延展,使作品具有了普遍性意義,使精神世界成為具有相關(guān)性和互通性之統(tǒng)一體,使音樂(lè)藝術(shù)史之審美闡釋成為現(xiàn)實(shí)。為了音樂(lè)創(chuàng)作,為了熟悉所描繪的環(huán)境與音樂(lè)人物造型,他深入部隊(duì)基層的戰(zhàn)士生活中,像普通戰(zhàn)士一樣為“祖國(guó)守著大橋”,盱衡九州,唯此一人耳。
曾健的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一種面向外部世界的創(chuàng)作。他將音樂(lè)藝術(shù)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集中到自己身上。曾健的審美意識(shí)與音樂(lè)藝術(shù)理念,已經(jīng)達(dá)到那種真正開(kāi)放和包容之境界,在他身上確確實(shí)實(shí)沒(méi)有半點(diǎn)自私自利、自怨自艾之弊。對(duì)于那些缺乏他者意識(shí)的“私有形態(tài)”之“消極創(chuàng)作”來(lái)講,曾健的音樂(lè)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確實(shí)具有指示正路之意義與補(bǔ)偏救弊之作用。任何藝術(shù)作品,均是作者情感、思想與人格之鏡像。即便在那些敘事性、甚至爵士音樂(lè)作品里,也有一個(gè)作者的形象融匯期間。曾健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他說(shuō):“音樂(lè)是正能量的傳遞,是情感的投射,是心靈的傾訴,是藝術(shù)的載體,是心靈的對(duì)話。是潛移默化的力量,是心靈的凈化,這是我70年來(lái)音樂(lè)生涯最重要的體驗(yàn)與總結(jié)。”這段話,從音樂(lè)創(chuàng)作之角度看,它無(wú)疑是深刻的。它揭示了這樣一個(gè)樸素的音樂(lè)藝術(shù)美學(xué)真理:音樂(lè)作品是作者的精神之樹(shù)結(jié)出的果實(shí);一切形式的創(chuàng)作,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著作者的靈魂。因此,曾健在接受音樂(lè)前賢的藝術(shù)觀點(diǎn)之同時(shí),他也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音樂(lè)家對(duì)自己的人格造型與靈魂的塑造問(wèn)題。他在自己內(nèi)心筑起了這樣一種自覺(jué)意識(shí):音樂(lè)創(chuàng)作上的一切均決定于音樂(lè)家自己的人格,他堅(jiān)持認(rèn)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豐碩成果,均是生命體驗(yàn)之結(jié)果,也是人生之感悟,是全部的生活積累與藝術(shù)的提煉。他曾很形象地比喻過(guò)自己的藝術(shù)人生,他說(shuō):“何謂人生?可以用四個(gè)字來(lái)概括:即琴、棋、書(shū)、畫(huà)。人生猶琴,是指音樂(lè)藝術(shù)的跌宕起伏,喜怒哀樂(lè);人生如棋,棋局難料,迎接挑戰(zhàn);人生似書(shū),字體有宋、楷、行、草;字猶人,是性格的寫(xiě)照;人生若畫(huà),一幅畫(huà)可以繽紛多彩,又可能是黑白顛倒;人生若行,走在旅途上,迎接艱辛,戰(zhàn)勝困難。”因此,離開(kāi)了音樂(lè)家的人生格調(diào),很多事情都根本無(wú)法說(shuō)清楚。所以,他在任何音樂(lè)場(chǎng)合,均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是心靈的凈化”這一理念。此一理念還告訴人們:音樂(lè)家創(chuàng)造音樂(lè)作品之同時(shí),也在不斷塑造著自己的形象——這個(gè)形象對(duì)時(shí)代來(lái)說(shuō),比他所創(chuàng)造的任何藝術(shù)典型都更具有意義:因?yàn)樵趪?guó)家將面臨需要大量有進(jìn)取心人的時(shí)代里,作曲家的的音樂(lè)造型是一個(gè)具體的、活生生的典型。音樂(lè)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種勞動(dòng),要求音樂(lè)家具備多方面的優(yōu)秀品質(zhì)。在塑造音樂(lè)藝術(shù)形象的過(guò)程中,同時(shí)也在塑造著自己的人格形象。曾健清楚音樂(lè)家最應(yīng)該具備的能力就是自省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自我審視的能力,此一點(diǎn),對(duì)于音樂(lè)家來(lái)說(shuō)是至關(guān)重要的。曾健的這些觀點(diǎn),包含著符合音樂(lè)藝術(shù)規(guī)律的真理性內(nèi)容。因?yàn)椋耙黄惨晦嗳艘讓?xiě),一生一世人難做”(曾健語(yǔ))。一個(gè)音樂(lè)家如果沒(méi)有健全的人格與高尚之精神,他就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優(yōu)秀的音樂(lè)形象;如果他沒(méi)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他就不能深刻地審視自己,也不能深刻地審視自己的音樂(lè)作品。在創(chuàng)作音樂(lè)作品的時(shí)候,音樂(lè)家如果意識(shí)不到自我之存在,將作品看作是一個(gè)與自己無(wú)關(guān)的他者的世界,那么,他就有可能喪失創(chuàng)作的責(zé)任感,就有可能隨隨便便地創(chuàng)作,就有可能對(duì)作品進(jìn)行話語(yǔ)歪曲。遇到接受者的不滿意與質(zhì)疑,他就會(huì)不停地辯解:這是音樂(lè)呀,是旋律需要那樣啊,與我無(wú)關(guān)嘛。然而,在曾健看來(lái),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作曲家之態(tài)度與意識(sh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反對(duì)那種完全排斥主觀態(tài)度的“零度”(羅蘭·巴特語(yǔ))創(chuàng)作。在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一個(gè)熱愛(ài)生活之人,絕不會(huì)是沒(méi)有態(tài)度之人,也不能滿足于把自己的態(tài)度隱藏起來(lái)。在曾健看來(lái),只有主體才能使整個(gè)體驗(yàn)活動(dòng)成為主體精神的意指活動(dòng),任何主客體意義之建構(gòu)或主體本我之反思活動(dòng),皆要建立在自我之澄明與自覺(jué)基點(diǎn)上,并在體驗(yàn)活動(dòng)中與自我保持認(rèn)同。主體是音樂(lè)審美體驗(yàn)活動(dòng)的承擔(dān)者及意義世界之稟有者。不同的意向行為方式將獲得不同的意義構(gòu)成,并在不同的意向行為主體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釋。在此,曾健是意向之發(fā)出者,正是在此種主體體驗(yàn)的意旨中,意義才得以呈現(xiàn)出來(lái)。是的,曾健體驗(yàn)的意向性是他永遠(yuǎn)處于主導(dǎo)地位,是在體驗(yàn)中被構(gòu)造的意義成為對(duì)他而言之意義,他依持著自己的本真信念,而成為世界意義之轉(zhuǎn)換者。因此,他堅(jiān)持認(rèn)為“音樂(lè)藝術(shù)是正能量的傳遞,是情感的投射,是心靈的傾訴,是審美藝術(shù)的載體,是心靈的對(duì)話”這一理念。在曾健的音樂(lè)作品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作曲家之存在,可以分明地看見(jiàn)作曲家自己的個(gè)性與價(jià)值觀。他所創(chuàng)造的自我造型,是一個(gè)高尚作曲家的造型。他嚴(yán)肅地生活,嚴(yán)肅地思考,嚴(yán)肅地創(chuàng)作。曾健與音樂(lè)前賢一樣,賦予音樂(lè)創(chuàng)作以神圣而莊嚴(yán)的性質(zhì)。音樂(lè)前賢對(duì)曾健的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人格境界方面,也見(jiàn)之于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和音樂(lè)技巧方面。曾健通過(guò)作品之方式——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進(jìn)行了具體的展現(xiàn),同時(shí),也通過(guò)言傳身教之方式,告訴音樂(lè)愛(ài)好者如何進(jìn)行音樂(lè)創(chuàng)作。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