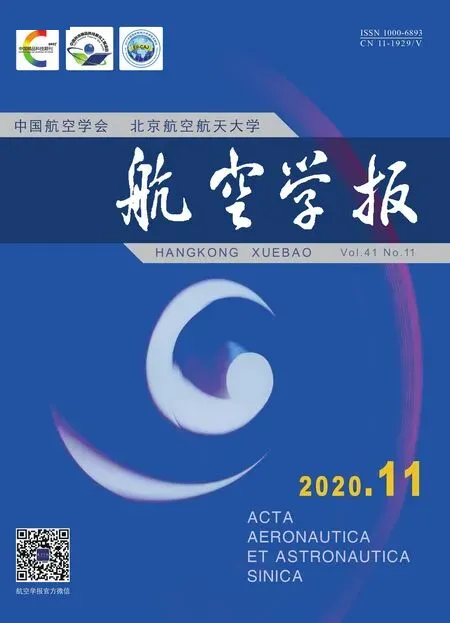高超聲速流動中噪聲與湍流度的關系
袁湘江,沙心國,時曉天,高軍
中國航天空氣動力技術研究院,北京 100074
邊界層轉捩與湍流問題是世紀難題,是一個工程應用領域共性的基礎科學問題[1]。自1883年英國的雷諾在圓管試驗中發現流動存在層流和湍流兩種流態至今,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研究者針對轉捩與湍流問題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依舊沒有很好地解決邊界層轉捩準確預測問題[2-7]。邊界層轉捩是一個初邊值問題,背景擾動通常歸于初值的范疇,但目前尚未查詢到理論上的描述報道。
湍流度是用于刻畫風洞中流場品質或來流擾動程度的物理量,對流動形態和性態都有重要影響。這一認識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球阻的測量實驗。人們發現在不同風洞所得到的臨界雷諾數(即球阻系數突然下降時刻的雷諾數),明顯受不同風洞中氣流擾動強度的影響。于是定義流體運動的脈動速度平方做時間平均后的均方根為湍流度,并將其作為衡量風洞中流動擾動程度或流場品質的一個重要參數。然而,真正認識到湍流度是影響邊界層流態的關鍵因素,則要歸功于穩定性理論的驗證試驗。Tollmien[8]和Schlichting[9]從理論上預測了流動失穩是由于流場中的小擾動激發了具有選擇性的、幅值呈指數增長的不穩定波動(T-S波)。但其后十多年并沒有得到試驗證實。事實上,這期間有不少人試圖驗證這一理論預測,比較著名的有Dryden[10]的工作,他使用熱線風速儀,沿空間坐標和時間序列,仔細測量了大量平板邊界層中的速度分布,但未能發現理論預測的T-S波。直到20世紀40年代, Schubauer和Skramstad[11]建造一個特殊風洞,將風洞的湍流度從1%~3%降低到0.02%,在這個風洞中的流動轉捩試驗,成功驗證了理論預測的不穩定波存在;同時,證實了從失穩點到轉捩點之間的距離,除了與不穩定擾動波的幅值增長率相關外,湍流度大小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另外,還發現早期試驗中未能探測到T-S波的原因是:1%的湍流度使得流動轉捩直接由流場中的擾動引起,換句話說,湍流度不僅可以左右失穩到轉捩的距離,甚至可改變轉捩的途徑[12]。
近年來,隨著高超聲速飛行器的發展,高超聲速邊界層轉捩已經成為制約高超聲速技術發展的瓶頸問題之一[13-15],Bertin和Cummings[16]指出在過去的50年中,雖然針對高超聲速邊界層轉捩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沒有獲得一個可以準確預測不同飛行條件下邊界層轉捩位置的半經驗模型。Bushnell[17]評價人們在預測高超聲速(甚至是超聲速)邊界層轉捩中就沒有成功過。Schneider[18]統計發現飛行試驗和地面風洞試驗中邊界層轉捩雷諾數的分布類似,但數據散度非常大,甚至能夠相差一個數量級。造成這種飛行試驗和地面風洞試驗轉捩雷諾數顯著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來流擾動。
在超/高超聲速領域,當涉及到來流擾動時幾乎不再使用湍流度,取而代之的是來流噪聲,衡量來流流場品質的指標變成了來流噪聲。Estorf[19]、Pate[20]以及Maslov[21]等針對來流噪聲與轉捩雷諾數的關系,以及噪聲對邊界層感受性的影響開展了大量研究。風洞來流流場品質評價指標改變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測量技術,受熱線強度問題、測量頻率范圍問題和響應關系不明確問題影響,常用于亞聲速風洞湍流度測量的熱線方法,在超/高超聲速風洞自由來流擾動測量中的應用受到很大限制[22]。高頻脈動壓力傳感器技術直接導致了高超聲速風洞流場脈動信息測量方法的重大改變。在其成熟前,熱線技術是主要的測量手段[23-24]。隨著其不斷成熟,利用該技術測量風洞來流總壓/靜壓脈動已成為高超聲速風洞來流擾動測量的主流方法[25-27]。熱線和脈動壓力測量均為接觸式測量技術,無法獲得超/高超聲速自由來流擾動的準確信息。近年發展的非介入式光學測量方法,很可能成為未來解決超/高超聲速風洞自由來流湍流度測量問題的途徑[28-30]。不可否認,在可壓縮流動中,自由來流湍流度測量比較困難。難道僅僅因為測量困難,就可以用風洞噪聲來替代湍流度嗎? Laufer[31]通過試驗給出了解釋,Laufer的試驗顯示當風洞自由來流馬赫數小于2.5時,穩壓段的湍流度對邊界層轉捩雷諾數有較大影響;但當自由來流馬赫數大于2.5后,穩壓段的湍流度對邊界層轉捩雷諾數并無影響。通過熱線測量分析,Laufer認為來流馬赫數大于2.5 時,Laval噴管湍流邊界層的輻射噪聲成為風洞來流擾動的主要來源。這個事實說明噪聲與湍流度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風洞噪聲是通過改變風洞來流擾動,進而影響轉捩雷諾數。并且根據Laufer試驗結果,當風洞來流達到高超聲速后,來流擾動的80%以上來自噪聲。由此可見,利用高超聲速風洞試驗研究轉捩時,強調噪聲是有試驗根據的。但這個事實有沒有理論依據,能不能從理論上揭示噪聲與湍流度的關系迄今尚未見相關理論研究報道。
長期的研究已經明確,在不考慮模型因素時,流場中擾動是造成風洞模擬轉捩現象與實際飛行環境轉捩現象不符的主要原因,而湍流度/噪聲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它不僅影響風洞試驗的轉捩位置、轉捩形態,甚至改變了轉捩途徑,進而造成飛行器地面模擬的氣動性質和流動現象,與實際飛行狀態存在差異。近年來的工程實踐說明,由于缺少風洞來流條件對轉捩影響的理論研究成果,難以建立令人信服的邊界層轉捩地面模擬天地一致性關系。事實上,目前高超聲速風洞的轉捩試驗結果,還遠不能滿足飛行器設計需求。而建立天地相關性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必須準確掌握風洞流場的擾動特性,但對于高超聲速風洞而言,來流湍流度的測量非常困難。Laufer的工作表明,高超聲速風洞來流擾動的絕大部分源自噪聲,而噪聲的測量技術相對成熟,因此,分析噪聲與湍流度的內在聯系,建立起它們之間的理論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Laufer的工作表明高超聲速風洞中流場的擾動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聲致擾動與非聲致擾動。本文首先圍繞聲致擾動機理,以及聲擾動與聲致速度擾動的關系開展研究。為揭示噪聲與湍流度的關系,理論分析了流場中聲擾動的特性,并探討了聲擾動與聲致速度擾動的內在聯系,建立了聲擾動與聲致湍流度的關系。另外,為了更全面了解速度擾動的影響因素,也討論并建立了非聲擾動與非聲致湍流度的關系。
1 有關噪聲的若干定義

(1)
(2)
(3)
(4)
2 理想均勻流體中的擾動波與湍流度
2.1 理想均勻流場的擾動波系
靜止空氣中聲波的傳播過程遵循聲波方程,運動流體中聲波傳播要滿足流體動力學方程。由于在空氣中傳播的聲波是縱波,又是典型的雙曲波。因此,研究流體中的聲波只需考慮描述流場雙曲波系的系統,梳理清楚聲波的特性。簡單起見,假定流體運動過程是絕熱、等熵,并且流體是無黏(或黏性可以忽略)的。描述這種氣體的動力學方程組可寫為
(5)
(6)
(7)

以U、V、W、p、ρ分別表示空間任意一點上3個方向的時間平均速度分量以及該點的平均壓力和密度。流場中引入小擾動,用u、v、w、p′、ρ′分別表示上述空間點上的3個方向瞬時的擾動速度分量、擾動壓力和擾動密度,且滿足小擾動假設,即擾動量與相應平均量相比都是小量。則瞬時的流動參量可表示為

(8)

(9)
(10)
(11)
(12)
(13)
設擾動具有行進波的形式,且α、β、γ分別代表x、y、z3個方向的波數,ω為頻率。基于超聲速流動中小擾動沿馬赫波傳播的事實,假設該流場中小擾動波為近似平面波,令[u1,v1,w1,p1,ρ1]分別表示小擾動量[u,v,w,p′,ρ′]的振幅,則
[u,v,w,p′,ρ′]=[u1,v1,w1,p1,ρ1]ei(αx+βy+γz-ω t)
(14)
將式(14)分別代入式(9)~式(13),利用等熵關系和完全氣體假設,易得擾動方程組:

(15)
式中:c為聲速,要使方程組(15)有非零解,根據線性方程組理論知,其充要條件是其系數矩陣不滿秩,即其系數行列式為零。若令上述系數矩陣的行列式為零,則有
(αU+βV+γW-ω)3[(αU+βV+γW-ω)2-
c2(α2+β2+γ2)]=0
(16)
方程(16)存在兩類解,第1類為3個重根解,即
αU+βV+γW-ω=0
(17)
第2類為

(18)
給出兩個解,即
(19)
(20)

(21)
由式(21)和行進波的定義式(14)可知,這一類雙曲波傳播的特征之一是波的相速度等于平均流動在波傳播方向的投影。將式(17)代入式(15)中的3個動量方程后,一致得出
p1=0
(22)
將式(17)與式(22)代入式(15)中的連續方程,則得到
αu1+βv1+γw1=0
(23)
通過上述推導可知,這類雙曲波還有兩個重要的物理特征,由式(23)可知這類波的傳播方向與流體微團的擾動運動方向垂直,即這類雙曲波是橫波;更重要的是式(22)說明這類波動不會引起壓力的變化,因此,這類波不可能是聲波,以下稱為非聲波。

(24)
(25)
由式(24)和式(25)可知,這一類雙曲波傳播的特征之一是波的相速度等于平均流動在波傳播方向的投影減去(加上)聲速,該特征與聲波的傳播特征相同。將式(24)和式(25)代入式(15)中的連續方程,得到
(26)
若將式(26)等號左邊的量看作擾動合速度的幅值,則與聲波的性質相符。同時由式(26)還可知,這類波動的擾動速度直接與擾動壓力成正比,即是縱波。由式(15)中的能量方程得
p1=c2ρ1
(27)
式(27)是典型的聲波方程,可見式(24)~式(27)定義的這類雙曲縱波是聲波。
2.2 湍流度的定義
采用2.1節中符號的定義,湍流度的定義為
(28)
式中:
或
3 聲波與湍流度的關系
由2.1節的討論可知,理想均勻流場中的擾動,可分為式(26)和式(27)表達的聲波擾動,以及式(22)和式(23)表達的非聲波擾動。考慮全文表達式銜接順暢、易讀和簡單,本節中表示擾動量的符號與2.1節相同,且意義不變。但由于本節主要探討聲波與聲致湍流度的關系,因此,表征擾動量的符號僅表示滿足式(26)和式(27)的聲致擾動量。
式(26)還可寫為

(29)
式(29)等號右端的正負號反映聲波導致的速度擾動,在平面波的假設下會形成兩個方向傳播的聲波,即與擾動速度同向和反向。聲波方程(27)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即以特定關聯形式的壓力擾動和密度擾動形成聲波。聲波傳播本質上是某些方向上的流體依次按照某種規律出現膨脹與壓縮現象的過程,當壓力增強時,會驅動流體微團向著某一方向運動,同時導致同一方向的密度增加,進而產生壓縮擾動和速度擾動;而在另一個方向上,物理現象正好相反,則發生膨脹擾動和反向的速度擾動。因此,式(29)的正負號反映了流體微團的單方向運動,對應于聲波的兩個方向傳播。
由于空氣中的聲波是典型的縱波,即聲波的傳播方向與流體微團的運動方向完全平行。對于與擾動速度方向一致的一支聲波,有
(30)
再考慮到上述聲波的傳播特性,于是式(29)可以寫為

(31)
即

(32)
由于擾動速度(u,v,w)與擾動壓力p′具有相同的行進波形式,式(32)等號兩邊同時乘以(ei(αx+βy+γz-ω t))2,然后積分,再取極限后,可以得到
(33)
根據湍流度的定義,式(28)整理為
(34)
式中:
(35)
其中:Ma表示來流馬赫數。
若考慮式(2)和式(3),式(34)還可以寫為
(36)
在式(36)的推導過程中用到2≈100.3的近似。式(36)進一步整理可得
(37)
4 非聲波與非聲致湍流度的關系
由式(22)和式(23)可知,這類波擾動壓力為零,并且是橫波,屬于非聲波(事實上這類波是流場中的渦波和熵波),本節主要探討非聲波與非聲致湍流度的關系。
式(23)等號左端項可寫為
αu1+βv1+γw1=(u1,v1,w1)·(α,β,γ)
(38)
對式(38)等號右端乘(u1,v1,w1),再結合式(23)得
[(u1,v1,w1)·(α,β,γ)](u1,v1,w1)=0
(39)
根據矢量運算規則:A×(B×C)=B(A·C)-C(A·B),式(39)可轉換為
(u1,v1,w1)×[(α,β,γ)×(u1,v1,w1)]-
(α,β,γ)[(u1,v1,w1)·(u1,v1,w1)]=0
或
[(u1,v1,w1)×(Ωx,Ωy,Ωz)]=
(40)

iΩxei(αx+βy+γz-ω t)
iΩyei(αx+βy+γz-ω t)
iΩzei(αx+βy+γz-ω t)
式中:Ωx=βw1-γv1;Ωy=γu1-αw1;Ωz=αv1-βu1。
再將式(40)兩邊同時左點積波矢(α,β,γ),則有
(α,β,γ)·[>(u1,v1,w1)×(Ωx,Ωy,Ωz)]=
(41)
依據矢量運算規則:A·(B×C)=C·(A×B),則式(41)可變換為
(Ωx,Ωy,Ωz)·[>(α,β,γ)×(u1,v1,w1)]=
(42)
或
(Ωx,Ωy,Ωz)·(Ωx,Ωy,Ωz)=
(43)
即
(44)

(45)
式中:Ωrms的定義為
其中:Ωxrms、Ωyrms、Ωzrms分別為Ωx、Ωy、Ωz的時間平均值。
根據湍流度的定義,式(45)可變換為
(46)
根據擾動旋度的定義可知,擾動旋度的強弱與流場均勻性密切相關。由式(37)和式(46)可知,高超聲速風洞中的湍流度一部分來自噪聲,一部分源于擾動旋度。由上述討論可知,對湍流度有貢獻的非聲致擾動只有渦擾動。
5 結 論
通過理論分析Euler系統中的雙曲波系,獲得了聲波與非聲波的傳播特點。首先,基于聲波的特征關系和噪聲強度的定義,推導了流場噪聲的聲壓級與聲致湍流度的關系;其次,基于非聲波的特征關系和擾動旋度的定義,推導了流場擾動旋度與非聲致湍流度的關系。根據上述討論,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 高超聲速流場的湍流度按照產生機制可分為兩類:聲致湍流度和非聲致湍流度,聲波與非聲波都可導致流場中的速度擾動,其中聲致擾動速度的運動方向與聲波的傳播方向平行,非聲致擾動速度的運動方向與非聲波的傳播方向垂直。
2) 聲致擾動與非聲致擾動都對流場中的湍流度有貢獻,聲致湍流度與噪聲強度相關,非聲致湍流度與擾動旋度相關。
3) 聲致湍流度與馬赫數直接相關,對于特定的馬赫數,流場中的Cp rms、SPL和NL與湍流度都成正相關關系。
4) 非聲致湍流度只與擾動旋度成正相關關系,即只有渦擾動對湍流度有貢獻,與馬赫數無直接關系。
致 謝
感謝李睿劬博士在公式推導過程中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