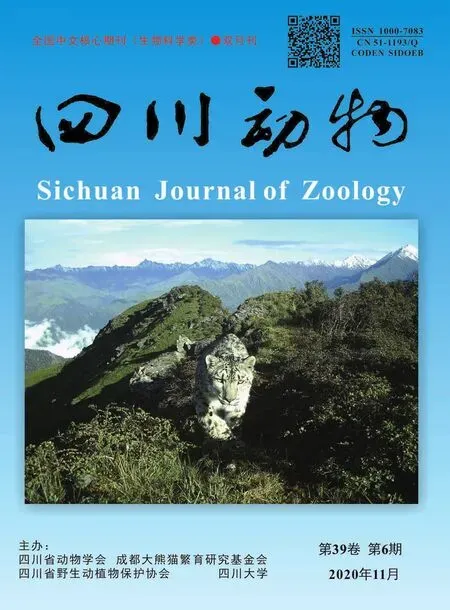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現(xiàn)狀探討
洪洋,張晉東,王玉君
(西華師范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四川南充637009)
雪豹Panthera uncia屬我國Ⅰ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是評價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重要指示物種,具有重要的保護和科研價值。雪豹主要分布在12個境內(nèi)有高山或高原的國家和地區(qū),如中國、阿富汗、不丹、印度等(馬鳴等,2013;唐卓等,2017)。
雪豹作為高海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維持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張榮等,2018)。然而,近幾十年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張使雪豹的棲息地面積急劇下降,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人豹沖突,部分地區(qū)牧民對雪豹的報復(fù)性捕殺愈演愈烈(Oli et al.,1994;Aryal et al.,2014a,2014b;劉浦江,韓海東,2015)。人類對雪豹的負面影響還表現(xiàn)在人類對雪豹食物的獵殺。相較于低海拔的肉食性動物,雪豹所能捕食的獵物種類較少,食物的豐富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雪豹的種群數(shù)量與空間分布(Oli,1993,1994;Casey,2018)。而過度的偷獵可能導(dǎo)致雪豹食物鏈的斷裂,威脅其生存。除去人為干擾,雪豹的生存同樣面臨著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Aryal et al.,2016)。目前全球氣溫逐漸升高,雪豹被迫往更高海拔的區(qū)域轉(zhuǎn)移,棲息地面積驟減,食物匱乏(Forrest et al.,2012;Pecl et al.,2017)。
基于上述原因,雪豹受到各國研究者的極大關(guān)注,并開展了一系列相關(guān)研究,以期能更好地保護雪豹。然而雪豹屬猛獸,警覺性高,主要棲息在高海拔且地形崎嶇的區(qū)域(Anwar et al.,2011),這給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的研究帶來極大的困難,導(dǎo)致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分散,缺乏系統(tǒng)性。本文對已有的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相關(guān)研究進行歸納與總結(jié),試圖了解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的研究現(xiàn)狀,同時分析當(dāng)前存在的問題,探討今后雪豹的研究方向,以期能為今后開展雪豹系統(tǒng)性的研究提供參考。
1 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方法概述
選擇正確的研究方法對研究工作的進行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目前雪豹的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方法大致可以整理為7種(表1)。

表1 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主要研究方法Table 1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research on Panthera unica
雪豹棲息地選擇與人為干擾的研究主要使用樣線法獲得雪豹與人類活動痕跡,以雪豹痕跡為中心建立10 m×10 m樣方,調(diào)查樣方內(nèi)的各種生境因子(徐峰等,2006a),同時結(jié)合半結(jié)構(gòu)訪談法(按照粗線條式的訪談提綱進行,訪談方式靈活多變的非正式訪談),獲取當(dāng)?shù)鼐用駥ρ┍膽B(tài)度,以及雪豹造成的傷害(Hussain,2000),以此達到了解雪豹如何進行棲息地選擇,并在其中找到緩解人豹沖突方法的研究目的。雪豹個體識別方法可分為2類,一是通過紅外相機照片,根據(jù)體表花紋特征進行識別(Jackson et al.,2006;馬鳴等,2006),二是通過采集雪豹糞便、毛發(fā)等樣品,利用相應(yīng)的DNA分析技術(shù)進行識別(Karmacharya et al.,2011)。雪豹種群數(shù)量分布的研究在個體識別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行統(tǒng)計,再結(jié)合標(biāo)志重捕分析方法(Janecka et al.,2008),即可獲得棲息地內(nèi)雪豹種群數(shù)量,整理之后便可明確全球范圍內(nèi)雪豹種群數(shù)量的分布情況。清楚了解雪豹的棲息地選擇情況以及種群數(shù)量等信息后,使用遙感監(jiān)測以及項圈跟蹤(Mccarthy et al.,2005)、紅外相機監(jiān)測(唐卓等,2017)等方法,即可對雪豹的活動與空間利用模式進行研究。雪豹食源組成的研究可通過糞便殘骸與糞便中的DNA進行鑒定(Anwar et al.,2011;陸琪等,2019),同時還可利用紅外相機等設(shè)備,通過雪豹食物的生物量消耗來進行鑒定(Oli,1994)。通過樣線法尋找雪豹糞便與毛發(fā)等樣品,獲得雪豹DNA后利用相應(yīng)的微觀技術(shù)(Karmacharya et al.,2011;周蕓蕓等,2014)可探究雪豹的遺傳多樣性。
當(dāng)前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以野外樣線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在不同的研究目的下使用相應(yīng)的實驗方法,且有多種選擇,但各種方法的使用相互重疊,設(shè)定的標(biāo)準(zhǔn)難以統(tǒng)一。為解決該問題,本文擬定了一條進行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系統(tǒng)研究的主要方法路徑,希望能為今后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系統(tǒng)性研究(實驗方法方面)提供參考(圖1)。

圖1 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系統(tǒng)研究方法路線Fig.1 Methodological road map of 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system research on Panthera unica
2 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成果概述
2.1 棲息地選擇
對雪豹棲息地選擇的研究表明,雪豹對棲息地植被類型的選擇傾向于灌叢與高山草甸,避開森林、荒漠;對生境平坦度(徐峰等,2006a)的選擇傾向于陡峭、崎嶇的區(qū)域,而避開平坦、開闊的區(qū)域(徐峰等,2005,2006b;Li et al.,2013)。雪豹在海拔2 000~4 500 m均有分布,隨季節(jié)的變化在不同海拔活動,當(dāng)處于2 000~3 000 m時,多選擇谷底;當(dāng)處于3 000~4 500 m時,多選擇山坡與山脊,且多利用陽坡而避開陰坡(廖炎發(fā),1985;喬麥菊等,2017)。由此可見,當(dāng)前雪豹棲息地選擇的研究暫未考慮雪豹對自然生境中植被的利用情況,如灌木的基徑、蓋度,草本的高度、蓋度等,明確雪豹對植被的利用情況,對于解釋雪豹捕食時的隱蔽行為有重要作用。
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雪豹與人類在生態(tài)位上的重疊不斷增加,二者沖突愈演愈烈(史曉昀等,2019)。面對人類活動的擴張,雪豹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選擇避讓,因此,解決人獸沖突不僅要明確雪豹對棲息地的生境選擇,還要明確人類對雪豹干擾的類型與強度。目前,棲息地中人類活動因子對雪豹影響的研究較少,僅涉及到人類報復(fù)性捕殺(Hussain,2000)、雪豹與家畜空間分布的重疊(史曉昀等,2019),而在分析與評估放牧、采藥、修建道路等人為活動帶來的影響,控制雪豹與人類的安全距離等方面的研究尚屬空白。研究者試圖通過相關(guān)保護政策來建立人類活動因子與自然生境因子之間的聯(lián)系,如提出一系列的激勵政策,減少人類負面干擾,改善棲息地自然生境條件,以緩解人與雪豹的沖突(Mishra et al.,2010;Li et al.,2013;Aryal et al.,2014a),以及通過雪豹的野外放歸,以維持相對穩(wěn)定的野外種群數(shù)量(Som&Kamal,2007;Jackson & Som,2009;Lovari et al.,2010)。
當(dāng)前雪豹棲息地研究主要以保護雪豹棲息環(huán)境為目的,人為干擾方面主要以如何減少與隔斷人為干擾為目的,兩者以相關(guān)保護政策(如沖突分析、損失鑒定、保險賠付等)為手段建立相關(guān)聯(lián)系,雖取得一定的保護成效,但并未觸及到緩解人豹沖突的核心,即如何減少雪豹與人類在生態(tài)位上的重疊,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yīng)著重探尋如何將二者進行緊密聯(lián)系,同時從雪豹生境選擇與人類干擾這2個導(dǎo)致沖突的源頭出發(fā),減少人與雪豹生態(tài)位重疊、緩解人豹沖突。
2.2 個體識別
個體識別在野生動物保護的研究中對于估測種群數(shù)量和研究動物行為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完善雪豹個體識別體系對于開展雪豹系統(tǒng)性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學(xué)者們利用多種方法開展雪豹的個體識別研究,如Riordan(1998)利用雪豹的足跡,使用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SOM)和貝葉斯方法,成功對雪豹個體進行識別;Jackson等(2006)通過正面、側(cè)面、傾斜面的相機配置,獲得不同角度的雪豹照片,并根據(jù)雪豹前肢、身體兩側(cè),以及尾巴背面的獨特花紋成功對2003年和2004年在印度拉達克赫米斯國家公園出現(xiàn)的雪豹進行個體識別;馬鳴等(2006)在國內(nèi)首次使用紅外相機技術(shù),并結(jié)合“雪后痕跡調(diào)查”的信息成功進行雪豹個體識別。2010年后雪豹個體識別中的宏觀手段逐漸減少,分子生物學(xué)手段逐漸增加,如Waits等(2010)從19只圈養(yǎng)雪豹中篩選出50個微衛(wèi)星位點,測定每個位點的多態(tài)性,選出10個多態(tài)性最高的微衛(wèi)星位點,以用于野生雪豹的個體識別;Karmacharya等(2011)利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也成功對尼泊爾博克順多國家公園和干成章嘉峰保護區(qū)的雪豹進行個體識別;Kyle等(2011)利用上述10個微衛(wèi)星位點成功對吉爾吉斯共和國薩里查特-埃爾塔什地區(qū)和占哥特狩獵保護區(qū)的野生雪豹個體進行識別;周蕓蕓等(2014)在青藏高原的三江源自然保護區(qū)、羌塘自然保護區(qū)以及甘肅的黨河南山地區(qū),獲得277份疑似雪豹糞便樣品,成功擴增mtDNA cyt b基因片段190份,并確定89份來自雪豹,通過微衛(wèi)星分析,確定來自48只不同的雪豹個體。
分子生物學(xué)方法的應(yīng)用,如DNA條形碼技術(shù)、微衛(wèi)星技術(shù),提高了個體識別的準(zhǔn)確性,減少了誤判,但如果僅使用分子生物學(xué)手段進行個體識別,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雪豹的糞便樣品收集較困難,且收集到的糞便樣品有一部分較陳舊,而分子生物學(xué)方法無法鑒別陳舊的糞便樣品。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yīng)增加野外調(diào)查,豐富雪豹足跡、刨痕等野外痕跡樣本,為利用痕跡進行個體識別提供更多參考。同時,雪豹各個角度照片的數(shù)據(jù)積累不足,如雪豹腹部的照片目前尚無記錄,因此還應(yīng)增加紅外相機布設(shè)角度,獲得更多角度的雪豹照片,利用人工智能(AI)、深度學(xué)習(xí)(趙婷婷等,2018;Hou et al.,2020)等技術(shù),提高雪豹個體識別準(zhǔn)確性。在保證一定準(zhǔn)確性的條件下,解決使用分子生物學(xué)方法研究結(jié)果不全面的弊端,最后將宏觀與分子生物學(xué)研究結(jié)果進行對比、印證,達到精準(zhǔn)識別雪豹的目的。
2.3 種群數(shù)量分布
明確雪豹的種群數(shù)量分布對雪豹保護區(qū)域的規(guī)劃有重要作用,但各國研究者仍未找到準(zhǔn)確估計雪豹種群數(shù)量的方法。目前雪豹在中國主要的分布區(qū)域有新疆、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地,雪豹種群數(shù)量的研究集中在新疆與四川,馬鳴等(2006)研究表明,在托木爾峰自然保護區(qū)邊緣的木扎特谷地的250 km2范圍內(nèi)存有5~8只雪豹,其密度為2~3.2只/100 km2;徐峰等(2011)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新疆托木爾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現(xiàn)存雪豹47.28~87.25只,其密度為1.99~3.47只/100 km2。雪豹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分布較廣,彭基泰(2009)指出在青藏高原東南橫斷山脈甘孜地區(qū)的雪豹種群數(shù)量為400~500只,其中石渠、新龍、德格、甘孜、白玉、理塘等6縣有51~78只。青海、甘肅、西藏等地的相關(guān)研究較少,Schaller等(1988)的研究表明生存于青海省與甘肅省西部邊緣的雪豹種群數(shù)量達到650只。西藏境內(nèi)雪豹種群數(shù)量則尚無相關(guān)報道。
巴基斯坦與尼泊爾為除中國外雪豹的主要分布區(qū)域,因此得到較多的關(guān)注,如 Hussain等(2003)估測巴爾蒂斯坦雪豹種群數(shù)量為90~120只,而整個巴基斯坦雪豹種群數(shù)量為300~420只。尼泊爾2個重要的雪豹分布區(qū)域——博克順多國家公園和干成章嘉峰保護區(qū)的雪豹種群密度為4只/100 km2和5只/100 km2(Karmacharya et al.,2011)。除以上2國外,其余國家的報道則相對較少,如印度和蒙古國的雪豹種群數(shù)量目前僅少部分地區(qū)有文獻報道,印度拉達克-赫米斯國家公園的雪豹種群數(shù)量為5只,蒙古國境內(nèi)戈壁沙漠區(qū)域的雪豹種群數(shù)量為16~19只,種群密度為4.9~5.9只/100 km2。在吉爾吉斯共和國,薩里查特-埃爾塔什地區(qū)雪豹種群密度為8.7只/100 km2,占哥特狩獵保護區(qū)雪豹密度為1.0只/100 km2(Janecka et al.,2008,2011;Kyle et al.,2011)。
有關(guān)雪豹種群數(shù)量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nèi),不同國家、地區(qū)發(fā)展不均衡。例如在我國,四川、新疆的研究較多、發(fā)展較快,西藏、青海等地研究較少、發(fā)展較慢。這種情況可能會導(dǎo)致不同的研究者對橫跨多個國家或地區(qū)的雪豹種群進行重復(fù)計數(shù),從而錯誤估計全球范圍內(nèi)的雪豹數(shù)量。因此,各國、各地區(qū)之間應(yīng)考慮統(tǒng)一的研究方法,以減小各國、各地區(qū)之間研究進度的差距,提高雪豹數(shù)量估計值的準(zhǔn)確性。
2.4 活動與空間利用模式
動物活動模式研究集中在動物的活動節(jié)律,以及影響動物活動因素的探討(張晉東等,2015),空間利用模式是指動物對棲息地內(nèi)環(huán)境資源的利用模式,影響著種群間的基因交流與生存發(fā)展(Roesnberg & Mckelvey,1999;王曉,張晉東,2019)。掌握雪豹活動與空間利用模式對于雪豹的野外保護工作的開展有重要作用。
目前關(guān)于雪豹活動與空間利用模式的研究集中在雪豹活動節(jié)律和家域范圍的探索,活動節(jié)律的研究較多,且研究方法也較成熟,如唐卓等(2017)發(fā)現(xiàn)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的雪豹年活動最高峰為1月,次高峰為8月,6月和7月活動最少。雪豹在夜間比白天更活躍,活動高峰為18:00—20:00,且日活動存在季節(jié)差異,夏秋季比冬春季更集中在夜間活動,與此同時,雪豹在夜間的活動受月相的影響,在月相更明亮的夜晚,雪豹的活動更頻繁。Wolf和Ale(2009)研究表明,雪豹的活動模式受地形、人類活動、主要食物等棲息地條件的影響,不同地區(qū)雪豹的空間利用模式存在差異。而雪豹家域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僅能對雪豹的大概家域進行預(yù)測,如Mccarthy等(2005)通過標(biāo)準(zhǔn)遙測技術(shù)估測蒙古國西南部阿爾泰山雪豹的活動范圍為13~141 km2,而通過項圈跟蹤得出該區(qū)域雪豹活動范圍為1 590~4 500 km2,上述結(jié)果差距較大,其原因在于遙測技術(shù)在估測雪豹家域范圍的應(yīng)用中成功率不高。研究表明,動物家域的計算受研究方法、計算模型等因素的影響(張晉東等,2013),而動物家域受季節(jié)變化、分布區(qū)域、種群數(shù)量、食性組成等因素的影響(張晉東,2012;Zhang et al.,2014),由此可見,雪豹家域的研究需考慮諸多因素,而目前雪豹家域研究的數(shù)據(jù)積累不足,難以進行區(qū)域間的對比,今后應(yīng)同時在多區(qū)域開展雪豹家域研究,比較研究結(jié)果,排除影響因素帶來的干擾,增強結(jié)果的準(zhǔn)確性與可信度。除此之外,在雪豹的活動與空間利用中,野生雪豹的野外遷移、交配行為、繁殖生態(tài)、家庭關(guān)系、壽命與年齡結(jié)構(gòu)等內(nèi)容均未涉及,僅圈養(yǎng)雪豹的飼養(yǎng)與繁殖有少量研究(張得良,權(quán)守元,2018)。因此,今后雪豹活動與空間利用模式的研究在進一步完善雪豹活動節(jié)律與家域研究的同時,也應(yīng)重視上述研究方向。
2.5 食源組成
雪豹作為唯一一種高海拔生存的大型貓科Felidae動物,其食物資源遠少于其他低海拔物種,雪豹如何利用較少的資源保持其生存發(fā)展引起研究人員的關(guān)注,同時雪豹食性的研究對于其他動物在食物資源方面的利用也有一定啟發(fā)作用,且研究雪豹食性對理解雪豹與同域動物間的相互作用有重大意義。目前研究發(fā)現(xiàn),雪豹在不同地區(qū)食性組成不同且各地雪豹食物儲量存在差異,我國雪豹的主要食物是巖羊Pseudois nayaur、旱獺Marmota spp.,包括喜馬拉雅旱獺 Marmota himalayana、紅旱獺Marmota caudata和灰旱獺Marmotabaibacina(Schaller et al.,1988;劉楚光等,2003;徐峰等,2007;陸琪等,2019)。巴基斯坦雪豹70%的食物來自家畜,即綿羊Ovis aries、山羊 Capra hircus、牛、牦牛Bos mutus、牛與牦牛的雜交種,30%來自野生動物(巖羊、捻角山羊Capra falconeri、鳥類)(Anwar et al.,2011)。尼泊爾雪豹的主要食物為喜馬拉雅塔爾羊Hemitragus jemlahicus與巖羊,除此之外,喜馬拉雅旱獺與羅伊爾鼠兔Odiotona royki也是雪豹重要的食物來源(Som,2012)。蒙古國的南戈壁地區(qū),雪豹的主要食物為西伯利亞北山羊Capra sibirica、山羊和盤羊 Ovis ammon(Wasim et al.,2012)。Lyngdoh等(2014)分析了全球范圍內(nèi)雪豹獵物消耗的頻率和消耗的生物量,從全球范圍總結(jié)出雪豹的主要食物為西伯利亞北山羊、巖羊、喜馬拉雅塔爾羊、盤羊和喜馬拉雅旱獺。
當(dāng)前研究大多只針對雪豹食源中的動物食源,而對植物食源研究較少,其原因在于當(dāng)前研究手段的限制,紅外相機監(jiān)測、獵物生物量估測、DNA條形技術(shù)等方法均只能用于雪豹動物食源的研究,糞便殘骸分析可對植物食源進行鑒別,但準(zhǔn)確性有所欠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應(yīng)積極探索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穩(wěn)定同位素法,此方法在其他動物食性的研究中取得顯著成果,且動物食源與植物食源的研究均可使用(張璇等,2013;趙璐等,2017;Teresa et al.,2019),明確雪豹植物食源,完善雪豹食源組成,對未來雪豹救助與人工繁育等有重要作用。
2.6 遺傳多樣性
隨著DNA提取與分析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試圖從分子生物學(xué)的角度對雪豹進行研究,了解雪豹的遺傳多樣性是研究雪豹生存適應(yīng)和物種進化的前提。張于光等(2009)基于糞便DNA成功證明青海省都蘭縣的宗加鄉(xiāng)、諾木紅鄉(xiāng)以及治多縣索加鄉(xiāng)的雪豹有著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周蕓蕓等(2014)在48只雪豹的mtDNA cyt b基因片段中檢測出13個多態(tài)性位點,定義9個單倍型,其中單倍型多態(tài)性0.776,核苷酸多態(tài)性1.50%,9個單倍型的遺傳距離為0.009~0.058,證明了分布在三江源保護區(qū)、羌塘保護區(qū)、甘肅黨河南山地區(qū)的雪豹存在遺傳多樣性。
另有遺傳多樣性的研究也解釋了一系列問題,于寧等(1996)通過構(gòu)建雪豹限制性核酸內(nèi)切酶圖譜,并通過限制性酶譜比較金錢豹P.pardus與雪豹的mtDNA,發(fā)現(xiàn)兩者的遺傳距離為0.075 33,未到達屬級分化,雪豹應(yīng)當(dāng)屬于豹屬Panthera,但因其形態(tài)、行為等特征不同于豹屬其他動物,推測雪豹應(yīng)為豹屬中的一個有效亞屬。Wei等(2009)利用設(shè)計的30個引物片段獲得雪豹線粒體全基因組,長度為16 773 bp。Cho等(2013)成功報道了雪豹適應(yīng)高海拔獨有的遺傳決定因素。
mtDNA cyt b基因片段的擴增和微衛(wèi)星分析技術(shù)已經(jīng)相對成熟(張于光等,2008;Karmacharya et al.,2011),Janecka等(2008)也成功設(shè)計了 1 組研究雪豹遺傳多樣性的線粒體DNA引物,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yīng)將雪豹遺傳多樣性的研究列為重點,探索目前尚未解決的一些問題,如雪豹的進化過程、全基因組測序等。
3 存在的問題與研究展望
關(guān)于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的研究,研究者已明確雪豹對地形、植被類型等多數(shù)自然生境因子的選擇情況(Li et al.,2013;喬麥菊等,2017),個體識別的準(zhǔn)確性也隨研究方法的改進而提高,種群數(shù)量在少數(shù)國家與地區(qū)被成功估算,活動節(jié)律的研究方法也較為成熟,同時基本確定了雪豹動物食源的組成(Lyngdoh et al.,2014),遺傳多樣性的研究在技術(shù)上獲得實踐與發(fā)展,也取得了相應(yīng)的研究成果(Karmacharya et al.,2011;周蕓蕓等,2014)。目前雪豹的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工作已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為了今后更好地開展全面且深入的雪豹研究,建議加強以下3個方面的相關(guān)工作。
3.1 各國、各地區(qū)間需加強合作
雪豹在全球范圍內(nèi)主要分布于中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蒙古國等國家(唐卓等,2017),在我國主要分布于四川、新疆、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劉沿江等,2019),在地理位置上均具有連續(xù)性,但目前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的研究表現(xiàn)為研究者在各國、各地區(qū)分別開展研究工作,彼此之間聯(lián)系不夠緊密,各國、各地區(qū)均未建立持續(xù)或者定期的監(jiān)測機制,方法與標(biāo)準(zhǔn)亦難以統(tǒng)一,導(dǎo)致今后很難在更大尺度上開展相應(yīng)的研究工作,從而很難為更大尺度上的雪豹保護政策制定提供科學(xué)依據(jù),因此,不同國家與不同地區(qū)之間的研究者應(yīng)加強合作與交流,共同搭建研究平臺,推動數(shù)據(jù)共享,以實現(xiàn)在更大尺度上開展雪豹生態(tài)與保護研究的目的。
3.2 人豹沖突下的保護政策研究需要加強
研究者對雪豹棲息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棲息地的自然條件,如海拔、植被類型等,而對雪豹與人類的沖突關(guān)注較少,且不夠深入,主要體現(xiàn)在目前雪豹的保護政策不完善,以及雪豹保護機構(gòu)對牧民家畜損失的賠償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如在我國四川邛崍山脈,存在較高的雪豹-家畜沖突風(fēng)險,但目前尚未制定出有效的保護管理政策(史曉昀等,2019);在巴爾蒂斯坦,人豹沖突嚴(yán)重,但雪豹的保護管理政策不完善,牧民對雪豹進行報復(fù)性捕殺,使得近年來該區(qū)域的雪豹數(shù)量銳減(Hussain et al.,2003)。對此,相應(yīng)的研究人員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激勵政策,如提高被捕家畜的賠償額度、為家畜圈舍進行加固、加強雪豹保護的宣傳工作等,試圖減緩人豹沖突,同時也為后續(xù)的研究積累寶貴經(jīng)驗。與此同時,雪豹保護與研究目前還存在許多尚未涉及的盲點,如落后地區(qū)的貧困問題、當(dāng)?shù)鼐用癖Wo意識不足、社區(qū)服務(wù)以及環(huán)保力量的扶持不足等,因此,深入了解各棲息地居民對雪豹的看法,尋找既能保護雪豹,又能保全當(dāng)?shù)鼐用窠?jīng)濟利益的保護策略,從根源上解決雪豹與人類的沖突,對于未來雪豹保護工作至關(guān)重要。
3.3 應(yīng)對氣候變化的研究不足
目前關(guān)于氣候變化對雪豹生存影響的研究較少(李小雨等,2019),對于雪豹如何應(yīng)對今后氣候變化的研究基本沒有。近年來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全球氣候變化加劇(Forrest et al.,2012),雪豹所分布的高山生態(tài)系統(tǒng)植被單一,抵抗力穩(wěn)定性較弱,對氣候變化敏感,氣候變化極有可能成為未來影響雪豹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氣候變化對雪豹的影響以及探索相應(yīng)的策略對于雪豹的保護工作有重大意義。
致謝:感謝佛羅里達大學(xué)生態(tài)與野生動植物系卞曉星博士,西華師范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侯金、羅歡在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意見;西華師范大學(xué)生命科學(xué)學(xué)院毛澤恩、蔡天貴在文獻整理方面給予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