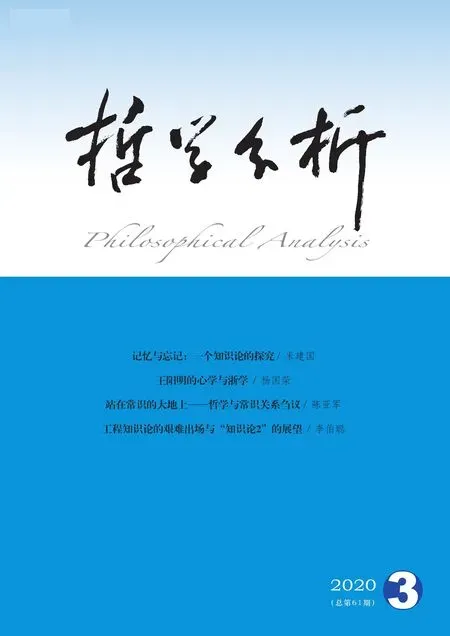工程知識論的艱難出場與“知識論2”的展望
李伯聰
本文將簡要討論三個基本觀點:人類的知識包括不同的類型,而工程知識正是其最重要的知識類型之一;知識論包括不同的分支,而工程知識論正是其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由于多種原因,古代知識論乃至近現代的知識論成為了“只研究科學知識而排斥工程知識的知識論” (可謂之“知識論1”),今后,應該在“綜合工程知識論、科學知識論、倫理知識論等知識論分支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研究所有知識類型的知識論”,可稱之為“知識論2”。這三個觀點牽涉的問題很多,本文只能對與其有關的部分問題進行一些初步、概略的分析和討論。
一、從知識分類和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談起
(一)“知識類型”:研究知識問題時必然出現的重要問題
一般地說,哲學家都高度重視人的認知能力并從哲學角度研究知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第一句話就是:“所有人在本性上都愿求知。”①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李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荀子在《解蔽》中也說:“凡可知②原作“凡以知”,據《荀子繹評》 (鄧漢卿著,長沙:岳麓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頁)、《荀子匯校匯注附考說》 (董治安等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0頁)改為“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在哲學家普遍高度重視知識的語境中,我們可以說甚至那些知識的懷疑論者也從“反面”凸顯了知識的重要性。
知識論(或曰認識論)③對“認識論”和“知識論”的關系,我國哲學界的認識不完全一致。本文中對于二者的含義采取不加區分的態度。以知識為哲學研究的對象,而知識又包括了形形色色、多種類型的知識。無論從學理方面看,還是從作為知識論研究對象的“知識現象本身的狀況”方面看,“知識分類”問題都順理成章且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知識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條件之 一。
雖然對于不同階層和職業的人來說,往往主要關注特定類型的知識(例如工匠主要關注“工程知識”),而不關注“知識的整體”;但是,對于古代哲學家來說,由于多種原因,他們大多著重從“整體”上研究知識問題,也就是把知識看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于是,哲學領域中的“知識論”主要也就成為了以“知識整體”為研究對象的領域。可是,這里緊接著又出現了一個需要辯證對待的方法論問題,即“整體”和“分類”的關系問題。如果不進行分類,“整體”就可能成為一個“帶有混沌性”的整體,為了走出“混沌”就必須進行分類。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古代哲學家往往都更加關注知識整體性問題,而較少有人明確地意識到“知識分類”問題也是一個“知識論中的重要問題”,知識論領域也很少出現“關于知識分類問題的哲學研究成果”。
當然,“很少”不意味著“沒有”。例如,在這方面,歐洲的某些哲學家以及我國北宋的張載都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張載首先從理論上明確提出和闡述了“知之分類”問題。他認為“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是兩類不同的知識:“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④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5頁。程頤也說:“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①轉引自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哲學問題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頁。張岱年認為:“德性所知,不是康德所講的純粹理性卻較接近于康德所講的實踐理性。”②同上,第505頁。張岱年原注:“其實也有很大的不同,決非一事。”
在比較中國哲學傳統和歐洲哲學傳統時,許多現代哲學家都認為中國哲學傳統更重視倫理問題而知識論研究較弱。陳嘉明甚至認為:“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知識論的地位乃是邊緣性的。”他又說:“就西方哲學而言,求‘真’的知識論構成了它的主流。其主要哲學家,從柏拉圖、康德到胡塞爾等,幾乎首先都是知識論的宗師。”③陳嘉明:《建構與范導——康德哲學的方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主編的話”第1頁。
如果說,古代歐洲哲學家已經高度重視研究知識論問題,那么,近代歐洲哲學史上出現了所謂認識論轉向,知識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就更加琳瑯滿目、百花齊放。可是,在琳瑯滿目、百花齊放的“知識論成果”中,卻較少有哲學家“直接指名道姓”地研究“知識分類”問題。
當然,如果不拘泥于“自報家門”,而是就“某個方面的內容屬性”來看,我們也可以承認哲學家關于“經驗知識”和“理性知識”的研究——如果從某個側面看——也是關于“兩種知識類型”的研究。可是,就哲學家在研究“經驗知識”和理性知識”時的“自覺認識”而言,他們很少有人“承認”這是“關于知識分類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就爭論焦點而言,我們更難以斷言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大派的論戰是有關“知識分類”問題的論戰。總而言之,在知識論領域的研究中,絕大多數哲學家都沒有明確意識到“知識分類”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沒有在“這個方向”進行專題和深入的哲學探索和開拓。
在近現代哲學家中只有少數人“明確地”涉及和關注了知識分類問題。例如,C. L.劉易斯在《對知識和評價的分析》中就明確談到了“知識的兩種類型”:經驗知識和分析性知識。④C. L.劉易斯:《對知識和評價的分析》,江傳月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雖然在哲學領域中對經驗知識和分析性知識的“二分”研究已經很多,因而這種二分式“劃分”也不是劉易斯的創見。可是,由于很少有人明確指出“這是知識分類問題”,我們認為,劉易斯能夠明確地將其“認定”為知識的兩種類型”并且從“知識類型劃分”角度對其進行討論,也可謂是一項重要的理論貢獻。
如果說,劉易斯只是對“知識類型(分類)”這個“主題”作出了“點題”性的貢獻,那么,科林斯就對知識分類問題作出了更具體的分析和更值得稱道的貢獻。科林斯把知識劃分為五種類型:觀念型知識、體知型知識、文化型知識、嵌入型知識、符號性知識①成素梅:《技能型知識與體知合一的認識論》,載《哲學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4頁。又,張帆在《科學、知識與行動:科林斯的科學哲學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1頁)一書中也介紹了科林斯關于知識分類的思想。,這就使對知識分類問題的認識更加具體化和深化了。
雖然明確關注知識分類問題的現代哲學家并非只有上述二人,但應該承認明確關注知識分類問題的哲學家不多。
(二) 科學知識、工程知識、倫理知識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
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進行理論研究時,“分類”都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方法和主題。如果沒有器物分類、行業分類、物種分類、學科分類、圖書分類等領域的“類型劃分”,人們就會生活在一個濃霧彌天的“混沌世界”中。在知識論領域,知識分類問題也是一個不能回避和不能忽視的問題。
“知識分類”是意義復雜、功能多樣的問題。為了不同的目的和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會劃分出不同的知識類型。例如,可以為了某個“實用性目的”而進行知識分類,也可以“從哲學角度”進行知識分類研究。
在知識論領域,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哲學性”的知識分類?可以具體劃分出哪些知識類型?這些都是應該深入研討而迄今很少深入研討的問題。但本文無意具體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本文來說,筆者只想簡單指出:以承認知識“可以分類”和“應該分類”為理論前提和背景,我們就可以承認工程知識、倫理知識和科學知識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②這個論斷只肯定了“這是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而沒有涉及“知識究竟應該依據什么標準分類”和“究竟應該具體劃分為多少類型”等問題。
在人類知識的發展史上,工程知識的起源最早(自人類起源就有了原始的工程知識③A. A. Harms,et al.,Engineering in Time,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04.),而倫理知識和科學知識的形成就要晚很多。
應該怎樣認識這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的相互關系呢?
一方面,不同類型的知識必然有不同的本性(本質)和不同的特征,正是這些不同的本性和特征“區分了”不同類型的知識,使它們成為了不可混淆的不同類型。另一方面,也不能認為不同類型的知識之間存在的“類型區別”是“界限絕對分明的絕對區別”,相反,應該承認不同類型的知識就“多方面具體內容和具體形式”而言往往出現相互重疊、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相互嵌套、相互轉化的關 系。
在認識“分類問題”時,原先有許多人都重視和強調以上所說的第一個方面,也就是立足于“本質主義”觀點和方法來認識分類問題。可是,在維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的觀點和方法以及“反本質主義”觀念流行之后,一些人又否認“本質”的“存在”,而只承認“無‘共同本性’的家族相似性”。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理解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和方法呢?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和方法意味著“絕對否認存在‘家族本性’”嗎?我們認為,在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中,不但蘊含了“家族”和“家族成員”這兩個概念,而且蘊含著“不同家族”這個概念。就“家族相似”這個概念和方法而言,它并沒有認為“任意的和隨機的兩個不同事物”都是相似的,而只承認“(同一)家族的成員”之間存在相似性。就此而言,可以認為“家族相似”概念和方法并沒有否認在“家族成員相似性”的深層”,同時也存在著“家族共性(家族本性)”。
總而言之,在認識“類型劃分”和“不同類型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時(本文關心的是“知識的類型劃分”和科學知識、工程知識、倫理知識的相互關系),我們應該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必須承認不同類型的知識就其“本性”或“核心特征”而言必定有“明確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知識在“邊緣區”往往是模糊的,常常出現交叉、滲透,乃至相互嵌套、相互轉化關系。人們不能因為前一個方面否定后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后一方面否認前一方面。例如,從本性上看,工程知識屬于“見聞之知”而倫理知識屬于“德性之知”;工程知識是關于人工物的創造和使用的知識,也是與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知識,而倫理知識是與上層建筑聯系在一起的知識,這就使工程知識與倫理知識在本性上有了不可混淆的區別。另一方面,由于工程知識是創造使用價值和為人類謀求福祉的知識,這又使工程知識必然與倫理知識有相互滲透和相互交叉的部分和成分,但這個“相互滲透和相互交叉關系”并不能成為否認工程知識和倫理知識是“兩類知識”的理由,不能因此而把工程知識和倫理知識混為一談。
這就是說,一方面,承認工程知識和倫理知識是兩類本性上有不同的知識不意味著不能承認二者也有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部分或成分。另一方面,承認二者有相互滲透的關系也不意味著可以否認二者在類型劃分上有確定性的區別,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除了相互滲透關系,工程知識和倫理知識還存在著可能“相互嵌套”和“相互轉化”的關系。
工程知識和科學知識——作為兩類不同的知識——的關系,也是“在本性上有明確區別”“在邊緣部分往往模糊滲透交叉”“往往多重嵌套”“可能相互轉化”的關系。可是,在認識工程知識與倫理知識的相互關系時,人們往往更多地犯“否認二者相互滲透”的錯誤;在認識工程知識與科學知識的相互關系時,人們往往更多犯否認二者有本質區別”的錯誤。
限于篇幅,本文以下的分析中將更多涉及工程知識和科學知識的類型區分和相互關系問題。
二、古代知識論的吊詭現象:重視知識但又排斥工程知識
回顧知識論的狀況和發展史,人們會看到一個顯得吊詭的現象:雖然人類進入文明時期后已經營造出了一個“(普遍)重視知識”的大環境,在哲學形成后,古代的絕大多數哲學家都“高度重視知識”并且承認工程知識是一個“獨立類型”的知識;可是,哲學家并沒有采取“同樣重視”“所有類型知識”的態度,而采取了只高度重視科學知識和倫理知識而貶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識的態度。更具體地說,工程知識不但沒有能夠“搭上‘重視知識’的順風車”而受到重視,反而在“重視知識這個‘大前提’和‘大環境’中”被嚴重貶低甚至被排斥在“應該重視的知識這個‘思想和口號’”之外,成為了“屬于知識但又被嚴重貶低甚至被排斥的知識類型”,對于這種狀況和現象確實需要用“吊詭”來形容了。
由于篇幅有限和為論述簡便,以下只講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兩個事例,而不再論及歐洲哲學史的類似情況。
在中國思想和文化史上,孔子是一個影響最大的人物。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是他那個時代知識最豐富的人。他不但掌握了豐富的政治、禮教、禮儀、歷史、倫理、制度、語言、音樂、射御、書數、草木鳥獸之名等多方面的知識,而且掌握了頗為豐富的“體力勞動”知 識。
孔子青少年時期生活在一個社會地位沒落的家庭,這使得他不得不掌握一定的體力勞動知識;另一方面,他努力學習其他方面的知識,特別是禮樂仁義知識,這就使他因為有豐富的知識而逐漸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名聲和地位,甚至成了傳授知識的“萬世師表”。可以說,孔子就是一個在重視知識的社會環境中因為掌握了豐富的知識而改變命運的典 型。
在孔子同時代的“知識豐富”的人中,許多人只有豐富的關于禮、樂、歷史、戰爭、祭祀等的知識,而在“體力勞動知識”方面基本上處于“無知”狀態,可是,孔子卻是一個少有的例外。
那么,孔子是如何看待這種“比較全面地掌握不同類型知識”的狀況呢?是否應該“同樣和同等”地重視工程知識呢?
根據《論語·子罕》的記載,達巷黨人稱贊孔子“博學”,并且首先就情不自禁地贊曰“大哉孔子”。太宰也情不自禁地評論說:“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這段記載中,孔子特別強調了他之所以“多能鄙事”,其原因是“少也賤” (社會地位卑賤)。對于孔子最后兩句話的含義,《論語集解》引包(咸)曰:“君子固不當多能也。”這就又表明孔子本人和歷代儒家一致認為“君子”不需要和不應當學習和掌握作為“多能”的“鄙事(之知)”。
什么是“鄙事(之知)”呢?《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這就使一心學習“農業知識”的樊遲碰了一鼻子灰。而更“要害”之點是孔子接下來的一段評論:“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這就是說,作為教育家的孔子不但明確而堅決地在理論上否定了耕稼等工程知識①廣義的工程知識包括農業知識在內。的意義和重要性,而且明確而堅決地在教育實踐中排除了工程知識在儒家教育體系中的位置。
到了戰國時期,大儒孟子又與治“神農之學”的徐行發生了一場涉及如何認識農業和紡織勞動知識的爭論。孟子說:“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滕文公上》)現代學者多從勞動分工的經濟學理論角度分析和評論這場爭論,也有學者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這場爭論,但從知識論角度看,這場爭論也是有關應該如何認識“不同類型的知識”的性質、特征、意義和功能的爭論。
工程活動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工程活動又以工程知識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馬克思說:“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②馬克思:《資本論》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工程活動和工程知識的關系是相互滲透、相互伴隨的關系,沒有人能夠否認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工程知識是“必不可少的知識類型”。
那么,誰掌握著工程知識呢?《宋書·沈慶之傳》云:“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于是,在很長時期中,與勞動分工和職業劃分相呼應、互為表里,出現了“不同類型的知識掌握在不同職業的人手中”的狀況。
許多現代學者都指出了古代中國哲學傳統和古代歐洲哲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可是,二者在貶低工程知識甚至排斥工程知識方面卻表現出了明顯的共同之處。
三、20世紀知識論研究中的三個新認識和新觀點
應該特別注意和特別強調指出的是,上述“吊詭狀態”在理論上和哲學史上都產生了嚴重后果和嚴重影響。從理論方面看,理論領域中本來應該“以全部知識類型為研究對象的知識論” (可謂之“知識論0”)變成了“‘唯一地以科學知識為研究對象’和‘不承認工程知識也是知識論研究對象’的知識論” (可謂之“知識論1”)。從知識論發展史方面看,由于歐洲哲學史上的絕大多數哲學家都忽視了“知識論0”而只承認“知識論1”,這就使得歐洲古希臘、中世紀和近代的“知識論發展史”主要成為了“知識論1的發展史”①本文不涉及“知識論0”在歷史上的萌芽、微弱存在和斷續發展問題。。
在這種“限定于以科學知識為全部知識”的知識論——即“知識論1”——發展史上,柏拉圖是影響最大的人物。柏拉圖提出的關于“知識是經過證實(有人譯為確證)的真信念”的思想成為了這種進路的知識論的核心觀念,他的這種觀點成了在歐洲知識論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之一。②胡軍:《知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6頁。
對于歐洲哲學史的發展,曾經有人提出近代歐洲哲學史出現了“認識論轉向”之說。應該注意,這個觀點只是說歐洲哲學史上就“哲學體系”而言發生了從本體論哲學向認識論哲學的“轉向”,而沒有說在“知識論領域”發生了“轉向”。相反地,可以說,在知識論領域和知識論的發展方向上,近代以來,從17世紀的笛卡爾和洛克到18世紀的康德,在知識論領域都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認識,取得了重大的理論成就。可是,這些知識論研究都是沿著古希臘開創的知識論傳統和方向的繼續發展,而沒有發生什么“知識論領域的轉向”。更具體地說,這些都是“知識論1方向”的延續和發展。
這種“以科學知識為知識的唯一類型和忽視工程知識”的“知識論1”在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中達到了一個新高峰,或者說有了極端表現。這個學派不但未能發覺和反思以往知識論傳統中“只承認科學知識是知識而排斥工程知識”的缺陷和錯誤,反而把傳統的缺陷和錯誤更加明確化和極端化了。《新編西方現代哲學》中說,這個學派“強調以科學為模式、以邏輯為手段、以物理學為統一語言,徹底改造哲學,使哲學完全成為一種科學的哲學”①劉放桐等:《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頁。。成素梅也說:“語言哲學家艾耶爾在1936年出版的《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中提出的‘證實原則’認為,‘沒有一個經驗領域原則上不可能歸于某種形式的科學規律之下,也沒有一個關于世界的思辨知識的類型原則上超出科學所能給予的力量的范圍’。也就是說,所有的知識只能是科學知識。”②成素梅:《“知識就是力量”的跨學科反思》,載《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1期。
如果說,從古希臘到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者在研究知識論時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自我約束在科學知識領域”而“對工程知識視而不見”,也就是在“知識論1方向上”“不思轉向”;那么,在20世紀中期以后,就有一些學者在研究知識論問題時,“自覺不自覺”地注意到“整個知識領域”中除科學知識外還有其他類型的知識。由于他們“不再局限于科學知識”而“放眼關注其他類型的知識”,這就使他們通過對“其他類型的知識”的研究而提出了一些具有“修正知識論1”特征的新認識和新觀點。對于這些新認識和新觀點,我們有理由將其稱為歐洲知識論發展史上對知識論1”的“轉向嘗試”。
在這些具有“知識論轉向色彩”的新認識和新觀點中,20世紀中葉之后提出的以下三個新認識和新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1)吉爾伯特·賴爾在1946年的論文和1949年出版的著作《心的概念》中,明確指出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命題性知識(knowing that)和操作性知識(knowing how)。③《心的概念》的中譯者徐大建把knowing how 翻譯為“知道怎樣做” (參見賴爾:《心的概念》,徐大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2頁),郁振華主張將其譯為“能力之知” (參見郁振華的《論能力之知:為賴爾一辯》,載《哲學研究》2010年第10期),筆者認為譯為“操作之知”或“操作性知識”更好一些。(2)邁克爾·波蘭尼在1958年出版的《個人知識》一書中提出,除可以言傳的“明述知識”外還有“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④參見波蘭尼:《個人知識》,徐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批判“離身認知”的基礎上,“具身認知” (embodied cognition)范式興起。葉浩生說:“具身認知目前已成為一股洶涌澎湃的學術思潮,對西方傳統認識論和認知科學造成巨大沖擊。”⑤葉浩生主編:《具身認知的原理與應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5頁。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但反映以上三個方面進展的一些重要外文論著陸續被譯為中文,而且出版了我國學者研究這三個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一些論著,例如《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⑥郁振華:《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具身認知的原理與應用》⑦葉浩生主編:《具身認知的原理與應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等。
STEP指令直接連接在左側母線上。STEP在SNXT指令之后,各工序之前配置,表示該工序開始(指定工序編號);在步梯形區域整體的最后配置,表示步梯形區域整體的結束(無工序編號)。
饒有趣味和發人深省的是,以上三種觀點都是針對“知識論1中的一個傳統概念”而提出了“另外一個關于知識的新概念”,從而形成了“三組”“對待性的知識概念”,分別用于指稱“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賴爾針對“命題性知識”而提出了“操作性知識”;波蘭尼針對“明述知識”而提出了“默會知識”①國內學者對tacit knowledge的譯法有“默會知識”“意會知識”“隱性知識”“隱含經驗類知識”等,本文采用“默會知識”。;具身認知范式倡導者針對“離身認知” (disembodied cognition)而提出了“具身認知”②國內學者對embodied cognition的譯法有“具身認知”“寓身認知”“涉身認知”“體化認知”等,本文采用“具身認知”。。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認為這“三組觀點”的“前支觀點” (命題性知識、明述知識、離身認知)“等同于”科學知識,也不能簡單化地認為這“三組觀點”中的“后支觀點” (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認知)“等同于”工程知識;但三個“前支觀點”與科學知識有不解之緣而三個“后支觀點”與工程知識有不解之緣乃是顯而易見和不能否認的。實際上,有些學者在進一步解釋和闡發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認知的內容和意義時,已經觸及它們與技術知識、工程知識的密切聯系。
孔子早就強調“名正才能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邏輯實證主義更反復強調“澄清概念的重要性”。由于賴爾、波蘭尼以及倡導具身認知的學者都沒有明確提出“工程知識”這個概念,特別是由于我們不能認為“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知識可以“等同于”工程知識,以及對于“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認知和工程知識的復雜關系目前也還未能有具體深入的闡釋,我們目前還只能說“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認知的提出意味著工程知識在理論舞臺上有了一個“戴了假面具”的“出場”,而不能認為它們是“工程知識”“作為一個理論概念”在理論舞臺上的“正式出 場”。
四、“工程知識”作為哲學概念在工程史學科中的出場
上文談到,在哲學形成以來的兩千多年中,許多哲學家都輕視、貶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識。在這種強大的思想傳統的影響和壓制下,“工程知識”一直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哲學概念”。甚至上文談到的20世紀中期以來通過操作性知識、默會知識、具身認知等概念而嘗試進行“知識論轉向”的哲學家也未能明確提出需要把“工程知識”確定為一個哲學概念。
回顧“最近期的歷史”,我們看到,首先完成把“工程知識”確立為一個哲學范疇的“理論任務”的是文森蒂——一位工程師兼工程史家。
文森蒂是一名工程師,“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曾任美國航空顧問委員會航空研究工程師和科學家,掌管過國家的超音速風洞實驗,在航空與航天飛機的設計上取得過重大成就。60年代以后,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著有《物理空氣動力學引論》,編有《應用力學》 《流體力學年度評論》,并對航空技術史有專門的研究”①張華夏、張志林:《技術解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頁。。
1990年,文森蒂出版了《工程師知道什么以及他們是如何知道的——航空歷史的分析研究》一書。文森蒂在該書第一章第一段就感慨萬千地說:“盡管工程研究人員付出巨大的努力與代價去獲取工程知識,但是工程知識的研究很少得到來自其他領域的學者關注。在研究工程時,其他領域的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它看作是應用科學。現代工程師們被認為是從科學家那里獲得他們的知識,并通過某些偶爾引人注目的但往往智力上無趣乏味的過程,運用這些知識來制造具體物件。根據這一觀點,科學認識論的研究應當自動包含工程知識的內容。但工程師從自身經驗認識到這一觀點是錯誤的,近幾十年來技術史學家們提出的敘述性與分析性的證據同樣也支持這種看法。由于工程師并不傾向于內省反思,而哲學家和史學家(也有部分例外)的技術專長有限,因此作為認識論分支的工程知識的特征直到現在才開始得到詳細地考察。”②沃爾特·G.文森蒂:《工程師知道什么以及他們是如何知道的——基于航空史的分析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在此書中,文森蒂具體深入地分析了5個工程設計知識的歷史案例:戴維斯機翼與翼型設計問題(1908—1945)、美國飛機的飛行品質規范(1918—1943)、控制體積分析(1912—1953)、杜蘭德與萊斯利的空氣螺旋槳試驗(1016—1926)、美國飛機的埋頭鉚接革新(1930—1950)。這5個案例分別涉及了5個與工程知識相關的理論問題:設計與知識的增長、設計要求的確定、設計的理論工具、設計數據、設計與生產。就整本書而言,文森蒂從多個方面具體而深入地闡釋了工程知識——主要聚焦于工程設計知識——的基本特征,比較全面而深入地闡釋了工程知識和科學知識是兩類不同的知識,強調必須把“工程知識”看作一個獨立的理論概念和哲學概念,而絕不能把工程知識看作科學知識的一個子集。該書于1997年榮獲了ASME(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國際歷史與傳統中心的工程師歷史學家獎。
由于該書在理論上首次明確地把“工程知識”確立為一個理論概念,這就意味著“工程知識”作為哲學概念首先在工程史領域“正式形成”和“正式出場”。工程知識的實際存在發展和工程知識的哲學研究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在古代,一方面,工程知識主要掌握在工匠手中,而古代的工匠又缺乏對自己掌握的工程知識進行理論深化和升華的能力,缺乏進行哲學思維的條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同時代的哲學家又普遍采取了貶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識的態度,這就使古代乃至近代一直未能形成關于工程知識的比較明確、系統的哲學理論,尤其是未能把“工程知識”明確為一個哲學概念。
在近現代歷史上,雖然工匠是直接推動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力階層”,但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工匠階層卻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而“工程師階層”乘勢興起。工程師階層興起后當仁不讓地成為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以及現代工程知識發展的最主要的推動力量。①李伯聰:《工程人才觀和工程教育觀的前世今生——工程教育哲學筆記之四》,載《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如果進行縱向比較,工程師階層和工匠階層有許多不同之處;如果進行橫向比較,現代工程師階層和科學家階層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如果說“近現代科學家階層”在登上歷史舞臺后很快就“介入”了哲學發展進程,那么,工程師階層在登上歷史舞臺后大多主要關注“工程知識自身”的發展,而很少“介入”哲學的發展進程。
工程師這種“很少介入哲學發展進程”的狀況無論對于哲學還是對于工程師自身都沒有好處,都是一個“遺憾”。這種狀況自然不可能“無限期延續”。現在我們看到,在“首先”把工程知識確立為一個哲學概念這方面,工程師取得了一鳴驚人的成就。
雖然“具體的工程知識”是最早出現的知識,具有科學知識“不可同日而語”的極其久遠的歷史,但是,就理論概括和哲學升華而言,“科學知識”早就被確立為哲學概念,而“工程知識”不但未能被確立為哲學概念,而且有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習慣性地反對把工程知識確立為獨立的哲學概念。由此可見,把“工程知識”確立為哲學概念遇到了非常特殊的境況,成了一個難上加難的任務。在完成這個難上加難任務的過程中,工程師和工程史家發揮了關鍵性的“臨門一腳”的作用。
從工程師階層和工程職業的發展進程看,工程師之所以能夠完成上述難上加難的任務,一方面是因為工程師具有與工匠、科學家和哲學家都不相同的特點,另一方面是因為工程師在一定程度上集成性地具有工匠、科學家和哲學家②米切姆認為,工程師是“后現代世界中不被承認的哲學家” (米切姆:《工程與哲學——歷史的、哲學的和批判的視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三者的特點,這才使得工程師“有潛力”和“有能力”完成“終于使工程知識這個哲學概念正式出場”的任務。
五、工程知識的哲學研究與工程知識論的出場
拉卡托斯有一個模仿康德的著名論斷:“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①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頁。毫無疑問,拉卡托斯論斷的精神對于工程史和工程哲學的關系也是適用的。
在“工程知識”這個概念在工程史領域明確提出后,雖然仍然有不少哲學專家對工程知識反應遲鈍,繼續持不屑一顧的態度,但也有哲學家順應新潮流,陸續開展了對“工程知識”的哲學研究。
首先是著名技術哲學家皮特于2001年在《技術》雜志上發表了《工程師知道什么》②皮特:《工程師知道什么》,載張華夏、張志林:《技術解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9頁。一文,這篇文章可能是專論“工程知識”問題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如果說文森蒂主要是從工程史角度和歷史案例分析方法闡述工程知識是一個特殊類型的知識,那么,皮特是著重從哲學研究和知識論角度論證這個觀點。皮特明確指出:工程知識和科學知識是兩個不同的知識類型和知識形式。科學知識有兩個主要特征:科學知識是受理論制約的;科學知識是被發展來解釋世界運轉方式的。與科學知識相反,工程知識是任務定向的。皮特承認工程知識具有“食譜知識”的樣式。但令人驚訝的是,對于皮特來說,這不但沒有成為貶低工程知識的理由,反而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任務定向的工程知識”需要針對“真實世界中的任務”可能遇到各種意外情況而獲取成功,因而,“工程知識似乎更加可靠,更加可信。具有更強的活力。因而,工程師知道的是什么東西,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任務,首要的就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任務是什么。”③同上,第138頁。
2005年,在第259次香山科學會議上,李伯聰也專門討論了工程知識問題。他指出:“在人類的知識總量中,工程知識——包括工程規劃知識、工程設計知識、工程管理知識、工程經濟知識、工程施工知識、工程安全知識、工程運行知識等——不但是數量最大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從知識分類和知識本性上看,還是‘本位性’的知識而不是‘派生性’的知識。”“當前在國內外都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即使可以承認古代的工程知識不以科學知識為前提或基礎,但在現代社會中,工程知識乃是(單純)應用科學的結果。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工程知識解釋為科學知識的派生知識’,雖然這種觀點相當流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工程知識本性的誤解。”①李伯聰:《工程創新與工程人才》,載杜澄、李伯聰主編:《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 (第2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頁。
李伯聰的上述文章還不是專題研究工程知識的論文。我國最早對工程知識進行“專題哲學研究”的學者是鄧波。他作為第一作者在2007年發表了《試論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和工程知識》②鄧波、賀凱:《試論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和工程知識》,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年第10期。,在2009年發表了《工程知識的科學技術維度與人文社會維度》③鄧波、羅麗:《工程知識的科學技術維度與人文社會維度》,載《自然辯證法通訊》2009年第4期。。鄧波強調指出,工程知識是不同于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知識類型和知識形態,工程知識既具有科學技術維度,又具有人文社會維度的復雜的知識類型,又具有獨特性、地域性、綜合性、可靠性、復雜性、協調性、情境性、現場發生性、難言性、不可復制性、優化性、評價的多元性。
2017年,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立項研究工程知識論,組織多位工程院院士和哲學專家參加研究,對有關工程知識的多方面的哲學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作為課題最終成果的《工程知識論》④殷瑞鈺、李伯聰、欒恩杰等:《工程知識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出。將于2020年出版。該書出版后將成為國內外第一本研究“工程知識論”的哲學專著。
六、多個“知識論分支”的形成發展與“知識論2”的前景展望
(一) 多個知識論“分支”的形成與繼續發展
本文開頭談到了知識分類問題,在本文結尾,需要談談與其密切聯系的“知識論分支”問題。陳嘉明有一本研究知識論的專著《知識與確證:當代知識論引論》。雖然其最后一章以“(知識論的)方法論與新分支”為標題,但這一章的正文中沒有直接而明確地分析和闡述“知識論分支”問題,特別是沒有直接而明確地說明所謂“知識論分支”的具體含義和發展前景如何,這似乎又在暗示該書作者對“知識論分支”這個概念持“謹慎態度”。這一章的內容包括三節:“自然主義的知識論”、“德性知識論”和“社會知識論”。⑤陳嘉明:《知識與確證:當代知識論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316頁。揣摩其內容和文義,其作者似乎意在指出“自然主義的知識論”是知識論研究的“新方法論”,而“德性知識論”和“社會知識論”是知識論的“新分支”。但耐人尋味的是,陳嘉明在正式行文中又沒有明確指明“德性知識論”和“社會知識論”是知識論的兩個“新分支”,而只明言其為“新方向”。所謂“(學術)方向”與“(學科)分支”,可能是一回事,也可能不是一回事。這里不討論二者的相互關系問題,以下只討論與“知識論分支”有關的一些問題。
有鑒于陳嘉明把“新方法與新分支”作為第六章的標題,我們也就“趁勢”把德性知識論” (作為第二節標題和內容)和“社會知識論” (作為第三節標題和內容)理解為知識論的“兩個新分支”,而不僅僅是“新方向”。
對于作為知識論“新分支”的社會知識論,陳嘉明說:“社會知識論是知識論領域中的一個新方向。”“在社會知識論者看來,傳統的,尤其是笛卡兒意義上的知識論屬于‘個體知識論’,其個體性表現在集中關注于認識主體孤立的心靈運作。然而,由于知識本身具有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密切協作與互動的性質,更使得個體知識論需要有一個對應物,這就是社會知識論。”①陳嘉明:《知識與確證:當代知識論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300頁。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文句的核心觀點是主張人類的知識需要劃分為“個體知識”和“社會知識”“兩大類”,從而需要形成“兩個不同的知識論分支”。社會知識論者要建立和發展出一個“知識論的新分支”——社會知識論,認為傳統知識論只代表“另外一個知識論分支”——個體知識論。
我們知道,對于分類問題,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會劃分出不同的“分類系統”。如果說,在進行“個體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兩類劃分”時,其依據的分類標準是對“認識主體的劃分”,那么,如果依據對“認識客體(對象)的劃分”而進行知識分類,人們就又可以劃分出“科學知識”“工程知識”“倫理知識”這三類知識,相應地,也可以形成“科學知識論”“工程知識論”和“倫理知識論”這三個不同的知識論分
支”。對于“倫理知識論”,上引陳嘉明著作的第六章第二節已經有專題論述,著重介紹了索薩的“德性知識論” (virtue epistemology),最近,我們又看到了新翻譯出版的道德知識論》②齊默曼:《道德知識論》,葉磊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年版。,這些都表明作為一個分支的“倫理知識論”——盡管難免還“不成熟”——“已經出場”了。
如果把科學知識論、工程知識論和倫理知識論看作知識論的“三個分支”而回顧其歷史軌跡和當前狀況,可以看出科學知識論的內容最為豐富,其發展和成長過程井然有序,形形色色的成果蔚為大觀,作為一個分支的“科學知識論”的理論大廈已經相當牢固。這就是說,科學知識論可以當之無愧地自稱已經發展成為知識論的一個“成熟的分支學科”。
相比之下,工程知識論只有若干點點滴滴和模模糊糊的歷史印痕,從比較嚴格的“哲學研究”的角度看,它在長期的歷史上只有偶然留下的個別“雪泥鴻爪”。雖然文森蒂在其著作中明確提出了“工程知識”這個概念,但他的著作屬于“工程史著作”而不屬于“哲學著作”,不是“知識論著作”。皮特的論文雖然是研究“工程知識”的哲學論文,但尚不能認為已經達到了奠定“工程知識論”理論框架的程度。上文談到,《工程知識論》將于2020年正式出版,從該書的研究過程①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自2004年起,連續而不間斷地“科研立項”研究工程哲學,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學》 (第1、2、3版)、《工程演化論》 《工程方法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于2018年立項研究“工程知識論”,即將出版的《工程知識論》就是該項研究的結項成果。從廣義上說,《工程知識論》一書是工程管理學部組織有關院士和哲學專家“持續16年研究工程哲學”而在“工程知識論”領域的標志性成果。、作者構成(包括多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哲學專家),特別是全書內容和結構(此處不贅言)看,該書的出版將會成為“工程知識論初步形成一個知識論分支”的標志。
可以看出,無論從歷史看還是從成果看,在科學知識論、工程知識論和倫理知識論這三個分支中,科學知識論都是最成熟的分支,而工程知識論只是新誕生的分支,倫理知識論則是幼年期的分支。
以上談到了多個知識論分支,可以預期,在今后的學術發展中,不但這些分支會有新進展,而且也不能排除會有其他新分支嶄露頭角。展望未來,這些知識論分支都將繼續有新的發展。
不同的知識論分支不但有不同的歷史源流和學術現狀,而且有不同的未來發展重點、發展路徑與發展戰略。就工程知識論這個新分支的未來發展而言,今后在研究成員和研究方式方面,應該特別注意加強“工程師、工程管理者和哲學家的學術研究聯盟”,使工程師、工程管理者和哲學家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從而推動工程知識論——作為一個新的知識論分支——更快、更深入地發展。就研究課題和理論主題而言,不但需要特別關注對工程知識、默會知識、操作性知識、具身知識的“相互關系研究”,而且需要特別關注對工程設計知識、工程集成知識、工程管理知識、工程評估知識等的理論研究。有理由預測,工程知識論有望成為21世紀在知識論領域發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二) 展望“知識論2”在21世紀的未來前景
知識論——這里主要指歐洲的知識論——有悠久的歷史傳統。由于多種原因,歐洲的知識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僅僅局限于研究“個體的科學知識”的哲學理論,本文將其稱為“知識論1”。
20世紀以來,“知識論1”的一些重大缺陷和局限性逐漸暴露出來,這就促使幾個新的知識論分支逐漸嶄露頭角。在這幾個新的知識論分支涌現之后,它們勢所必然地要成為人們回顧歷史、評估現狀和展望未來的“新立足點”。站在“新立足點”上,人們不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傳統知識論” (即“知識論1”)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評估知識論的宏觀現狀與形勢,展望知識論的未來方向和前景。
站在“知識論新分支”的“立足點”上分析形勢和展望前景,人們會強烈感受到原先那個“知識論1”正面臨著“歷史性轉型”和“學術體系更新換代”的機遇與形勢——已經有兩千年歷史的“知識論1”需要被“更新換代”為“知識論2”了。
在“知識論2”的視野中,不但需要大力拓展和深化各個“知識論分支” (包括作為“傳統分支”的個體知識論和科學知識論以及作為“新分支”的工程知識論、社會知識論、倫理知識論),而且需要研究“各個不同分支”的“相互關系”,而更關鍵之處是需要在全面思考各個分支的性質、特征和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索和逐步建構“知識論2”的“整體性系統性理論大廈”——這才是21世紀知識論領域最大的挑戰和在展望未來時出現的最激動人心的前景。
如果說傳統的“知識論1”把“確證”當作知識論的主要任務,那么,對于“知識論2”來說,就需要更加關注“設計思維”“操作知識”“程序知識”“人工物知識”“評價知識”“制度知識”“社會知識”“知識要素”“知識集成”“知識系統”“知識轉化”“知識管理”等問題。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21世紀的哲學家應該在“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統一中實現從“傳統的知識論1”向“知識論2”的“轉型”,努力逐步完成為“知識論2”理論大廈“初步奠基”的任務。在本文最后,我愿與知識論領域中進行學術探索的“同道”共同品味王維的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