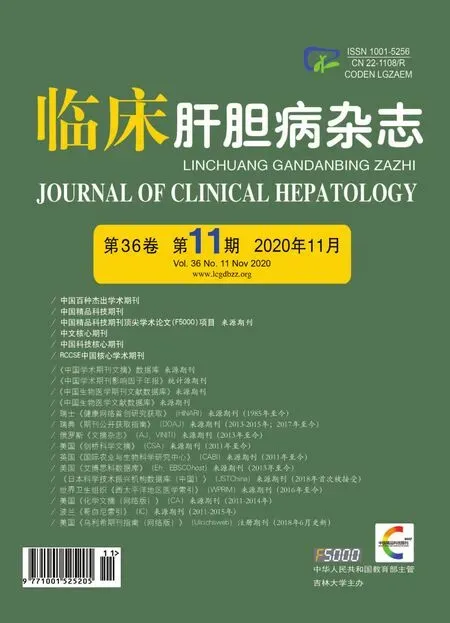高血壓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關系
王 欣, 胡義揚,2,3, 劉 平,2,3, 馮 琴,2,3
1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上海 201203; 2 上海市中醫臨床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1203;3 肝腎疾病病證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1203
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為影響全球約17億人口生命健康的第一大慢性肝病,該疾病譜從單純性脂肪肝擴展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后者可發展為晚期肝纖維化、肝硬化或肝細胞癌[1]。最新Meta分析顯示,我國NAFLD發病率已達29.2%,NAFLD的防治面臨巨大挑戰[2]。此外,很大一部分NAFLD患者存在代謝共病,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肝外癌的風險[3]。高血壓是一種由遺傳傾向和環境危險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多因素疾病,是世界范圍內心血管疾病和早死的主要原因,目前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挑戰[4]。由于NAFLD和高血壓同為代謝綜合征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通常共存;因此,兩種疾病之間的關系受到大家的關注。
本文根據現有研究資料,綜述NAFLD與高血壓之間的聯系,并闡述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的可能共同機制;另外介紹降壓藥在NAFLD治療中的應用現狀,為臨床治療高血壓合并NAFLD提供借鑒。
1 高血壓與NAFLD相互影響
最新流行病學研究[5]顯示,約有50%的高血壓患者患有NAFLD;同時,NAFLD患者的高血壓患病率明顯高于普通人群,并且NAFLD的嚴重程度也與高血壓的發病相關[5-7]。
1.1 NAFLD是高血壓發病的危險因素 一些橫斷面研究[6,8]表明NAFLD的存在和嚴重程度與血壓升高、高血壓前期和高血壓的存在有關。López-Suárez等[5]的研究表明,經超聲診斷的NAFLD患者的高血壓患病率比無NAFLD患者高21.2%,即使在非高血壓患者中,也發現NAFLD與正常高收縮壓獨立相關,但與正常高舒張壓無關。我國的一項調查研究[8]表明,與肥胖NAFLD相比,瘦人NAFLD與高血壓的相關性更強(OR=1.72)。Lorbeer等[6]對384例受試者進行核磁共振肝脂肪分數(hepatic fat fraction,HFF)測定,并研究其與收縮壓和舒張壓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HFF水平與收縮壓和舒張壓呈正相關,門靜脈和肝右葉HFF水平與高血壓的高發率呈線性相關,但肝左葉高水平HFF與高血壓的相關性不強。HFF預測高血壓的最佳有效值分別為肝左葉3.6%、門靜脈5.1%和肝右葉6.8%。
橫斷面研究表明NAFLD與高血壓之間存在相關性,前瞻性研究更能分析兩者之間的具體關系。一項縱向研究[9]分析了肝酶指標、肝臟脂肪指數(fatty liver index,FLI)與高血壓發病的關系,研究人員對2565例無高血壓的受試者進行9年隨訪,結果發現,在隨訪期間共有1021例受試者出現高血壓。校正了混雜因素后,發現GGT和FLI升高與高血壓發病呈正相關,當GGT>30 U/L時可以預測高血壓的發病風險,基線時FLI>30的患者較FLI<30的患者在9年后發生高血壓的風險顯著增加(OR=1.73),而基線時FLI>60的患者發生高血壓的風險更大(OR=3.02)。另一項研究[10]根據FLI將1521例成年人分為無脂肪肝(FLI≤30),疑似脂肪肝組(30
1.2 高血壓是NAFLD發病及進展的危險因素 另外一些研究也同樣證實了高血壓與NAFLD患病的相關性。溫州醫科大學的一項橫斷面研究[13]表明,非高血壓患者血壓水平與NAFLD發病率呈正相關,研究人員將所有非高血壓患者收縮壓和舒張壓分為四個分位,發現隨著收縮壓和舒張壓的升高,NAFLD的患病率也逐漸升高。在另一項包含5362例中年男性和女性的橫斷面研究[7]中發現,高血壓和高血壓前期是超聲診斷NAFLD的危險因素,高血壓前期患者NAFLD的發生率比血壓正常患者高出30%,而患有高血壓的人群NAFLD的發生率則比血壓正常患者高出80%。另外,研究者使用無創性FIB-4危險評分來評估NAFLD患者肝纖維化嚴重程度,結果發現,高血壓患者發生纖維化的風險高于高血壓前期和血壓正常患者。同時,在高血壓患者中,血壓的有效控制也可以對肝纖維化的進展起保護作用。Wang等[14]研究結果表明,高血壓患者NAFLD患病率明顯高于非高血壓患者,同時研究人員將所有836例患者根據ESC/ESH 2007指南分為正常組、正常血壓升高組、1級高血壓組、2級高血壓組、3級高血壓組,結果發現隨著血壓的不斷升高,NAFLD的患病率也逐漸升高。
高血壓患病及嚴重程度除了與NAFLD的發生呈正相關,一些研究發現高血壓還能影響NAFLD疾病的進展。Ma等[15]對1051例受試者(其中有187例患有脂肪肝)進行6年隨訪,結果發現,基線無脂肪肝的864例受試者在6年的隨訪期內有101例發生脂肪肝;調整了混雜因素后發現高血壓和2型糖尿病可以預測NAFLD的發生,特別是舒張壓是脂肪肝發病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因子。另一項研究[16]對NAFLD患者進行肝活檢,研究高血壓與NAFLD肝纖維化之間的關系。該研究對271例肝酶異常且活檢證實患有NAFLD的肥胖患者分別在首次和至少5年后進行兩次肝活檢,其中149例患者分別在5~8年(中位時間為6.4年)內接受了第二次肝活檢,有53%的患者出現了纖維化進展,并發現高血壓和較高的胰島素抵抗指數(homeostatic model assessment-insulin resistance,HOME-IR)是預測肝纖維化進展的獨立危險因素。一項Meta分析[17]納入了11項隊列研究,411例經活檢證實的NAFLD患者,在經過平均3.5年的隨訪后發現,有33.6%的患者出現纖維化進展,并且高血壓與肝纖維化的進展相關(OR=1.94)。基于以上證據,2016年歐洲NAFLD臨床實踐指南[18]建議對NAFLD合并高血壓的患者進行更密切的監測,因為兩種疾病共存會加速NAFLD進展。
2 高血壓與NAFLD相互影響的共同機制
NAFLD與高血壓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性被很多研究證實,哪些是兩者相互影響的可能的機制呢?目前,胰島素抵抗(IR)、腸道菌群和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被認為是可以溝通兩者的共同發病機制。
2.1 胰島素抵抗(IR) IR是代謝綜合征的一個重要特征,與肥胖、糖耐量減低、血脂異常,NAFLD和高血壓有關,其主要標志是高胰島素血癥[19]。IR很可能是二者相互影響最重要的可能機制。
IR在NAFLD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1)升高胰島素和血糖水平,激活碳水化合物反應元件結合蛋白,從而促進葡萄糖轉化為脂肪酸相關基因的轉錄;(2)激活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選擇性地抑制胰島素的降糖作用,促進肝臟脂質從頭合成增加;(3)增加游離脂肪酸的釋放,抑制脂肪酸的β氧化,導致氧化應激;(4)增加肝臟巨噬細胞中促炎因子如:IL-6、TNFα的釋放,引起肝臟炎癥;(5)抑制極低密度脂蛋白輸出[20-21]。
在高血壓發病機制相關研究中發現,IR也是高血壓的一個重要發病機制。其中,胰島素受體底物2主要介導胰島素對腎小管的影響對調節血壓有著重要作用[22-23]。在近端小管中,胰島素可以刺激頂端膜上的3型Na+/H+轉換器和Na-K-ATPase,促進近端小管中鈉的再吸收。另外,胰島素也可以激活上皮鈉通道,進而促進遠端腎小管對鈉的重吸收[24]。以上作用機制均可導致水鈉潴留,使外周循環血容量擴大,進而導致高血壓。除此之外,胰島素通過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途徑誘導內皮細胞產生一氧化氮而引起血管舒張。但在IR狀態下,這一途徑受損,刺激血管收縮,導致高血壓的發生[25]。
2.2 腸道菌群 人體內大約有1014多種微生物,對維持人體健康起著重要作用[26]。近年來,大量研究[27-28]揭示了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物在NAFLD與高血壓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腸道菌群影響NAFLD的主要機制有:(1)腸道菌群過度生長會改變腸道通透性,是內毒素經門靜脈進入肝臟,誘發肝臟炎癥;(2)腸道菌群代謝物短鏈脂肪酸可以影響能量代謝,肝臟免疫和肝臟脂肪沉積;(3)影響膽汁酸代謝,調節法尼醇X受體功能,從而影響NAFLD的發生;(4)影響膽堿代謝,降低膽堿水平,催化膽堿轉化為有毒的氧化三甲胺,促進NAFLD的發生;(5)產生內源性乙醇,促進脂質過氧化以及誘導內毒素血癥[26,29]。近年來,隨著代謝組學的廣泛應用,研究發現,高血壓的發生也與腸道菌群有關。其機制如下:(1)代謝產物如短鏈脂肪酸,氧化三甲胺被黏膜吸收進入血液循環后調控血壓;(2)可以通過影響5-羥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產生,調節鈉代謝影響血壓;(3)通過腸道炎癥和免疫反應調控血壓[28,30]。
2.3 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 原發性高血壓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已知體內有許多系統與血壓的調節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RAAS。它是一種激素級聯反應,負責控制心血管、腎臟和腎上腺功能。該系統由血管緊張素原、腎素、血管緊張素轉化酶、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Ang)及其相應的受體構成。血管緊張素原在腎素的水解下可轉化為10肽的Ang Ι,后者又可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的作用下切去兩個氨基酸轉化為Ang Ⅱ,Ang Ⅱ作用于血管緊張素受體亞型1,產生收縮血管,促進腎上腺皮質釋放醛固酮,增加血容量,升高血壓等作用[31]。Ang Ⅱ 被認為是RAAS對系統性血壓調節的最終效應物,被證實參與了NAFLD發生和發展[32]。其可能機制如下:(1)Ang Ⅱ 可以增加血清游離脂肪酸利用率,減少脂肪酸β氧化,增加脂肪從頭合成進而參與肝臟脂肪合成與代謝;(2)通過抑制肝臟線粒體功能,增加活性氧的產生而引發氧化應激;(3)激活肝臟中TNF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IL-6等促炎因子,誘發肝臟炎癥;(4)激活肝星狀細胞,促進纖維化[33]。另外有研究[34]也證實,激活RAAS系統可以激活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增加肝臟脂質沉積,而抑制肝臟RAAS可減緩脂肪變性與壞死性炎癥的進展,并防止纖維化的發生[35]。
3 抗高血壓藥對NAFLD的治療效果
鑒于NAFLD與高血壓密切相關,并且RAAS作為高血壓最主要的發病機制,也參與了NAFLD的發生。因此,許多臨床試驗通過RAAS抑制藥及利尿劑觀察其在降低血壓的同時是否也對NAFLD有治療作用(表1)。
Polyzos等[36]對活檢證實的NAFLD患者使用螺內酯聯合維生素E治療52周后結果顯示,聯合用藥可降低HOME-IR和脂肪肝評分。RAAS在NAFLD和高血壓的發生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RAAS抑制藥(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和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對NAFLD患者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治療選擇[39]。在一項小型臨床研究[37]中,7例患有NAFLD合并高血壓的患者服用氯沙坦治療48周。通過肝活檢,觀察到患者肝功能顯著改善,5例患者炎癥評分下降,4例患者纖維化分期改善。此外,Georgescu等[38]對54例患有NAFLD合并高血壓的患者被分配接受纈沙坦或替米沙坦治療。經過20個月的隨訪,通過組織學檢查進行評估顯示,兩種藥物均能改善IR和肝纖維化,但替米沙坦療效更好。然而,以上臨床結果均來源于小型隨機研究。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和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的廣泛應用是進行大規模隨機研究的一個障礙。最近的一項隨機雙盲對照試驗[40]旨在研究214例經組織活檢證實的NAFLD患者服用氯沙坦的抗纖維化作用,但是由于一部分患者在招募階段已經服用降壓藥,因此實驗最終失敗。
4 小結
本文綜述了高血壓與NAFLD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相互影響的可能機制,同時介紹了降壓藥在NAFLD治療中的應用。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發病有很強的關聯性,NAFLD是高血壓發病的危險因素,高血壓不僅是NAFLD發病更是其進展為肝纖維化的危險因素。IR、腸道菌群的改變,以及RAAS可能是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的共同可能機制。在NAFLD治療方面,RAAS抑制劑主要是ARB已進行了相關臨床試驗,其可以通過減輕肝脂肪變性,改善肝功能,抑制纖維化進展,從而對NAFLD起到良好的治療效果。

表1 抗高血壓藥治療NAFLD的臨床療效
目前關于兩者關系的臨床研究包含了疾病不同嚴重程度的個體,同時應用了超聲、核磁共振、肝活檢等多種診斷工具,并且具有肥胖、2型糖尿病、IR和種族等殘余混雜因素,這些都對二者關系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今后的研究應該以組織學作為NAFLD的診斷標準,同時基于大規模、長期的前瞻性研究,排除潛在的混雜因素,進一步明確證明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時,深入了解NAFLD與高血壓相互影響的機制,這將有利于新藥的研發,這也是NAFLD合并高血壓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作者貢獻聲明:王欣負責撰寫論文;胡義揚、劉平負責審校;馮琴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