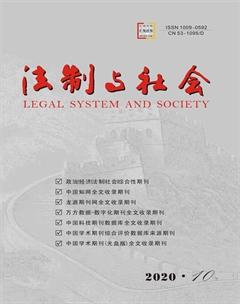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基礎
徐玉生
關鍵詞認罪認罰 契約性 可期待利益
2019年10月最高法、最高檢察、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較全面的規范了認罪認罰具體實施辦法。但是,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否具有契約屬性不明確,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具結書的法律定位不明,尤其是當事人反悔后對案件的處理,以致出現不同法院出現“同案不同審”。筆者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建立在被追訴人與公權力機關互相信任、彼此協商的基礎之上的,即契約性基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基礎如下。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主體
認罪認罰制度主要表現方式就是具結書的簽署,從外觀上看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署人只有被追訴人單方簽署,因此有學者認為可以把認罪認罰具結書視作被追訴人的單方聲明書,只要一審法院還沒作出判決,就允許被追訴人撤回認罪認罰具結書。如果這樣理解,那么具結書對被追訴人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與強制力。抑或把認罪認罰具結書當作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保證書,其只對被追訴人有法律約束力與強制力,要求被追訴人不得隨意變更或撤回具結書。如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缺少契約所應具備雙方的主體性,那么被追訴人所追求的“從寬”將無相對方可協商,自然導致“從寬”待遇無處索取。筆者認為公權力機關、被追訴人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主體,被追訴人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就是雙方達成協議的書面契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簽署的具結書是被追訴人與國家之間的書面契約,具有法律約束力,契約雙方均有義務履行和遵守契約。如果拋開認罪認罰案件的公權力屬性,那么控辯雙方為了達到協商一致的目的,其雙方地位應盡量平等,這樣才能平等對話。陳瑞華教授認為如果契約要取得相應的平衡結果,那么契約雙方就應具有基本均衡的信息來源以及大體相同的知識技能和彼此尊重對方選擇的可能性。目前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書主要以制度的設計保證最低限度的平等性,相關認罪認罰具結書的配套文書都是為了保證被追訴人的信息知曉權利,保證協商雙方大體平衡的信息來源。再如值班律師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都是為了保證被追訴人不因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欠缺而導致對協商內容產生誤解。在訴訟職權主義的我國,嚴格來說代表國家的公權力的檢察機關不能與被追訴人進行認罪認罰從寬協商,但是隨著社會人權理念的發展,人權理念理已然被我國法律體系所接受,被追訴人的訴訟主體地位逐漸升高,平等對話的可能性已經建立,打破了我國傳統的刑事訴訟職權主義模式。控辯雙方的地位平等與合同雙方主體的平等相似,只有先構建“邀約”的契約性主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才有“合約”的主體表達性。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內容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內容為協議的達成以及司法資源的節省創造基礎性條件。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然存在著“交易”“協商”屬性。在經濟學領域交易為社會創造財富,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論述了交易是如何讓社會財富增加的。
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交易”,而“交易”的進行可以節省司法資源,從總體上來說也屬于創造了財富。顧永忠教授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吸收了美國辯訴交易的合理成分”,英美當事人主義理論框架下的辯訴交易,交易雙方可以達成合意,訴訟標的或有關權利當事人可以進行處分或放棄。
從訴訟標的角度出發,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包括訴訟程序上的從簡以及實體裁量上的從寬。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內容具有“可交易”性,“程序從簡”可以提高司法效率,緩解現階段我國的“案多人少”窘境,從經濟角度出發自然節省了社會資源;“實體從寬”給了被追訴人可期待利益,“從寬”當然是被追訴人的契約內容。“程序從簡”與“實體從寬”可以看成契約雙方協商的“籌碼”,在雙方各取所需,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情況下雙方進行博弈,最終以將協商內容訂立,達成契約。
程序從簡包括未決前的有關強制措施,這符合我國認罪認罰制度的全覆蓋性,即從偵查到審判均允許認罪認罰,有學者認為未決羈押限制了被追訴人的人身自由,也限制了被追訴人獲取案件信息的相關渠道,如有學者認為被追訴人作出認罪認罰決定時應保證其人身處于相對自由的狀態。。審前的強制措施是被追訴人與公權力機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內容,《指導意見》以專章規定了強制措施的適用,如第20、21條逮捕的適用與逮捕的變更。強調強制措施的適用以及建議及時變更,說明為了達到“可契約性”,審判前的強制措施適用是被追訴人最終能否從寬的“晴雨表”。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體制中,雖然罪名、量刑是以審判為中心,但是認罪認罰的協議達成是在起訴階段,甚至可以提前到偵查階段。在具結書的簽署過程中,被追訴人與檢查機關是主要的參與者,這種制度的設計符合我國的職權主義模式、以審判為中心模式。從《指導意見》的總體框架來看,在認罪認罰后“從寬”的把握里并沒有把強制措施的適用、變更歸入“實體從寬”,筆者認為應該把強制措施歸入“從寬”,因為強制措施從寬對被追訴人來說是實際意義上的“從寬”。
首先,強制措施的適用、變更是被追訴人享受從寬待遇的伊始。雖然審前羈押屬于確保被追訴人及時到案,案件的審理可以順利進行,本質上不屬于刑罰,但是對于被追訴人來說就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如果以自由來衡量,那么審判前的強制羈押措施就是刑罰“提前”實施。況且對于審前的實際羈押,在判決后可以折抵部分自由刑的刑罰,被追訴人可能更倚重審前強制措施的從寬,因此為了具結書的從寬待遇的“徹底”履行,那么就有必要把強制措施歸入“從寬”的范圍。
其次,強制措施的適用、變更適用是司法機關“節約司法資源”“緩和社會矛盾”的部分契約性內容。“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
因此,刑事司法體系的目標應包括程序效率與成本。速裁程序與簡易程序在案件審理時間、審理人員數量也做簡化規定,符合從時間的效率上最求司法正義。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可期待利益性”契約基礎
被追訴人希望通過認罪認罰獲得從寬,公權力機關希望通過認罪認罰節省司法資源,雙方所具有的可期待利益是具結書的簽署基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自由”“平等”“安全”以契約的方式組合成可期待利益,并在各方的參與下保證制度的切實可行。
首先,“自由”是可期待利益的主要成分。“自由”即是司法機關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可讓與待遇,也是被追訴人期待的利益。如前文所述,“自由”也表現在對審前強制措施的選擇適用上,既然認罪認罰從寬最終是表現在裁判結果上,那么在調查評估被追訴人的社會危險性后,在結果可預期時,提前將審判結果提前“兌現”,這種“兌現”在偵查、起訴階段自然具有可行性,即可節省司法資源,又可給被追訴人從善的動力。
其次,“平等”是可期待利益的對話基礎,在實踐中“坦白從寬”制度難以實現,大部分與“平等”有關,被追訴人不信任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的契約性承諾,進而產生抵觸情緒,最終導致案件在證據的形成、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獲得上消耗更多的司法成本。認罪認罰制度將可能的罪名與量刑幅度或者明確的量刑建議呈現給被追訴人,減少了被追訴人對案件審理結果不確定性的擔憂,根源上減少了被追訴人反悔或撤回認罪認罰的可能性,自然減少了司法資源的耗費,也減少了刑訊逼供等冤假錯案的產生。“平等”可視為國家公權力姿態的“放低”,將被追訴人視為可對話協商的相對方,既符合現今人權保護的觀念,也符合現階段刑訴法對裁判“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要求。
最后,“安全”是可期待利益是否具有可獲得性的衡量標準。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安全”體現在審前羈押、受害人諒解、審后被追訴人對刑罰的接納性態度,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圍內,可以與被追訴人進行強制措施的選用協商。評價“安全”標準的高低經常以“社會危險性”來衡量,《刑訴法》也以“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為界限作為適用速裁的條件,將社會危險性進行明確的劃分,進而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最終節省司法資源的目的。
四、結論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契約性基礎存在,表明認罪認罰具結書具有契約性,而契約一旦達成則不允許任意一方隨意反悔,在保證認罪認罰具結書簽署時的真實性、自愿性、合法性之后,具結書的簽署自然具有高度的雙方合意,理應高強度的約束契約雙方。在認罪認罰的制度設計上可以增加雙方的毀約成本,以改變現階段只注重程序反轉,而輕視違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