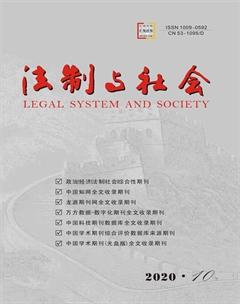論監察調查中律師介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崔宇笛
關鍵詞監察 辯護 可行性 必要性
一、律師介入調查程序的必要性研究
(一)被調查人在調查程序中處于弱勢,需要法律幫助
首先,被調查人一般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在被監察委采取強制措施后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因此,若賦予律師在調查程序中介入的權利,將能平衡被調查人與監察委之間的力量不對等,提升被調查人對監察委的防御能力。
其次,在法律賦予律師介入調查程序之后,律師能夠為被調查人申請排非。在僅允許律師介入調查程序且不進行其他立法修改的情況下,律師可以依據《高檢規則》第65條“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應當依法排除……不得作為移送審查起訴……的依據”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調查階段申請排非具有重大意義,其能夠盡早地發現并否認通過非法途徑收集的證據,防止其流入后續程序對被調查人造成人身、財產的損失。因此,盡早地排非能夠預防冤假錯案的再現,更好地維護刑事訴訟環境和社會秩序。
最后,目前學界存在調查權即偵查權的學說,如人民大學的陳衛東教授、清華大學的張建偉教授、四川大學的龍宗智教授等,筆者認同并支持此觀點,因為二者在時問、目的、手段上存在較大程度的吻合。如龍宗智教授所言:“職務犯罪調查具有犯罪偵查之實,而無犯罪偵查之名。”進而,主張此觀點的律師便可以在對《刑訴法》條文解讀時將“偵查機關”“偵查人員”與“監察機關”“監察機關辦案人員”進行等量代換。再以《刑訴法》第4l條為依據,在調查程序中搜集可能在審查起訴階段申請檢察院補充移送前程序中遺漏的有利被調查人的證據,以此來保護被調查人權利,約束國家公權力。
(二)《監察法》的排非規定存在疏漏,被調查人的權利遭受威脅
《監察法》對于防止監察委非法取證只有第33條后半部分原則性的規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案件處置的依據。”和第40條后半段的:“嚴禁以威脅、引誘、欺騙等其他方法收集證據,嚴禁侮辱、打罵、虐待、體罰或者變相體罰被調查人和涉案人員。”既有規則又有原則,這看似是很完善的排非規定。
首先,筆者對上述規范的意義表示肯定,因為其對于排除非法供述而言著實完善,但其似乎對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實物證據不太適用。因為若監察委想偽造或者以非法方法收集書證、物證,其無需威脅、引誘、欺騙、打罵被調查人。這就意味著監察委雖然不能以打罵、威脅、引誘等方式收集供述之類的言詞證據,但對于搜集其他實物證據而言,當前并沒無其他具體的法律規則來制約他,唯有《監察法》第33條后半段的法律原則能夠起到較為薄弱的作用。而當這些證據收集完成后,完全可以與其他合法的供述一起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這對于被調查人而言是非常大的威脅。
(三)維護刑事訴訟程序正義
程序法治,是指通過構建和完善程序法律制度來實現國家法治目標的模式,其核心是程序正義。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專家武欽殿法官曾說:“程序正義是結果正義的前提”。筆者認為,當刑訴程序偏離了程序正義,結果正義將失去最基礎的制約,社會秩序與公平正義將無法得到保障。在《監察法》出臺前,職務犯罪偵查權歸檢察院享有,且此程序允許律師介入,受律師的監督。但在《監察法》出臺后,職務犯罪調查權歸監察委享有,律師不再被允許介入,其律師幫助權被剝奪,監察委也失去了來自律師的外部監督,其惡果是職務犯罪案件辦案程序不透明,非法取證如刑訊逼供的滋生,甚至最終冤假錯案率的升高。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缺乏律師介入的調查程序會影響監察委員會的公信力,不利于在社會中形成信仰程序正義的良好法治風氣。不僅如此,調查程序與偵查程序在法條上存在的明顯差異將會影響當前正在進行的兩法銜接工程的效率,延緩刑訴體制改革的進程。由此可見,允許律師介入調查程序是一件法治行動,其能夠更好地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程序正義。
二、律師介入調查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一)現行法條存在律師介入的法理可能性
首先,調查活動應受何種規范調整?通過對比《監察法》與《刑訴法》在職務犯罪刑訴程序中的職能,筆者認為《監察法》規定的調查活動是職務犯罪刑訴程序中的一個子環節,《刑訴法》則是統領整個刑訴程序的母法。因此可以將它們視為調整刑事訴訟的“根本法”和“基本法”,這也意味著調查活動需要受雙重約束。同時,《監察法》中有關調查的規定又像是為追訴特定犯罪活動的“特別立法”,《刑訴法》中的偵查章節則是為打擊一般罪名而設立的“一般法”。正因為一般法有著為特別法補漏的功能,如《合同法》有著對《海商法》關于海上貨運合同權利義務的空白進行補充的作用,筆者便將《刑訴法》第14條中關于公檢法三機關保護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法律原則補充到職務犯罪辯護中來了。這樣,即使在職務犯罪刑訴程序中不存在公安機關,檢察院仍需依據本條保障被調查人的辯護權,并且本條并沒有限定辯護權存在的時間,因此律師在調查階段可向檢察院主張此法條,便依法有權進入到調查階段為被調查人提供法律服務了。
誠然,會有反對聲音基于《刑訴法》第34條第二款“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內,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予以反駁,但此條是在規定審查起訴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該如何保障自己的辯護權,這和審查起訴前被調查人如何保護自己的辯護權不沖突。
(二)律師如何介入調查程序的構想
1.關于律師介入時間點的構想
我國《刑訴法》規定,一般犯罪嫌疑人有權申請辯護的時間起點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筆者認為若未來《監察法》將律師介入調查程序寫入其中,可以規定被調查人在被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有權申請辯護與法律幫助。
首先,基于被調查人的需求而言,在被監察委采取留置措施之前,被調查人并不需要較強程度的援助。如在談話、進行自我陳述等程序中,被調查人受到的人身自由限制較少,心理壓力較小,被調查人可以通過自身能力對自己的權利進行初步保護。然而,若被調查人被監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其將面臨被限制在留置場地的局面,其人身自由將會被較大程度地剝奪,不僅如此,被調查人與外部環境的交流機會和自由度也會被壓縮,這將導致被調查人與監察委問的信息不對等逐漸被拉大。監察委非法取證的可能性也會隨之被加大。
其次,從實踐經驗來看,自從2012年《刑訴法》修改以來,增強律師在刑訴程序中的介入對我國人權保護意義重大,在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律師能夠在偵查階段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偵查階段申請逮捕羈押必要性審查,同時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申請變更強制措施。這雖不能讓所有委托人都能得到撤案、不起訴或宣告無罪的結果,但這能保障讓無罪的嫌疑人盡快得到法律的肯定,讓有罪的嫌疑人得到應有的權利保障。律師在刑訴程序中的介入已然成為公平與正義的降臨,在我國刑事訴訟司法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對于時間點的構想同樣可以借鑒域外經驗,比如。香港《廉政公署(被扣留者的處理)令》第四條中表明:“(1)被扣留者須獲給予合理機會,以便與法律顧問通訊,并在一名廉署人員在場但聽不見的情況下與其法律顧問商議,除非此項通訊或商議對有關的涉嫌罪行的調查或執法會構成不合理的阻礙或延遲。”香港特別行政區允許律師在當事人被“扣留”后介入程序。“扣留”與“留置”含義近似,皆意在將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在特定時間與地點內進行適當限制。故我國《監察法》在未來修改時,可以此作為參考。
2.關于律師介入內容的構想
(1)會見通信權。不論是在一般刑事犯罪刑訴程序,還是在職務犯罪刑訴程序中,會見權是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基礎。假設允許律師介入但未賦予其會見權,律師仍無法了解到偵查機關或是監察委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的線索,進而無法申請監察委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不僅如此,假如不賦予律師與職務犯罪被調查人會見的權利,律師還無法得知強制措施的適用是否存在違反程序正義的情形。再退一步講,律師若沒有會見權,僅憑當事人的電話轉述與家屬轉述,其甚至無法全面了解案件真相,為委托人提供正確、有效的法律幫助。因此,筆者認為,保障律師的會見權是架構律師介入內容的首個步驟。
(2)調查取證權。假如僅賦予律師介入的權利但未規定其享有調查取證權。則律師在現行《監察法》創設的司法環境下仍無法獲取能夠證明被調查人無罪、罪輕的證據。因為《監察法》未規定律師在監察委調查取證時能夠在場,進而律師無法發覺監察委是否在收集能夠證明被調查人有罪、最重的證據的同時收集了能夠證明其無罪、罪輕的證據。因此,律師從而無法預判下一步是否針需要在審查起訴階段申請檢察院補充移送監察委搜集的,對被調查人有利的證據。這不利于保護被調查人的權利,并且會使律師陷入能夠介入調查但卻無能為力的窘境。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另一方面能夠加強被調查人方的力量,使其可以防御監察委的非法取證,并對監察委證明力不足的證據鏈進行攻擊。更深層次地講,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則可以倒逼監察委強化自身辦案質量,確保職務犯罪刑事訴訟程序的高效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