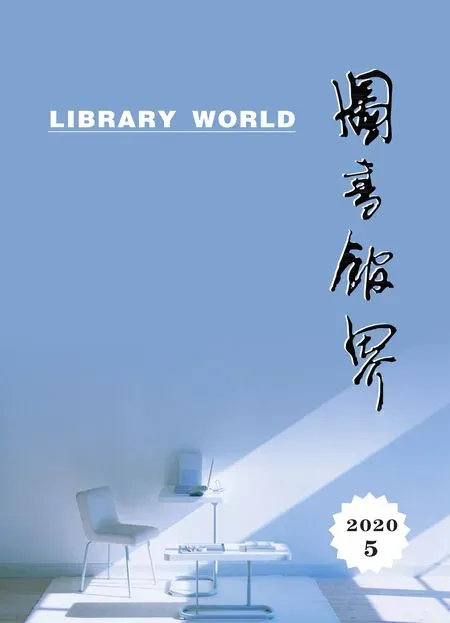點亮童夢:鄉村民間圖書館融入鄉村兒童閱讀生活研究
張書美
(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江西 南昌 330022)
民國時期著名圖書館學家李鐘履曾言:“城市里之圖書館,猶如錦上添花;鄉村里之圖書館猶如雪中送碳(1)此二處“碳”字應為現代漢語中的“炭”,即“雪中送炭”。。錦上無花,不失其綺麗;而雪中無碳(2)此二處“碳”字應為現代漢語中的“炭”,即“雪中送炭”。,則凍餒相隨矣。”[1]短短數言,深刻揭示了鄉村圖書館的社會功用。但無論是在遠去的民國,還是在經濟文化高速發展的今天,那些交通不便、經濟落后的偏僻農村仍處于公共文化服務網絡的末端,成為公共文化均等服務的痛點。為了彌補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一些鄉賢在當地創辦民間圖書館造福桑梓,為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山區的公共文化空間再造,鄉村文化火種保存、基層文化均等服務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助力鄉村兒童閱讀方面,鄉村民間圖書館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放眼我國廣袤的鄉野大地,一所所民間圖書館恰似那星星點點的知識明燈,照亮了鄉村兒童的未來之路。
1 我國鄉村兒童閱讀困境分析
1.1 鄉村兒童閱讀資源相對貧乏
2018年的《鄉村兒童閱讀報告》以中西部貧困農村兒童閱讀現狀為聚焦點,揭示了受訪兒童年課外閱讀量及其家庭藏書情況。大部分農村兒童年閱讀量少于10本,近20%的鄉村兒童根本沒有閱讀過課外書[2]。當城市兒童對海量閱讀資源目不暇接時,不少鄉村兒童的閱讀還停留在簡單的課本和教輔類圖書上。與城市同齡兒童相比,閱讀資源貧乏已成為制約鄉村兒童閱讀能力及身心發展的極大瓶頸。
雖然,近年來隨著農村教育扶貧政策的實施和社會公益力量的介入,一些鄉村學校的圖書室、圖書角也漸漸充實起來,但外來的閱讀資源能否接地氣,能否真正融入當地鄉村兒童的日常閱讀中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畢竟,有時甘甜的“淮南之橘”在不同的環境下容易變成苦澀的“淮北之枳”。
1.2 鄉村兒童閱讀熱情不高
2018年的《鄉村兒童閱讀報告》顯示,鄉村兒童對課外書的態度呈現出較為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超過2/3的鄉村兒童表示喜歡閱讀課外書;另一方面,鄉村兒童實際課外閱讀量卻很低,年閱讀量絕大多數低于6本[2]。這種矛盾的現象背后,固然有閱讀資源貧乏的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兒童閱讀熱情不高所致。他們喜歡的圖書學校圖書館鮮有入藏,因為閱讀環境的問題,除了必讀書目之外,沒有更好的、能讓他們自由閱讀的條件,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磨滅了他們的閱讀興趣。閱讀內容及要求過于“標準化”,根本沒有顧及鄉村兒童多元化的閱讀興趣及對寬松閑適閱讀環境的需求[3]。上述種種原因,使得學校圖書館即便有萬卷叢書,也難以避免門可羅雀的冷清。
在當下新農村建設中,一些基層政府著力發展地方經濟時,也在關懷鄉村兒童文化生活。例如,通過建設“留守兒童書屋”來豐富鄉村兒童的閱讀生活,滋潤留守兒童的心靈。這本是改善鄉村兒童閱讀境況的大好之機,卻存在人書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在農村大環境催生的種種功利目標下,鄉村兒童難以對閱讀產生濃厚興趣。
1.3 鄉村兒童家庭閱讀環境缺失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站,也是閱讀的第一個場所。2016年發布的《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大力倡導家庭閱讀、親子閱讀,呼吁父母和未成年人監護人發揮言傳身教的作用,號召全社會攜手共建少年兒童的良好閱讀環境[4]。但鄉村兒童的課外閱讀普遍缺少家長的參與和陪伴,這種現狀不僅廣泛存在于我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在經濟發達的東部農村也并不罕見。鄉村兒童的父母因為生活需要,其中一方或雙方選擇外出打工,導致兒童被動留守比例較高。即便留守在家的父母也極少有意識地陪伴孩子閱讀,有近90%的農村兒童父母自己平時從不讀書,這種患“閱讀恐懼癥”的父母又豈能發揮閱讀的示范引領作用?“大部分鄉村家庭或家長在兒童課外閱讀中普遍缺席”[2]是普遍現象。
其實,親子閱讀最重要的不是讀了什么,而是父母與孩子之間有了近距離的接觸,可以更有效地進行情感溝通,這種無言的陪伴對于孩子完整人格的塑造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知名兒童閱讀專家錢伯斯在他著名的“閱讀循環圈”理論中指出,在兒童的閱讀過程中,一個有協助能力的成人不可或缺,而這個有協助能力的人,或是家長,或是老師。與將絕大部分家庭資源都傾斜給孩子的城市家長相比,身處鄉村的家長習慣性地將教育的責任完全推給老師[5]。鄉村兒童閱讀依靠家庭無望,單純依賴學校也不通,亟須多方力量的關注,如鄉村民間圖書館的閱讀援助。
2 鄉村民間圖書館融入鄉村兒童閱讀生活的可能性
2.1 鄉村民間圖書館與鄉村兒童閱讀存在閱讀心理上的高度契合
閱讀的世界是人出于追求自由的本性,而在精神文化活動中開辟的一塊神圣的領地[6]。兒童的年齡特點,決定了其思維具有童話般的色彩和夢幻般的心理需求。閱讀這一具有內化性的行為,可以較好地滿足兒童想象的空間。對于孩子的內心,好的書籍與游戲同樣重要,他們也是孩子身心健康發展重要的閱讀主體[7]。通過對全國絕大多數的鄉村民間圖書館讀者群體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兒童已成為最重要的閱讀群體之一,特別是在寒暑假,各地的鄉村民間圖書館更是成了孩子們的集聚地。正是兒童對公共文化產品的強烈需求,使得包括興辦圖書館在內的社會公益行為有了實施的社會基礎。
鄉村民間圖書館多由鄉賢創辦,其公益性特點極為鮮明。它的出現為鄉民提供了健康的文化娛樂及知識服務,給貧困地區的留守兒童帶去了溫暖和智慧。面對處于公共文化服務匱乏的鄉村,面對屬于弱勢讀者群體的少年兒童,鄉村民間圖書館文化扶助的意愿就更為強烈[8]239。此外,鄉村民間圖書館針對兒童的種種閱讀公益活動,其性質還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與學校閱讀的強制性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寬松與純粹的閱讀更受到鄉村兒童的歡迎[9]。鄉村民間圖書館與鄉村兒童在閱讀心理上的高度契合,為充實和豐富鄉村兒童閱讀生活提供了無限可能。
2.2 鄉村民間圖書館具備融入鄉村兒童閱讀的物質基礎
鄉村民間圖書館館址的選擇大多是依校傍路的位置,例如,山東小河圖書館就坐落在山東沂南曹家小河村中心主路旁,鄰近劉家嶺村和杜家洼村小學。據不完全統計,小河圖書館十年來借閱人數超萬人次,附近各村的孩子占據了絕大多數。小河圖書館因時常更新的圖書以及便利的閱讀環境,成為周邊孩子們閑暇時最喜愛的鄉村文化空間[10]。廣西東蘭縣健將圖書館坐落在通往委榮小學必經之路的村路邊,因離小學近,小學生們常常三五成群,徜徉在圖書館里沉沉不知歸[8]43。
鄉村民間圖書館不僅在館址的選擇上主動靠近兒童,而且在圖書入藏方面也能精準定位。例如,在河南平輿縣寧莊村趙彥良書屋,考慮到該村的閱讀人口以留守兒童為主,館長趙彥良一方面加大兒童讀物的收藏力度,另一方面著力改善書屋的閱讀環境,努力滿足留守兒童的閱讀需求。可以說,鄉村民間圖書館的客觀存在及其設施的逐步完善,給鄉村兒童的童年增添了些許墨香與夢想。
2.3 鄉村民間圖書館館長具有播種鄉村文化的公益自覺
全國各地鄉村民間圖書館館長群體心懷善念,內心充盈著播種文化的公益自覺,克服缺資金、缺資源、缺人才的種種困難,靠著對文化的執著與堅守,在窮鄉僻壤的山溝中,拼盡全力播下一粒粒智慧的幼芽,期待有一天他們會長成參天大樹。鄉村民間圖書館館長對自身文化播種人的身份認同和公益自覺,是其開展鄉村兒童閱讀服務的情感基礎。
例如,地處偏遠山區的江西凈坑書舍館長曹煌春,1987年開始自籌資金創辦了老崗村的首個家庭圖書館——凈坑書舍,免費服務鄉民。凈坑書舍的出現凈化了村民賭博的不良風氣,孩子們在上山捉鳥、下河摸魚之余,更多的是結伴來書屋閱讀的場景。2006年,時任中央文明辦協調組組長涂更新專程來到凈坑書舍,他對曹煌春免費辦館服務鄉梓的精神贊譽有加:“這么多年,沒要國家一分錢,自己想辦法辦起了這么一個書屋,讓農村群眾有一個汲取精神食糧的好去處,真不容易”。像曹煌春這樣傾一腔熱情盡一份責任、克服困難辦好書屋、傳播知識服務鄉民的鄉村民間圖書館館長還有許多。他們對播種鄉村文化的那份責任與自覺,使鄉村兒童課余假日才有處可歸、有書可讀、有心可依。
3 鄉村民間圖書館融入鄉村兒童閱讀生活的路徑
3.1 用產生共情的讀物吸引鄉村兒童閱讀
兒童讀物的選擇是兒童閱讀活動中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錢伯斯指出,選書是“閱讀循環”的第一個步驟,是閱讀活動的開始,也是后續良好閱讀習慣養成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1]。因此,針對不同的閱讀對象,選擇適合的讀物就顯得至關重要。鄉村兒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處于好奇心強烈的幼童年時期,卻生活在信息相對閉塞的鄉村。鄉村民間圖書館在選擇兒童讀物時,需要根據鄉村兒童的特點,進行更細心的選擇。除了考慮鄉村兒童的年齡、性別及心理發展水平等基本問題,還要兼顧他們的興趣愛好及生活經驗,特別是能產生共情體驗的生活經驗,這對吸引他們的閱讀注意力頗為有效[11]。
生活環境對兒童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巨大的,對于鄉村兒童來說,他們更青睞于閱讀表達剛毅、陽光、自信、鄉土及獨立理念的文本。這是因為兒童在閱讀時會經歷一個文字和圖像解碼的過程,他們常將書中的內容與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凡是不能喚起直接經驗的閱讀對鄉村兒童而言都是抽象和困難的[12]。真正持續且深層的閱讀動力,往往來自共情體驗。其實,我們在閱讀外面世界的同時,也是在閱讀自己的經歷和內心,相似的生活場景及人生經歷更能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引起共鳴。所以,鄉村民間圖書館在采選兒童讀物時,要多關注那些能夠激發鄉村兒童共情體驗的圖書。
3.2 用活泛的閱讀活動激勵鄉村兒童閱讀
習近平總書記說:“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人得到智慧啟發,讓人滋養浩然之氣。”如今全民閱讀現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連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堅持少兒優先,保障重點”[13]的發展導向對發展兒童閱讀事業意義重大。從宏觀層面來說,無論是國家還是教師、家長對少兒閱讀都非常重視,但是具體到微觀層面卻存在這樣的認知誤區,即“簡單地將閱讀作為教會兒童識字的工具,或過早強調將兒童的讀書活動作為兒童獲取信息和知識的主要工具”[5]。兒童研究專家舒華認為,這是中國兒童早期閱讀存在的最主要問題。教師及家長的功利性閱讀導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制約了兒童的閱讀興趣,特別是在閱讀資源本就貧乏的鄉村這種問題更加突出。
而那些純粹為了播種文化的鄉村民間圖書館,因地制宜、因時而動推出了一系列頗具特色的閱讀推廣活動,則無心插柳地激發了鄉村兒童參與閱讀的興趣。例如,廣西天等縣鹿溪公益圖書室,以貧困山區青少年弱勢群體(包括孤兒、留守兒童和貧困學生等)為主要關注對象,除了堅持圖書室常規“陣地服務”,還積極開展輻射鄉村的“延伸服務”:到偏僻的山村建立愛心流動圖書角;用大篷車將豐富多彩的閱讀活動送到大山深處的留守兒童身邊;舉辦主題讀書會、“最美家鄉”征文征畫成果展、城鄉小讀者聯誼會、暑期快樂英語學習、關注孤兒成長的交流聯誼活動等豐富多彩的閱讀活動,既融入了農村兒童的生活,也滋潤了他們的童心[8]180。
3.3 借力公益組織促進鄉村兒童閱讀
許多鄉村民間圖書館雖然有敬業樂業、無私奉獻的館長勉力維持,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公益性的鄉村民間圖書館若僅靠館長一己之力,很難開拓更多創新業務。因此,鄉村民間圖書館亟須借力公益組織促進鄉村兒童閱讀事業。有些組織協調能力強,經濟實力雄厚,公益意愿明顯的民間公益組織,以廣大貧困山區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致力于基層文化事業的發展,其機構宗旨與鄉村民間圖書館不謀而合,這為鄉村民間圖書館借力公益組織提供了良好契機。
目前,我國民間公益組織援建鄉村民間圖書館的模式主要有獨建、捐建、合建等形式。無論何種模式,每個公益組織都希望能從自身專長出發,深度參與鄉村民間圖書館的建設。他們各有特色,在調動、運用社會資源方面,互相聯手,互相借力,協同作戰。他們在民間圖書館的建設、管理及服務中發揮各種潛能,創造出一般公共圖書館所不可能完成的業績[14]。這正是鄉村民間圖書館借力發展的良機。
事實上,一些信息敏銳的鄉村民間圖書館人已積極行動起來,向相關公益組織提交兒童閱讀項目資助申請。例如,河北“農家女書社”創辦人房紅霞于2015年9月提交的鄉村家庭閱讀點建設項目得到了“合萬邦小微公益基金”的資助。該項目是以鄉村民間圖書館為“根據地”,在北永安村挑選適宜的8個家庭(特別是有留守兒童的家庭)建立家庭閱讀點,使其成為鄉村圖書館的“末梢神經”[15]。家庭閱讀點以自家為軸心,向同學、朋友、鄰居輻射,形成了一個“以家庭帶動鄰里,共同悅讀”的尚讀文化圈,對改善和優化鄉村閱讀環境起到了以點帶面的作用。
4 結 語
鄉村民間圖書館的創辦者大多是來自本土有文化、有抱負的鄉賢,他們自覺擎起“山村文化播種人”的火炬,主動聯系公益組織壯大力量,大力收藏適宜的兒童讀物,深入家庭拓展服務陣地,積極融入鄉村兒童閱讀生活。鄉村民間圖書館開展的眾多貼近鄉土、富含地方特色的服務活動,最終為當地閱讀環境帶來了根本性改變,有力助推了鄉村兒童閱讀環境的改善。隨著國家公共文化政策的逐步實施,公共文化服務必將逐步深入城鄉基層,鄉村民間圖書館的服務空間肯定會受到不小沖擊。但“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迎來“機”,鄉村民間圖書館也要善于在“危”中求“機”,正如遼寧莊河農民科技書屋就積極融入公共圖書館分館建設的時代潮流中,借著與大連少兒圖書館業務合作之東風,解決了自身新書更新的后顧之憂。可以說,正是鄉村民間圖書館常年默默無言的文化堅守,才讓鄉村兒童飛翔的夢想多了一絲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