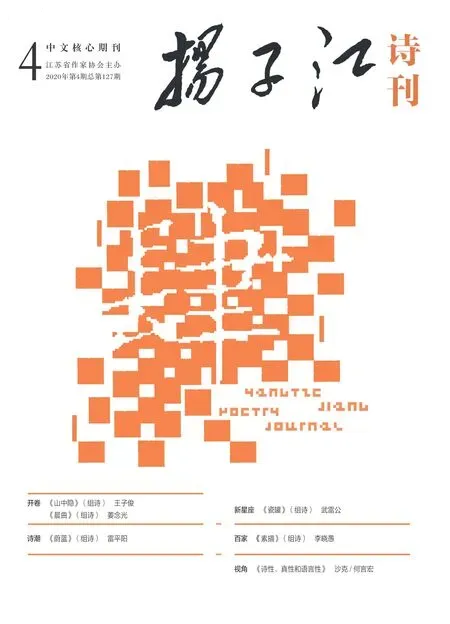山中隱(組詩)
王子俊
在云南和四川分界的山脊上,如果風從云南吹出來
花一天的時間驅車
基本上就能把諸山
轉繞一圈。
但我更喜歡一早就獨坐在云南和四川分界的
山脊上,
等那些云南的風,
沿相同的路徑,翻山越嶺地過四川來。
我也一直在等,那些陡坡上,
一抱粗的云南松,
展開,撲打。
在我看來,它們多像一群啞巴,
“想到自己的一生”
就握緊拳頭,
拼命捶打自己的胸脯。
……兩省的地盤上,緩慢吃草的云南矮腳馬
似乎沒想做出選擇。
那些來自馬群們變化的
影子,
仿佛一生也只習慣于捕撈自己的身體。
與靈山寺的烏鴉相遇
我和剃度了三年的比曲小師兄,
坐在靈山寺最舊的那個庭院,白條凳上。
陽光那么暖,
老方丈敲了三下銅鐘,
那多年久違的烏鴉,嘶啞著呱聲,就過來了。
是三只靈山寺涼滑天空掠過的烏鴉,
是黑而不是白的,
不是愛倫坡的烏鴉。
我遙看鸚鵡山上,草木葳蕤,
對比曲小師兄說,
“風真好。
我喜歡的,這綿延,這烏鴉投下的搖晃,
像院中那株快枯死的老桃樹,
今年,桃花硬是紅了那么三朵、五朵。”
和比曲小師兄去馬尿河看梅
初五時,比曲小師兄說,
“走,我帶你到馬尿河,去看河邊的紅梅,
花,該是開了。”
比曲小師兄滿心歡喜,
帶我,各騎一匹矮腳小牝馬,
沿著斜坡小路,一路踏踏,跑進了馬尿河。
不料,去年倉促的暖,
讓河邊的紅梅,孤零零,僅散八九朵的紅。
比曲失望了十秒,喊了一聲“啊莫莫”
跳入河中。
他撈上回水處漂浮的五六片紅,
他的手,仿佛緊緊握著了馬尿河的血管。
山中隱
碰巧路經丙谷時,我誤入過一處無名的山林,
聽到蜂鳥鳴,這可歸入到意外之喜。
踏進了,就壯膽在林間,和孤月一起發會兒呆。
當夜游神也行,即便心生涼意,也不打緊。
犍為縣大多數養豬戶每年飼養的生豬為500~1 000頭,在建設養殖場地時,通常為隨意建設,場地設置比較簡陋[2],養殖戶在選址時以自己的承包地為主,部分養豬戶為方便銷售,會將養殖場地設置在交通道路旁,增加了疫病傳入的幾率。部分養殖場地地勢較低,污水灌溉現象顯著,且在布局養殖場時,未能嚴格劃分管理區域與生活、生產區域,養殖污水未經消毒排入溝渠內,為生豬自產自銷戶防疫工作帶來較大的難度,不利于生豬自產自銷事業的發展。
山上種植不過二三十年的白桉樹,長出大片的紋飾
低調,內斂。
山中,已鼓盡聲息。
此間早無打柴人,我向誰,打聽山中事?
白桉樹下,突然有了光,
……群峰之上,還是原先那片星辰。
無窮盡的一天
最好的一天,我可以把它寫給東邊營盤山,
也可以寫給
西面的菩薩巖。
但我只愿意把它,寫給云南和四川共有的
白馬林場。
看吧……這無窮盡的一天,
山頂上
安放著層林盡染,
秋日,
最終藏回了背陰的那一大片云南松。
夜讀《小倉山房尺牘》有感
我承認,
自己讀第一篇《答鎮江黃太守》時,
文言文已讓我極度陌生
和不適。
半月后,艱難讀至《再與西圃》,
自己如在黑黢黢的
臘月夜
無法孤眠。走出門外,那些不可見的梅花正開,雪亂飛。
突然安寧
……安寧河,
我再次準備好滿河的鵝卵石,和光滑,
這,是我所能給你的禮物。
我會寫到安寧河突然安寧,
綿延登上斜坡,
明月突然孤寂。
我寫出了和解的方法,沿河二三十里,
有一小片濕地,
幾只站立的白鶴,彼此正吞食一條活鯽魚。
它們仰起細脖,
抖動,卡出的鯁,意義重大。
一些世事艱難,它終需有人來吞下,
一些人和事,寫出來也是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