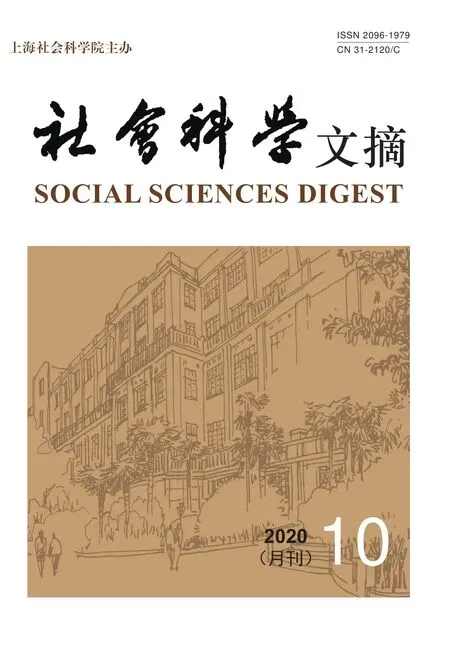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百年回顧與展望
文/王南湜
百年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發生了多次形態變化。在現今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從而亦對中國哲學精神的偉大復興提出急切要求之際,對作為中國社會之主導性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發展進程作一回顧和展望,意義重大。
百年回顧與展望從何切入?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百年回顧和展望,要從本質結構或根本問題上對其變遷進行一種深層分析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改變世界的理論旨趣必然具有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雙重訴求。解釋世界就是將世界之存在、變化和發展以某種具有確定性的法則加以描述,而這要求世界本身在某種意義上是決定論的;而改變世界則要求世界是可改變的,要為人的能動性留下余地,即在某種意義上是非決定論的。
理論對于改變世界的實踐或行動來說,是從兩個并非一致的方面發生作用的:一個方面是建構實踐主體的意志或目的,即引導主體意志或目的;另一個方面是建構實踐主體的手段,或指導、設計實際行動或實踐的具體進程。就建構實踐主體的意志或目的而言,與解釋世界是少數精英人物便可執行的事情不同,改變世界卻非多數人即群眾參與不可,因而,如何動員群眾投身其中,便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而正是這種雙重訴求及其間的多重關聯方式,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內在地包含著決定論與能動論的張力或矛盾,也正是這一關系問題的不同存在方式與不同解決方式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存在形態的變遷或進展。如果我們抓住了這一根本問題,就能夠達致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展之深層把握。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在張力之初現
李大釗作為在中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百年回顧與展望繞不過去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與后來的諸多論者不同,李大釗初次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深切地意識到了其中所內含的決定論與能動論之間的張力。
李大釗和李達早期所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唯物史觀,而從瞿秋白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卻偏重于辯證唯物主義,并趨向于體系化。這一變化除了受傳播的路徑依賴之限制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的內在需要恐怕是一個主導性原因。但遺憾的是,這后一方面卻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而要理解這一轉變,便必須從馬克思主義之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之雙重訴求上去看。
若是單從解釋世界之訴求來看,從日本傳入的唯物史觀,作為恩格斯稱之為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無疑是馬克思主義之核心內容,從而具有理論自身的正統性,理當以之為主導。但若從改變世界的訴求來看,問題卻又有所不同了。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是作為眾多社會主義理論之一種而為人們所知道的,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乃是為當時幾乎所有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所普遍信仰者。但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凸顯了出來,引起了一些先進分子的特別關注,意欲在中國仿效而行,以圖一舉而使中國亦挺立于世界,擺脫近百年之屈辱。這便是要將馬克思主義之社會主義付諸實施,付諸于改變世界。而要有效地改變世界,便不能僅靠少數先進分子,且需要極其廣泛的群眾性實踐主體參與其中。而當馬克思主義從眾多外來的“主義”中脫穎而出,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所選中之時,便立即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使其成為廣大國人所信奉之“主義”,而不僅僅是少數先進分子的“主義”。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的工作便是,通過論辯駁倒其他競爭性的“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獲得全勝。事實上,五四時期的數次思想論爭,即“問題與主義”論爭、社會主義問題論爭、無政府主義問題論爭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唯物辯證法論爭,都是一種通過論辯駁倒競爭性對手而擴大自身影響的特殊的傳播行為。與此同時,通過通俗化的宣傳,使廣大民眾首先是廣大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亦是壯大自身的傳播所必須的。基于自然科學之巨大成功的決定論,在論戰中無疑具有無可辯駁的理論力量,而體系化則更使得這種力量匯聚為一體,成為難以戰勝的精銳之師。因而,要使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一種決定論的體系化是必不可少的。
教科書體系何以大獲成功又何以被詬病?
教科書體系在近40年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詬病,這應當從其改變世界的功用方面理解。體系化的教科書之主要功能在于動員群眾和收攏人心去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之目標。這一體系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其決定論而指證了合于群眾所欲的革命目的的正當性和可實現性,因而起到了動員群眾參與其中的重大作用。但到新中國建立后,革命目的的正當性與可實現性問題已成為不言而喻之事,無須再行證明;而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后,對于動員群眾而言,一個新的方面便凸顯了出來,那便是為能動性正名。建設一個新的世界,必須設定人的能動的創造性,即預設世界是非決定論的,以使得活動主體具有可進行創造的空間,而非是被決定論性質的規律所全然支配的。然而,在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之時,教科書體系不僅未意識到現實實踐方式的轉變對于其提出了新的理論任務,而且更進一步借助蘇聯專家之權威和國家意識形態之力量對其決定論體系加大推廣,這就埋下了后來被批評和詬病的種子。教科書體系所持決定論原則的弊端,導致不得不由毛澤東直接出面來強調能動性的方面。而這樣一來,便導致將作為意志目的建構的理論與指導實踐手段建構的理論合二為一,進而有可能導致將建構意志目的之用的能動性直接移植到對于實踐手段的建構上,從而埋下過度夸大人的能動性的種子。
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再理解
在這一時期,還有一種不能忽視的哲學,那就是毛澤東哲學。以往對毛澤東哲學的理解,多是將之納入到蘇聯教科書體系之中去,以便排列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前后順次相繼的編年序列,但卻未曾想到,這樣一來卻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解造成了嚴重的障礙。為了更好地把握毛澤東哲學,我們亦須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之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雙重訴求去尋找新的理解。
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所要求的具有決定論性質的體系化理論,雖然在理論上是戰勝競爭性對手的利器,但當其直接進入到具體實踐之中時,卻往往導致相反的結果,成為導致實踐失敗的根源。這便是教條主義支配政治實踐而實行左傾冒險主義,從而導致多次失敗的原因。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呢?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這兩種訴求的互相沖突,已表明這一問題注定是無法以一種理論的方式予以解決的。因此,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論智慧的實踐智慧了。這便是毛澤東的貢獻所在。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與毛澤東兼具理論家和實踐家的雙重身份分不開的,同時也與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影響有莫大之關聯。
毛澤東是認真研究過蘇聯教科書的,但他并不滿意于這種帶有明顯理論哲學傾向的教科書體系,他以自己的方式對之進行了超越和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便是基于實踐哲學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和理論運用的具體性原則。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存在著一個雙重結構:一方面強調“自覺能動性”;另一方面則是“實事求是”。亦即強調能動論與決定論的辯證關系。
毛澤東對于能動論和決定論關系問題的解決方式,顯然不同于教科書體系那種理論哲學的方式,可以說是一種實踐智慧或實踐辯證法的方式。這種解決方式不同于理論智慧追求確定性的方式,對于在多大程度上發揮能動性的作用,對于具體的情景具有極大的依賴性。在變動性極大的戰爭中,能動性能夠獲得極大的發揮條件;而在經濟建設中,能動性的作用則會受到客觀條件的較大制約,若不加以適當調整,則有可能導致嚴重失誤。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于能動性之強調,若從建構實踐手段方面看,由于過度強調能動性,無疑是出現了失誤,但若從對教科書體系在建構主體的意志目的方面的能動性缺失之糾偏方面看,則又有著需要加以肯定的意義。也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復雜交錯的狀況,才導致后來關于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與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中對于實踐概念之不同方面的強調,以及后來人們在評論這兩場理論討論中的某些誤解與錯評。
實踐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與實踐唯物主義的興起
由于存在著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雙重邏輯,這兩場解放思想運動事實上在對于新的理論需求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在改變世界的邏輯方面,由于所要改變的是長期以來過分夸大主觀能動性、夸大思想觀念與上層建筑作用之弊,因而,理論界頗具針對性地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命題,回歸實事求是,回歸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
盡管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無疑與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有著密切關聯,但卻不能將之簡單地視為同一思想事件。就哲學理論而言,理論界所面對的并非是社會實踐中因脫離實事求是原則而出現的那些問題,而是如何在理論上合理地說明人的能動活動與社會客觀規律的關系問題,亦即能動論與決定論的關系問題。既然成體系存在且居于主導地位的哲學理論便是教科書所主張的決定論體系,因而,這一討論便必然主要地是針對這種決定論體系的,即要破除這種機械決定論而為能動論張目。這一目標顯然是與回歸實事求是的實踐目標不盡相同的。前者在于強調實踐之客觀性,以糾正“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之傾向,而后者則傾向于強調實踐中人的能動性,這又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毛澤東關于教科書體系之決定論傾向糾偏之延續和發展。由于存在著這種目標的不同,對于這兩場理論討論便不能以同一標準去加以評論,而是要基于各自不同的目標去看。
主體性哲學的得與失
實踐唯物主義大討論將主體能動性引入以往的決定論體系之中,這可以說是對主體性哲學的一種弘揚。這種弘揚乃是對于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于人的能動性發展之吁求在哲學理論上的一種回應。但中國社會發展所吁求的并不只是人的能動性,同時也吁求把握客觀規律的科學精神,以便能夠有效地改變世界。而實踐唯物主義和主體性哲學討論的進一步發展,便也不可避免地導向了對于這一理論趨向中所存在問題的反思。
由于盧卡奇所開創的對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主義闡釋的重大影響,中國學界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之最后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其進路亦同樣是一種黑格爾主義闡釋的進路,因而,盧卡奇哲學的問題實際上也可以說是黑格爾主義闡釋之一般性問題,這無疑也構成了中國學界實踐唯物主義理論發展的一般問題,或者說,構成了實踐唯物主義理路發展的一般前景。而盧卡奇哲學的主要問題在于,在反對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闡釋時,走向了黑格爾哲學,過多地“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了,這使得其在發展人的能動性時失去了現實性,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那樣,將“能動的方面”給“抽象地發展了”。而中國學界之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主義闡釋,大致上并未超出盧卡奇之進路,因而其理論上的困難便也與之相同。這一反思也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黑格爾主義闡釋方式的反思。
回過頭來看,教科書體系之決定論闡釋,雖然片面,但亦自有其合理之處。事實上,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確是一部科學著作,而科學著作自然是要以決定論的方式去進行論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也在這部著作中明確表達了其決定論指向:“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因此,對于馬克思哲學的決定論闡釋亦是有其依據的。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是馬克思不僅早年批評舊唯物主義缺失能動性,而且在中期著作中肯定“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在后期對于“自由王國”的構想中,無疑是以世界在某種程度上的非決定論和人的能動性存在為前提的。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從理論上合理地解決這一關系問題,而不是趨向一個方面,取消此一問題。就此而言,對黑格爾主義闡釋進路之抽象地發展主體能動性的反思,對教科書決定論體系的重估,并不意味著重返那種忽視主體能動性的舊唯物主義決定論體系,而是要重返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改變世界的哲學所必須面對的能動論與決定論的內在張力這一根本問題,而歸根到底,就是基于何種出發點去解決或處理這一根本問題的問題。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百年發展之啟示
回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百年發展,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未來發展而言,我們能獲得以下啟示:
首先,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進程所遵循的不是一個單一的邏輯,而是一個涉及解釋世界的理論智慧與改變世界的實踐智慧的雙重邏輯,那么,對這一進程的理解和考察,也就必須遵循這一雙重邏輯來進行。既然解釋世界的理論智慧與改變世界的實踐智慧各有其目的,那么,對這兩個方面便需依據不同的目的而分別評價之。
其次,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雙重訴求與雙重邏輯的區分,并不意味著將之分解開來即可萬事大吉。即便人們在理論上以某種方式將上述雙重邏輯統合為一個一元論體系,也還只是在理論上解決了問題,尚未及于實踐。在實際生活中這兩種訴求、兩種邏輯是交織在一起的,因而,在將一項具體實踐付諸實行之時,必須將這些不同訴求與邏輯放置在一起加以綜合考慮,并權衡各種因素在其中的份量,以便設置具體的行動方案。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實踐辯證法當有發揮作用之大空間。由于以往相關研究的缺失,因而,我們應當更為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這一方面的研究,并通過這種研究,構建起一種實踐中有效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或實踐辯證法來。
再次,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包含著價值理想的建構與實踐手段的建構之雙重原理,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便也必定包含這兩個方面的中國化。且這一中國化是一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持續地與時俱進的過程,因而,人們也必須隨著社會歷史條件之變遷而在新的條件下以新的思路推進這一過程。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巨變從而也就給人們提出了新的任務:既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更多的是聚焦于方法論方面,而在如今中國社會發展取得如此成就,價值理想方面的深度中國化問題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方面,如果要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深入國人之心,成為國人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將其源于希臘文明之自由王國理想與中國傳統之“民胞物與”式的天人合一理想相融合,以“民胞物與”的理想去闡釋“自由王國”的理想,并由此重建中國傳統之天人合一理想,便是我們當今應當加大力度深入進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