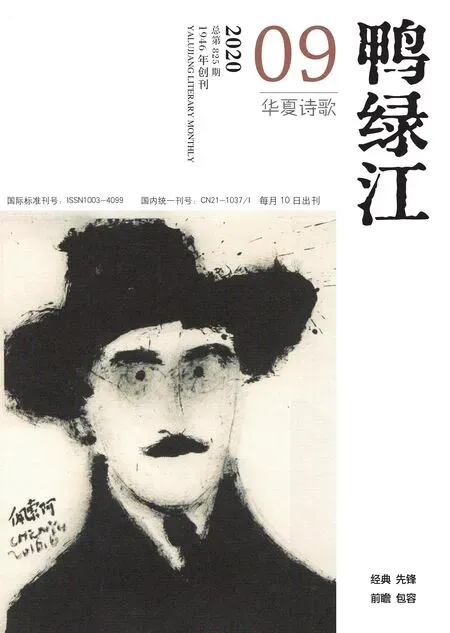梁平的詩
盲點
面對萬紫千紅,
一直找不到我的那一款顏色。
有過形形色色的身份,只留下一張身份證。
閱人無數(shù),好看不好看,有瓜葛沒瓜葛,
男人女人或者不男不女的人,
都只能讀一個臉譜。
我對自己的盲點不以為恥,
甚至希望能夠發(fā)揚光大,
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事理,
這樣我才會真的我行我素,事不關(guān)己。
我知道自己還藏有一顆子彈,
擔心哪一天子彈出膛,傷及無辜。
所以我要對自己的盲點精心呵護,
如同呵護自己的眼睛。
我要把盲點繡成一朵花,人見人愛,
讓世間所有的子彈生銹,成為啞子。
北京是一個遙遠的地方
北京很遙遠,
我在成都夜深人靜的時候,
曾經(jīng)想過它究竟有多遠?
就像失眠從一開始數(shù)數(shù),
數(shù)到數(shù)不清楚就迷迷糊糊了。
我從一環(huán)路開始往外數(shù),
數(shù)到二百五十環(huán)還格外清醒,
仿佛看見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
看見故宮里走出太監(jiān)和丫鬟,
我確定我認識他們,
而他們不認識我。
于是繼續(xù)向外,走得精疲力盡,
北京真的很遙遠。
隔空
很南的南方,
與西南構(gòu)成一個死角。
我不喜歡北方,所以北方的雨雪與霧霾,
胡同與四合庭院,冰糖葫蘆,
與我沒有關(guān)系,沒有惦記。
而珠江的三角,每個角都是死角,
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動。
就像蟄伏的海龜,在礁石的縫隙里與世隔絕,
深居簡出。
我居然能夠隔空看見這個死角,
與我的起承轉(zhuǎn)合如此匹配,
水系飽滿,草木欣榮。
從天府廣場穿堂而過
十六年的成都,
沒有在天府廣場留下腳印,
讓我感到很羞恥。有人一直在那里,
俯瞰山呼海嘯,意志堅如磐石。
而我總是向右、向左、轉(zhuǎn)圈,
然后揚長而去。為此,
我羞于提及,罪不可赦。
那天,在右方向的指示牌前,
停車、下車、站立、整理衣衫,
從天府廣場穿堂而過——
三個少女在玩手機,
兩個巡警英姿颯爽,
一個環(huán)衛(wèi)工埋頭看不見年齡,
我一分為二,一個在行走,
另一個,被裝進黑色塑料袋。
一陣風從背后吹來,有點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