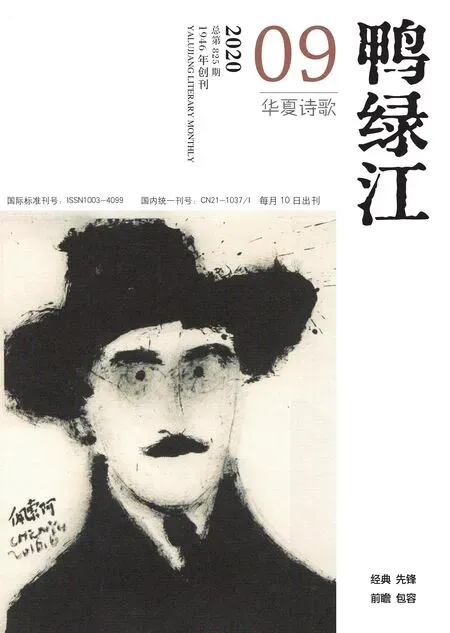譚詩錄:實然非實然之間
李瑾
詩歌和自我
詩人就是當下、“大眾”的敵人。
詩人首先要做自己的敵人:如果不能拋棄自己,只能淪落而泯然眾人矣。
拋棄即重生。詩歌毋寧說是詩人自祭的哀歌。
詩歌和自我
詩歌是“天”啟的。詩歌之偉大不在于她是最高語言或最崇高的審美感受,而在于她提醒我們如何面對自我——或者說,詩歌即自我,即存在。我的意思是,詩歌牽引著我們不斷回歸本我,通過觀照“我”之本然,證明人的存在首先歸屬于“我”,然后才臣服于抽象的外部法則。當我說詩歌即自我、即生存時,意味著人建立在孤獨的自我感受之上——內在體驗才是人的根本。我不承認這是唯心主義的立場。相反,我堅持認為這是神圣的完整自我和超驗的自由個我相統一的立場,這一統一,表明人是超越主客二分的主體。毫無疑問,詩歌作為即時的思維、情感,其最大功用是將人送回自己身上,讓他成為自己——一旦詩歌讓人體驗到了自己,自我就有了建立的可能。
我想,人們可能會有這樣的悲觀:我們渴望著美好生活,卻時時陷入人的泥淖和丑陋中;我們眼中的遠方和詩歌,無法遮蔽現實(甚至詩人)的灰暗和無情。當我們面對這些,還會認為這是啟蒙過的人嗎?這是理性主義的人嗎?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是,又不是。必須指出,即便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的人,也會將人絕對化、抽象化——那些試圖滅絕種族或對否定意見采取決絕態度/措施的人,難道體驗不到自己的存在?錯了,他們恰恰是最精致的自我主義者。顯然,我們可以說,對自我的發現/建立,還天然地包括對他者存在的允諾。這個意義上,自我是絕對的我,卻不是唯一的我,如果把自我當作唯一的神,我即不存在了——孤立的我毫無疑問是動物的、隔絕的,與這個世界水火不容的。
詩歌一直對人的異化保持警惕,盡管她自己也時時刻刻面臨著異化。通常而言,我們認為自我的建立是在同客體的對峙過程中實現的。也就是說,自我建立于擺脫一切外在關系之際。然而,鮮有人認識到,當我們同客體對峙時,已經落入外部關系內,淪為被規訓過了的徒有其名的主體——也就是說,我們在生產著不屬于我們的“我們”,而是商品、工具和理性的犧牲物。詩歌提醒我們,人是自覺的,也是包容的,人必須建立在主客體的相互認同而非排斥、吞噬中。這就是說,詩歌讓自我發現了存在的奧秘:通過確立內在的我、精神的我,才能將人立起來。這個意義上,人是一個過程,而不是實在物;人是一種勞動,而不是勞動結果;人是一種自在體驗,而不是客觀經驗。
詩歌之所以能建立自我,源于她挖掘出了人格的豐富性和完滿性——詩歌作為一種精神、行動而非文體確立了內在個我,亦即通過找尋客觀之人的內在性指定了他是“那個人”。要注意的是,這個內在性雖是本質的,卻不是排他的,而是存在于或者本然于主客體間、物內外里和時空之中,亦即人是一種規律和關聯,他不能脫離自然而自行確認自己。詩歌探討的恰恰是這種規律和關聯——一切外部關系都無法顯示內在,無法顯示生命的本源,雖然這些都要在關系中確立,但人的向內尋找(內向挖掘)是自覺的、積極的、純粹的,而不是服膺于某種意欲的:建立自己,正是去意欲的過程。當然,這一意欲是完全的本能,而非合理的存在。
詩歌能做到將“我”指定/還原為“那個人”,并非身份上的——在身份上,我們都已隸屬于現代或當下,這是比機構還要龐大而莫名的東西,我們被剝奪了自然而然的人格,甚至被規定唯有張大私欲/私欲才能找到自我。這里要說明,對“我”的指定是內在精神上的。通常我們將人數眾多的、指標意義上的他者視為烏合之眾,恰恰是這些若有若無的“大眾”統治著我們。詩歌是大眾的反叛或反撥,她公布著詩人的秘密,并將內在個我袒露出來,成為一個實在的超越。這個意義上,詩人就是當下、“大眾”的敵人。當然,詩人首先要做的是自己的敵人,如果他不能拋棄自己,只能淪落而泯然眾人矣。拋棄即重生。這里,詩歌毋寧說是詩人自祭的哀歌。
作為自我的認定方式,詩歌其實是一種抗議,盡管有時候毫無用處,但她至少在表明,“我”不是抽象的大眾,也不是模糊的平等,更不是約化的自由,而是十分完滿的有生命力表現的人。毫無疑問,詩歌更多時候體現出恐懼、焦慮和絕望,甚至表現出無名的虛無,一種失去希望的、吞噬全部精神的對個我的占據——必須指出,這不是詩歌自身造成的,而是社會被制度化以后留給人們的后遺癥。當然,詩歌中的“病”更多的是立場、態度,對毀滅的純粹駁斥——人所失去的自我反省的自覺性在詩歌這里萌芽了。假如沒有詩歌,人還會剩余什么呢?畢竟,這是我們賴以認識自我存在的透視鏡。
但是,我們的危險在于,詩歌和她的出發者都會陷入固定的框框中。也就是說,我們雖然神經健全,意識清醒,不過對自己是人和實在,特別是作為人的責任上,一無所知。我們只沉浸于眼前的事物和法則中,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人虛無,詩歌也虛無,詩歌不是表現出痛感,而是跟隨人本身平庸地即在著,完全失去自我超越的能力,似乎當前之觸感即是生命本身,即是永恒。這種情況下,詩歌需要扔掉那些對經驗的、現象的實存的追逐,是本體世界而不是經驗世界規定了何者為人/詩。事實上,我尚找不出詩歌突破自身困境的理由,因為我們雖然生活在悲劇之中,卻認識不到這種悲劇體驗是一種新的開始。
盡管如此,我還是將詩歌當作本體世界中的一個核心部分,當作人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一種最為徹底的方式。因為唯有詩歌才能提醒我們,人自身即存有無限超越、無限發展的可能——生活讓“我”成為囚徒,詩歌讓“我”重獲自由。這個意義上,當詩歌被吟詠而出之際,實際上是新的個人主義誕生之時。
詩歌和理智
詩歌對“立人”之關鍵之所以重大,不在于社會日常中理智缺位,而在于感性缺位。
感性在創造詩歌的同時,創造著我們人類自身。
立人是詩歌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這是詩歌內設的唯一目的。亦即,詩歌是人獲得新的“上帝”的一種途徑。必須指出,詩歌作為即時的思維、情感,是感性的;但肉體化的詩歌,則是理智的——文字是文明的、理智的最高形式,思維落實到文字上,意味著獲得了價值性約束。當詩歌和人等同起來,表明人從自然狀態脫離出來,從即物直觀擺脫出來。不管這種脫離、擺脫會不會將人引向另外一種“狀態”,詩歌絕不是人的純粹性的體現,乃不爭的事實。這種說法是否會推翻如下一個既定結論,即意力是世界之本體,人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這確實是個問題。
切實地看,詩歌中包含了對烏托邦的設想和對意識形態的投入,不管烏托邦、意識形態是人、物還是道、器。這個意義上,詩歌是理想的概念化事物。但不論如何解說,詩歌到底被感性統領還是被理智支配,都需要辨析明白。否則,無法確定人與神的關系、責任和各自的歸屬。若詩歌是感性的,則否定了神、規律的存在;若詩歌是理智的,人的罪惡就不需要自己負責——天、規律就是惡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傾向于將詩歌理解為一種感性的理智化和理智的感性化的集束,二者互立互破,表現為人的社會性實踐。也就是說,詩歌一則是生命精神,一則是道德實踐,是人對自身狀態合理引導下的自由判斷和選擇:一個粗俗的譬如是,假定我丟失了一只雞,詩歌是批評、批判,而不是悍婦式的罵街。
這就是說,人可以假定為抒情的或敘事的,但詩歌絕不只是激情或情緒,詩歌中有一種文化、藝術甚至社會自覺,這種自覺不會拋棄思維的激蕩,但也不會被其湮滅——惟熱血或惟科學都會導致詩歌包括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不過,必須指出,對感情和理智的強調并非天然導出二元對立,而是說,二者可以相互涵蓋,而不是機械化地以一方判斷另一方。實際上,當我們在爭論詩歌是感性的還是理智的之時,并不清楚自己意欲何為。因為他們之中的任意一方,對于人這個具體的實在而言,都不具有本體價值。也就是說,人的本體價值內在于本能,又外顯于道德,唯有二者統一,才會造成人的偉大。
但是,二者之統一或互為并不是說彼此生成。必須指出,感性和理智的矛盾中,感性是本源的、第一位的。詩歌雖然經由理智而為藝術反應,但人根本是感性的,是本能的仆從,而理智是感性的產物,即內在于本能之中——本能并不意味著人完全受欲望統治,欲望只會撕碎人,而不會立人,本能還存在建設性之一面,它規定人必須服從于存在這個最高價值。存在意味著人的本能中有克制自己的本能。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感性與理智的關系,當理智表現為單純的理性主義,將人當作理性的奴隸,感性則從欲望即人的本真狀態出發喚醒內在個我的存在。當感性表現為純粹的動物主義,讓人性陷入真空之中,理智則將人引導回存在的既定秩序軌道。
當辯明了感性、理智之關系,我們才可以放心地說,詩歌是一種深邃的自我和本能,一種對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創造。就此而言,詩歌之所謂立人,不過是將蒙垢的內在個我發掘出來。而通常講的實踐理性,不過是聽從主體需要的具體活動,而非超驗的形上存在——亦即理智固然具有能動性,但它是被支配的,它除了根據感性的需要提供邏輯服務,不再具有其他價值。由此可見,詩歌是一種理性的情緒,其在對生活的反射中創造著普遍價值,一個真正的詩人、一首真正的詩歌都被充實了感性的理智,當我們說詩歌是烏托邦、意識形態時,不過在尋找我們自身——一個有待培育主體精神的軀殼。
在這個論域中,肉體化的詩歌實際上是即時思維情感的理智性符號。當然,我們可以說詩歌是感性的,感性是她的內在、外在和全部,但詩歌絕不只是內在個我的瞬間狀態,而是超越個人的、以具象為出發點的抽象思維。人就是在具象和抽象的沖突和激發中提煉出來的,詩歌在表現純粹的自我。這沒有錯,但純粹的自我存在于普遍的人類情感中,當我們詠嘆,其實是發出一種帶有共鳴之音的回聲。也就是說,詩歌寫作是詩人的認知活動的外在體現,而認知則有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從局部到全體的過程:所謂的內在個我邏輯上是經驗的產物,詩歌則由自由意志(內設道德實踐)指引自己的發生。
人是靈肉一體的。當我們談及自由意志時,實際上是說人雖然還是自然狀態的人,但它具備著理智化的可能。否則,將完全臣服于動物性。不過,必須尊重生命本能并將其落實到人性、人格中,若缺少這個前提去提理智,將扼殺人之為人亦即人的天性。這里,我更傾向于將感性視為人建立自己的最大驅動力——這是人的生命之所在。假若失去了感性,人將會失去作為自己的需要,而詩歌則和皮毛一般,則是可有可無的呻吟或裝飾。需要強調的是,當我們張揚理智或道德實踐時,要認識到這樣一個前提,感性永遠不會衰退或削減,其遭受的壓制愈大,自塑性越強——它一直支配著人的一切構建性行動。
追根究底,詩歌對“立人”之關鍵之所以重大,不在于社會日常中理智缺位,而在于感性缺位。感性在創造詩歌的同時,創造著我們人類自身。企圖抹殺感性的意義,無疑也在抹殺理智——理智是什么?是最大的感性,最強的欲望。當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會追溯出人的起點,并完成他的創造,一種生命自我的道德實踐。
詩歌和虛構
虛構是關于事物之存在的反映。任何一種講述都是存在的而非編造的。
虛構是事物本真的象征或重現。邏輯上存在比真實更符合事實。
當我們在詩歌中分辨不出誰是誰的對象和影子時,偉大的虛構才算完成。
整個世界都是虛構的,即世界是由人類的想象安排出來的,一旦離開想象,我們賴以生存的萬事萬物都面臨崩塌,除非借助另外一種虛構進行重建——遺憾的是,虛構只有一種。詩歌在本源上是敘事而非抒情的,她是有關世界存在的一種自足性話語,當詩歌試圖講述、完成自身時,虛構就隨之而來。這個意義上,詩歌即虛構,一種關于傾向、立場的建立和輸出——此過程中,將進行種種符碼的編譯。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界定一個基本觀點,虛構是關于事物之存在的反映,它要表明的是,任何一種講述都是存在的而非編造的。也就是說,虛構是事物本真的象征或重現。不過,存在和真實并不是同一個概念。比如,你可以假定龍是存在的,但它卻不是真實的,但是就世界之生成及其意義而言,邏輯上存在比真實更符合事實。
“真實”意味著眼前之物,而存在則是一種規律、氣或者說我們對事物抽象的、整體的認知和把握。在詩歌中,真實是沒有意義的,只有表現為存在,她才會和人這種最高的精神實體結合起來。虛構意味著什么呢?它至少表明,詩歌在講述一個事件、構建一個圖景時,這個事件、圖景以內在個我的體驗、經驗為藍本,卻并不是直接投影,而是經由語言的加工進入讀者精神世界——虛構意味著詩歌內置了主觀真實的想象和看法。
我相信一個讀者在面對一首詩歌時,他首先關注的并不是詩人的想法——而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都不會把讀者當作隱私的窺探者——相反,他不過是想尋找自己的影子或個我問題在他者那里的回應,亦即通過詩歌這個載體,獲得對個體的認知和被解釋——即便一個小小的感動或共鳴,都是對自我的一次全新體驗和進入。
通常而言,一首好的詩歌從來都不會引起人們有關真偽的懷疑,宣稱詩中之這個是不存在的,即其中之描述并不是來自于現實的生活,也與我無關。相反,其提供的不同時空、情境恰恰能夠有效地擊中我。對讀者而言,詩歌描述的雖非身受,卻是感同,她能夠很好地讓讀者切入自屬的心理空間。我個人的意見是,虛構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則詩人借助虛構的東西表達自己,一則詩歌對讀者而言是另在、虛構的(詩歌并非讀者切身之經驗)。這樣一來,虛構的意義在于,讀者通過虛構獲得了共鳴性體驗,這種體驗可以讓他更好地發現個我的內在尤其是此在。甚至可以這樣說,虛構是關于“我”的存在的邏輯指證。當我們被一首詩歌打動,只能說其中之存在讓陌生、隔絕甚至并不同在的我們建立了“是”的聯系。
一個疑問是,虛構為什么能夠建立起存在,或者說詩歌為什么會借助虛構來表達自己。我的解答很簡單,虛構比真實更接近于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真實固然是生活日常,但它時時刻刻發生著,并不能確定人之為人的本性,唯有虛構能夠將存在作為通感之體驗提煉出來,在內在個我和他者之間標志出個性的共識、共在——顯然,虛構通過具體而抽象的講述,引起了讀者關于“我”的主動想象,或喚醒了某種身臨其境的參與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最能反映人的此在和打動人即在的,就是虛構。如果說詩歌還有可用的表達技藝,無非是如何通過虛構營造豐盈的代入感。
虛構的真實雖然并不是即在的“真”,卻是本然的“實”。有意思的是,閱讀過程中,很少有人反感或抗拒虛構——恰恰相反,虛構被認為是一種動人而高超的技藝,根源就在于,這些虛構之物就存在于我們唯一真實的現實世界或我們內心中。也就是說,詩歌創作的目的并不是記錄,而是表達,表達必須將體驗抽象為經驗才能落實到精神深處。毫無疑問,詩歌中的事物是虛構的,但卻是抽象的實體,其產生于我們對整個世界和自我之實存的理解把握上。亦即,當一個虛構的事物進入詩歌時,便成為承載著存在和客觀的精神之物。而且,它還附加了我們潛在的有時無法說出的主觀意識。
虛構背后隱藏著一套真實不虛的敘事、情感邏輯,這就是說,虛構不過是一種必要的、以之表達我們客觀存在的修辭手法,但真實永遠是生活的底色,你無法想象人類存在于無稽不實之中——我們并不是憑空臆造或憑空抓取生活的人。這么說來,詩歌中的事件、情緒在源點上必須是真實的。否則,即是我們對自身的否定和遺棄。詩歌優劣的鑒定標準是能否以虛構的事物表達真實的存在,假若硬生生虛構生活特別是即時情境,只能稱之為偽敘事、抒情——這種堆砌語詞的無病呻吟之作,如今大行其道,比比皆是,行之者不以為非,反以詩人自居。
虛構是一種廣義的自我命名或自我認證行為,它代表著定性而非斷語。當一個虛構的事物產生時,無論正經還是荒誕,都意味著在現實中有必然的存在或對應物。虛構更傾向于一種認識論而非方法論,而它自身也通過虛與實的對立遞進出我們的立場和態度。當我們在詩歌中分辨不出誰是誰的對象和影子時,偉大的虛構才算完成。
如果我們虛構,一定是為了更好、更完整地表達、認識自己——而真實,并不足以代表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