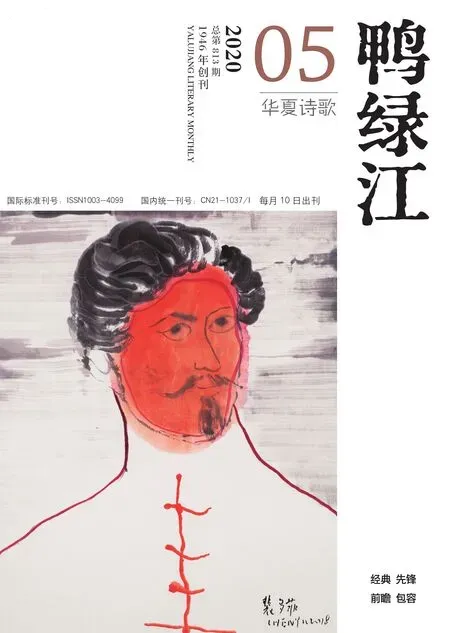從“私人檔案”勘探的秘密編碼
——探尋梁平《時間筆記》中的理想主義精神
耿占春
梁平作為中國詩壇宿將,在四十余年的寫作生涯里,他的詩歌皆可看作帶著轟鳴的鉆桿,一寸寸深入地心巖層。當他決意要用詩實現其生命的徹底性,他全部的詩篇就成為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聲。《時間筆記》是梁平的第12 部詩集,評論家認為這是繼《重慶書》《三十年河東》和《家譜》之后的又一巔峰作品。詩中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詩人在追求此理想過程中的率真、堅忍、無所不及的姿態令人深省。詩集中的《欲望》《石頭記》《耳順》《盲點》等充滿了突圍的隱喻和寓托,真正地書寫了人間煙火。梁平借用充滿智慧的治療型的語言,傳記經驗的敘述,心理分析式的個人歷史,尋找到平復焦慮和隔閡的話語途徑。《時間筆記》無疑是一部骨肉豐滿的虔誠之作。
“文字長出的藤蔓相互糾纏”
看到《時間筆記》的時候,我以為它呈現的是一部長時段的作品,沒想到這部詩集基本上都是梁平的近作。而就其所顯露的心跡而言,又的確可以視為長時段的生活所醞釀的變化在近期的一個呈現。這種變化是詩人情感從外向內的推進,從宏闊向幽微的調試,在“大我”與“小我”之間構成血與肉的關聯,在人與人、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各種沖突與隔閡中達成和解。很明顯,這個變化的根本所在,是在努力甚至是執拗地推進情感的強度。《時間筆記》的命名似乎與讀者達成了一個契約,即我們可以將他的詩歌視為一種個人化的記錄,一個人的心路歷程。《時間筆記》就是詩人的心路筆記,它的所指、能指又絕不是簡單的個人履歷,而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作為社會里的“個人”繁復的內心狀態。打開《時間筆記》,或許就能找到詩歌的秘密編碼,披閱一份新鮮、異質、妙趣橫生的《私人檔案》——
世紀之交,單純與文字為伍,
在《紅巖》看紅梅花開了三茬。
解放碑的某個小巷還有人對接暗號,
沙利文的刀叉不見了蹤跡。
一枚閑子被《星星》喚醒,
從沙坪壩經桑家坡直抵燕魯公所,
組織給我接風在克拉瑪依,
新華路一個有隱蔽意味的地方。
紅星路上沒有紅顏色的星星,
慘白的星光爬上額頭分行,
第一行和最后一行都掛在鐵門上,
與滄桑越來越匹配。
十五年以后,我把星星的密電碼,
在星光燦爛的夜晚交給了接頭人,
不帶走一個標點符號。
九眼橋在那天夜里,失眠了。
少陵老爺子夜游浣花溪
和我不期而遇,小店里喝的那杯酒,
有點猛,在茅屋折騰了一宿,
醒來發話,過來種植點花草吧。
花甲挪窩《草堂》扎寨,
還是那套種植的手藝,橫撇豎捺。
茅屋沒有崗哨,沒有磚瓦磕磕碰碰,
隨心所欲、所不欲。是為記。
果然是“私人檔案”,詩人提供了幾個清晰的時間節點,還有作為生活路標的幾個地點、幾個相關人物和三份知名雜志,但這份“私人檔案”的書寫又充滿暗號和密碼,“紅梅”“星星”“茅屋”之類既是寫實又是隱喻,由此它顯現了詩歌的本義,即使是白話詩,即使是一種自白,詩人也沒有放棄它一定的秘傳屬性,尤其是在廣告的直白意圖和大眾傳播的顯白話語里,詩歌依然使用著一種幽微的語言,有如擔憂一旦沒有了密碼與秘傳,某些與詩歌有關的真理就會消失,或者被誤讀。
詩人的這份“私人檔案”并非一目了然,在詩歌寫作中,詩人既孜孜于自我分析,又傾向于自我掩飾,甚至有時候也不免渴望自我圣化,很難說這是本意還是無奈之舉。詩人說,《我被我自己掩蓋》——
我被一本書掩蓋,
文字長出的藤蔓相互糾纏,
從頭到尾都是死結,身體已經虛脫。
我被一個夢掩蓋,
斷片與連環鋪開的情節清晰,
梅花落了,枝頭的雪壓啞了風的呼嘯。
除了書和夢,詩人寫到,“我被一句話掩蓋”,無法區分“舞臺與世界”,真實與幻影;最終,“我被我自己掩蓋,草堂的荒草爬滿了額頭”,顯然,“掩蓋”既有遮蔽也有遮護的意味。就像梁平在一些詩中,既揭破面具又使用面具,既以夢揭示現實又以夢掩飾自我。但自我遮護似乎并不是梁平的個性,他在詩中更多的是在贊美“裸露”和坦誠。他說,“裸露是很美好的詞”,一如《石頭記》所說,“我的前世就是一塊石頭”——
讓我今生還債。風雨、雷電,
不過是舒筋活血。
我不用面具,不會變臉,
所有身外之物生無可戀。
應該是已經習慣了被踩踏,
明明白白的墊底。
在“我被一本書掩蓋”,被夢、被話語以至被我自己掩蓋的認知之后,梁平很快說出反語敘述,“不用面具,不會變臉”,如赤裸的石頭。詩人說他就這樣做“墊底”的石頭,“如果這樣都有人被絆了腳”,他勸人“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一直在原地,赤裸裸”。與梁平詩歌增加著的反語修辭相比,這里的敘述雖不算深刻,但依舊有點咄咄逼人。
無論是掩蓋還是坦誠,似乎都與人的需求或欲望有關,詩人承認他的《欲望》,但他也愿意如此看待自身,“我的欲望一天天減少”——
曾經有過的忌恨、委屈和傷痛,
一點一點從身體剝離,不再惦記,
醒悟之后,行走身輕如燕。
“我是在熬過許多暗夜之后,讀懂了時間”,不再有紛爭與忌恨,他提供了一個時辰以見證這一點,這是孟子所說的平明之際羲皇的時間。“天亮得比以前早了,窗外的鳥,它們的歌唱總是那么干凈,我和它們一樣有了銀鈴般的笑聲。”這就是他此刻的意愿,質疑自己曾經的欲望與動機,摒棄自身的執念,同時隱含著對他人看法的修正。這是詩人天真的一面。
他如此自白說:“我的七情六欲已經清空為零,但不是行尸走肉,過眼的云煙,一一辨認,點到為止。”
我們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詩人所說,因為他一直在制造自我的反語,他一直在使用著反語敘述。至少這是詩人心跡的表露,他稱自己《深居簡出》,滿眼是一個祥和的世界,“騎馬挎槍的年代已經過去,天地之間只有山水。……與鄰居微笑,與糾結告別”,我們是否該相信這個“閑庭信步”的詩人,“熟視無睹樹上站立的那只白鷺”,而且他告訴我們“那是一只讀過唐詩的白鷺,心生善意,含情脈脈”,連懷孕的貓也在“伸展四肢的瑜伽”。他說,“我早起沏好的竹葉青,茶針慢慢打開”,似乎沏茶、茶葉在水中舒展,都是一種主體性的心理過程的顯現,“溫潤而平和”。
在詩人的整體語境中,不好斷言“與糾結告別”微笑的面孔是內在真實狀態還是他希望自己顯現出來的狀態。但至少,詩人希望的是走向中庸之道而非極端處境。詩人說自己已到了《耳順》的年紀,沒有“掩飾、躲閃、忌諱”——
耳順,就是眼順、心順,
逢場不再作戲,馬放南山,
刀槍入庫,生旦凈末丑卸了裝,
過眼云煙心生憐憫。
耳順能夠接納各種聲音,
從低音炮到海豚音,
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
甚至花腔,民謠,搖滾,嘻哈,
皆可入心入耳。
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雜音,
都可以婉轉,動聽。
詩歌的傳記經驗所表達的并非一些事件的編年史,而是變化著的心理軌跡,內心的欲望與愿望也是它的一部分,“耳順”不同于“順耳”,“眼順”不是“順眼”,“心順”也未必是“順心”。順耳、順眼、順心差不多是一種自然事態,耳順卻是一種主觀性,一種人們普遍渴望抵達的主觀性。前者由環境宰制,后者由自身決定。由此而言,當詩人一再表示《卸下》或《舍得》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是自我勸慰還是事實陳述,“卸下面具”,卸下“裝扮,赤裸”。他說,“與世無爭是一種突圍,突出四面埋伏的圍困”,把“看重的放下”,“任何時候都不要咬牙切齒,清淡一杯茶,潤肺明目,看天天藍,看云云白”(《卸下》);“藍天在上,白云在上,遇見藍天白云沒有人不自慚形穢。所有身外之物開始脫落……”(《舍與得》)。通常而言,耳順的修為是在一些價值含混的乃至相互沖突的社會環境中產生,有時候是為著讓主體性的感知與無價值的事實之鏈斷開,即讓“身外之物脫落”,有時候卻是一種沒有價值觀的修煉,讓主體的感知與價值之鏈分開。
就像詩人總在裸露與掩蓋之間游移,他也在欲望的清空與欲望的搏擊之間游移,梁平總是制造自己的反語敘述,在放言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際,詩人旋即又承認《我肉身里住著孫悟空》,他真是一個表現自我矛盾的高手。不過,他希望“無休止的博弈和廝殺,并不影響我面對世界的表情,真誠、溫和而慈祥。我清點身體內部歷經的劫數,向每一處傷痛致敬”。他對受傷的自身致敬又為他可能帶來傷害的能力擔憂,“我知道自己還藏有一顆子彈,擔心哪一天子彈出膛,傷及無辜”,因此,“盲點”或“盲目”也是雙重意味的,所以他甘愿“讓世間所有的子彈生銹,成為啞子”(《盲點》)。
受傷與傷害或許體現了一種身體的社會屬性,既是生活敘述又似乎包含著一種轉義,在我們的時代,所有的行為都有自己的反面,所有的價值都產生了含混與歧義,所有的事物都感染了另一種屬性。他在《經常做重復的夢》中說,“……這個夢是一次殺戮,涉及掩蓋、追蹤、反追蹤,和亡命天涯。我對此耿耿于懷,這與我日常的慈祥相悖,與我周邊的云淡風輕,構成兩個世界”。
我懷疑夢里的另一個我,
才是真實的我。
我與刀光劍影斗智斗勇,
都有柳暗花明的勝算,
甄別、斡旋、偵察和反偵察,
從來沒有失控。
而我只是在夢醒之后,
發現夢里那些相同的布局,
完全是子虛烏有。
如果不存在神秘主義的解釋的話,如此可疑的“夢里的另一個我”,讓詩人自身感到如此陌生的另一個我,或許源于多變的社會生活狀態中的某種集體潛意識。在一個劇烈變遷的社會歷史階段,在欲望與無欲的掙扎中,似乎每個人都在“掩蓋”與“裸露”之間擺動,每個人都會成為兩個(或更多)相互分離的人,每個人的每個時刻或許都是相互分離的人。詩人力圖在不斷制造出反語的過程中與一個確定的自我保持距離。
夢的時間或許是事實世界的一個諷喻性的敘述。夢是事實世界的寓言。這是一個風輕云淡的世界,也是一個刀光劍影的世界。對個人生活而言的刀光劍影或許純屬子虛烏有,但卻揭示了人們所熟知的社會情境。在利益急劇增長而不能共享的時代,社會性的互利模式已經轉換為無法遏制的互害模式。詩人的無意識場景確然無疑地揭露了真實的社會生活場景。人們總是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我夢里都是神出鬼沒,
那天神對我說,
賜你萬能的權力,詛咒你敵人。
我在手機上翻檢所有的名錄,
都笑容可掬,沒有。
鬼又過來,拿一帖索命符,
去把你身邊的小人帶來。
我省略了學生時代,從職場過濾,
也找不到可以送帖的人。
世界很大分不清子丑寅卯,
習慣忽冷忽熱的面具,
看淡漸行漸遠的背影。
與人過招是前世修來的緣分,
輕易指認敵人和小人,
自己就小了。
因為有如此之多的煩惱、敵意與焦慮,才有這么多的自我勸慰。在充滿反語的敘述話語中,梁平的詩抵達了一個反諷的生活時刻。他希望從這種焦慮狀態中解脫出來,一個證明就是他將這一切視為“前世修來的緣分”,即使擁有如夢中天神賦予的超自然力,他也想棄絕那種帶來敵意和傷害的能力。詩人注重的,是對友誼的渴望、對坦誠的向往、對戒備與敵意的棄絕,以及由此而來的豁達心智的養成。如《花名冊》一詩所說,“別在生命的嘔心瀝血里,假設敵意與對抗,平心靜氣”。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在無欲與欲望之間,在裸露與掩蓋之間,在友情與敵意之間,詩人在不斷地游移擺動,因為他并不能確定是環境決定論還是個人的主觀修為才是整個事態的焦點,社會心態的改變過于劇烈,時代的巋然不變也無法撼動,以至于古典社會的倫理不再起真實的作用,無欲與耳順也缺乏真實的生活根基。詩人所做的,也是在不斷地制造反語,以便與自身永遠區別開來,在下一個時刻,與自己不統一。他說,《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所以面對你就是一個問題。
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
比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
你是不是你不重要,
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
鏡子面前我看不見自己,
別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見自己,
我是我自己的錯覺。
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閡,
跟自己一次又一次發生沖突。
我需要從另一個方向,
找回自己……
真正反省的時刻終于到來了: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這里需要偏離一下傳記心理學的描述,關注一下詩歌中的悖謬修辭。對詩人來說,修辭即意味著一種隱秘的修行。詩歌中的修辭意味著對一種隱而不彰的意義模式的探究,我們在此意義上說它是內心深處的修行方式。比起“所謂胸懷,就是放得下鮮花,拿得起滿世界的荊棘”這樣的格言化的表達,“我是我自己的錯覺”,我“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閡”,體現出更富于現代意義的內在省思。打個比方說,如果詩歌中的雋語警句或格言風格是修行的“顯宗”部分,“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這樣的修辭則是修行的“密宗”領域。再換個說法,前者指向對他人的教誨,后者則歸于慎獨。
詩人尋找著自己的《過敏原》是什么,過敏既是身體上的又是心理性的,當“皮膚上的戰事蔓延至胸腔”,他看見路易斯·辛普森關于詩人要有一個好胃口的告誡,“消化橡皮、煤、鈾、月亮和詩”,讓他“羞愧于我的自愛自憐”,便“忘了夜幕放大的恐懼,在鏡子前端正衣冠。大義凜然地出門、下樓、發動汽車”——
我不是去醫院,而是漫無目的,
想隨機遇見我的過敏原,
一個紅燈,或者一顆子彈。
在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里,“端正衣冠”“大義凜然”的姿態幾乎具有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喜劇性意味。如果說梁平的詩沒有陷入顧影自憐的話,恰恰是因為他在某種反語敘事中將自我喜劇化了,將自我理解為一個諷刺性的和嬉戲性的形象似乎更自然一些。對社會生活的精確感知和荒誕不經的夢幻感受,成就了一種既荒謬又浪漫的風格。詩人意識到,或許自己《有病》,但“問題在于這絕不是某個偶然,而是我的常態”。不要輕易忘記,他習慣于制造自己的反語,他說,《我是一個病句》——
其實,我的病句并不傳染,
如此而已,我確信,
我們同病相憐。
讀者也未能幸免:我們同病相憐。在一個無序或失序的時代里,在一個啟動了互害模式的社會環境里,詩歌可能帶來一種同情之理解,孵育著我們內心的自由與寬容。在尋找“過敏原”的同時他也在尋求著自身的《免疫力》,這首詩從“感冒不期而遇”的日常敘述出發,寫到“病毒環游我的身體”,然而漸漸進入疾病與免疫力的轉義敘事,“我的醫生朋友說我自作自受,說免疫力下降,無藥能敵”——
免疫力被敏感偷走了,
免疫力被遲鈍偷走了,
免疫力被無辜偷走了,
免疫力被牽掛偷走了,
免疫力被心亂如麻的長夜偷走了,
病毒乘虛而入,身體潰不成軍。
而已,只能自己下處方——
最好的藥是找回睡眠,
凈心、凈身、凈念,
睡個糊涂覺,諸事視而不見,
不聞不問不明不白,
一覺醒來,還是麗日清風。
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詩人是患者又是分析師,詩是癥候表征、病理分析又是一紙處方。讓詩人糾結的是,無論是敏感還是遲鈍,無辜還是牽掛,都是心亂如麻,都是過敏原,都在降低免疫力。心態或情態的產生指向一個充斥過敏原的外部世界,內心生活的及物性帶來了內心世界的非自主性,詩人的方劑是古典修養的“凈心、凈身、凈念”,是古典的坐忘或清空,或難得糊涂,然而現代生活的特性恰恰與之相反。這是沖突的核心,不只是人與人的沖突,不僅是人與自身的沖突,也是自然秩序(自然時序)與社會失序之間的沖突。
詩人一面告誡自己需時時警惕,“羊出沒和狼出沒,在我這里都有十面埋伏”,“季節變幻,即使改頭換面,我也不能口無遮攔”(《冬至這天我格外警惕》);一面又是反語敘述,書寫著“自由、慈祥、心無旁騖”的心境;“石頭落下,碎了,樹葉化成云,天空好藍,好晴朗”(《一片樹葉在半空》)。他書寫著安詳的生活,安逸于竹葉青和青花郎,“知己、知人、知冷暖”(《我的南方不是很南》);“隨手翻看枕邊的皇歷,有提示——‘諸神上天,百無禁忌’知道了什么叫恍然大悟”,“一只白鷺飛過水面”(《小年》);一面是足不出戶,“精心圈養我的文字”(《十字路口》);同時又是“中秋沒有月亮,暴雨灌滿的夜”,又是難以安頓身心的失眠,“東南西北的門上了鎖,我不能進出,不能游刃,身心找不到地方安頓”(《宅》)。似乎在人的煩惱與焦慮之下,隱藏著無數的秘密,其實在焦慮之下并沒有什么更深的奧秘,普遍焦慮的心態才是這個時代的秘密。無論是荒誕的夢還是失眠,都指向這個世俗時代的負面秘密。
在這些傳記性敘述中,并沒有提供那些軼事性的個人史,詩歌的自我書寫所提供的個人信息既多又少,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無疑是很少的,是一種“掩蓋”,但在心跡表露的意義上又是信息極多的。在梁平的詩歌中,有關心跡、心境的描述相當豐富,他揭示出個性的陰影、夢幻、情緒及其動機,與人爭辯、自我對話與勸說,并將有關敘述系統地融入社會生活史的脈絡之中。與之同時,這一自我對話的過程也是詩人在詩歌寫作中不斷制造自身反語的過程,以至于我們不能確認詩人的自我質疑是他最終的看法。
詩人似乎一直受到《流言蜚語》的攪擾,“一直在醞釀一份悼詞,寫給鬧騰的季節”,他“在舊年的檔案里翻檢,找不到春暖和花開”,唯有“倒春寒”。他寫到,一個人走了,“這個季節花開在病房”,花、冬季、病房的并置如同謊言,艷麗是詭異的,“窗外嘰嘰喳喳”的麻雀,“怎么聽都是流言蜚語”。看起來耳順是困難的,雖然他說過“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雜音,都可以婉轉,動聽”。個人的心態也像這個世界,無端,失序,反復無常。我們不會驚訝于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厭倦”情緒——
厭倦時刻分明一日三餐。
厭倦早出晚歸兩點一線。
厭倦書桌前半真半假的抒情。
厭倦陽臺上一絲不茍的色彩。
厭倦甜言蜜語。
厭倦風花雪月。
厭倦瓜熟蒂落。
厭倦水到渠成。
厭倦陰影虛設的清涼。
厭倦落葉鋪滿的哀嘆。
厭倦口蜜腹劍勾心斗角。
厭倦虛情假意心照不宣。
至此而言,這是對厭倦情緒的常規表達,但這首詩卻是反語性的《喜歡厭倦》,后面的詩句則轉向明顯的反語敘述,“循規蹈矩順理成章按部就班,讓我遲鈍、萎靡、不堪,形同行尸走肉。厭倦,厭倦,厭倦流連忘返,把過去的每一寸光陰,清空。留一塊傷疤,獨自刀耕火種,日月可鑒”。梁平經常翻轉詩歌中的命題,也經常翻轉其情緒。因為,厭倦突然變成了清空的方式。
在難辨真情假意和流言蜚語的時代,詩人告誡自己,不僅《有些話可以不說》,而且《有些事可以不做》,“比如告密,盯梢。地上一片落葉的動靜,夜半一句夢話的甄別,一個似是而非的背影進了小巷,與你無關……”這是斷絕不必要的及物狀態,為著回歸自己。似乎詩人再次《心甘情愿》地回到最普通的生活中來,“從做爺爺那天開始,我就當孫子了”,“不能在好端端漢語里爆粗,口無遮攔”,“再也沒有橫眉冷對”,“記住所有人的笑臉”。
從詩人對自我反方向的驚覺、對疾病和過敏原的診斷,到對免疫力的失去與康復嘗試,乃至企圖從“厭倦”這樣一種負面情緒中擺脫欲望與塵世的糾纏,梁平越來越喜歡使用一種治療型的語言,傳記經驗的敘述越來越向個人心理分析史的方向傾斜,尋找著平復焦慮的話語途徑。詩人一再地在欲望與無欲、掛心與厭倦、掩蓋與袒露的縫隙里吐露著心跡,也描述著個人生活史的軌跡,“我從酒局出逃,在南河苑陽臺上獨飲霓虹”,“隱秘的疼痛,沒有蛛絲馬跡。與醉相擁,夜半孤獨醒來,坐守一顆寒星”(《那天立秋》);在南河苑的書房里感知季節變化,“我的書房是我的江山,列陣的書脊和密集的蔥蘢,浩蕩千軍萬馬,我在,我不在,它們都在”(《晚上七點》);如果這些也可以視為個人傳記經驗的話,如《露天電影》所說,“這是一個年代記憶”,“城市籃球場,鄉村的曬壩,標配一塊大白布和高音喇叭,如果有星星和月亮,真是浪漫。……遇上激動人心的時候,滿場集體吼一句臺詞”。需要探究的是,往昔的歲月所發生的一切,如何構成了個人傳記經驗的底色,“一個年代記憶”如何成為一代人并不健康的欲望導師,就像詩人所說的電影里的“女特務”,兼具政治上的壞和感性上的美,“漂亮得讓人不能忘記”。一般而言,個人的傳記書寫就其回憶的特性而言,總是追溯性的和退行性的。
“重慶,成都,生活的儲存與流放”
隨著自我認知的擴展,成都地理與重慶地理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詩人傳記體驗的一部分,他書寫著新的愚昧時代的《惜字宮》,或再也找不到救命稻草的《草的市》(草市街),他追溯著往日《富興堂書莊》所承載的“蜀中盆地的市井傳說,節氣演變,寺廟里的晨鐘暮鼓”,考據著“檀木雕版上”的秘聞和“古城興衰與滄桑”。而今,詩人生活在作為歷史遺跡的《燕魯公所》,這里曾是“那些飄飛馬褂長辮的朝野”的落腳之地,“在這三進式樣的老院子……嵌入商賈與官差的馬蹄聲”,“磚的棱、勾心斗角的屋檐”之會館變成了公所,“司職于接風、踐行、聯絡情感”,而今“燕魯公除了留下名字,什么都沒有了,青灰色的磚和雕窗,片甲不留”,在一條昏暗的小巷里唯余“面目全非的三間老屋”,但詩人說,“我在。在這里看書、寫詩,安靜得可以獨自澎湃”。
雖然隱秘的榮耀和驚心動魄的歷史銷聲匿跡了,但即使物質消失了,曾經存在過的一切依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如給人留下社會心理陰影的落魂橋,“我曾在這條街上走動,夜深人靜”,“那是長衫長辮穿行的年代,華陽府行刑的劊子手,赤裸上身滿臉橫肉的刀客,在那里舞蹈,長辮咬在嘴里,落地的是人頭、寒光和血”,“那些場景,在街的盡頭拼出三個鮮紅的大字——落魂橋。落虹與落魂,幾百年過去,一抹云煙,有多少魂魄可以升起彩虹?”(《落虹橋》)。如果說落魂橋是舊社會的集體記憶,《某某某墓》則屬于個人記憶的一部分,“沙坪壩是城市唯一的平地,公園里的樹綠得發冷,即使最熱的時候進來,笑聲也會凍僵”。
“裸露的墳場”如同“舊年的傷疤”,那是“一百顆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一下子“封存了體溫”。在很多詩篇中,詩人描述了他生活過和正生活的地方,它們形成了一個地方的氛圍,就像空氣那樣不可見,但卻被人無意識地呼吸著,即使沒有進入人們的意識,也會潛入人的無意識。似乎沒有理由排除,梁平詩歌中的追殺與搏擊,這源自于古老的歷史,即使它們已經被人遺忘。
對個人生活史的追蹤,詩人一直追溯到“未曾謀面的祖籍”,“我的年輕、年邁的祖母,以及她們的祖母、祖母的祖母”,她們那些“游刃有余,習慣了刀剪在紙上的說話”,她們生命中的“那些故事的片段與細節,那些哀樂與喜怒,那些隱秘”(《剪紙》),似乎仍然與詩人有關;還有在“舊社會”運送槍支的《老爺子》,“我無法想象那些水運的槍支”,從“重慶到漢口”,“如何安全抵達”,“那些槍口,最后對準了誰?老爺子從來沒有提及”,只為“養家糊口”的“老爺子從來不看天上的風云,只管地上的煙火,拖兒帶女,踉踉蹌蹌走進新的社會和時代”。從這些追憶性的傳記式敘述中,可以發現一種自覺地挖掘“時間”或“自我”地層的意圖,在追溯籍貫時他說,“我不在那里生長,那是我的歸宿”,“爺爺的墓碑是家譜的節選”,“爺爺就是我的豐都”(《豐都》)。就像一部真實的傳記那樣,時間和家族譜系的回溯成為一個必要的部分。
最終,詩人發現自己真正的歸宿是在文字中,他說,“我睡在一張紙上”,“都拼接成漢字,清瘦、飽滿,或者殘損,那是我一生健全的檔案”。在梁平看來,不管殘損還是健全,詩歌都是他最真實的私人檔案。作為生活史或事件史,詩歌定當不會成為個人“一生健全的檔案”,但作為一種精神生活史或心理軌跡的記錄,詩歌留下了豐富多樣的內在體驗。而且,詩人相信,“我在紙上的一詠三嘆,被自己珍藏,成為絕唱”(《一張紙上》);他在另一首詩里說,“如虎,如豹”,“我的文字,和我一樣桀驁,積攢了一生的氣血,咄咄逼人”(《十字路口》)。梁平對自己文字的想象亦是如此相反,“一詠三嘆”似乎依然是“咄咄逼人”的反語。
作為個人傳記書寫的詩歌或許最終不過是一種修辭與“想象”,對梁平來說,更是一種反語敘述的過程,“越是虛無縹緲越具體。我自己姓甚名誰已經迷糊,想象過于奢侈,場景似是而非”(《想象》),但無疑的是,其間也透露出無足輕重的真實信息,如《墓志銘》所記錄:“我的祖籍、出生地,我的姓氏、名字、階段性的身高,我血脈里的嘉陵江和長江……”生活或許平淡無奇,而諸多矛盾沖突也轉向了它的轉義,“安逸、散漫、麻辣也柔和”,就像詩人的文字與性情,總在“茶”和“酒”之間,可以“赴湯蹈火”,亦能“溫文爾雅”。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私人檔案”到“墓志銘”——
重慶,成都,生活的儲存與流放,
我身在其中,健在。
我叫梁平,省略了履歷,
同名同姓成千上萬,只有你,
能夠指認,而且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