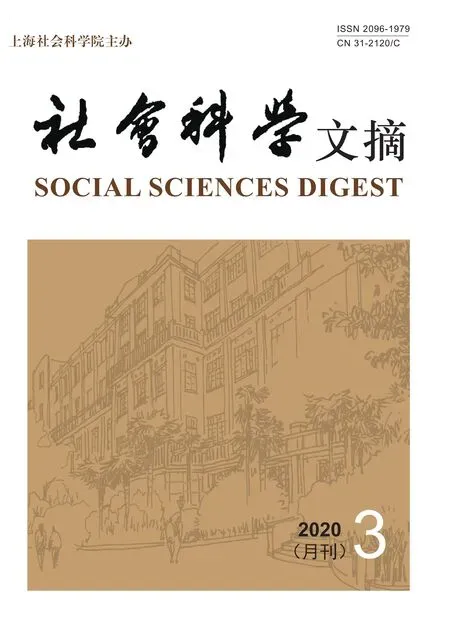西歷·國歷·公歷:近代中國的歷法“正名”
晚清時期,推行來自西方的陽歷成為政治改革的訴求之一,但未及改歷,清王朝已土崩瓦解。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孫中山宣布使用陽歷。在民國初期陽歷的宣傳與推行過程中,面對民眾習于舊歷的社會心態與風俗習慣,趨新人士及政府一方面通過具體措施來擴大陽歷的使用范圍;另一方面通過改換歷法名稱,以彰顯新歷法“革新”的意義,由此使得歷法名稱發生了巨大變化。
夷洋轉換:從“西洋歷”到“太陽歷”
中國傳統歷法是兼顧月亮繞地球和地球繞太陽運動周期的陰陽合歷,而自明末以后傳入中國的儒略歷和格里高利歷都是參考地球繞太陽運動周期的陽歷。明末清初之際,以湯若望等人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迎合歷法改革的需求,將當時西方天文學最新的成果介紹到中國,對中國歷法發展做出了貢獻。1645年湯若望將《崇禎歷書》改編、進呈,得到清廷重用,并以順治帝題名“西洋新法歷書”刊行天下,此后欽天監依此編訂的歷書封面都題有“欽天監依西洋新法印造時憲歷日頒行天下”字樣。不過,由于傳教士制作的“西洋新歷”帶有西方背景和宗教目的,引發了維護儒學地位者的強烈反對,強化了時人對中西歷法的區分意識。其中,楊光先與湯若望之爭更是將中西歷法置于對立的境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明末清初到鴉片戰爭前夕,在夷夏之辨的思想背景之下,時人對世界的認識框架仍是以華夏為核心,遵循了文化從內向外、由高到低的層級秩序。所以當西方歷算某些方面超越了中國歷法時,夷夏之辨所形成的層級秩序就受到了挑戰。而通過“西學中源”的論說,認定西洋歷法不過是華夏世界“禮失于野”的結果,就解決了“夏不如夷”的理論困境。晚清時人則將道器分離,提出即便技藝不如西洋,但西洋先進的觀測技藝卻說明了“圣人之道”的正確。由此可見,正是由于歷法在宣示正朔、構建社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加之夷夏之辨的思想氛圍,時人試圖將“西洋歷”的作用限于技藝層面,以維護華夏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也反映了人們不得不用而又心存排斥的復雜心態。
鴉片戰爭之后,“夷夏之辨”的世界認知框架逐漸走向崩潰,西方現代科學技術與知識日益廣泛地進入中國,趨新崇洋成為社會思潮,這就使得時人對西洋歷法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到了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郭嵩燾為代表的趨新之士,已經能較為準確地看待中西歷法的差異,對西洋歷的優點亦能肯定。在這一轉變中,時人逐漸了解到西洋歷法之精髓,此前對西洋歷法鄙棄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西洋歷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肯定。
隨著對西洋歷法的了解日深,晚清時人開始從歷法使用“普遍性”的角度來述論使用西洋歷法的積極意義,也促使帶有西方背景的“西洋歷”逐漸向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太陽歷”轉變。梳理晚清“西洋歷”(西歷)蛻變為“太陽歷”(陽歷)的過程,其背后的思想原因十分值得分析:一是“太陽歷”比“西洋歷”的名稱更符合歷法本身的特點,且從晚清時人的述論來看,現代人的社會活動與太陽的關系更為密切,加之太陽歷不隔年置閏月,反利于財政、教育、農事等的安排,從實用角度更有利于社會時間秩序的構建;二是“太陽歷”或“陽歷”的名稱已經超越了“西洋”的地理局限,開始成為世界通用的歷法,其中包含了近代國人追尋公理公例、意圖富國強兵的愿望;三是伴隨著西方國家在全球的擴張,以“陽歷”命名的格里高利歷在19世紀后期已成為全球通用的時間體系,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與國家構建都受到這一時間體系的影響。
“與世界大同”:國歷與公歷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陽歷成為政府主導推行的歷法。但由于普通民眾在知識體系和日常生活中對陽歷的陌生感,陽歷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色彩等,使得陽歷在民初的推行面臨諸多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改換陽歷的名稱,重構陽歷的思想因素,就成為民初推行新歷的重要舉措之一。
將陽歷的宗教內涵和使用的普遍性進行區分,是時人重構陽歷思想因素的基本路徑。晚清時期,康有為、劉師培和章太炎等人,都受到了基督紀年方式的影響,試圖模仿它在中國建立起一以貫之的紀年體系,分別提出了“孔子紀年”“黃帝紀年”和“西周共和元年紀年”等主張。不過,在他們的述論中,將“基督紀年”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因素視為“公理”“公例”,用以述論各自紀年主張的合理性。因而,當民初陽歷推行不暢時,將宗教性因素從陽歷中剝離出來,就成為時人的重要嘗試。其中錢玄同的論述最具有代表性。1919年11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歷紀年》一文,集中地闡釋了他將“基督紀年”改稱“世界公歷紀年”的緣由。在他看來,基督紀年的廣泛傳播已經使其逐漸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局限,成為一種更具有普遍性的計時工具。這一主張相比于清末梁啟超的《紀年公理》《太陽歷法議》等文章,更加著重從時間計量符號簡便易行的角度來述論使用陽歷之必要性,重構了“陽歷”的內容意涵,使之成為世人眼中的“公共歷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們逐步去掉了這一歷法原來所具有的宗教性因素。
而“國歷”名稱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國歷運動。早在1922年錢玄同就已經提出了“國歷”一詞,指稱“中華民國之歷法”,用以對抗守舊的“滿清遺老”。但將“國歷”名稱擴展到整個社會,則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推動的“廢除舊歷,普用國歷”運動。這次改歷運動比民國之初廢除陰歷運動,規模更大,影響更廣。盡管國歷包含了溝通中西的便利性,但其塑造民國認同的指向,也彰顯了“國歷”名稱更為強烈的政治意涵。
“公歷”與“國歷”實際上指同一歷法,但名稱的差異仍表明兩者意涵指向的區別:“國歷”名稱意在強調該歷法為中華民國使用之歷法,欲強化中華民國之權威;而“公歷”的名稱,正是消解了陽歷的西方色彩和宗教性因素,更強調了這一歷法使用的普遍性。不過,1912年孫中山在宣布使用陽歷的同時,也使用中華民國紀年。所以,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華民國紀年”和“國歷”名稱與強調世界大同的“公歷”存在著內在的矛盾。盡管“國歷”為“陽歷”的別稱,“公歷”也是指同一歷法,但“國歷”還應該包括了“中華民國紀年”這一內容,其名稱蘊含的民族主義因素,也在一定范圍內制約了“公歷”名稱的傳播。
知識重構:陰歷、舊歷、廢歷和農歷
陽歷名稱蛻變為“國歷”和“公歷”,是政府及時人構建新時間秩序的努力之一。不過,阻礙新時間體系推廣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傳統歷法的深厚基礎及其使用的廣泛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除了通過政策法令限制或廢止陰歷,還試圖從名稱上對陰歷進行重構。而這種重構則是在參照陽歷名稱下進行的,并與陽歷、新歷等名稱形成了一種區隔對立的關系。
就以“陰歷”名稱的蛻變來看,在明末清初西洋歷法進入中國后,當時人們為了區分西洋歷法,將中國傳統歷法稱為“中歷”。進入晚清之后,隨著人們對西洋歷法的“陽歷”特點認識深入,以“陽歷”作為參照,“陰歷”的名稱才日漸流行。而中西新舊二元話語體系的形成,“陰歷”與“陽歷”名稱日漸固化,反過來影響了時人對中西兩種歷法內涵的認識。中國傳統歷法兼顧地球繞日和月繞地球周期運動。但更多的人將陽歷和陰歷對立而論,這種名稱上的區分,導致時人忽略了中國傳統歷法作為陰陽合歷的特點,且因民國建立之后新舊歷法的對立而進一步固化。這些例證至少說明,“陽歷”名稱的廣泛傳播,已經成為新歷的代名詞;而中國傳統歷法則被局限到與之相對的“陰歷”框架之內,并且在陽歷的參照之下喪失了原有的豐富內涵。此種情況在北京政府時期的官定歷書中有最直接的反映,歷日編排以陽歷為主導,一般放置于歷書的上方,而陰歷則附于陽歷之下。到了20世紀30年代,伴隨著聲勢浩大的國歷運動,新編訂的官定歷書甚至要刪去以往歷書中的朔望等內容,因為它們屬于清代官定歷書的“陰歷”內容。
由于“陽歷”作為塑造政治權威與革新社會的重要標志,與之相對的“陰歷”就成為了新秩序構建和社會革新的障礙。在清末民初主張革新歷法的人看來,陽歷是西方國家富強文明的重要標志,使用陽歷可以讓中國耳目一新,“與世界各強國共進文明”,而“陰歷”則是中西交通和中國進步的障礙。另一方面,伴隨著西方國際體系在全球的擴展,格列高利歷逐漸成為全球通用時間體系,中國要置身于這一國際體系自然需要遵從其時間秩序。時人已經認識到推行陽歷是中弱西強的結果,預設了陽歷比陰歷更為現代,實際上是期望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從而實現富強。因此,陰陽、新舊與中弱西強的處境產生了直接關聯,兩者也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陽歷被中華民國確立為官定歷法,自然就成為當政者統一時政和塑造權威的工具,而制約陽歷推行的陰歷就成為新秩序構建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新歷”指稱“陽歷”所要凸顯的正是這一歷法對于構建新政治秩序的意義。與此對照,作為傳統象征和代表的“陰歷”無法滿足趨新時人革新之期待,被稱為“舊歷”,甚至是“廢歷”。推行新歷遇到阻礙,使得趨新之士的改歷主張愈加極端,必欲廢除舊歷而后快。正是在這種取向之下,北京政府時期中央觀象臺通過“查禁私歷”和“刪改舊歷”,以實現“時政劃一”的目標,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推行國歷運動,徹底禁止陰歷的使用,并將使用陰歷視為落后、反動的標志,甚至宣揚“徹底革命,非實行國歷廢除舊歷不可”!這些做法都加劇了歷法新舊對立的二元格局。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時人將“科學性”視為陽歷最突出的特點,與之相對,附著了傳統信仰習俗的陰歷則被視為“迷信”的代表。盡管陽歷與陰歷各有利弊,但在清末民初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中,時人并不能客觀理性地看待兩種歷法各自的優劣。更為關鍵的是,在時人看來,這一歷法是以現代科學作為基礎,進一步強化了陽歷“先進”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舊歷附加了太多的神煞宜忌,在時人看來,使用陰歷就有助長“迷信”的消極作用。而時人也正是參照了具有“革命”“進步”和“科學”特質的陽歷,對陰歷名稱及內涵進行了重構,形成了新舊中西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陰歷”從晚清時期著重反映歷法特點的名稱,到民國時期逐漸被趨新之士和政府當局賦予了更多負面的含義,進而蛻變為“舊歷”“廢歷”,被塑造成了“專制”“落后”和“迷信”的面目。這一變化過程也凸顯了“陽歷”以及“新歷”“公歷”等名稱的“積極”意義。
而“農歷”名稱的出現,既是歷法新舊之爭的副產品,也是歷法改革者對陰歷廣泛使用現實的妥協。“農歷”名稱的重構,是在科學與權威的視角下進行,從科學的角度而言,廢止舊歷以及附著于舊歷之上的迷信習俗,僅僅將能夠指導農業生產的科學知識納入到“農歷”中,從而構建“科學”的歷法,以便與國歷保持一致。從權威的角度來看,趨新之士與政府都希望在農村推行國歷,以實現時政統一,強化政府的政治權威。經過重構的“農歷”,盡管其名稱得到了更廣泛的使用,但依從于原有時間體系所構建的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并未得到徹底的改造。以科學的名義試圖改正民眾的民俗習慣,以權威的名義推行與民眾生活不相協調的時間體系,反而導致了官民之間的對立,“農歷”作為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在實際使用中逐漸成為“舊歷”的代名詞。這也是西歷成為“國歷”,變為更具普遍意義的“公歷”,相對立的“中歷”、“農歷”蛻變為地方性及局部性的計時體系和知識體系的過程。
余論
清末民初之際,西洋歷法從外在于中國的時間架構,變成為中國社會時間秩序的主導,并成為時人眼中的“公共歷法”,其中名稱的轉換至關重要。“國歷”“公歷”等新詞語的引入,也是趨新時人與政府試圖通過改換歷法名稱,在西方主導的民族國家體系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嘗試。通過歷法正名,為中國嵌入世界通用時間體系掃除了學理上的障礙,又凸顯了中國在接納這一時間體系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而在中西二元話語體系中的新舊陰陽卻具有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交錯的意涵指向。如“陽歷”蛻為“國歷”,其中的民族主義因素并不是對傳統的固守,而是對西方“先進”歷法的借鑒;而“公歷”的世界主義指向雖更為明確,卻是以消解了“陽歷”的西方特色為前提,與已淪為地方性時間的中國傳統歷法相對立的。
從更深層次上看,全球時間標準化進程既消解了中國傳統時間體系的獨立性,又加劇了清末民初以來社會時間的紛歧,使得歷法名稱及其使用的統一問題得以凸顯。以標準化時間為基礎所構建的現代工業、學校教育、財政預算及國際交往等方面,都成為推動中國在歷法時間上趨同西方的重要因素。但清末民初歷法改革導致的陰歷與陽歷并存,反倒使得原有的單一歷法體系變成了陰陽并存的二元格局,給社會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這些對陰歷和陽歷便利性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在中國被納入到全球標準時間體系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討論的預設都是以強勢的陽歷作為參照,進而比較兩種歷法的優劣,而陽歷的“正名”無非是要構建其在時間秩序中的主導性地位。
正是由于時人賦予歷法變革極為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推行陽歷所具有的革新作用,也使得近代中國歷法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國家危亡情感訴求的結果。因而時人論述陽歷的優點時,對這一異質歷法體系與中國文化傳統、信仰習俗之間的沖突,并無足夠的認識。特別是在趨新崇洋的背景之下,反思西歷使用困境的文章并未得到人們的重視。不過近代中國面對全球標準時間不斷擴張的大勢,以及國人革新社會的強烈訴求,有關中國歷法的理性言論并未得到時人足夠重視。
更值得關注的是,通過晚清民國時期歷法名稱改換,政府與民眾在歷法使用、名稱改換上呈現出對立之勢。一方面,民國時期政府通過推行陽歷,并通過在官定歷書中刪除陰歷,期望以這種方式實現“時政劃一”的目標,但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強行改換歷法名稱和禁止使用舊歷,又強化了陰歷與陽歷等名稱的對立,使得人們在認識中國歷法變化時,捉襟見肘:被重構的歷法名稱難以涵蓋歷法本身所包含的豐富意義,其中陰歷的名稱與實際之間難以完全吻合,甚至影響了后人對中國傳統歷法的理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國歷法的正名運動,并非呈現出線性的演化更替進程,時至今日,公歷、陽歷、陰歷、農歷等歷法名稱仍然被廣泛使用,盡管已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但各自仍有較為清晰的論域范圍和內容指向。這也是近代歷法“正名”運動留下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