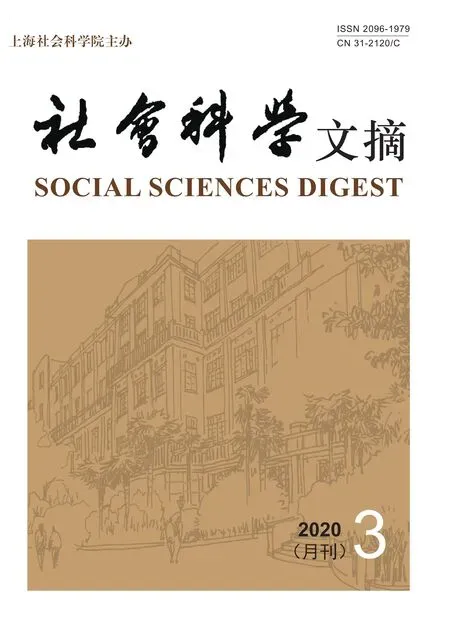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從民族主義到新世界主義
大國成長的持續性和大國崛起后在當今世界舞臺上究竟應該扮演什么樣的國際角色,關鍵取決于支撐大國成長進程的價值。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是什么?回顧中國近代史以來的現代化歷史和中國的大國成長進程,我們不難發現,自鴉片戰爭開啟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歷經了一個轉換過程,最初是以民族主義為價值基礎,到后來尤其是自20世紀最后十年以來,中國崛起成為對世界有深刻影響的亞洲國家,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出來,中國的世界主義主張也逐漸上升為可以取代民族主義主張的價值,而這種世界主義又與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相結合并對“天下主義”進行了新的改造,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崛起的價值主張和價值基礎。
民族主義與中國崛起的時間維度
中國的民族主義始于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此前只有“華夏”與“蠻夷”之別,并無民族主義。“華”“夷”的認知是“天下”的不同角色定位,是對儒家中心與儒家所浸染程度不同的稱謂,所以“天下”不是指國家,而是世界或中華帝國。而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就是一個從“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民族是現代國家的基礎,而民族主義則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力量。因此,對民族主義的討論不能離開現代國家。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才產生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這個思潮首先是以民族復興、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甚至可以說,這就是鴉片戰爭后推動民族主義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卷入20世紀的兩股力量,是推進中國逐漸從宗法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兩大輪子。在中國,以“民族復興”的民族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是根源于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反思。一般來說,民族主義往往具有保守性、自我封閉性,但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反思所引發的中國民族主義卻是開放的、積極進取的。這就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和“放眼向洋看世界”的主張。這兩者是一個統一的思想,使得中國的“民族性不僅沒有泯滅,反而與改革和進步相連,升華為自覺的愛國主義了”。
然而,林則徐、魏源等“師夷長技”的目的是“制夷”,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制夷”的根本所在。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后,一大批士大夫開始思考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王朝如何振興,這是在遭到太平天國的嚴重打擊之后王朝的自我警醒;二是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中國的自我圖強問題。因此,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興起的以“自強”為內容的洋務運動,最初主要是買洋槍鎮壓農民運動為主,到后來農民運動失敗后則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蘊,即洋務派開始思考中國的民族產業和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問題了。因此,在東方,“民族主義的新穎之處在于其政治自覺”。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自覺”就是國家的現代化(當時都稱為“近代化”)。從民族自覺到現代化這個過程,是中國民族主義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過,當時中國的現代化依然主要是學習西方的技術,體制則必須保留中國既有的體制,也就是堅持“中體西用”的原則。但洋務運動最終因“體”“用”的矛盾而陷入困境,中國的現代化也僅僅邁出了一小步。
甲午戰爭失敗,知識分子從“中體西用”中擺脫出來,開始對中國既有的制度進行反思,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但卻把這個制度再造的偉大工程寄托于一個皇帝。這件事表明知識分子對革命的認識不足,以為僅憑愛國之心就可以再造一個制度。這顯然是幼稚的,所以制度再造歸于失敗。制度反思的過程也是民主啟蒙的過程,尤其是伴隨戰爭而來的歐風美雨激蕩著古老的華夏,確實是既有腥風血雨,也包含著潤物無聲的和暢惠風。而民主的啟蒙正是這種“惠風”,給中國社會“滋潤”出了一種革命的力量,并主張對中國社會進行“舊邦新造”,從而使中國從制度反思走向制度革命。制度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但中國社會也進入最黑暗和最動蕩的時期。理論上來說,革命成功將有利于民族復興和現代化,可是革命成功反而使社會陷入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卻又“以最嚴酷的方式把這種積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們的眼前”,不過所謂否極泰來,“它又往往成為社會轉機的起點”。這個轉機的起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從此之后,中國自鴉片戰爭失敗后的民族主義內涵,從民族復興而后加上現代化,再而后加上社會主義的內涵,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特有的內涵,即“民族復興、現代化、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內涵。中國崛起的進程也正是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開啟的,三位一體的民族主義內涵,則是中國崛起在時間即歷史這一維度上的思想基礎和目標訴求。
民族主義與中國崛起的空間維度
從空間維度來認識民族主義與中國崛起的關系問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崛起放在同一時期世界發展的框架之中來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如果說從時間維度看,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于認識到中國內部的貧弱而強調自強,并通過自強來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從而達到民族復興、現代化的目標,最后這種民族主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并以社會主義來統合民族復興、現代化的使命的,那么,從空間維度看,中國的民族主義則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由于中國曾經遭遇外國列強的侵略,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帶有強烈的悲情色彩;二是由于中國實力的增強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具有強烈的自負感,而這種自負感卻又與歷史的悲情結合在一起,因而這種民族主義往往具有排外性、對外的拒斥性。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的結果會導致中國重新走向自我封閉,至少會在民族心理上走向封閉。當然,上述兩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總是以愛國主義的面貌出現,以至于理性的人都不敢隨便反對,若出來反對就有可能被冠以“賣國”的帽子。
第一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認識世界的視角上是“歷史的眼光”,也就是即便已經是21世紀,但中國充滿悲情色彩的民族主義往往把具體的國家放在歷史中,以這個國家在歷史上對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來安置該國在中國與該國關系中的角色。實際上,盡管中國與具體的其他一個國家都處在21世紀的雙邊關系上,但因將對方角色凝滯,從而導致空間與角色的時間錯位。這就是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進攻性民族主義”,也有中國學者稱之為“雪恥型民族主義”,其“不僅僅在于它對戰爭的狂熱或者說反人道主義的立場,而在于它極大地封閉了民族的政治想象與智慧的空間,最終成為一種自我顛覆的運動,將民族引向更為深重的災難與自我毀滅”。由此可見,進攻性民族主義(也包括悲情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健康的民族心理表現。誠然,我們對歷史上所遭遇的悲劇和外來的侵略要始終牢記,要成為一種國家記憶、集體記憶,但處于大國成長中的民族不能永遠生活在歷史的悲情之中,更不能有要“雪恥”的、進攻性的民族心理。
第二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認識外界時常常是盯住別國的問題,卻專注于自己哪怕是僅有的一點優勢,用自己的優勢與他國的劣勢相比,以凸顯自己的優勢,也就是一種自負心理或者叫“自負型民族主義”。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近代史上有過,主要表現為文化保守主義,主要代表包括早期的辜鴻銘、林琴南、杜亞泉等,后期的常燕生、釋太虛等,他們主張維護中國傳統,倡導“中國本位”文化,“從固有道德建設現代中國文化”。文化自負的根源在于自唐宋以來中國領先于世界的農耕文明和經濟成就,宋代更是達到了中國乃至世界農耕文明的頂峰。在182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爆發前的20年,大清帝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加之中國社會的自我封閉,以至于對西方發生的一切都毫無知曉,還沉睡在“天朝大國”的美夢之中。類似當時的自負感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則以超乎尋常的“自戀感”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自戀感”大致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即經濟實力)的提升而不斷膨脹。
由此可見,在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中時,民族主義的確是社會動員、民族動員、國家動員最重要也是最為有效的工具。作為革命動員的工具,民族主義從價值來看是正義性的。因為殖民主義確實給落后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悲劇。但是,在和平時期,民族主義卻很容易與民粹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混為一談,甚至可以說,當今各國的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各種主義的大雜燴,這可能會抵消民族主義積極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全球治理又是相對立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民族主義卻堅守傳統的主權理念,成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堅決抵制者。這種情況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都廣泛地存在著。執政者必須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來使用好這把雙刃劍,既要使之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利劍,又不至于傷及執政者本身。
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與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的變遷
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的變遷是隨著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而發生變化的。近代史上,中國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弱者,因此必須以民族之大義來進行民族動員以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爭奪民族獨立的意識形態和革命動員工具。中國從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承擔著反帝反封建的雙重革命任務。這兩種革命都是基于民族主義的價值理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過程中,民族主義也是最重要的工具。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后被卷入西方的現代性進程的,并且在反西方現代性的過程中,中國也吸收了類似于民族主義這種現代性元素,且內化為中國國民性的構成要素。在這個內化的過程中,發軔于西方現代性的民族主義被中國吸收后迅速成為抵制西方殖民主義等的意識形態。因此,啟蒙在中國就是為了救亡,作為西方現代性產物的民族主義在這個時候才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以至于同樣是西方現代性產物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即便作為民族主義對立面也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在東方的巨大勝利。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國際角色轉換的過程中自然就向國際主義轉向。這種轉向是以民族主義為底色的,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被“世界革命論”的國際主義埋藏在深處。因此,在20世紀后半期的大部分時間里,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來看,無論蘇聯還是中國民族主義向國際主義的轉向,實際上都是把民族主義從一個國家內部放大到持同樣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家和有著同樣被殖民經歷的國家之中,從而在形式上使得國際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民族主義的一個“變種”。所以,有學者指出:“國際主義每向前發展一步,都面臨著復雜的民族問題、國家利益原則等觀念運動的考驗與制約。”
不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民族主義摒棄了以意識形態為分水嶺的國際主義,重新回到國家利益上來,民族主義得到再次弘揚。所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之后較長時期內,中國民族主義所持的主張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向外學習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這種開放的民族主義使中國在全球化中獲得了最大的收益,中國崛起的進程也正是中國以開放的姿態融入全球化和國際體系的進程。因此,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化進程,不只是中國國際責任的內容,也是中國開放的民族主義主張。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崛起必然要對國際體系和整個國際社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西方看來是以西方的“他者”角色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國這樣的主導國對中國的遏制就在所難免。而伴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而來的,是西方對中國的各種負面輿論,其中包括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中國顛覆論”“修昔底德陷阱論”等,從而激起了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關鍵是,當今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像近代史上缺乏物質支撐的民族主義,而是在中國較為堅實的經濟實力支撐下的民族主義,它更加有底氣,或者說是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自信的民族主義。如果這樣的民族主義與近代歷史上因失敗而產生的恥辱感結合起來,那么,為了解決“挨罵”的問題,它最容易滑落成為前面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其結果就是排外、拒外、仇外而走向自負式的封閉,諸如砸日系汽車、砸韓系汽車、拒用蘋果手機等,無不呈現出民粹化傾向,用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來展現和平時期的民粹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往往以愛國主義的面貌出現,但這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或者說也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與全球化、全球治理是相對立的。一方面,全球化、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卻堅守傳統的狹隘國家利益理念并以此抵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是融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程才得以崛起的。因此,非理性的民族主義、非理性的愛國主義并不是真正的愛國,而是在愛國主義的面紗下發泄潛藏在內心的悲情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民族心理對一個國家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一個大國的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理,更需要理性的民族主義。只有善于向世界學習的民族主義才是健康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心理才能支撐大國的持續成長進程,并為大國崛起提供持久不衰的動力。
中國崛起的世界訴求與中國的世界主義創新
民族主義既然無法為中國的大國成長提供持久動力,那么中國的崛起將以什么為價值基礎呢?有學者提出了“天下觀”的想象,認為“天下”是“中國式的兼容普遍主義”,“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礎”,“天下體系是一個反帝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向世界萬民平等開放的政治體系,天下不僅‘無外’而且‘為公’”。然而,分封制瓦解以后,‘大一統’的專制政治體制對‘天下’重新進行了闡釋,其華夷觀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那種‘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天下觀’,迅速被強大皇權之下‘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天下觀’所取代”。顯然,這種天下主義具有武力征服的內容,不可能是當今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
也有學者提出從歐洲的世界主義中去尋找相應的價值。誠然,世界主義有某種合理的價值。然而,世界主義所堅持的道德普遍主義“包含絕對主義、本質主義和一元論的成分,認為人類社會中存在著某種終極的絕對合理的而又被普遍運用的一元化價值標準”。因而,源自于古希臘的世界主義并非大國成長既有的價值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崛起的方式因國家的特殊國情、國家的特殊品格等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從西方的文化中去尋找價值基礎。中國的崛起方式與歷史上西方大國崛起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的崛起不是一種純粹以追求硬實力為目的的“工具性崛起”,而是一種內涵式的制度性崛起。所以,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一定是既要有中國歷史文化價值,也應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價值,是二者的有機結合和內在統一;同時,還包含著對世界主義在當代世界創新的價值。
首先,所謂中國歷史文化價值,就是指“天下主義”內涵的當代轉換和革新,而轉換與革新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以“天下”的情懷來抑制狹隘的民族主義。把天下主義與民族主義放在一起進行討論是不合適的,但這里的“天下主義”是指被轉變為當下意義中的“天下主義”,從而避免了兩種主義的時空穿越。在當今借用天下主義不是為了恢復中國歷史上的秩序,而是因為天下主義的確還存在著“無外”的內容,正如孔子所說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孔子這句話就是說,“天下”是沒有明確邊界的,而許倬云將孔子的話闡釋為:“沒有絕對的 ‘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把這一思想引進到當今以抑制偏狹的、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方可為中國崛起的價值基礎創新提供可能。
其次,既然是“無外”和“沒有絕對的‘他者’”,那么這種思想就完全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思想相結合,這種結合將為走向超越源自古希臘的世界主義創造可能。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的思想指出:只有在這種自覺的經濟制度安排下,每個人才能全面發展自己的能力并獲得自由。“這種”自覺的經濟制度安排是指,第一,這是一種自覺的制度安排,它克服以前一切時代發展條件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第二,這一制度安排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只有達到“人自身的解放”,才能實現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恩格斯在 《〈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就指出: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從政治解放、社會解放到“人類解放”,“人類解放”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全部思想的主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天下主義能夠結合并創新世界主義的理論可能。
最后,中國的世界主義創新就是以中國式的世界主義“修正”西方的世界主義。中國的政治學理論之所以長期賦予世界主義以負面的意義,就是因為西方的世界主義是個體主義的世界主義,主張世界主義“宣揚漠視民族傳統,民族文化,以至于放棄民族主權的政治思想”。而中國的世界主義創新則強調在堅持各自民族傳統、民族文化的前提下,謀求互利共贏的全球主義的世界主義。因此,中國新世界主義主張:一是“各美其美”,也就是各自尊重自身的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二是“美人之美”,也就是彼此尊重對方的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以及彼此的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三是“美美與共”,即在互信、互利、平等、協商的前提下進行跨文化交流和共同增進利益,從而夯實新世界主義的物質基礎;四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內容的“天下大同”,也即是中國倡導并與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體人們為了人類共同的利益與安全而結成的共同體,完全是全球主義的性質,是新世界主義的具體載體。
結束語
民族主義是一種革命動員工具,也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作為社會動員的工具,可以作為凝聚國民的重要意識形態,但也是自我封閉、盲目自信的籬笆,它本質上具有不可克服的狹隘性。因此,我們不能因民族主義在革命時期的“必要性、功能性與根植性”,就否定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即“導致分裂、動蕩和破壞的能力”。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治理更加迫切的當今時代,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功能更加突出。由此可見,民族主義絕對不能作為支撐中國大國成長的價值,也無法支撐中國崛起的進程。
天下主義是一種歷史的文化想象,不是現實的價值。尤其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以及由此引發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的崩潰,表明西周以來的中國古典式的天下主義盡管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與現代世界中的民族主義浪潮并不相容,正是現代民族主義與西方殖民主義促使了中國天下主義體系的解體。而所謂的“新天下主義”不過是一種想象,或者說只是一個“空籃子”,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世界主義雖然在西方是主流的價值取向,也曾經對中國社會有重要影響,但世界主義不僅在西方存在著不同流派,而且內涵也大相徑庭。而近代中國對世界主義的移植也并沒有完全消化其內容,有的甚至是囫圇吞棗。因此,不加分析地移植西方的任何價值都會使中國的大國成長進程受挫。中國式的新世界主義應該是在遏制民族主義的消極功能前提下,既秉承“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中國天下主義傳統,又對世界主義的積極價值善于“拿來”。中國的價值創新不是無中生有的創新,而是在傳統性、民族性、時代性、世界性統一的前提下的科學創新。這種創新的價值才是中國大國成長和不斷崛起的價值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