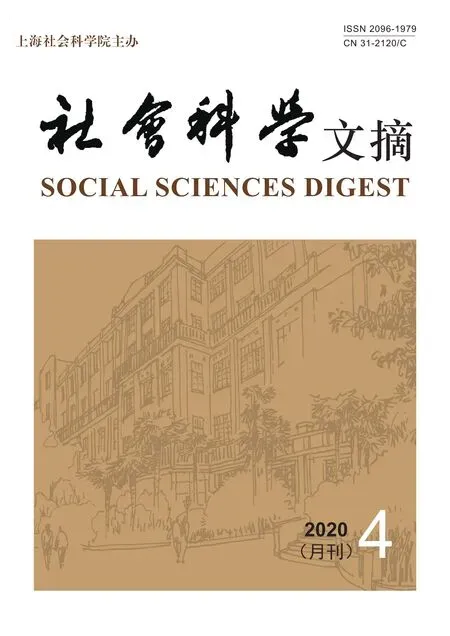全球金融危機后匯率理論和政策的反思與新進展
文/劉凱 肖柏高 王度州
對于開放經濟體來說,匯率決定機制及匯率政策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市場穩定的重要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主流經濟學界對匯率理論以及相關政策的研究與反思有了新的進展,政策界對開放環境下的匯率政策制定也有了新的觀點。系統梳理這些新進展和新觀點,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匯率決定機制以及國際匯率政策實踐的認識。
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基于購買力平價、利率平價、泰勒規則、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等來探討匯率決定機制的研究取得了值得關注的進展。
(一)基于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匯率決定機制研究新進展
購買力平價理論是最古老的匯率決定理論之一,雖然其簡單易懂,但所謂“購買力平價之謎”一直困擾著學術界。“購買力平價之謎”是指在短期存在價格黏性的情況下,各種名義沖擊導致了實際匯率相對于購買力平價匯率有大幅度的偏離,而且實際匯率收斂到購買力平價匯率的速度顯著慢于黏性價格調整時間。
針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新進展主要來自從微觀層面和異質性視角來解釋“購買力平價之謎”。Imbs等人將購買力平價理論的研究由宏觀視角深入到部門商品的微觀層面,他們提出,部門價格的異質動態性是導致實際匯率波動大、收斂慢的原因。異質性的來源包括部門商品可貿易性、關稅、生產鏈的市場權力、價格黏性等,然而以往對購買力平價的實證研究均忽略了這一點。
在Imbs等的基礎上,Carvalho &Nechio通過比較一個新凱恩斯主義多部門模型和一個單部門模型來試圖解釋部門價格異質性的加總過程是如何導致實際匯率產生更大的偏離持續性和更復雜的運動。單部門模型和多部門模型分別對應著Imbs等中排除部門價格異質性效應和未排除異質性的兩種情況。
也有文獻認為,產生“購買力平價之謎”的原因在于微觀價格和宏觀價格層面受到的沖擊不同。Bergin等認為,微觀價格和宏觀價格受到的沖擊和調整機制是不一樣的。微觀層面的商品價格調整受一價定律約束,當進行加總時,對商品價格的異質性微觀沖擊有正有負,所以它們對宏觀價格的效應會被中和為零。因此,宏觀價格偏離由宏觀沖擊決定,跟微觀價格異質性無關,且宏觀價格的調整通過名義匯率渠道來實現。
(二)基于利率平價理論的匯率決定機制研究新進展
利率平價分為拋補利率平價(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CIP)和非拋補利率平價(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UIP),它們的區別在于是否使用遠期匯率合約。
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后,CIP出現了顯著、持續性的偏離。Avdjiev等、Du等認為,CIP的偏離應該從銀行業找原因。CIP的偏離意味著套利行為無法進行,而套利行為能否順利進行與跨境銀行的美元借貸能力(做市能力)密切相關。而《巴塞爾協議 Ⅲ》以及《多德-弗蘭克法案》對銀行杠桿率、經營業務等監管要求大大限制了銀行參與套利的能力和意愿。Iida 等則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貨幣政策的分歧對各自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造成的不同影響,是導致CIP偏離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實證研究基本都拒絕了UIP假設,但得益于不斷豐富的長期遠期匯率合約和債券數據以及新興市場數據,2008年以來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對UIP比較有利的結論。最新文獻對于UIP偏離有不同的解釋。Colacito&Croce、Bansal &Shaliastovich等認為,經濟增長、通脹等的不確定性以及國內外消費的條件方差的差異導致了UIP偏離。Chen &Tsang則提出,以往UIP的研究中用于表示市場期望的變量是不準確的,他們發現用收益率曲線來推測市場期望能得出更好的結果。Evans &Lyons等從外匯市場的微觀結構——市場信息和市場參與者展開。他們認為以往宏觀模型的普遍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匯率最關鍵的決定因素或許不是宏觀經濟因素,而可能是微觀結構。市場參與者行為因素也被認為是UIP偏離的重要原因,Bacchetta &van Wincoop、Ilut以及Burnside等分別考察了不頻繁做決策、厭惡模糊、過度自信的投資者是如何導致外匯市場失靈進而導致UIP無法成立的。
(三)基于泰勒規則或開放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匯率決定機制研究
如果兩國的央行根據泰勒規則設定名義利率,而且名義匯率遵循UIP條件,那么實際匯率就由預期通脹差異和產出缺口差異決定,這就是基于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機制。在此基礎上,一些開放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文獻,在假定UIP條件成立和央行施行泰勒規則的前提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了除貿易套利和利率套利之外的其他眾多因素對匯率決定機制的影響。
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流動性枯竭和經濟衰退等問題,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紛紛出臺了量化寬松等非傳統的貨幣政策,也出現了零利率下限的現象,這對傳統泰勒規則的適用性提出了疑問。為了適應新情況,Curdia&Michael提出,泰勒規則要納入金融條件以及要對利差項進行調整等。Taylor還指出,美國央行的泰勒規則由金融危機前的線性形式轉變成為危機后的非線性形式。因此,如果泰勒規則本身需要調整和修改,那么基于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模型是否還表現良好則需要重新驗證。Molodtsova &Papell將代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金融壓力的指標納入了泰勒規則,他們發現基于修改過的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模型在預測上仍然有更佳的表現。
DSGE模型是當前開放宏觀研究中最主流的模型,Alvarez &Kehoe、Verdelhan 利用這類模型研究了當本國和外國消費者及投資者擁有不同的風險偏好及效用函數,或者面臨不同沖擊時,這些差異如何導致了資產風險溢價的變化,進而導致了UIP的失效。Adolfson使用歐元區的數據,對含有名義剛性和真實摩擦的DSGE模型進行貝葉斯估算發現,實際匯率的變動主要來源于“開放經濟”沖擊,也就是進出口加價(import and export markup)、風險升水、非對稱技術沖擊等,只有很少一部分來自產出的波動,這對匯率與經濟基本變量不相關之謎提供了一個解釋。
(四)其他匯率決定機制研究新進展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的匯率決定機制新觀點:
1.共同因子模型
大量文獻表明,雙邊匯率之間存在聯動效應。Greenaway-McGrevy等進一步發現,在控制了雙邊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后,雙邊匯率仍受一些共同因子的影響,這些共同因子驅動著匯率聯動變化。共同因子模型的優點在于它考慮到了現代國際匯率體系是一個多邊匯率體系,不像傳統研究只單純地研究兩國之間的匯率而忽視第三國或共同因子的影響。但是,共同因子模型的難點和缺點均在于:研究者依據自己的經驗來確定共同因子的經濟學意義,而這并沒有清晰、明確的理論支持。
2.基于外部失衡說的匯率決定模型
從宏觀層面來看,經常賬戶失衡及資本賬戶失衡無疑是影響匯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有文獻從外部失衡的視角來探討匯率的決定機制。Gourinchas &Rey(下文簡稱為GR)考慮了美國的外部失衡對于美元匯率的重要影響。當前的外部失衡意味著未來凈出口和外國資產回報的調整,而匯率是調整的關鍵因素。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前的對外部門經濟條件已經蘊含了未來匯率的變動信息。對于GR模型的有效性,Gourinchas &Rey、Della Corte等的實證研究和Alquist &Chinn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
3.基于大宗商品價格的匯率決定模型
Chen等提出,大宗商品的價格也許可以作為大宗商品出口國(如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貨幣匯率的解釋變量。這些小型開放經濟體其貨幣匯率較少受干預,且大宗商品出口占他們總出口的份額都比較大,但它們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又是價格接受者,所以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對于他們的匯率來說是較大的外生沖擊。但是,基于大宗商品價格的匯率決定模型的實證檢驗結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商品價格和匯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并不明確。
理論與現實:匯率決定理論的實證檢驗與匯率預測
綜合現有的對匯率決定理論進行實證檢驗以及匯率預測的文獻來看,可以得出以下3個基本結論:
(一)所用數據的時間期限、頻率等特征會影響匯率理論的實證檢驗結果
同一個模型,同一個國家,如果用不同時間段的數據來檢驗,得出的結果可能會不同,這往往是因為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例如全球金融危機之前CIP是基本成立的,之后CIP出現了顯著的背離。
所選數據的時間頻率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例如,一些文獻試圖研究UIP條件下貨幣政策沖擊對匯率的影響機制,如果選取周度或月度甚至季度匯率數據,那么將難以排除匯率壓力對央行貨幣政策的反向因果關系;若選擇日度或更高頻的數據,那么這個問題則能得到較大緩解。當然,使用高頻的數據難以反映貨幣政策的持續性影響。
(二)基于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模型似乎比其他匯率決定模型表現得更好
Molodtsova &Papell、Mark、Wang &Wu的研究均發現,基于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模型無論是在樣本內還是樣本外預測中,都要優于PPP、UIP以及隨機游走模型。Rossi&Inoue則指出,基于泰勒規則的匯率決定模型對隨機游走模型的優越性在不同的時間窗口選擇下都是成立的。
(三)混合模型能夠提高對匯率的預測能力
Mark、Rossi等認為,匯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相關性不高,并非是宏觀變量沒有蘊含匯率信息,而是相關模型沒有選擇正確的變量。或者說,驅動匯率波動的變量是不斷變化的,而這些變量難以被單一模型捕捉到。因此,匯率決定模型常常在某些時間段表現比較好,但是在更長的或者其它時期內卻表現不佳。為了解決這一問題,Balke等、Park &Park 通過允許參數變動來體現不同時段各變量在決定匯率走勢時所擁有的權重是變化的,他們的模型表現出更強的預測能力。Wright則利用貝葉斯模型平均的方法將不同模型的預測結果進行加權平均,得出了經貝葉斯平均的模型顯著優于隨機游走模型的結論。
全球金融危機后匯率政策方面的反思與新進展
(一)各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新變化:浮動還是維持穩定
匯率的自由浮動制與穩定制的優劣之爭一直沒有停止。但從現實情況看,金融危機后,實行匯率穩定制的國家數量增加,而實行浮動制的國家減少。
匯率制度的選擇,本質上取決于其宏觀經濟績效。從防范宏觀經濟波動和經濟金融危機的視角來看,匯率浮動或者穩定的抉擇問題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更為重要,因為過去發生的貨幣危機大多發生在新興經濟體,而多數新興經濟體面臨或者正在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對于一國貨幣危機的發生,一些傳統文獻認為,極端的匯率制度(完全固定和完全浮動)通常是有紀律性的,而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型匯率制度因為缺乏約束性而容易導致危機的發生。但Combes等人的研究認為,貨幣危機的發生跟匯率制度沒有直接聯系,國內的宏觀政策才是主因。從長期經濟增長的視角來看,實證研究認為匯率制度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似乎并不明確。從現實情況來看,一般來說,擁有大量外幣計價債務和貨幣錯配的國家傾向于選擇盯住制(硬或者軟)來減少匯率劇烈波動造成的損失,那些以往信譽不佳的國家也更可能選擇盯住某種貨幣來增強其政策公信度。發達國家則更多地選擇浮動匯率制度。
(二)對貨幣政策的新認識:匯率是否該被納入央行反應函數
長期以來,匯率因素不是貨幣政策研究中被考慮的因素,但是卻是新興國家常用的政策工具。最早于1990年被新西蘭采用、后逐步擴散到近30個國家的通脹目標制貨幣政策,一般要求匯率是完全自由浮動的,其否定央行干預匯率的必要性。盡管通脹目標制有利于增強央行公信力并降低通脹率,但是伴隨而來的過高的匯率波動會給金融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帶來貿易損失、輸入型通脹等方面的問題,這也是新興經濟體害怕浮動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針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究都趨向于支持央行應該將匯率納入考慮范圍,建議這些國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采取適當靈活的匯率干預政策。
(三)“三元悖論”與“二元悖論”之爭
以Rey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三元悖論”需讓位于“二元悖論”,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中心國家(美國)驅動的國際金融體系中杠杠率、信貸增長和信貸流動的周期性變化,在資本自由流動和浮動匯率制下,仍然能傳導到其他國家,進而導致他國貨幣政策失效。目前學術界對于“二元悖論”在多大程度上成立還存在爭議。伍戈和陸簡針對中國的分析指出,“二元悖論”或許可以成立,但需要滿足一定的臨界條件。Aizenman等、Obstfeld等的實證研究結果與“三元悖論”一致,拒絕“二元悖論”。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本文對于人民幣匯率決定機理的啟示是,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也是復雜的,購買力平價背后的貿易套利動機、利率平價背后的利率套利動機以及其他眾多因素都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分析和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動需要借助多種模型、從多個維度進行考察。另外,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而言,適度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加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總體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符合國際經驗的。尤其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猶存、對外金融風險較大的背景下,這樣的機制是防范對外金融風險、避免內外金融風險惡性聯動以及維護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必要舉措。但是應該看到,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管理”有余而“浮動”不足,中國應該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適當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以更好地維持貨幣政策有效性和平抑宏觀經濟波動。
而對于開放環境下的貨幣政策制定,中國貨幣當局應該避免兩個極端:完全服務于匯率穩定或者完全不顧匯率穩定。中國的貨幣政策在實現產出穩定和通脹穩定這一主要目標的同時,還應該適度關注匯率穩定。劉凱和李育通過構建美元本位下多國DSGE模型分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也得出了類似結論。至于匯率因素在中國貨幣政策制定中的權重應該為多大,則需要進一步的定量研究。另外,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溢出效應較為明顯,“二元悖論”等相關研究要引起重視,中國的匯率政策與金融開放政策制定要充分吸取歷史上新興經濟體金融危機的教訓、要能切實防范貨幣危機的發生以及內外部金融風險的惡性聯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