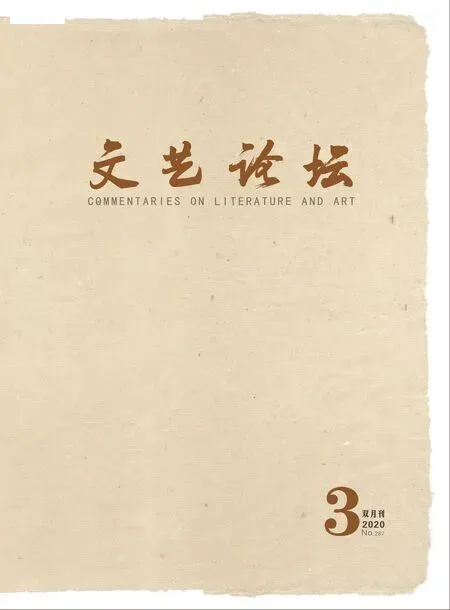愛(ài)的回歸
——重讀王躍文《愛(ài)歷元年》
◎ 劉雪琳
在小說(shuō)《愛(ài)歷元年》的封面上,有這樣一段話:“一部無(wú)比誠(chéng)實(shí)的愛(ài)情之書(shū)、命運(yùn)之書(shū)和人性之書(shū),多角度呈現(xiàn)了愛(ài)情世界里欲望的沖撞、內(nèi)心的迷亂和人性中善與美的升華。”這是初讀《愛(ài)歷元年》的感想。這本書(shū)從出版到現(xiàn)在,一晃六個(gè)年頭過(guò)去了,在數(shù)次的閱讀中,我又有了一種全新的感受,《愛(ài)歷元年》對(duì)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來(lái)中國(guó)人精神生活的變化進(jìn)行了忠實(shí)記錄,使得它不僅是一部簡(jiǎn)單的愛(ài)情小說(shuō),作家王躍文從宏觀視野和微觀筆觸同時(shí)入手,通過(guò)呈現(xiàn)出脫胎于當(dāng)下但又比當(dāng)下更令人深思和追問(wèn)的現(xiàn)實(shí),描繪出了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來(lái)人的情感危機(jī)與靈魂變異的時(shí)代剪影,而透過(guò)這一剪影,我們捕捉到的是愛(ài)的回歸。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lái)就是一個(gè)充滿愛(ài)的民族,“仁者愛(ài)人”,愛(ài)就是善,愛(ài)就是親情、就是友情。《愛(ài)歷元年》秉持著這樣一個(gè)亙古不變的理念,將愛(ài)放在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的大背景中,展現(xiàn)它的生長(zhǎng)、發(fā)展、變化的軌跡。盡管愛(ài)在其中歷經(jīng)磨難,充滿曲折,飽含艱辛,但作家相信,它終能戰(zhàn)勝苦難,一如既往。呼喚愛(ài)的回歸,就是《愛(ài)歷元年》貫穿始終的主題。
一
初看之下,《愛(ài)歷元年》通過(guò)一對(duì)知識(shí)分子的中年危機(jī),講述了知識(shí)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或者說(shuō)是一部愛(ài)情小說(shuō)。但實(shí)際上本書(shū)所展現(xiàn)的,則是一個(gè)更為宏大的場(chǎng)景,他從一個(gè)家庭出發(fā),展現(xiàn)了處于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人們精神困惑與掙扎的歷程,從而折射出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來(lái)中國(guó)社會(huì)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變遷。在書(shū)中,作家努力尋找著宏大背景下“愛(ài)”如何走出困境、重獲新生的方式,從而為呼喚愛(ài)的回歸作了一次生動(dòng)而形象地闡釋,這不是一次簡(jiǎn)單的回歸,而是跨越三十多年的愛(ài)的回歸。
《愛(ài)歷元年》從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寫(xiě)到二十一世紀(jì),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間跨度較長(zhǎng),重點(diǎn)寫(xiě)了兩個(gè)大的場(chǎng)域:小縣城、大都市;寫(xiě)了三代人,父輩、子輩、孫輩;就主角孫離、喜子等而言,從青年寫(xiě)到了中年。細(xì)細(xì)品味之中,我們能看到,這部作品描繪了一幅改革開(kāi)放三十多年來(lái)發(fā)展的軌跡圖,并再現(xiàn)了三代人的生活變化與精神面貌。孫離的父親從508 廠下放到鄉(xiāng)村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辦了養(yǎng)豬場(chǎng),承包了萬(wàn)畝山林,成了萬(wàn)元戶,最先買(mǎi)上了電視機(jī);弟弟孫卻先是經(jīng)商,發(fā)財(cái)后又通過(guò)結(jié)交上層,準(zhǔn)備參選人大代表;兒子亦赤從小學(xué)習(xí)優(yōu)異,雖然考上了上海的醫(yī)學(xué)院,卻酷愛(ài)文學(xué)和音樂(lè),性子也冷冷的,桀驁不訓(xùn),與父母關(guān)系疏遠(yuǎn)。作品還寫(xiě)到了改革開(kāi)放后的另一種現(xiàn)狀,進(jìn)城打工的農(nóng)民越來(lái)越多,農(nóng)田無(wú)人耕作,變得荒蕪;社會(huì)風(fēng)氣發(fā)生變化,道德出現(xiàn)滑坡。
的確,三十多年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但具體到經(jīng)歷的每一天,又都是普通尋常的。作品的生活畫(huà)面感很強(qiáng),不僅瑣碎的日常生活時(shí)有涉及,強(qiáng)制拆遷、官場(chǎng)腐敗、人大政協(xié)選舉、教育困局、工廠改革、醫(yī)療失誤、交易式婚姻、上訪等社會(huì)性問(wèn)題也沒(méi)有回避,都有較為深入的挖掘,其深刻的表達(dá),嚴(yán)峻的關(guān)切,讓人深思。應(yīng)該說(shuō),面對(duì)復(fù)雜多變的三十多年,作家是緊貼著生活寫(xiě)的,自然流暢,隨著時(shí)間推移,一步一步展開(kāi)。
王躍文在談到這部作品時(shí)說(shuō),“這部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初衷,源于對(duì)近二三十年來(lái)時(shí)世變遷的觀察和焦慮。這些年中國(guó)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沒(méi)有想清楚,就在倉(cāng)促間上路了。不管是彎路、歧途、迷宮,我們都大踏步地走了過(guò)去,我想應(yīng)該到了慢下來(lái)、好好想想的時(shí)候了。這就是問(wèn)題所在,我們走得太快,我們還沒(méi)有想明白,我們倉(cāng)促間上了路。盡管我們大踏步地走過(guò)來(lái)了,但我們卻丟失了很多東西,這中間,就包括愛(ài)。許多東西,丟失了也在所難免,如此一個(gè)時(shí)間的跨度,不丟失東西是不可能的。有些東西,丟失了就丟失了,可能也不足惜,有些東西,可能就是本不該丟失的,但由于各種原因,丟失了,怎么辦?是否可能找回,能否回歸?比如,愛(ài)就是如此,它丟失了沒(méi)有?如果丟失了,又如何找回?”《愛(ài)歷元年》首先做的,就是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回答。
二
呼喚愛(ài)的回歸,自然也就意味著愛(ài)已丟失。孫離與喜子的愛(ài)確曾丟失過(guò),這也是《愛(ài)歷元年》作為重點(diǎn)呈現(xiàn)給讀者的。
孫離和喜子是同一所中學(xué)的語(yǔ)文老師,這兩位富有浪漫情懷的年輕人,互相被對(duì)方身上的精神氣質(zhì)所吸引而墜入愛(ài)河。“愛(ài)歷”本身指向的就是男女情感,“我想造一個(gè)屬于我們自己的年歷,叫愛(ài)歷”。“我們的愛(ài)歷元年,就從你像仙子降到我眼前算起。”這是孫離為他和喜子的愛(ài)情量身定制的紀(jì)年法,意在向愛(ài)情致敬。愛(ài)情的開(kāi)始都是美好的,在孫離心中,“我夜里想著玫瑰色光邊的你,想象神話里說(shuō)的仙女下凡,應(yīng)該就是你這樣子”。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們志同道合,他們有著相同的理想與價(jià)值追求。
但是,“他倆甜蜜了沒(méi)多久,慢慢就開(kāi)始吵架。大事也吵,小事也吵”,孫離喜子的美好愛(ài)情,很快因?yàn)樯钪须u毛蒜皮的瑣事而磨損,褪去了初期的激情和甜蜜。甚至“懷上孩子的頭兩個(gè)月,喜子每天夜里都在同孫離爭(zhēng)吵。兩人爭(zhēng)來(lái)爭(zhēng)去,頭都爭(zhēng)暈了,有時(shí)候會(huì)忘記爭(zhēng)的是什么,反正擰著對(duì)方就是贏家”。兒子“亦赤”的到來(lái),使這個(gè)家庭更為完整,從此之后,親情本應(yīng)是他們生活的主旋律。然而,這樣的美好并沒(méi)有一直走下去。
表面看來(lái),是他們的精神追求有了差異,由此出發(fā),對(duì)身邊人與事的態(tài)度差異也漸漸顯山露水。喜子上進(jìn)心強(qiáng),有個(gè)性,剛生完孩子,就準(zhǔn)備考研,并與校長(zhǎng)發(fā)生了面對(duì)面的爭(zhēng)執(zhí),為了離開(kāi),她甚至還勸孫離“別寫(xiě)小說(shuō)了,好好兒進(jìn)修文憑。沒(méi)有過(guò)硬的文憑,哪里都別想去”。而孫離呢,時(shí)常沉迷于自己的所思所想乃至失眠,卻對(duì)喜子絕口不提,即使被追問(wèn)道出內(nèi)心想法,卻是遭到喜子的挖苦和疑忌。這則使人洞察到,這兩人之間的生活有了同床異夢(mèng)的感覺(jué)。悲劇或許就從這里產(chǎn)生。孫離和喜子都誤入了歧途,一個(gè)人的浪漫,在另一個(gè)人眼里竟然成了“瘋子”舉動(dòng)。夫妻本是親人,不同的精神向度和價(jià)值追求,本可以在親情的維度里得到調(diào)節(jié),但這似乎已不可能。從“元年”出發(fā)的夫妻,相互之間的話語(yǔ)已經(jīng)很少,超越生活層面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溝通幾乎沒(méi)有,漸行漸遠(yuǎn)的裂縫已被身邊的這些瑣事無(wú)情地撕開(kāi)。
終于,喜子通過(guò)考研擺脫了破舊的小縣城和無(wú)趣無(wú)望的中學(xué)教師生活,走上了通過(guò)個(gè)人奮斗而成功的道路。喜子走了,赴上海讀研深造,留下了孫離,繼續(xù)在縣城學(xué)校教書(shū)寫(xiě)作、撫養(yǎng)兒子。自此,融入了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喜子就以另一種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孫離面前,兩人的“分道揚(yáng)鑣”就此開(kāi)始。兩地分居,精神追求日漸不同,看似成了兩人愛(ài)情丟失甚至各自出軌的主要原因。
三
其實(shí),親情已逝才是其中無(wú)法回避的根由所在。孫離與喜子各自的出軌,與其說(shuō)是對(duì)愛(ài)情的背叛,不如說(shuō)是親情的遠(yuǎn)去。管中窺豹,隔膜只是背叛的開(kāi)始,誘惑才是愛(ài)情的殺手。
《愛(ài)歷元年》寫(xiě)了一對(duì)夫妻曲折的情感經(jīng)歷,與這段情感經(jīng)歷相聯(lián)系的,是一個(gè)家庭復(fù)雜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在這樣一個(gè)復(fù)雜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作家對(duì)人性的心理進(jìn)行了真誠(chéng)地探索,從而將中國(guó)人這三十多年間的精神走向、情感方式和內(nèi)心靈魂折射出來(lái),勾勒出社會(huì)生活的喜怒哀樂(lè)和酸甜苦辣,“我寫(xiě)小說(shuō),只關(guān)心人性”,作者借主人公孫離之口說(shuō)出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初衷。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的三十多年,社會(huì)生活的變化翻天覆地,人們所面臨的誘惑也越來(lái)越多,人們一方面困囿于物質(zhì)牢籠,另一方面又深陷感情陷阱,名聲、權(quán)力、欲望等使人意亂情迷、道德淪落。因此,《愛(ài)歷元年》也深刻地道出了當(dāng)下時(shí)代欲望與愛(ài)戀、出走與回歸的復(fù)雜糾結(jié),這既是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真實(shí)寫(xiě)照,也顯示出人類生活的某種難以逃脫的普遍性生存困境。對(duì)此,作家自己就曾講過(guò),他想寫(xiě)“知識(shí)分子的中年危機(jī)”,而不僅僅是感情危機(jī)或“婚姻出軌”。
從“愛(ài)歷元年”出發(fā),我們看到了孫離與喜子悲喜交織的情感歷程,作為副線,還有孫卻和小君、馬波和葉子等,他們的感情和婚姻,也無(wú)一例外地走入了困境。孫離和喜子,從對(duì)愛(ài)情的堅(jiān)守到背離,是在一條生活向好的道路上發(fā)生的,這也是中國(guó)多數(shù)夫妻的典型狀態(tài)。他們從鄉(xiāng)村走向城市,從底層走向中產(chǎn),反倒不能忠誠(chéng)相守了。對(duì)于“孫離喜子們”尋求婚外戀的緣由,《愛(ài)歷元年》也做出了闡釋。畢業(yè)于名牌大學(xué)的記者李樵,走進(jìn)了孫離的生活中,他們談天說(shuō)地,相見(jiàn)恨晚,很快,李樵成了孫離戀愛(ài)時(shí)的另一個(gè)“喜子”。孫離與李樵因愛(ài)而性,兩人在身體欲望的釋放中獲得了心靈上的進(jìn)一步提升,彼此都似乎從對(duì)方的身上找到了超凡脫俗的力量。背叛幾乎同步進(jìn)行。喜子與謝湘安也陷入熱戀之中。喜子在年輕的謝湘安身上找到了被保護(hù)的安全感,那些曾經(jīng)的委屈,事業(yè)遭遇的壓力,與孫離在日常生活中的爭(zhēng)執(zhí)偏離,因?yàn)橛辛酥x湘安的存在,喜子找到了一處可避風(fēng)躲雨的情感港灣。那種孫離在教室里講墮馬髻、在河邊見(jiàn)識(shí)蒹葭時(shí)的感受又回來(lái)了。
雖然孫離與喜子都分別找到了曾經(jīng)擁有的生活激情,然而,另一個(gè)殘酷的現(xiàn)實(shí)是,孫離和喜子之間,除了夫妻共處時(shí)日常的問(wèn)候,精神的交流幾近沒(méi)有。另外的兩對(duì)夫妻也好不到哪里去,孫離的弟弟孫卻發(fā)家致富后開(kāi)始拈花惹草,冷落結(jié)發(fā)妻子吳小君;孫離的朋友、宗教局副局長(zhǎng)馬波則因?yàn)槠拮拥牟录伞⑼碌南莺Γ萑氲教疑侣勚校Y(jié)果婚姻破裂,丟了官位。從青年到中年,愛(ài)情在他們身上都已經(jīng)蕩然無(wú)存。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雖然社會(huì)獲得了飛速的發(fā)展,但新形勢(shì)下涌入的利益沖擊、權(quán)力威逼、金錢(qián)誘惑和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也帶來(lái)了不少的挑戰(zhàn)與威脅。王躍文之所以以改革開(kāi)放這樣一個(gè)大背景來(lái)寫(xiě)《愛(ài)歷元年》,就在于告訴人們,面對(duì)生活中的各種誘惑,精神追求的不同,理想目標(biāo)的差異,只是一種不同的人生選擇,并不一定要以犧牲親情為代價(jià),也不應(yīng)該成為背叛愛(ài)情的借口。守住親情,愛(ài)自然就能堅(jiān)守。
四
回歸親情,這是回歸愛(ài)的必然選擇。《愛(ài)歷元年》當(dāng)然也是圍繞愛(ài)情展開(kāi)。“元年”的愛(ài)情肯定是美好的,但之后呢?對(duì)于那些在婚姻中變得迷茫的家庭來(lái)說(shuō),愛(ài)情如何持續(xù)?親情如何長(zhǎng)久?《愛(ài)歷元年》的高超之處,就在于通過(guò)親情的回歸,給出了這些問(wèn)題的答案。
通過(guò)內(nèi)心的抗?fàn)巵?lái)獲得自我救贖,從而悄然回歸到親情上來(lái),這是《愛(ài)歷元年》的書(shū)寫(xiě),是經(jīng)歷心靈磨礪之后的自我凈化和自我完善。王躍文所書(shū)寫(xiě)的孫離與喜子的“返回”,是家庭、道德、寬容、向善和愛(ài)的力量,讓他們最終迷途知返,回歸理性,重啟“愛(ài)歷元年”。主人公的名字就蘊(yùn)含了這一點(diǎn):由近乎離散的無(wú)奈到回復(fù)原點(diǎn)的欣喜。
與那些始亂終棄、分道揚(yáng)鑣、悲絕的出軌相比較,《愛(ài)歷元年》中的孫離和喜子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事件后,慢慢看到了對(duì)方內(nèi)心深處最美好的品質(zhì),果敢地從情感的泥淖中抽身而出,斬?cái)嗨烈庾涕L(zhǎng)的欲望,不再在互相傷害的道路上愈行愈遠(yuǎn),而是決定向美向善向責(zé)任靠攏,讓親情得以回歸。
很多人都認(rèn)為《愛(ài)歷元年》最終帶來(lái)的溫暖,是男女主人公在經(jīng)歷了情感波折之后,對(duì)己對(duì)人有了更加清醒的認(rèn)識(shí),繼而開(kāi)始了向善的追求與愛(ài)的回歸。“孫離很想告訴喜子,他至今不敢想起一個(gè)女人,一想起,他胸口就會(huì)鈍鈍地痛;但他和她的故事早已結(jié)束。喜子自己的故事,卻永遠(yuǎn)不想讓孫離知道。喜子只想安心地守在孫離身邊,變得越來(lái)越老,朝著他傻笑。”這份脫胎于自擾中的自省,證明了面對(duì)時(shí)代的變化,人們依然還有不斷更新自我的必要,還有繼續(xù)成長(zhǎng)的空間。這也是這部小說(shuō)的張力所在,它表現(xiàn)“人性的暗角”,也在發(fā)掘“人性的光芒”,并借光芒照亮那個(gè)幽暗之地。錯(cuò)抱親子事件與孫離的捐腎之舉,有人認(rèn)為是該書(shū)的敗筆所在,或許還有更好的結(jié)尾,這無(wú)法否定。但我以為,這樣的安排,恰是在昭示著一種親情的回歸。在情愛(ài)的蕪雜中,王躍文為筆下的主人公選擇了通過(guò)親情修復(fù)心靈失衡的這樣一種方式。由于感受到了親情,在愧疚和懺悔之中,喜子“主動(dòng)撤退”,孫離的回歸雖是被動(dòng)的,但也是平靜、溫和的,之所以如此,也是由于親情的支撐。孫離和喜子曾經(jīng)的淳樸善良、潔身自好等傳統(tǒng)美德,成了治“病”的最好良藥。亦赤的回歸,更是為這個(gè)家庭帶來(lái)了新的生機(jī),“媽媽,在拉薩/淚水把天空洗得更藍(lán)/雪山多么遼闊/格桑花讓我念想親人……媽媽,與其讓你如此牽掛/不如你帶我回家。”孫卻“病”后大徹大悟,毅然帶著妻子小君開(kāi)上房車(chē)走進(jìn)美麗的大自然,走向原野鄉(xiāng)村,并決定在鄉(xiāng)下捐建一所小學(xué),“后半輩子只做兩件事,教書(shū),陪父母、陪老婆孩子”,也是回到了久違的親情上來(lái)。這就是這部小說(shuō)的可貴之處,夫妻沒(méi)有離散,婚姻沒(méi)有重組,父母與子女達(dá)成和解,背離之后又和好如初的結(jié)局,體現(xiàn)了作家對(duì)人類愛(ài)情觸及本質(zhì)的追問(wèn),讓人沐浴到了人性中最初也最本真的親情的溫暖。
五
回歸善良,是《愛(ài)歷元年》呼喚的另一種愛(ài)的回歸,這也是《愛(ài)歷元年》為我們展現(xiàn)的另外一面。
孫離始終是一個(gè)充滿善意的人,這是讓我們感到欣喜的。在喜子遠(yuǎn)赴上海讀書(shū)期間,孫離獨(dú)自帶著兒子住在教師宿舍,隨之發(fā)生的“小英事件”讓他“身陷囹圄”。有些懵懂無(wú)知的小英對(duì)孫離萌生了朦朧的情愫,后來(lái)小英懷孕,她的哥哥宋小兵為訛錢(qián)嫁禍給孫離,隨后又將她賣(mài)給一個(gè)男人做老婆。我們看到,小說(shuō)一直未點(diǎn)破小英為何不站出來(lái)替孫離辯白,也未揭開(kāi)小英懷孕的謎底,只是借孫離的口表達(dá)了惋惜與憤懣。這種惋惜與憤懣流露出孫離內(nèi)心善的底色,對(duì)受難者小英深表同情,卻正好與社會(huì)人心之惡形成尖銳的對(duì)比,對(duì)地痞流氓宋小兵的丑惡嘴臉也暗含了各種批判。這樣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我們不曾少聞,沒(méi)有是非標(biāo)準(zhǔn)、出賣(mài)良心的小英們,無(wú)理取鬧、金錢(qián)至上的宋小兵們,都是被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無(wú)知綁架的人。讓人遺憾的是,小英對(duì)自我的悲劇命運(yùn)渾然不覺(jué),且無(wú)從反抗,甚至“傳承”至了下一代。
小英的兒子江陀子參與了拆遷辦對(duì)南津渡老街的深夜“強(qiáng)拆”,開(kāi)鏟車(chē)鏟倒房屋時(shí)砸死了被請(qǐng)來(lái)留守房子的母親小英,兒子成了殺死母親的“兇手”。事情發(fā)生后,相關(guān)部門(mén)對(duì)事故的處理是“掩蓋真相、推卸責(zé)任、找替罪羊”。拆遷公司找江陀子“私了”,就是出一大筆錢(qián)讓他主動(dòng)承擔(dān)全部罪名。于是,“一個(gè)母親冤里冤枉在睡夢(mèng)里被自己兒子挖死了,她無(wú)罪的兒子還要頂罪坐牢”。可恨的是,江陀子還來(lái)不及給母親送葬,果斷選擇了坐牢。在江陀子心里,錢(qián)成了他的一切,“他想用這些錢(qián)把家里老房子翻新,余下的錢(qián)做本錢(qián),跟爸爸一起開(kāi)個(gè)小門(mén)面做生意”,這樣就可以過(guò)上好的生活。江陀子已在卑微低賤的生活中喪失了起碼的價(jià)值判斷。所謂的正義、公理、尊嚴(yán)等,在他眼中一錢(qián)不值,他需要的首先是生存,是改變自己、改變家庭生存下去,他的選擇也是在底層掙扎的人對(duì)金錢(qián)的屈從和自我犧牲。
從“小英事件”到“江陀子事件”,孫離糾纏其中,盡管當(dāng)年聲名受損,甚至被剝奪上課的資格憤而離開(kāi)縣城,但當(dāng)他在夜總會(huì)偶遇小英、在何公廟碰到江陀子,卻依然托馬波為江陀子找到開(kāi)鏟車(chē)的差事,并在深夜為可憐的小英送木炭取暖等行動(dòng),卻是寫(xiě)出了孫離本性中善良悲憫的品質(zhì)。也正是有了他的對(duì)照,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的其他人物,如拆遷辦龍主任、派出所覃副所長(zhǎng)的眾生相,社會(huì)變遷中人性的善惡躍然紙上。
聚焦現(xiàn)實(shí),《愛(ài)歷元年》呈現(xiàn)了兩個(gè)極端的群體,一端是底層的弱勢(shì)群體,一端是有權(quán)有勢(shì)的既得利益者。這是一種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比,前者還在為溫飽殫精竭慮時(shí),后者卻為所欲為以至無(wú)所不能。在這里,權(quán)錢(qián)成了一切,善良也變得遙不可及。孫卻為當(dāng)上人大代表,四處“活動(dòng)”,搞權(quán)錢(qián)交易;陳院長(zhǎng)的兒子醉駕撞死了人,遠(yuǎn)在歐洲的他僅是花筆錢(qián)、幾句話就擺平了;與馬波一起競(jìng)爭(zhēng)局長(zhǎng)之位的對(duì)手,以傳布“誹聞”、造謠發(fā)帖的不正當(dāng)手段成功上位。如此等等,讓我們感到,這個(gè)社會(huì)的是非已經(jīng)顛倒,在道德淪喪、錢(qián)權(quán)當(dāng)?shù)赖拇蟓h(huán)境下,人性的善良受到了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對(duì)各種紛繁復(fù)雜的真相的揭示,緣于王躍文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敏銳觀察和深刻體驗(yàn),正是在這樣的深刻感受中,《愛(ài)歷元年》呼喚善良的回歸。
回歸善良,這是王躍文的期待,但整個(gè)社會(huì)的善良回歸,必然與社會(huì)大的背景的改變緊緊聯(lián)在一起。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這一點(diǎn)已從《愛(ài)歷元年》所描繪的親情、善性中表現(xiàn)出來(lái)。王躍文相信這一天肯定會(huì)來(lái),也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lái)。
《愛(ài)歷元年》的經(jīng)典意義也許正在于此。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如果我們?cè)賮?lái)研究改革開(kāi)放三十年中國(gu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人們的精神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那時(shí)人們就會(huì)從這一作品所呼喚的愛(ài)的回歸中,感受到它深入現(xiàn)實(shí)的力度、揭示情感的深度和展現(xiàn)人性的強(qiáng)度,作品的魅力也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