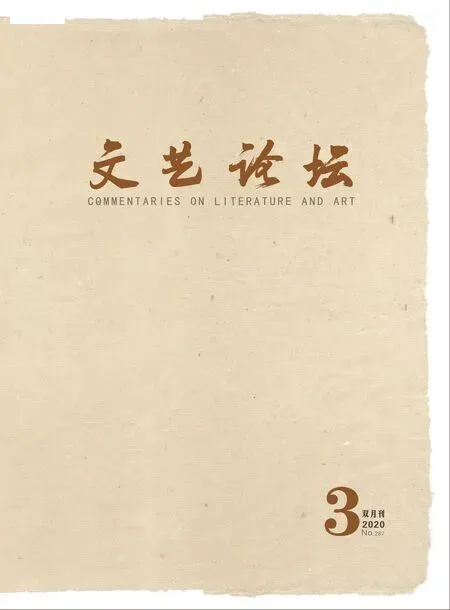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字思維”與鄭敏對母語文學理論的現代性重構
◎ 辛捷璐 楊經建
“20 世紀,也許一個‘革命和戰爭’喧囂的世紀并未改變歷史,而一個悄然‘語言轉向’的世紀卻改變了人。”“語言轉向”不僅改變了人,而且首先改變了作為“人學”的文學。不難發現,1980 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在很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語言的變遷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的面貌。有人稱1980 年代“語言意識的覺醒”昭示著文學主體性的成熟,有人更是將“語言的自覺”譽為1980 年代中國文學關鍵性的實績,“以‘語言意識的覺醒’為契機所啟動的八十年代文學語言實踐,在九十年代被視為一次重大的文學變革的先兆,再一次啟動了對文學語言和漢民族‘母語’的世紀變革的全面反省。”這意味著,“語言的自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學事實,同時也彰顯著母語寫作意識的覺醒,作家李銳稱之為“建立起現代漢語的主體性”:“在這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這些后來者,要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建立起現代漢語的主體性,要用自己充滿獨創性的創作建立起現代漢語的自信心。這是每個漢語寫作者無法推脫的歷史責任。”賈平凹在《懷念狼》的“后記”中提出“新漢語寫作”的概念:“二十世紀末,或許二十一世紀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這種探索應建立于新漢語文學的基礎上,漢語文學有著它的民族性,即獨特于西方的思維與美學。”
誠然,中國作家使用的語言只能是漢語言母語,文學創作也必須重視語言,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但重視語言并不等于“語言的自覺”。因為,重視語言本來就是所有(語種) 文學創作的一般要求,對于中國作家來說,真正的“語言的自覺”不但要深切了解漢語言母語的特點,認識它與其他語種的區別,更需要自覺地在母語文學意識的規引下創作。這就是說,雖然作家們在“語言的自覺”的感召下,探詢了母語寫作的種種可能,但是,倘若沒有理論上的清醒,依然不能視為嚴格意義上的“自覺”。在我看來,理論上的“語言的自覺”所指的是就母語文學的理論話語的現代性重構,也即,“‘漢語主體性’的語言自覺,必然意味著對于作為母語的漢語的親近、敬惜、衛護與責任,以及對漢語/母語寫作的自信與責任,并且以對母語的自覺與否作為評判文學寫作的價值與有效性的重要基準。”
在此意義上,鄭敏發表在《文學評論》 1993年第3 期上的《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一文,可以被當作母語文學理論性重構的肇始。當鄭敏在文章中宣示,“我們正在悄悄地經歷一場語言現代化的轉變”,這場轉變同時也是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中國文學正在經歷著的又一次相當巨大的語言變革時,實際上揭開了1990年代母語文學理論性重構的大幕。雖然,鄭敏的有關見解曾引起爭論,所謂見仁見智,但她的這番舉措對母語文學理論性重構卻是一次充滿對話性精神的切磋和嘗試。
二
索緒爾的“音本位”在德里達的解構批判下得以遏制。德里達在《文字學》 (1967) 一書中,針對索緒爾褒揚語言(言說) 而貶抑文字(書寫) 表示,言說具有不確定性和意義含糊性,書寫也并非只是思想蹩腳的復述。事實上,書寫以銘刻方式來維持符號的持久直覺,它都能使作者在言說中“出場”,且獲得一種時空超越性。德里達解構了索緒爾的“音本位”,致使文字書寫上升到重要地位,從邊緣移到中心。
漢語言母語是一種以象形表意為基本特征的語言體系,它能使人通過象形文字這一符號把握到其中蘊涵的原始意象;其因“形”見“義”或以“形”會“意”體現的是漢民族的文化心理,這使得漢字與漢語具有一致性,并成為中國人文化行為的精神理據。
“對于‘字本位’的漢語來說,漢字就是漢語的本體。在中國文化史上,文字與語言高度統一。”正因為這樣,1990 年代以來以徐通鏘為代表的語言學學者提出了漢語研究的“字本位”說,得到語言學界眾多的呼應。
當“字本位”說發酵并影響、擴展到作為“語言的藝術”的文學領域后,便被轉化、改述為“字思維”論。“字思維”論由畫家石虎提出,最早在詩歌界引起反響和應和。《詩探索》雜志以此為契機進行了長達6 年的深入討論,成為世紀之交詩學界一個顯豁的“學術事件”。“漢字字象的思維意義是絕對的,第一位的。……漢字以小寓大,以字寓道,是宇宙的內在本質之本元形式。每一個漢字的內涵,遠遠不是字典所能容納的。因此漢字不聽命語法。它甚至可自由并置成辭。一個字甚至可大于一篇文章。所以漢字的單字不僅僅構成語言,單字也支配語言,甚至支配思想。”在這場討論中,大部分參與者認同石虎的相關論述,這也說明了“字思維”論與“字本位”說有同質同構之妙。另一方面,不同于“字本位”的語言學研究指歸,“字思維”把“字”(文字) 視為一個美學、文學范疇,它“不僅加深了對漢字文化內涵的認識,而且涉及到對母語文化獨特性的思考,涉及到古老的中國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銜接,這對于中國的現代詩學建設是有深遠意義的。”作家汪曾祺就將“字思維”稱為“漢字思維”:“中國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國有文化的人,與其說是用漢語思維,不如說是用漢字思維。”如果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那么漢語言母語文學便是文字的藝術——漢字創造的藝術。汪曾祺所謂的“漢字思維”,與母語文化的語言本性互為印證、互為指涉,不啻為對母語文學是“文字的藝術”的一種現代性陳述。“漢字既是漢文化存在的基本條件,又是這種文化不停地自我重建的生產方式,因此,中國學術的基本問題是漢字性問題。這樣,我們就可能建設、反思、發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這實際上意味著,“字思維”成為1990 年代前后母語文學理論性重構“文字學轉向”的表征。而母語文學理論性重構的“文字學轉向”的本質,就是在現代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的融通中,重新確認漢字在1990 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文學承擔使命和文化融合前景。
三
在前述的《詩探索》雜志組織的“字思維”討論中,身兼學者和詩人的鄭敏也積極參與,她指出“‘字思維’的提出對我來講更多的是啟發我們去感受隱含在每個字的形象中的文化思維,這種在有形的文字后一些隱約存在的審美活動使得整個文本增加不少感性的、豐富的主體性,……漢字的內涵的智慧、哲思與造形美并不應當在欣賞與評論中與文本割裂,它們如嵌在藝術品上的寶石,雖各自有光輝,卻在組成整體中存在。”從母語文學的理論性重構層面追詢“字思維”,鄭敏采用的是解構—結構(建構) 的致思方式,“石虎先生的短短幾千字的短文觸及20 世紀以來西方現代詩論家從范諾洛薩到龐德、艾略特所日夜思考的現代詩觀,同時又是尼采、索緒爾、海德格爾、拉康、德里達等西方現當代語言哲學家所不斷闡述的當代最新西方語言哲學,即結構一解構語言哲學”。
鄭敏受索緒爾的啟發又不限于索緒爾。索緒爾把語言從主體的控制和對實在的依賴中解放,為西方文學反抗“詞”與“物”對應的“自然”寫作和主體性的“幻覺”,以及強調寫作“不及物”“作者已死”的形式主義詩學,提供了語言學根據,奠定了結構主義文論的思想基礎與方法論基礎。一方面,它強調“人為性”“差異性”“規則”“權力”,對以往的工具論語言觀具有革命性意義;另一方面,它并不能暢通無阻地運用于“話語”(discourse)現象的文學語言,因為它隱含著一種缺乏人文精神的“共時性范式”,在某種意義上把文學當作“語言形式”,類似于把“詩學”等同于“語言學”,催生出強化語言科學意義而不利于人類詩化生存的東西。
鄭敏的漢語新詩研究的前提是語言的“文字性”和漢字的“象形性”。這和她對漢語的基本理解相關:漢語的基礎在文字的“視、形”,拼音文字的基礎為“聽、聲”。她談“漢字”意在突出漢語較之于西方語言的特點,旨在凸顯漢語新詩和中國新文學的母語根基和民族文化身份。她指出,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認為作為“能指”的聲音符號與其“所指”的概念之關系是全然武斷的。
對于五四白話文運動和后來的文學大眾化運動,鄭敏雖然籠統地表示“無望提供解答,只是想把問題展開,引起人們的好奇和興趣。”但當她從“字思維”層面予以嚴格意義上的推究,指出文字的唯一的功能就是“白”——以語法正確且用字通俗來明白如話地傳達信息時,還是以其鮮明的語言立場和詩學理念表露出自己的態度和傾向:由于語言轉型本身的不徹底性和未完成性,五四白話文運動和后來的文學大眾化運動“草率地將語表層的淺白(用字通俗和語法通順)看成改革的目標”。而“要使以簡單句為基礎的白話口語立即肩負起表達20 世紀人們復雜的思維與感情,和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豐富質地的職能”,就成為實際上不可能的事情。
很明顯,她持論的理據是漢語言母語,準確地說是漢字的“審美和詩意價值”,并引借德里達的論述佐證,她還以解構主義觀點來闡揚漢字的優勢和特點。解構語言學運用“歧異”和“蹤跡”學說,力求強化“能指”和“所指”關系之間的滑動性,以此延擴符號的運行、活動范圍,力求把文本從主題的統馭下釋放,不斷開發文本閱讀的審美效果。這種“文本間”的閱讀方式是解構式閱讀區別于傳統閱讀之處。而漢字的文本就具有“文本間”性,它一般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部分組合而成,其象形、會意、指事的是構字規則自然而然地兼容各種組合,而“偏旁”和“部首”又將其自身的蹤跡融入字中,這種多元化結構在一個字內的交織,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的余地和闡釋的空間;所以漢字的表達不是“獨奏”而是多聲部“重奏”,從而獲得不同凡響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旨。易言之,面對西方拼音文字的“貧乏和缺乏活力”以及“失去語言的豐富的層次和隱含的潛意。”主張以“心靈的書寫”,“歧異”的多元性和變化性,“蹤跡”的無形中的有形以及自由來往,給拼音文字重新注入新的生命力。而這些恰恰是“漢字本有的特點”。漢字不但沒有必要去看齊西方的拼音文字,相反,漢字已成為西方當代語言學(解構語言學) 追求的東西。
在鄭敏心目中,對于漢語新詩和母語文學來說,無論是“文言”還是“白話”,“口語”還是“書面語”,“語言的實質不是它的喧囂的表層,而是那深處的無聲。”(《世紀末的回顧》) 以漢字為基礎的漢語言母語和民族心靈、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心靈、心態、思維方式與語言文字互為內外,互相形成,相互激發,相互依存。”倘若無視這樣的互文性關系,無疑是一種“幼稚的空想”。“關鍵的是對漢語文字的現代化改造,是否應當從‘推倒’傳統出發,還是從繼承母語的傳統出發,而加以革新。”以漢字為本體的母語寫作是中國人心靈書寫的方式,漢字以自身的詩性本質和文化蘊涵溝通了母語文學的古今差異。
“母語文學”原本就是一種關于“母語”的文學現象,研究它不可避免地要論及漢語言文字。“字思維”作為母語文學現代性重構的學術話語方式,是對文學是語言藝術的一種現代性反思。“字思維”與母語文學現代性重構的邏輯關聯,并不意味著將后者當作前者的有效性、合法性的實驗基地,而是把母語文學視為一個形式與意義有機統一的整體,通過對文本語言的微言大義來闡發其現代性重構中所蘊藏的價值內涵,進而使人堅信:中國文學的命運必然和漢語——以象形文字為基礎建構起來的語言緊密聯系在一起。“抓住‘漢字性’這個最根本的中國話語方式,中國的文學史、語言學史,思想史等等可能要重寫。”
注釋:
①任洪淵:《漢語紅移——多文體書寫的漢語文化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42 頁。
②鐘海帆:《語言意識的覺醒及其他》,《讀書》1987 年第10 期。
③張頤武:《在邊緣處追索》,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 頁。
④旻樂:《母語與寫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 頁。
⑤李銳:《春色何必看鄰家——從長篇小說的文體變化淺議當代漢語的主體性》,《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2期。
⑥賈平凹:《懷念狼·后記》,《收獲》2000 年第3 期。
⑦何言宏:《語言生命觀和語言本體觀——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語言自覺》,《甘肅社會科學》2003 年第4期。
⑧參見王岳川:《漢字文化與漢語思想——兼論“字思維”理論》,《詩探索》1997 年第2 輯。
⑨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 年版,第89-90 頁。
⑩石虎:《論字思維》,《詩探索》1996 年第2 輯。
?吳思敬:《“字思維”說與現代詩學建設》,《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2 年第2 期。
?汪曾祺:《“揉面”——談語言》,《花溪》1982 年第3 期。
??孟華:《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2 頁、第272-273 頁。
??鄭敏:《余波粼粼:“‘字思維’與中國現代詩學研討會”的追思》,《詩探索》1997 年第1 輯。
?參見趙奎英:《當代文藝學研究趨向與“語言學轉向”的關系》,《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6 期。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文學評論》1993 年第3 期。
?鄭敏:《漢字與解構閱讀》,《文藝爭鳴》1992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