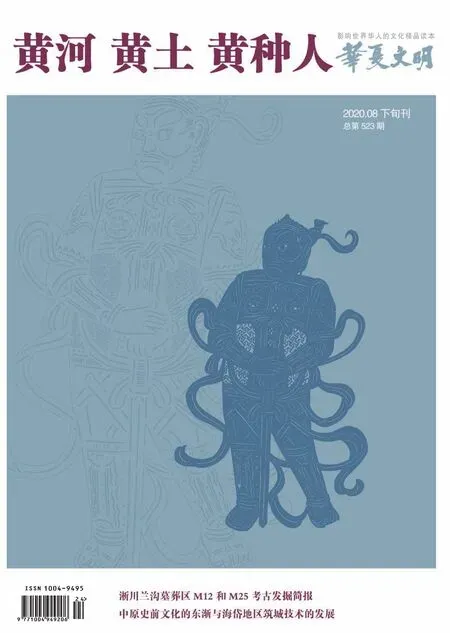牛河梁遺址出土玉貝的考古學研究
范杰
20 世紀80 年代, 遼寧省牛河梁遺址中采集到了3 件玉貝。 由于出土層位缺失,其文化歸屬產生了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兩種爭論性意見。 同時,玉貝仿制的寶貝科海貝只生長于水溫較高的低緯度海域,由此衍生出的遼西與熱帶地區的長距離海陸互動以及玉貝在社會中的作用和意義等相關問題,其認識也相當模糊。基于此,筆者擬以牛河梁遺址出土玉貝為切入點,對其文化歸屬、文化交流路徑、社會功用等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
一、出土玉貝概況
牛河梁遺址是1981 年在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發現的,1983 年10 月開始正式發掘。 其中第二地點的發掘工作從1983 年一直持續到1998 年。 其間,在1985 年夏季,發掘人員在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沖溝內清理出3 枚玉貝。 玉貝呈白色,并有紅褐色土沁,皆經過磨制。 平面為不甚規則的橢圓形,橫截面中間稍厚,兩側稍薄,邊緣圓鈍。 器體正面長端刻一通體凹槽,在凹槽兩端各鉆一孔。 凹槽兩側刻畫數道平行短線,其余部分不見紋飾。 背面較光滑,并磨出一小塊臺面。
N2Z1C:3,正面稍鼓,背面較平。 凹槽稍寬而深,槽內可見刻槽時所留的凸棱。 凹槽口部較窄,底部較寬,邊緣較為圓滑。這一形態應是使用較為圓滑的工具,分別在凹槽處兩次斜向磨制形成的。 槽兩側分別有9 條和12 條短線,略偏斜。 短線在靠近凹槽處逐漸變寬,可知短線是由外向內刻畫而成。 該器物通體長2.1 厘米、寬1.75 厘米、厚0.65 厘米,凹槽寬0.25~0.3 厘米、深0.25 厘米,孔徑0.2 厘 米。 (圖1-1)N2Z1C:4, 形 制 與N2Z1C:3 基本相同。 正面稍鼓,背面稍平,凹槽較寬,槽內可見刻槽痕。 槽兩側分別刻出11 條和13 條平行短線,基本與凹槽垂直。器體長2.3 厘米、寬1.75 厘米、厚0.75 厘米,凹槽寬0.3 厘米、深0.25 厘米,孔徑0.2 厘米。 (圖1-2)N2Z1C:5,體量在三者中較小,正面和背面都較鼓,凹槽較窄,底部呈V 形。凹槽兩側皆刻有13 條短線,線長短不一,刻畫較淺。 雙孔從凹槽外緣鉆起,兩孔間另有一淺凹槽將兩者相連。 背部另見2 組不甚對稱的斜穿透孔,可見其佩戴方式與前兩者應當稍有差異。 器體長2 厘米、寬1.4 厘米、厚0.7 厘米,凹槽寬0.2 厘米、深0.15 厘米,孔徑0.2~0.35 厘米[1]。 (圖1-3)
觀三者形態,應是模仿海生的寶貝科海貝類制作的。 寶貝科海貝種類眾多,全部為海生貝類,一般統稱為寶貝或寶螺。 其外形呈橢圓形,殼口狹長,兩唇有齒狀結構,一般長約2.5 厘米,寬約2 厘米。 在世界上熱帶和亞熱帶等水溫較高海域的潮間帶到較深的海底均有分布。 我國則主要分布于浙江以南的廣大區域,其中臺灣、海南沿岸和南海海域數量較多[2]。由此可見,遼西地區與熱帶海洋地區在很早之前便已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三者在細節上雖略有差異, 但在材質、造型、工藝、體量等方面基本相同,應當為同一時期的遺物。三者中,N2Z1C:3 和N2Z1C:4的形態基本一致, 應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或出自同一墓葬。 同時兩者背部并不像天然寶貝那樣鼓圓,而是均磨出小臺面。 這應是仿制背部經過磨平的寶貝, 學術界稱其為“磨背式”寶貝[3]或磨貝[4]。
需要注意的是,原報告稱玉貝玉色為白色, 但此種白色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白玉之白,而是玉石的白化現象,其玉色也稱為“雞骨白”。 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受到自然或人為造成的高溫、強酸、強堿環境的影響,玉石會改變結構,從而褪色變白[5]。 而在埋藏過程中,受到風化淋濾和滲透膠結作用的影響,也會產生白化現象[6]。除此之外,中堿性環境中鈣鹽也會沉積滲透至玉器表面,進而形成鈣化現象[7]。有學者提出,一些白化現象是祭祀儀式中為達到通神的目的而對玉器進行燒燎的結果[8]。
二、文化歸屬與年代分析
一般認為,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并未發現除紅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遺存,因而確認該遺址是一處性質較為單純的紅山文化遺址, 由此認定這3 件玉貝屬于紅山文化。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系的羅泰教授則提出,玉貝并沒有明確的地層關系,且在牛河梁遺址范圍內包含多種文化遺存,其有可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留下的①這一觀點是2017 年10 月在美國加州舉辦的以“探索早期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為中心議題的學術研討會中提出的。詳見會議摘要——中美考古學者:探尋早期中國文明。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8863。
需要注意的是,對第二地點一號冢性質較為單純的認識并不準確。 在第二地點四號冢Z4A 冢體的積石中發現的三座墓葬應當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 三者皆利用冢體碎石修筑墓壙,其下疊壓或打破冢體頂部的堆石結構,開口于冢上第二層,可見其年代要晚于Z4A 所代表的紅山文化晚期遺存。墓葬中出土一件銅耳飾和一件天河石質的墜珠。 其中銅耳飾兩端皆有明顯斷茬。 其一端稍尖,一端稍扁,形態、大小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常見的一端尖圓、一端被鍛打成扁三角形的耳飾基本一致。 另一件墜珠為不規則柱狀多面體, 這種幾何形墜珠在紅山文化中尚未發現,但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偶有出土。 由這兩件器物可以斷定這三座墓葬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也發現了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房址、灰坑、環壕、寨墻等遺跡,并出土較多陶、玉、石、骨、角等材質的遺物。 第一地點、第十五地點等遺址的山下均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第二地點在20世紀40 年代修建錦承鐵路時被挖走大量積石, 而附近居民也長期在此耕作和取石,這勢必對紅山文化地層之上的其他遺存造成破壞。 而這3 件玉貝是否因此散落于沖溝之內,也值得考慮。

圖1 牛河梁遺址出土玉貝
在無法從出土地層明確其年代的前提下, 我們試對器物形態和制作工藝進行分析。紅山文化未見相關遺物,暫不討論。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寶貝和仿貝,其中內蒙古敖漢大甸子遺址出土了寶貝、蚌制仿貝和鉛制仿貝,共1212 枚。 其中寶貝共659枚,皆磨去背部,以便于穿孔。 (圖2-1)蚌制仿貝共552 枚,皆用蚌殼磨成橢圓形片,于隆起一面刻一凹槽。 (圖2-2)鉛制仿貝1枚,系用范合鑄,形態與磨背寶貝相同[9]。 (圖2-3)遼寧北票豐下遺址出土10 枚寶貝[10],其從背部兩端穿孔, 并在兩側刻槽, 形態甚異。(圖2-4)內蒙古敖漢旗范杖子[11]和庫倫旗胡金稿[12]等遺址也有報道。 很顯然,夏家店下層文化寶貝和仿貝形態與牛河梁玉貝有較大差異。

圖2 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寶貝和仿貝
從制作特點看,玉貝的鉆孔除前后對鉆外, 在N2Z1C:5 背部還發現兩對斜向鉆孔。夏家店下層文化完全不見斜向鉆孔的方式,而在牛河梁、那斯臺、東山嘴、胡頭溝、半拉山等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玉器中,皆可發現一組乃至多組同類鉆孔。 這類孔一般是用實心鉆斜向對鉆和開孔[13],以片狀的動物形玉器較為多見,用以連綴衣物。 其他同時期乃至更早的考古學文化中,這一鉆孔方式并不普遍,因此可以將其視為紅山文化的特征。 可見這3 枚玉貝應屬于紅山文化,同時也表明其并不是其他文化的舶來品,而是在當地制作的。
出現仿貝的地方必然使用或加工過天然海貝,由此可以確認紅山文化中應有寶貝的存在。 在吉林白城雙塔一期遺存中發現了距今1 萬年左右的“磨貝”式海貝。 經鑒定為黃寶螺,屬寶貝科[14]。 白城地處松嫩平原南緣,其位置較遼西地區更加深入內陸,在與熱帶海洋地區進行交流之時,遼西地區則是必經之路。 在距今8000 年前后的興隆洼文化中,白音長汗遺址出土了數件由東海舟蚶制作而成的裝飾品,其產地應當為中國東南沿海。 在紅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中,大南溝遺址出土了1 枚榧螺科海貝墜飾,該海貝主要生長在溫度較高的海域,而這同樣是寶貝科海貝的主要分布區域。 可見遼西與溫暖海域人群有著頻繁互動,紅山文化便由此獲得了寶貝。
同時,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海生貝類,并在紅山文化生產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 在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的紅山文化遺存中,一處窖藏坑H17 內發現了290 余枚毛蚶的貝殼,約三分之一有鉆孔。 這是迄今為止紅山文化遺址出土海貝最多的遺址[15]。 魏家窩鋪遺址發現兩類海生貝類,其中一類為毛蚶,共3 件,分屬兩個個體,頂部有穿孔。 另一類為簾蛤科海貝, 共計8 件, 至少分屬3個個體,部分殼體有加工痕跡[16]。 西水泉遺址發現蚌器28 件,包括飾件和刀兩種,皆有穿孔。 發掘者認為其用料與赤峰紅山遺址所出相同,為海產的紫斑文蛤[17]。 而在紅山文化中,與其生產、生活、祭祀等活動有著緊密關系的動物,如豬、鹿、熊、蛇、蠶、鳥、龜等,皆會以玉雕琢其形象[18],因此,以玉制貝便順理成章了。
三、來源與傳播路徑
遼西地區以及周邊海域并不生長寶貝,因而紅山文化寶貝的來源與路徑便成為需要探討的問題。 有關中國寶貝科海貝的來源與傳播路徑,論著頗豐,歸納起來可分為三種認識。 第一種以考古發現、傳世文獻和品種鑒定為依據,認為寶貝科海貝是從包括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在內的西太平洋,沿海岸線北上或從陸路傳播到內陸地區[19]。 第二種觀點認為, 中國發現的寶貝科海貝來自印度洋,其線路又可以分為兩條。 其一是從印度洋沿岸的印度和中南半島向北傳播到云南地區[20],其二是北方草原地帶連接印度洋和中國內陸地區[21]。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海貝傳播可能存在多條路線[22]。 可見,傳播路線雖有差異,但寶貝的來源地不外乎中國沿海地區和印度洋沿岸。
雖然國內年代最早的寶貝距今已有萬余年,但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再未發現相關遺物。 可見這一時期寶貝的傳播應當具有偶然性,尚未形成大規模使用寶貝的趨勢。直到距今5500—5000 年的紅山文化晚期,才在黃河上游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早中期墓葬[23]以及廣西內陸地區的沖塘遺址[24]中再次出土相關遺物。 其中,前兩者所在北方地區從此開始大量出現寶貝。 這表明中國對寶貝需求的擴大是從距今5500—5000 年開始的。
廣西沖塘遺址距南海并不遙遠,其寶貝科海貝應當來源于南海。 其后,距今4000 年左右的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遺址也出土了1枚寶貝。 可見有學者提出的史前南海沿岸不生產寶貝的說法并不準確。 然而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東南沿海地區雖發現了有豐富的貝丘遺址且沿岸皆有寶貝生長,但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內并不見寶貝的身影。 可見該區域對于寶貝的獲取尚停留在偶發的階段,影響范圍也僅限周邊地區。 我國南海沿岸居民未出現同時期北方地區對于寶貝的偏愛并賦予其特殊含義的現象。 雖然無法排除通過多次交換從而傳播到北方的可能性,但從發展態勢和現有考古材料看,這一假設的可能性并不大。
同時,紅山文化的波及范圍不包括這一區域。 多連玉璧是紅山文化對外影響范圍最大的一類器物, 其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周河、野店、花廳、尉遲寺、小徐莊等遺址,崧澤文化的營盤山、青墩等遺址,凌家灘文化的凌家灘遺址,薛家崗文化的塞墩遺址皆有發現。 紅山文化對相鄰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江淮之間的凌家灘文化有著重要影響。 但到長江北岸,其影響力明顯下降。 從遺址的地理位置看, 其波及范圍最終停留在了長江一線,尚未觸及南海沿岸的寶貝產地。 這或可進一步證實紅山文化寶貝并不來源于南海沿岸史前文化。
相比較而言,紅山文化向西獲得寶貝的可能性更大。 靠近印度洋的南歐、西亞、中亞和南亞以及中國西北的甘青地區出土的寶貝的年代存在明顯的西早東晚的趨勢。 目前已知最早的寶貝, 發現于法國境內的Langerie-Basse 洞穴和Barma-Grande 洞穴[25]以及以色列Skhul[26]等,分布于地中海沿岸及其周邊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遺址。 距今1 萬年左右的納吐夫文化,發現有人頭骨中以寶貝代替眼睛的現象。 寶貝的使用在西亞地區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距今8000—6000 年, 寶貝開始在中亞的哲通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梅爾加赫文化[27]中以及伊朗高原[28]等地區出現。
而在距今5500—5000 年, 寶貝同時出現于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中。 其后在龍山時期,甘青地區出土寶貝或仿貝的遺址愈加密集。 而同時期更偏東的陜西石峁、寨峁等遺址[29],山西下靳、陶寺等遺址[30],內蒙古朱開溝遺址[31]才始見寶貝或仿貝。 甘青地區南部的西藏昌都卡若遺址[32]和四川理縣建山寨遺址[33]也是這一時期首次發現寶貝。 寶貝出現在歐亞大陸各地的時間差異,應當是文化傳播的結果。 而甘青地區的寶貝應當是向西通過河西走廊連接歐亞草原地帶獲得的。
而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位于歐亞草原地帶東部,其與歐亞草原腹地有著頻繁且暢通的交流與互動。 其常見的平底筒形罐不僅普遍存在于東北地區和內蒙古東南部,在內蒙古中部距今6200—5500 年的仰韶文化王墓山坡下類型和距今5500—5000 年的海生不浪文化中也有類似器物。 而更靠西的俄羅斯米努辛斯克盆地、新西伯利亞、托姆斯克、阿爾泰等地區, 也常發現距今4000 年左右的同類器物[34]。 紅山文化中出土大量的體態豐腴的女性陶塑、具有歐羅巴人種特征的石像、 石制容器等遺物則是與更為遙遠的中亞、西亞地區存在文化交流的證明。 而在同一時期的歐亞草原腹地的遺址中也時有寶貝出土,可見紅山文化已經與擁有寶貝的史前居民有接觸。 這提醒我們,紅山文化很有可能并未經過河西走廊,而是直接通過歐亞草原地帶獲得印度洋的寶貝。
四、社會功用和影響
史前寶貝和仿貝大多出自墓葬。 由于多有鉆孔,因而被認為是裝飾品,或是身份和財富的象征。 也有學者提出其具有生殖崇拜的含義。 需要注意的是,玉器在紅山文化中具有祭祀祖先和天神的作用。 因而紅山文化玉貝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單純的裝飾品或者象征物品,而是用于祭祀的禮儀用品。 而在歐亞草原地帶,寶貝同樣具有除裝飾品和身份象征之外的含義。 耶利哥遺址有以石膏涂抹頭骨,并用寶貝代指眼睛的現象,其所在的房址則被認為是一處祭室[35]。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遺址的寶貝皆與海螺一起出土,而海螺在當時是一種重要的禮儀用具[36],寶貝應當有著近似的作用。 而模仿寶貝制作的玉貝,顯然是將這種外來文化符號融入了紅山文化的祭祀體系之中。
這一行為在紅山文化中并不是孤例,晚期盛行的刃邊玉璧和多連玉璧類玉器,其在中國東北地區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出現甚早,可追溯至萬年以前。 黑龍江小南山遺址發現有距今9000 年左右的玉璧,其孔甚小,體量不大,但皆為刃狀邊,器物形態上與紅山文化玉璧存在明顯的演變規律,可見有由北向南傳播的趨勢。 這種早期玉璧也應當有著較為特殊的含義。
同一時期,各式小型的裸體女性造像也開始在祭壇和積石冢等祭祀遺存中被發現。造像以夸張的方式突出了女性的乳房、腹部和臀部,而對頭部與腳部進行了簡化。 而這種特征的女性造像在歐洲和西亞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便已經出現,被認為是豐產巫術的“道具”[37],并在紅山文化的祭祀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紅山文化祭祀性彩陶中常見勾卷狀和幾何形的紋飾,其被認為是受到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影響而產生的。 而這類紋飾并不是單純為了裝飾,有學者提出彩陶紋飾具有“原始巫術禮儀的圖騰含義”[38],而這種勾卷狀的彩陶紋飾則是“神目”[39]。 同樣,凌家灘文化出土的玉人、玉龍、玉鳥、玉璧、連璧、玉箍形器等玉器在紅山文化中也有發現,而這些玉器在兩地均為祭祀用品,其含義是相近的。
這意味著,紅山文化與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不止于物質層面,還包括對不同文化中祭祀元素的吸納和改造,并將其融入自身的祭祀體系中。 這應當與紅山文化神權至上的社會性質有著密切聯系。 蘇秉琦先生將國家形成的過程分為三種模式,即原生型、續生型和次生型[40]。 他將紅山文化向國家邁進的過程歸納為原生型,這一認識在當時來看具有相當的準確性和前瞻性。隨著考古資料的豐富和研究的逐漸深入,我們進一步確認紅山文化傳承并發展了遼西史前文化的部分文化傳統。 同時也應注意到,以寶貝為代表的外來祭祀性因素對紅山文化的影響。 這些因素又集中出現于紅山文化晚期這一關鍵的時間節點,其對當時社會的塑造或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與紅山文化同期乃至更早的考古學文化中皆未發現玉貝。 其后已知年代相對較早的玉貝發現于成都金沙遺址Ⅰ區 “梅苑”東北部地點[41](圖3-1),年代相當于商代晚期。 而中原地區則在西周時期才有玉貝出現。 因而紅山文化玉貝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貝。 從仿貝的角度看,最早的仿貝為蘭州花寨子半山類型墓葬出土的1 件陶貝。 陶貝由白色黏土燒制而成,呈橢圓形,中間磨出半圓形凹槽,周圍刻有鋸齒狀紋飾,形似海貝,但不見穿孔,時間距今4700—4300 年[42]。(圖3-2)其年代晚于紅山文化玉貝。 其后在青海柳灣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墓葬出土多件石貝,石貝一面略鼓,鼓面有一豎線劃槽,槽兩邊有數道短線橫劃紋,刻槽上下端各穿一孔,年代距今4300—4000 年[43]。 (圖3-3)其形態與紅山文化玉貝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大約同一時期,下靳遺址出土的石灰貝刻槽內部也為上下兩個鉆孔,其基本特征與紅山文化玉貝相同。 但形體更加修長,且僅一側有短斜線。 (圖3-4)其中是否存在著仿貝上的文化交流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紅山文化玉貝作為中國境內目前所知最早的仿貝是沒有疑問的。

圖3 出土仿貝
五、結語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不是一處性質單純的遺跡,玉貝也并無明確地層,這為判斷其文化歸屬和年代帶來了一定難度。 但從制作工藝、 文化傳統、 社會背景等方面分析,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3 件玉貝應當屬于紅山文化晚期的遺物, 而非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遺留。 同時,玉貝在當地是模仿寶貝科海貝制作的, 不是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的舶來品。 其不僅是中國境內最早的玉貝,而且是最早的仿貝,對同類器物具有文化發生學意義。
依目前的考古材料,尚無法完全確認玉貝所仿制的寶貝科海貝的來源。 但歐亞草原地帶出土的寶貝科海貝有由西向東傳播的趨勢,似與文化傳播有關。 與此同時,遼西地區與中亞、 西亞之間的文化交流很早便開始了,并在紅山文化時代達到了頂峰。可見兩地在人群與物質上的交換已經相當頻繁。 而紅山文化同中國南海沿岸的史前文化的交流并不顯著, 出土材料也遠不如同時期的北方地區。 可見紅山文化通過歐亞草原通道獲得印度洋的寶貝科海貝的可能性更大。
在漢代“鑿空”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之前,歐亞草原地帶一直是中國史前文化與中亞、西亞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冶煉技術,造車、養馬、種植小麥等技術和物產獲取,以及中原地區的諸多文化因素的向西傳播,也多經這一區域。 而中國北方史前寶貝的西來, 是距今5000 年前后,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諸文化交流互動的又一證明。
此外在紅山文化晚期,海貝同其他外來祭祀因素被吸納到紅山文化的祭祀體系中。這可能是神權在紅山文化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使得其與其他文化交流時更加偏向祭祀方面的互動。 然而這些外來祭祀因素在紅山文化晚期社會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對塑造當時社會形態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并由此對紅山文化向文明社會邁進的 “原生型”模式進行重新審視,則是今后相關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