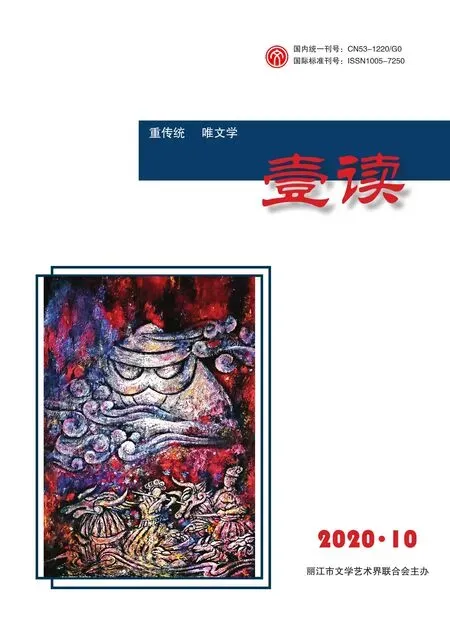遠徙的族譜(外一篇)
大爺爺活著的時候常念叨:“光廷慶長運,必潤有余芳,爾心存明躍,啟翊昭吉堂。”讀著很押韻,和一首詩別無兩樣。然而不是,這是我們云南宣威范氏字輩的排序。
他說人不能忘記字輩,字輩是一個家族的根系,記住字輩就能找到根,到哪都能說清來路。
族譜上說宣威的范姓全是從江蘇遷過來的,一開始是遷到宣威來賓街道,后來慢慢分散到各個鄉鎮。隨著時間推移,宣威格宜鎮的范氏字輩演變成了:“學全,茂文運自守,歷紀芳恒源,振聲耀元漢,福澤堂。”但無論如何演變,我們遇到一起,只要說出各自的字輩,就能知道誰的輩分高,誰的輩分低。
記得剛剛寫文的時候,偶然認識一個寫小說的女作家,沒想到一聊,居然是家門族人,她的丈夫按照字輩我應該叫三爹,她也就成了我三媽。在此后的日子里,她給了我很多幫助。如果沒有族譜,我和她即使是對面而坐,也是不知道有這一層關系的。
幾年前,老家還是一個煤礦大縣的時候,鄉里有很多外省人。因為以江蘇浙江一帶居多,我們就叫他們“江浙人”。當時以為這是鄉里哪個文化人想出的新名詞,后來才知道原來外面一直這么叫。
我家旁邊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個煤礦,一開始老板是我們村的,出過一次事故就賣給了江蘇老板,理所當然就成了江蘇煤礦。村里的路上慢慢也多了一些江蘇來的新面孔,說著我們聽不懂的口音,穿著時髦的衣服。
年齡不大的我只是遠遠看著,不敢上前搭話,偶爾遇見和我說話的外省人,一扭頭就跑了,心里還有點恐懼。
他們的到來并沒有給村里造成不好的影響,反而帶來了不少好處。他們向村里人買雞蛋、肉雞、豬肉,也買一些蔬菜,久而久之,村里人還在村子近處的地里專門開辟一塊地種菜賣給外省人。這些零碎的錢對農村人來說已經不是小數目了,我們上學的書本費,生活費都是向外省人賣東西后一點點積攢起來的。
煤礦上給外來務工的人在村子對面的一片荒地上蓋了宿舍樓,整整齊齊的兩排樓房,算得上鄉里最好的房子了。房子施工的時候村里很多人都去工地上干活了,男人一天八十,女人一天五十。干了四個多月才把房子建好,澆頂那天鞭炮響了一個多小時,煤礦上宰了十幾頭羊。
一開始路上才見得到煤礦工人,房子蓋好不多久就能看見一些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孩子,也有年齡稍大的婦人。他們的到來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天天一吃完飯就坐在一起談論有關外省人的話題,有人甚至說他們以后可能就定居在這了。不過這都是瞎說,后來他們走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可信的推測。
我們村剛好在煤礦和礦工住宿樓之間,煤礦工人上下班都要經過村子。我們年齡小的每天都趴在路邊看他們,煤礦工人們穿著藏青色的棉服,戴著一個有燈頭的安全帽,老遠就能聽見高筒水鞋發出的噠噠聲。現在想來那時的我好奇心還是很重的,對未知的人和事很上心,哪怕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云朵一大塊一大塊地掛在山頂上,風一吹就跑起來,還能變幻出很多種不同的圖形。在七八月的山里,雨水很多,西南季風像是刮不完一樣,大雨小雨一陣接一陣地往下倒。有時下的大雨能沖垮一座小山,大風能刮倒一棵大樹,夜晚睡在床上聽著呼呼大作的風聲特別嚇人。
我大伯一家去了蒙自打工,老家人認為房子沒有人住容易壞,大爺爺就從老房子搬到大伯家的新房子里。新房子蓋在公路邊,一層三間的平房,蓋的時候為了應對雨水天,特地把房檐蓋得往外出。這樣能在房檐下堆東西,也能讓過路人躲雨。
山里的雨水說來就來,真有“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意思,出門還是日頭高照,沒準過一會兒就烏云密布,大雨頃刻而至。煤礦工人又常常不帶雨傘,下班回家遇到大雨就會在大伯家房檐下躲雨。大爺爺看他們在房檐下,二話不說就讓他們進屋,嘴里說“淋濕的身子一遇冷風容易著涼,快進屋吧!”他們遲疑一會兒,客氣地說一聲謝謝就跟著進屋了。
他們會說普通話,大爺爺聽得懂,聊天后得知進屋的人里面有一個也姓范,江蘇人,只是他叫什么名字我當初就沒有記下,接下來只能用“他”來代稱了。
這可把大爺爺高興壞了,他忙著問什么字輩,很遺憾,字輩對不上。不過大爺爺找出族譜,他一頁一頁地翻給那個姓范的江蘇人看。他看了也是大喜,沒想到在千里之外的地方還能找到自己的家門族人,這對身在異鄉的他來說是一種很大的安慰。
聊到后面,大爺爺還問了他家里有幾個人,父母年紀多大這些家常問題,在我看來他們就像兩個很熟的老友一樣,絲毫沒有陌生感。也許這就是族譜的作用,維系了家族的親緣關系,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加方便。
我們宣威的范姓是從南京搬來的,和南京應該能合得上,而他們的字輩是:“學敦效守克訓”。我大爺爺說:“不一樣,畢竟我們都搬過來幾百年了。”是啊,我們都從南京搬來云南幾百年,當年遷來的兩個先輩如今也有一個龐大的族系了。
從那以后他叫我大爺爺大爹,我大爺爺當他是侄子,沒有血緣關系的人靠族譜成了親人。我們這個遠方來的親戚在村里還比較受歡迎,時間一長他和村里人熟絡了,晚上還會去串門。誰家有個什么事也會叫上他來吃一頓飯,他也會給我大爺爺買一些煙酒。這樣良好的關系延續了兩年多,直到國家不讓過度開采礦產資源,煤礦被強制關停。
那是他離開云南回江蘇的前一天,也是他最后一次去大爺爺那里。那天晚上已經摸黑了,他拎著兩瓶酒來找大爺爺,說他要回家了,以后都不會再來。我看得出大爺爺挺難受,好一會兒才說:“也挺好,在外面的人早晚都要回家。”大爺爺從櫥柜里拿出兩個酒杯,他們就那樣干喝白酒,喝了一晚上。他讓大爺爺和他去一趟江蘇,看看他們那里的祖墳,看看曾經我們老祖宗從江蘇遷到云南走過的路。
對于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大爺爺來說,他很想去看一看,又怕麻煩別人,最后還是沒有去。他一直勸大爺爺,還說路費和吃住他都包,就當是去侄子家玩幾天。可大爺爺執意不去,他也就沒有再說。臨出門大爺爺讓他明天早上來吃一頓飯再去坐車,他只說了一句好。
大爺爺那天早早地起來殺了一只雞,他來的時候我在門口坐著。換了一身衣服的他,就像是另一個人,那種蒼老臟亂的感覺一點也沒有了。許是以前長久在井下作業,煤灰遮住了他原本的模樣,現在看上去還挺白凈,真有江南人的一股子秀氣。
飯間大爺爺不停給他夾菜,讓他多吃點,回江蘇就吃不到這的雞肉了。我當時雖然不是很懂,但我也希望時間過得慢一點,讓大爺爺和他多待一會兒,讓這段因族譜而產生的親情走得慢一些。可時間不會因為誰不想就會變慢,一頓飯總歸是會吃完的。
送他上車的時候大爺爺向他招手,他也向大爺爺招手,我看見他哭了,大爺爺也哭了。走后他再也沒有回來過,大爺爺也沒有再提起他,就好像我們村從來沒有來過這樣一個人,過去兩年多關于他的事都是一場夢。
他走了以后,大爺爺便常說要去一趟江蘇,看看祖墳。我們沒有在意,只是近幾年他提的次數越來越多,又提起我們那個遠方的親戚。大爺爺還關心他的生活是不是更好了,去江蘇應該看一下他。可這些大爺爺都沒能實現,他去世的太突然。頭天還織背簍,第二天早上發現沒有起床,去床邊一看,人已經僵硬了。我們都沒有反應過來,他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他死前幾個月嘴里念叨:“生命就像太陽落山,回家的人就是大山的影子。”我想他應該是提前預料到一些事了。大爺爺到死都沒有去一次江蘇看看祖墳,也沒能再見上他一面。
家里的族譜又要重新修訂了,這些年村里很多老人去世了,又新添了很多小孩,舊族譜上面的內容早就該更新了。只是這次修訂,大爺爺將會填成已亡故。生命就如同潮水,在漫長的起起伏伏后,終歸是要平靜下來的。
竹子的故事
淡竹葉氣味辛平,大寒,無毒;主治心煩、尿赤、小便不利。苦竹葉氣味苦冷、無毒;主治口瘡、目痛、失眠、中風。
——《本草綱目》
一
竹子在我的家鄉是最常見不過的植物,隨意生長在溝澗陡坡,既能防止松軟的紅土垮塌,又能帶來不錯的經濟效益。
蘇軾說過:“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瘦,無竹使人俗。”
在云南,我驚訝地發現:“有人家,必有竹。有竹,必有人家。”大多數人家直接把竹子種在房前屋后,少有離得遠的。這樣做,一來是為了點綴村莊,使得村子里看著春意盎然,營造出田野山鄉的別趣。二來是為了方便日后砍伐竹子以供人使用。
竹葉形如柳葉,只是微帶些許毛刺,摸上去有一種辣手的感覺。老家人將那些細毛稱之為“竹毛”,竹毛極細極尖,很容易刺入人的肌膚之中。雖然不會有什么太嚴重的后果,但也會使人感覺渾身癢痛得緊。小時候我和小伙伴一去竹林里玩,大人看見了就會叫我們快點出來,就是沒有看見,我們一回家他們就知道我們去了哪里,一身的小紅點騙不了人。
老家的竹子一年常綠,中等粗細,既不像楚雄一帶的龍竹那般粗大,也不像涼山地區的荊竹那般細小。每年春天一到,紅土里冒出尖尖的筍芽,它們提前把春天到來的訊息泄露給忙春耕的父老。我的爺爺這個時候總是家里最忙的,他扛著使用多年的鋤頭天天往山上跑,那把錚亮的鋤頭就像爺爺一樣對春天充滿了熱烈的愛意。
一鋤,兩鋤,爺爺以慣性的經驗挖起竹根。他給我說:“不能損壞太大,否則移栽活不了;不需太多根莖,否則泥土太多不便運往山澗。”他說完后看了看我,我一句話都沒有說,他又看看挖到一半的竹根,又說了一句:“以前我也是這樣帶你爸爸來挖竹根的。”
他常常提到我爸,在他眼里我爸是他三個兒子中最中意的一個。他給我說我爸曾經是鄉里的第一名,曾經寫字有多么的好,曾經……有時候他說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了,眼里盡是悲傷。曾經的事記起的越多,他就越難過,還不如讓曾經在他的記憶中消失。
1997年的夏末,兩口棺材抬進了村子。漆樹漆的棺材是最地道的,烏黑發亮,還防蟲腐。這兩口棺材里躺著兩個年輕人,一個二十二歲,一個十九歲。一個是我爸爸,一個是我小叔,我爺爺的兩個兒子。
村里的老人給我說當時爺爺一滴眼淚都沒有掉,奶奶哭成了淚人。我知道他心里比誰都苦,可作為一家之主,他不能哭。老家在下棺之前要給亡者洗身子,本來這項工作一般是由同輩年長者完成,可爺爺執意要為兩個兒子洗身子。
棺材葬在我家房子背后不遠的一座小山上,站在房子旁邊就能看到。我小的時候常常看到爺爺一個人坐在花荒樹下往山上看,那時候我也學著爺爺,可是什么都看不到,還問爺爺在看什么。現在我懂了,每次回家都會陪爺爺一起看山,看山上睡著的人。
奶奶說爺爺從那以后變得沉默了,很少見到他笑。他把時間交付給了田地和一叢叢翠綠的竹子。爺爺種竹子不是興起,這源于我的老祖。我老祖是遠近聞名的篾匠,他可以用竹子編織農村人所需的很多生活品,諸如:簸箕、籃子、竹椅、竹席、花籃……老祖的手藝也就順其自然地傳到了爺爺他們三兄弟的手上,也算是一種求生的技藝吧!
荒山,垮山,溝澗,這些地方漸漸多了爺爺的身影,最后融為了一體。他像一頭有使不完力氣的牛,背著包滿泥土的竹根穿行在山里。他用了幾年的時間把能種的旮旯地都滿上了竹子。
烏蒙山多雨水,多大風,多悲傷,經歷兩三年洗禮后竹子長成了竹林。它們隨風搖曳,它們發出沙沙的笑聲,它們填補了爺爺心中的荒涼。
老家有一句話叫:“有媽生,沒媽養。”這句話用在我身上正合適不過。爸爸去世三個月后,我出生了。本該歡喜一場的事卻引來更大的悲傷。我的母親在生下我的第三天就悄悄走了,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這一去就是二十一年。她沒有給我吃過一口奶,沒有抱過我一下。似乎事情并沒有那么容易就結束,我緊接著就發了高燒。老家的醫療水平有限,爺爺奶奶背著我連夜往市里跑。老家離市里有三十多里,沒有找到車,爺爺奶奶換著把我背到了市醫院。
市醫院的醫生說:“孩子還太小,不能用太多藥,你回家用竹葉煮水給他喝。”竹葉水可以治療發熱,回到家里爺爺把竹葉水和奶粉混在一起給我吃。奶粉袋子現在已經被蟲蛀蝕出一個個小洞,但竹林越來越龐大了。
我的記憶中總是喝竹葉水,爺爺總是在種竹子。
一晃,我已經二十一歲,爺爺也年近古稀。他曾因腰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不能行走,去了好多醫院治了都沒有效果,最后在一個小醫院扎銀針扎好了。他說:“中醫很好,你小時候發熱就是中藥治好的。”是啊,中醫很好,它已經在我們國家存在了幾千年。
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我遵循他的意愿報了中醫藥大學,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笑了,他的笑讓我眼里泛起了苦澀。
竹葉:性甘、淡、寒;歸心、肺、胃經;功效清熱除煩,生津,利尿。
竹子治好過我的病,也讓我的爺爺找到了生活的趣意。甘味能和能緩,能讓人忘記曾經的疼痛。
二
操一技而養家,這或許是很多人都向往的生活。
我的家鄉,營上村。幾乎每家都有竹林,幾乎每家的男人都能編織竹器。不同的是,有人技藝高超,有人手藝低劣。在我記憶里,爺爺輩的老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編織竹筐,他們手下生風一般,快得看不清竹絲從手下飄過的影子。
鄉上有一條街,街的盡頭就是專門給篾匠們開辟了售賣竹器的場地。地皮不大,也就一百多米,但每到街子天就能看見上百個篾匠在那里賣竹器。其中就有我的爺爺,他一般只織籃子,他說:“籃子用處多,農村人,需要的就是籃子。”
我知道,他是不想讓老祖傳給他的技藝變得生疏,就死守著織籃子。
吃完早飯,天還沒亮明,林子里已經有一些不知名的鳥兒在鳴叫,它們是早起的鳥兒,我們是早起的人,為的都是能有飯吃。
爺爺背著七個大籃子,我背著兩個小籃子,祖孫倆就趁著天邊的一點光亮趕路。這條路是鄉里通往城里的唯一一條路,那時候還是土路,只要有小東方車一過,空中就會揚起一層一層的灰,一張嘴就跑進嘴里去了。沿著大路走上四十分鐘,然后拐進一個小村子,岔到河邊,就能沿著河堤走了。
河堤是很多年以前修建的,有些地方已經磨損得厲害,但有一點好處,比走大路近。小河里的水很清,看得見里面搖搖晃晃的水草,河風吹到臉上,涼酥酥的。爺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趕,真希望能這樣一直走下去。
到了街子上,各自找一個好位置,放下背上的籃子。接下來就是等,你不用喊,有人要買會主動過來詢問價格。一番討價還價之后,價格合適就買賣,價格不合適就擺手離開。
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賣五六個,運氣不好,一個也賣不出去。不論賣得出去,還是賣不出去,傍晚回家之前,爺爺都會帶我去路邊吃一碗米線,大碗的,我常常喝得連湯都不剩下,末了還會舔一舔碗沿。
就是這樣的日子,在我高中以前一直重復,直到我進城讀書。爺爺就是憑借織籃子這一技藝把我撫養成大學生的。這也是他最自豪的事,從他和別人交談的語氣中就能聽出來。
鄉里的土路變成了硬化路,人的心也變得躁動起來了。一到開年,村里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老人小孩。地里的莊稼沒人管,漸漸地也就荒廢了。看著雜草叢生的土地,爺爺長長嘆了一口氣。
出門打工的人越來越多,誰也拉不住。主要是沒有人拉,為了生活,為了遠離閉塞的山村,大家都竭盡全力地往外跑。
村里的竹子沒有人砍,籃子織出來沒有人買,竹林一天比一天茂密,竹藝人的手藝卻日漸生疏了。
這可如何是好啊!難道鄉里的竹藝就要失傳了嗎?不,鄉里的老篾匠們把目光轉移到了更年輕的孫子輩。他們教授小孩子砍竹子,織籃子,倒是真教會了一些人。就連我這個讀了大學的人都跟在后面學習。
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老家下了我自出生以來見過的最大的一場雪。山上的草木像是被人潑上膩子水,僵直的軀干一動不動。就是下雪最大那幾天,爺爺有一個籃子快要織好了,可還缺一個背手的竹絲。奶奶說放在那,等天放晴了再去砍,他就是執意要去。等村里人發現他的時候已經躺在溝里了,抬到醫院一檢查,肋骨斷了三根。
從那以后,爺爺就不再織籃子了,想織我們也不讓織。他更沉默了,不說什么話,一天就是坐在屋檐下,嘴里叼著旱煙袋。
其實我知道,他閑不住,就想去織幾個籃子。不為錢,就為不讓自己的手和竹子產生隔閡。
放假回家,和奶奶商量以后,決定讓爺爺重新織籃子,不再約束他。他那天高興得像個考了一百分的孩子,嘴都合不攏,看著他高興,我也放心了。這或許就是一個老匠人對自己手藝的執著吧,不分手藝高雅,不分職業低賤,有的只是熱愛和付出。
三
小姑遠嫁玉溪,幾年不回一次家,爺爺想她也只能一年去一次。
太遠了,坐完班車換火車,接著又坐班車。早上七點多出發,深夜才能到,遙遠的路途和高額的車費把爺爺和小姑分隔得不留余地。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爺爺為了有個伴,把我也帶去了玉溪。那是我第一次進城,第一次坐這么久的班車,班車搖搖晃晃,我也搖搖晃晃。上車的時候我就想,我一定要緊緊地盯著車窗外面,看清所過的高樓大廈,然后回來告訴奶奶。可我不爭氣,一上車就暈的不行,還吐了幾次。接著就靠在爺爺的大腿上睡著了,醒來已經到了曲靖市里。
班車在半路停車加油,有人下車上廁所,有人下車買吃的。停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賣炸豆腐的小攤,車里的人好幾個都去買了,我就是那個時候醒來的。爺爺問:“餓嗎?”我不敢讓爺爺亂花錢,我知道他沒有錢。口水不斷的往肚子里吞,就像是口水也有炸豆腐的香味,爺爺看了我一眼就下車去了。我眼看著他走到炸豆腐攤,買了兩串,一串有方方正正的四塊豆腐。爺爺回來,豆腐全給我了,他一塊也沒吃。他說:“我不餓。”但爺爺分明很喜歡吃豆腐,每年過年都要讓奶奶磨了黃豆做一些。
坐車的人坐了一天,車子也跑了一天。車屁股里冒出黑黑的濃煙,一出排氣管就四散而去了,好像它們被束縛了很久,終于回歸到了曠野。
班車到昆明的時候,我從車窗里看見了一棟大樓,上面的字我認識——明珠大廈。我當時驚嘆于這樓的高,怕是昆明最高的樓了。在那棟樓的旁邊有一個巷道,巷子里有人賣籃子。賣主是一個年邁的老者,似乎比我爺爺還老,現在想來,肯定比我爺爺老。他守著跟前的幾個籃子,像是守著自己孩子,還不時抬頭看一眼走過去的人。就在那樣的黃昏里,他變成了金黃色,所以我至今還能記得他。
爺爺也看到了,他對我說:“那里那個老人也是織籃子的,不過這里怎么賣得出去呢?”說完看了我一眼,我沒有給他回答,他又自言自語地重復了一遍。
我還不懂什么是“紅燈停,綠燈行”,只記得車子在城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什么時候出城都沒有注意到。
在玉溪汽車站,夜晚很冷,滇高原的晚上總是這樣,喜歡無緣無故地刮一些不知名的風。風在耳邊低吟,伴著蟲子的淺唱,小姑就走到了跟前。她接過爺爺手里的包,看到我背上的小籃子,高興地說:“小籃子,這么好的小籃子也只有家那邊才會有。”爺爺滿意地笑了,說就是的。
小姑生了一個表弟,她給婆家傳了宗接了代。自然在家里的地位也一下子高了起來,我們都原以為她的好日子來了,不成想后來還是離婚了。離婚的官司打了半年多,婆家不想讓她帶走一分錢,想用持久戰的辦法拖垮她。最終婚還是離了,表弟判給了小姑,只是孩子一直身體不好,治病欠下了一大筆錢。
在小姑家的時候,每天早上都是我和她去買菜,買菜背的就是爺爺織的小籃子。玉溪人沒有見過這種籃子,他們用一種奇怪的眼神考量著我,準確地說,是考量我背上的籃子。
有人開口問:“這個是什么東西?”
我說:“籃子。”
那人聽得懂我說的話,但不知道何為籃子,說了一句:“這東西不好用啊,干嘛不用手提袋買菜?”我一時間找不出回他的話,走了。
竹子織的籃子、簸箕、背簍,正漸漸地從我們視野里消失,可能再過幾年就再也見不到了。
竹織品的制作換不來大錢,年輕人劃不來學這門手藝,人家還不如去工廠上班,一個月多則五六千,少也有三四千。在玉溪待了十天,每個人見到我背上的籃子都會問,但都給了它否定態度。
回到家,爺爺還是會去竹林里砍竹子織籃子,只是賣出去的越來越少。有一天傍晚,小姑帶著四歲的表弟回到了老家。爺爺在房子背后的空地織籃子,奶奶在下面的圈里喂豬,是我第一個看見她的。我急忙把這個消息告訴爺爺奶奶,他們放下手里的活回了屋里。
小姑說:“我要離婚。”爺爺奶奶驚呆了,他們怎么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小姑細說之后我們才了解情況,原來小姑父一喝酒就發酒瘋,發酒瘋就會打小姑,剛嫁過去的時候就會打,只是小姑一直沒有給家里說。最近一兩年喝酒發酒瘋的頻率增加,打起人來手下也沒有輕重,小姑不敢再待下去了。
小姑離婚后沒幾天,爺爺說:“我年紀大了,不織籃子了,操不動這個心了。”爺爺不織籃子以后,村里的老人們也陸陸續續不織了,年輕人又沒有習得這一技藝。曾經在鄉里引以為豪的技藝慢慢遠去,快工業化代替慢勞動的手工業成了必然趨勢,很多東西注定只能是歷史記憶。

文明麗江 有你有我

攝影/吳雯

博瓦·公高
博瓦·公高(又名:和正明),納西族摩梭人。1992年畢業于云南藝術學院。云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云南油畫學會理事。作品曾在國內外及省市參展,并被收藏。
創作簡歷:
1992年7月,畢業創作作品《麗江古鎮》,云南藝術學院收藏。
2001年7月麗江,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80 周年畫展。
2005年2月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美術作品展。
2008年8月昆明,參加人類最后的母系王國——中國百名著名畫家瀘沽湖摩梭文化采風創作展。
2012年4月昆明,參加云南油畫學會第二屆美術作品展。
2014年12月昆明,參加油畫新表現工作室“反璞求真”瀘沽湖寫生展。
2015年11月昆明,參加“流光·對照——中國十三位藝術家赴泰國寫生作品展”。
2015年12月法國,參加2015年法國對比藝術沙龍展中國藝術展。
2016年1月新加坡,參加“流光·對照”——藝術改變生活·中國十三位藝術家赴泰北寫生作品展。
2016年6月昆明,參加2016中國·南亞東南亞國際美術展。
2018年5月,參加意大利西西里島巴勒莫市國際藝術交流節美術作品展。
2019年11月麗江,參加第六次“返樸歸真”——瀘沽湖藝術創作與展覽。
2019年11月昆明,參加第六次“返樸歸真”——瀘沽湖藝術創作與展覽。

格姆女神山

永恒的祈禱

有佛塔的摩梭人家

盼

李錫路,白族,1979年生于麗江九河。從事木雕行業20年,2015年在古城創辦“木荷堂”。木雕創作以禪意為主,別具意韻。2017年受聘為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師。2018年受邀為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工藝美術品設計專業指導委員會委員。2019年榮獲麗江市“八個一百”人才工程“百名工匠”榮譽稱號。
李錫路木雕作品

魚·水

飄

大圣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