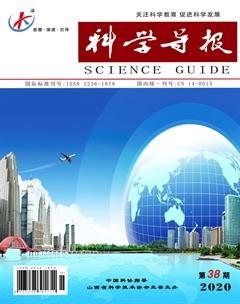“美政”理想 自由精神
摘 要:莊子是把他所認為的“至德之世”當作自己的理想社會而加以追求的。他還特別強調作為個體“人”的品質精神,以及葆有美好品德修養的重要性,并把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當成自己具有自由精神的“底線”。而屈原則把實現“美政”的目標,看作自己的理想追求,且始終不渝。莊子與屈原雖然都生活在“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時代,但他們都成為自己理想追求的忠誠實踐者。
關鍵詞:至德之世;美政理想;自由精神
一、莊子的理想社會
莊子是把他所認為的“至德之世”,當作自己的理想社會而加以追求的;而莊子所謂的“至德之世”,實際上就是“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1]96。莊子對于“至德之世”的集中表述,見于《胠篋》《馬蹄》《天地》等諸篇文字: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胠篋》[2]357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馬蹄》[2]334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為)[無]跡,事而無傳。
——《天地》[2]445
如此的美好社會與純真的情感,顯得是那樣平靜而安然:天空閃爍著自由而燦爛的光輝,大地則充滿了溫馨的陽光雨露;大家和睦相處,人人幸福愉快。這里沒有戰爭的刀光劍影,沒有災難的肆虐橫生,沒有無休止的剝削壓榨,沒有彼此間的爾虞我詐。尤其是莊子對“至德之世”的描繪展示,非常平實素樸,自然直觀,事例多于論證,敘述多于闡釋,并且還極富想象的色彩。這或許就是“中國哲學家慣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3]10的慣常手法。
正是由于這種“至德之世”包含著莊子過多的主觀成分以及想象因素,所體現的核心精神也以“原始共產主義”作為明顯的特征,因此頗遭后人詬病。如“莊子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認為甚么都不可靠,……這種虛無主義思想一則反映了沒落階級對現實的不滿,因此對任何事物都采取否定態度,二則反映了沒落階級找不到出路,對任何事物都喪失了信心。”[4]363又如“《馬蹄》篇中說明了‘圣人‘禮樂‘仁義是危害人性的。這看法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禮樂制度的最后破產,因此由否定‘禮樂仁義的治世作用,進而否定禮樂制度本身;另方面是由于舊制度已崩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當一切補救都只能引起混亂時,便索性提倡‘無為。顯然,作者是以‘虛無觀念反對禮樂,他所理想的是無知無欲萬物靜止的世界”[5] 443等等。其實,如果拋開理想主義的思想創造而更多地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特別是人們所承受的巨大沖擊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空前災難時,或許就容易理解莊子為什么要把昔日的“至德之世”,當作現實的“理想世界”而加以追求的內在緣由。
二、莊子所處的時代特點
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6]575
這是顧炎武說到中國社會由“春秋”而至“戰國”的諸多時代特點。
“那是一個天崩地坼、‘美好的舊社會徹底瓦解,殘酷的新制度已經來臨的時代,就是說,保存著氏族傳統的經濟政治體制的早期奴隸社會已經崩潰,物質文明在迅速發展,歷史在大踏步前進,生產、消費在大規模地擴大,財富、享受、欲望在不斷積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剝削、掠奪、壓迫日益劇烈。‘無恥者富,多信者顯,貪婪無恥,狡黠自私,陰險毒辣……,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罪惡和苦難怵目驚心,從未曾有。人在日益被‘物所統治,被自己所造成的財富、權勢、野心、貪欲所統治,它們已經成為巨大的異己力量,主宰、支配、控制著人們的身心”。[7]1776]
這是李澤厚對于整個戰國時代特點所做的概括分析。
莊子的一生就所處在這樣的一個年代里①。他曾經對于自己所處的時代,發出憤怒地詛咒和尖銳地批判: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
——《在宥》[2]377
莊子又說: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無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人間世》[2]181
這是一個不能對人的生存提供絲毫保證的時代,是一個沒有任何希望的時代。尤其是那些殘暴血腥的諸多國君,他們是無可救藥的統治者,更是喪心病狂的災難制造者: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圣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人間世》[2]139
因此,強烈的批判精神,徹底否定現實的勇氣和決心,集中表現出莊子“辨激悲抑之人”的特點。從某種程度上看,莊子或許就是以肯定遠古的決絕,憤怒地批判現實,并且點燃自己“理想世界”火炬的。聯系費希特評論盧梭的一段話,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莊子是有啟發的,因為莊子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他那個時代里的盧梭。費希特說:
“他(盧梭)”以這種卓越的教養賦予他的一切優勢進行工作,以便盡可能使全人類相信他的主張的準確性,并勸說全人類回到他所贊頌的自然狀態中去。在他看來,走回頭路就是進步;在他看來,這個已經離棄的自然狀態就是現在已經被敗壞的和畸形發展的人類最后應當奔赴的最終目標。因此,他恰恰做著我們做著的事情;他進行工作,是為了按自己的方式推動人類前進,促使人類奔向自己最后的、最高的目標。”[8]32
三、莊子所強調的自由精神
莊子在強調“至德之世”具有無限的身心自由時,特別強調了作為個體“人”的品質精神,也就是莊子在別處說過的,人不能“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齊物論》)。人應當努力地擺脫世俗的煩惱與羈絆,無拘無束,自在逍遙。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精神追求特性的人,不僅要始終葆有美好的品德修養,還要把不與殘暴的統治者合作,當成保持自己自由精神的“底線”。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于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 ??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之知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秋水》[2]605
“吾將曳尾于塗中”的堅定,表明莊子的高潔。因為在他看來,“死為留骨而貴”是徹頭徹尾的虛榮,遠不若“生而曳尾于塗中”的真實自在;而所謂的“愿以境內累矣”則是“誤入歧途”的荒唐,把真實的“自我”喪失掉了。而“惠子相梁”則突出表現了莊子的境界精神,他不僅把世俗所推崇的功名富貴,視若糞土,更把“士人”飛黃騰達的最終結果——獲取“相位”,看作是極其骯臟、齷齪的“腐鼠”,不屑一顧。“鵷鶵”的這種價值取向,當然是莊子自由精神、獨立人格的切實體現。其冷靜清醒、睿智理性的境界精神,則堪稱“士”的楷模。
四、屈原的政治理想
與莊子相比,雖然屈原所處的時代與之相同①,但其“理想世界”則有所不同。屈原是把實現“美政”的目標,當作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加以追求的。“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離騷》),鮮明地表現出他的志向所在。顯然,王室的淵源,高貴的出身,特別是曾經所擔任“左徒”的要職,以及“王甚任之”,“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的從政經歷,使屈原無論如何也不能像莊子那樣袖手旁觀。
于是屈原滿懷希望,投身于為理想而奮斗的激情燃燒之中。他在《離騷》中深情地寫道: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陂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離騷》[9]6
為了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美好的生命: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離騷》[9]15
屈原還特別強調,一個圣明的君主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與足夠的威望,必須時時刻刻考慮到人民的利益得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地享有國家: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
——《離騷》[9]22
與此同時,圣明的君王還要能夠選擇賢能的臣子,要以他們的才干為重,而不關乎他們的出身與經歷如何。所以,屈原在歌頌夏禹商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的同時,又特別舉出傅說、呂望、百里奚等身處低位而終遇明君的事例,強調只有明君賢臣共同的努力,才能真正地有所作為,從而創造出國家的“美政”。
五、屈原所崇尚的品質精神
屈原還在自己莊嚴的奮斗當中,把自身崇高品質的葆有,以及嚴格的自身道德修養,看得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離騷》[9]3
為了自己的“好修以為常”,屈原甘愿付出任何的代價,并且無怨無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離騷》[9]17
最終,屈原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獻于自己的理想之前的: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離騷》[9]43
雖然莊子與屈原都生活在“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戰國時代,但他們始終沒有受這一時代惡劣風氣的影響,而是懷抱著自己的理想追求與道德操守,堅定不移,始終如一,最終到達了“千古一人”(宣穎 贊莊子)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 贊屈原)的崇高境界。盡管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世界”與追求方式有所不同,但相同的道德操守與審美價值取向,則使他們成為實現自己理想的忠誠實踐者。
參考文獻
[1] 范文瀾.中國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4]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 楊公驥.中國文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6] 顧炎武.日知錄(楊若萍 注)[M].武漢:崇文書局,2017.
[7]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與人的使命(梁志學 沈真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9] 屈原.楚辭譯注(李山 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作者簡介:梁克隆,男,中華女子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中華女子學院校級課題階段成果,項目編號:KY2019-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