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村子看中國
——讀《云南三村》

1990年版《云南三村》封面,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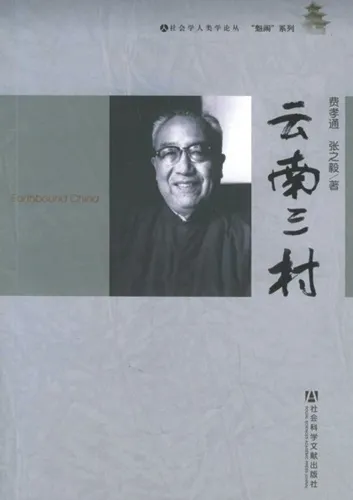
2006年版《云南三村》封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月24日是費孝通先生逝世15周年,推介他的《云南三村》,一面自然是為了紀念逝者,另一面則為更了解我們當下正在發生的改變。這個改變,最緊要的一件是今年正在做最后沖刺的脫貧攻堅。農村的貧困,是中國沉重的歷史問題,這個問題并非這些年才被發現。一生探尋“志在富民”學術的費孝通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聚焦在這個問題,《云南三村》正凝聚了他對這個問題富有啟迪性的思考。
知識是“糧食”
《云南三村》是三篇論文合集,包括《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和商業》。第一次結集出版是在美國,是英文版。自1945年后,在英語國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對這本費孝通、張之毅合著的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縛下的中國》),并不陌生。
這三篇文章雖然各自獨立,但卻有一個共同的宗旨。這個宗旨,往小處說,是費孝通個人的研究取向,往大處說,則關乎抗戰建國背景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費孝通開始著手《云南三村》中第一篇《祿村農田》的田野調查。這個時間距離他抵達昆明只有短短2個星期。此前,28歲的費孝通從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畢業歸國,抵達昆明后被云南大學社會學系聘為助理教授。幾乎才安頓下來,他就立即著手云南農村的調查。
“為什么這樣迫不及待?”
費孝通自問自答說:
“我當時覺得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后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在抗日的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云南三村·序》)
學者有很多類型,費孝通屬于學以致用一派。
1937年,還在倫敦讀博的他,就明確表達過他的不同看法。在給《益世報》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過寄生生活的學者們的辯護詞是‘為研究而研究’;我不贊同‘尊重學問’,我只知道‘真正的學問’是有用的知識。學問可能是裝飾品(有功能),也可能是糧食(也有功能),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愿選擇糧食。”
費孝通一方面對學術的意義和價值非常有信心——相信學術會成為“糧食”,“給掌握社會變遷的人提供實際方法”;另一方面又勇于承擔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他把自己比作戰場上的士兵,紀律要求士兵不能臨陣脫逃,“紀律”同樣要求他堅持生產有用的知識。
解剖“麻雀”
費孝通對知識有用的信念,除了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較為普遍的責任擔當,還源自他對生產知識的那套新方法的信心。
這種方法,就是以村子為單位,進行田野調查,并比較不同的村子,以求得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而在獲得基本事實之后,進一步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這個方法被費孝通比擬為解剖麻雀。他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江村經濟》一書中的“江村”。江村,是化名,真實身份是江蘇吳縣的開弦弓村,費孝通1936年在這里調查了幾個月。費孝通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開弦弓村。這個書的副標題是“中國農民的生活”。費孝通對開弦弓是否足以代表中國,并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一入職云大,他就立即著手“祿村”的調查,希望從云南“內地農村”這種不同于開弦弓的類型中找到中國農村社會的共性。“祿村”“易村”和“玉村”,都是他和助手張之毅精心選出來的“麻雀”。
從方法上講,費孝通從村子入手展開社會研究,并非沒有爭議。讓一個幾十戶人的村子,代表偌大的中國農村社會,有學者就不同意。比如,費孝通在清華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導師——俄國人類學家史國祿,就是批評者之一。他認為研究中國,不能漫無目的地研究一個個村莊,而應該研究“人種群體”。
但費孝通有他的堅持。他認為中國農村社會,雖然看似遼闊,其實村子之間具有很多共性,如果挑出一個村子進行仔細的解剖,從中總結出一些理論,然后再研究其他類型的村子,以作進一步的比較,那最終就會不斷地豐富從具體研究中得來的這些理論。而這樣的理論,更有可能指導農村的社會變革。
云南“三村”的狀況
1936年在開弦弓做調查時,費孝通發現這個過去蠶絲業發達的江南小村,正經歷著衰敗。衰敗似乎是一系列連鎖反應。蠶絲業原本是農村重要的手工業,但隨著現代工商業的入侵,機器的替代性影響,手工業面臨衰退。農民的貧困化,高利貸盤剝,使很多農民把土地賣給城里人。于是造成土地權的外流,出現地主不生活在農村,而生活在城鎮的現象。
從開弦弓的個案,費孝通還無法驗證中國農村是否普遍經歷著這種變遷。為此,他組織了對云南三個村子土地制度的調查。
祿村是最早被用來解剖的內地“麻雀”,其調查范圍和報告的撰寫,為另外兩村樹立了典范。
1938年和1939年,費孝通兩次到祿村調查,他的田野點是今天祿豐縣金山鎮大北廠村。這個村子在祿豐縣城邊,屬于壩區,交通比較便捷,一條連接附近鹽礦和縣城的鹽道從村子穿過。
祿村是傳統農業的典型,全村人口122戶,人均土地5.7畝,而易村則是手工業和農業并重,玉村則體現了受工商業影響下的云南農村的新變局。這三個村子,與江村都有所不同,但也都面臨相似的歷史局勢。
整體看,農村不僅貧困,而且貧富不均。貧窮根源在哪里?從土地制度看,土地即使平均分配,祿村這樣的村子,也無法過上富裕生活,因為農業產出有限。《云南三村》并沒有給出出路,但卻敏銳地提示了問題所在。
費孝通總結說,農村的農業生產,總量上不足以消化所有勞動力,而農閑時節勞動力閑置更多。所以,農業中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就是農村解決貧困的關鍵。
為此,他研究了手工業發達的易村。易村人口57戶,土地212畝,人均只有9分地。土地無法滿足生計,所以他們發展家庭副業和手工業。易村地處江邊,竹林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
圍繞這一資源,他們發展了精湛的竹編技術和造紙手工業。費孝通估計,易村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家靠竹編貼補生活(全村有9人專織篾器),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家則靠造土紙生活變得較為富裕。易村的造紙,大概是民國初年四川人傳入的技術。這個行業不僅有技術積累,也有資本積累。據估計,當時建造一個紙坊,設備要一千多元,維持一個作坊全年開工需要流動資金五千多元。易村有9個紙坊,分屬20家坊主,其經濟規模可見一斑。——織篾器的收入與之形成對照,平均每人一年通過織篾器大約可收入72元(每天人均6角)。易村造紙的富戶,1939年調查時,已經有人把剩余的資本用來置地。他們到外村買地收租。
玉村的背景更復雜一些,但張之毅調查時,農業勞動力同樣是核心議題。玉村的調查,時間是1940年-1941年,這里地處玉溪城郊,靠近馬幫大站,交通便利。玉村的農業資源在城鎮背景下,有很大優勢。除種植水稻,村民有的還發展蔬菜種植,專門為市鎮供應蔬菜。紡織也是重要的家庭副業。婦女們自備織機,在家織布。原材料棉紗是從玉溪布商那里賒來,她們把織好的布再賣給布商,中間與原料的差價,就是她們的微薄的工資。
費孝通認為,農工相輔這一點上,玉村和江村類似。另外,馬幫運輸中致富的人家,大多發財后就從玉村搬到市鎮去住,把家里的土地租給本村人經營,成為離地地主。這點似乎也和江村1930年代的情況相似。
三村的變遷
《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書名是Earthbound China。這個由費孝通翻譯的書名,很有深意。“被土地束縛的中國”,一面他用云南農村指代中國,說明經由江村研究一路走來,他已經確信在云南看到的情況,反映了普遍的中國;另一方面也提示了農村的某種癥結,土地提供生存資源,但土地也是一種“束縛”。把剩余勞動力從“束縛”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其他產業上,是解決貧困問題的一個方向。
1990年,費孝通對云南三村有過一次回訪。一方面印證了三個村子在費孝通、張之毅調查后,繼續發生類似江村一樣的變遷;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從農業生產中釋放出來,農村社會變遷加劇,而歷史性的貧困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
以祿村為例,1942年后,祿村由于抗戰和內戰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苛捐雜稅、政治腐敗等等問題,農民日益貧困,貧困迫使部分農民把土地賣給城鎮的富戶,就像1936年費孝通在江村看到的一樣。1950年,全村的耕地,已有20%屬于“外籍地主”,這個數據反映了祿村一定程度上成了另一個“江村”。而與此同時,農業也進一步萎縮。在這之后的近10年間,祿村人口增加44.5%,耕地面積增加18%,但糧食產量卻下降了30%。
1980年代后,實行土地包產到戶的祿村又呈現出另一種面貌。一面是糧食產量穩步增長,另一面則是隨著農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較大的調整。
1983年,全村一共477個勞動力,當時耕地只需要270個勞動力就足夠經營,剩余200多個勞動力,而其中130人參加了5個自愿組成的基建隊,到祿豐縣城從事基建工作。此外,除了原有的馬匹運輸、修理打鐵、編織等之外,豆腐、米線、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飯站、小百貨店、冷飲店等服務業也在村子繁榮起來。總計51人參加了16種行業。
產業結構的比例,農業和工副業:1978年是7:3,1985年是5.5:4.5,1989年是4:6。祿村這個農業村,因為靠近城鎮,在改革開放后,發生了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遷。
1990年重訪祿村時,費孝通還發現,這里開始出現了鄉鎮企業。一個叫王興國的30多歲青年,最早是賣糧大戶,隨后組建基建隊,再后來回村開冰棒廠、冷飲店、旅館,最后開辦了塑料廠。費孝通觀察這種塑料廠在蘇北農村也有,時間上只晚了五六年。
費孝通總結說,“單靠農業祿村富不起來。”“人多地少的農村該怎樣利用農業里的剩余勞動力來從事生產,一直是嚴重的問題。” (費孝通:《重訪云南三村》)
易村、玉村也都經歷各自軌跡上的變化,但又和祿村一樣有著某種共同的趨勢。
易村原屬易門縣,后劃歸祿豐縣。費孝通他們做調查的村子,是今天的恐龍山鎮李珍莊村。這個交通閉塞的村子,經歷了“三起三落”。第一次衰落是1942年的霍亂,導致人口減少,勞動力不足。易村的竹編和造紙,1980年又遭遇原料方面的重創。當時土地承包到戶,但竹林沒有承包。所以,怕吃虧的群眾,蜂擁而上砍竹子,以致“易村原來在綠汁江兩岸秘密的竹林所剩無幾。……土紙作坊從此倒閉,直到現在(1990)沒有恢復”(費孝通:《重訪云南三村》)。2010年,“志在富民的足跡——紀念費孝通百年誕辰大型新聞行動紀實”的采訪組重訪易村,了解到易村的新變化。“易村土法造紙的手工業已經消失。目前,土法造紙技術正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易村正在搞大棚蔬菜種植,而江邊的竹林也已恢復。
變化最大的是玉村。1990年費孝通到玉溪,已找不到當年的田野點。地處玉溪城郊的玉村,農村經濟發展已經與其他兩個村子拉開了更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