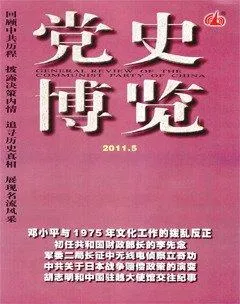鄧穎超:帶病參加長征的女紅軍
鄧穎超是紅一方面軍中參加長征的30名女紅軍之一。1992年7月11日,她與世長辭,走完了自己光輝的人生征程。《人民日報》7月17日刊出的《鄧穎超同志光輝戰斗的一生》,對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德高望重的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在紅軍長征中的經歷只提了一筆:“1934年10月,帶病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然而,她當時是怎樣帶病參加長征,她在長征中有什么樣的經歷,以及數十年后又是怎樣回顧長征路,口述長征事。撰寫長征史的呢?
長征出發時,她曾向黨組織要求留在江西蘇區
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廣西南寧。曾在北京、天津平民學校和女子師范讀書。后曾任小學教員。1925年3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8月初,調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兼婦女部部長,8月8日與周恩來結為伴侶。1927年5月從廣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主任。1928年5月初隨周恩來赴莫斯科,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黨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機關黨總支書記。她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中央紅軍的長征。
鄧穎超從小體質就差,患過肺結核病。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后,由于工作勞累,飲食營養不足,她的肺病又一次復發,并且逐漸嚴重。當時的環境十分艱苦,缺醫少藥,她的肺病得不到醫治,以致咳血不止。長征出發時,她曾向黨組織要求留在江西蘇區,一方面養病,一方面做點工作,免得給領導和同志們增加麻煩和負擔。但中央決定讓她隨同紅軍走,她只好堅決服從。
當時的“走”與“留”,都是由各級黨組織所決定的,鄧穎超假若被留在江西蘇區,即使不會被敵人抓去,也是兇多吉少,生命難保。在她走后不久。被留在蘇區的她的母親楊振德醫生,就曾被敵人抓入監牢。鄧穎超經常說她是長征過來的幸存者。
記憶中的“又一次”慘烈戰斗
長征途中。鄧穎超作為一名休養員,被編入紅軍總衛生部的干部休養連,躺在擔架上隨軍行動。由于肺病纏身,體質虛弱,休養連不僅為她配有一副擔架,同時還配有一匹馬。
當時,前有敵軍阻攔,后有敵軍追趕,頭上還有敵機轟炸,腳下又是坎坷艱險的道路,紅軍指戰員忍受饑渴,人困馬乏,幾乎是晝夜兼程,還要隨時隨地跟敵人戰斗。情況緊急時,部隊往往是邊走邊打,且戰且走,既要沖破前面攔路堵截的敵人,還要擊退后面蜂擁而至的追兵。
長征途中,那些近在眼前、迫在眉睫的大小戰斗,在鄧穎超的記憶中就有數次之多。她曾這樣回憶說:“又有一次。我們正在貴州境內行軍。一天下午,我們剛走到貴陽西南距離紫云縣城不遠的山腳下,大隊人馬正準備爬山,忽然飛來敵機數架,瘋狂投彈、掃射,有一些同志被炸傷炸死……”
這是1935年4月中旬。紅軍在由貴陽進入紫云縣境內時發生的事。
當時,國民黨軍飛機出動頻繁,沿途跟蹤,輪番轟炸,紅軍一面進行偽裝防空,一面緊急向西行進。一天下午,據說前面將要翻越一座大山,休養連大隊人馬聚集在山腳下,等待了很久。
鄧穎超覺得久等下去不是辦法,就同她的馬夫一起,牽著馬向山坡上走去。就在這時,有數架敵機突然飛臨上空,先是一陣猛烈掃射,接著又是一陣震耳欲聾的狂轟濫炸……
危急關頭,鄧穎超和她的馬夫就近潛入半山坡上的小樹林子里,躲過了這場猝不及防的災難。事后,當她走出樹林子時,在那大隊人馬聚集的山腳下,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亂不堪的凄慘景象。休養連傷亡了l0多名同志,牲口和物資也損失不少。隨同休養連行動的毛澤東夫人賀子珍、羅炳輝夫人楊厚珍二人,都在這次轟炸中不幸身負重傷。
長征途中護理身患重病的周恩來
1935年7月初,紅軍大部隊由兩河口經卓克基到達蘆花(今黑水)地區,就地駐扎籌集糧食。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各一部,于7月16日占領毛爾蓋,殲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一個營。此后不久,鄧穎超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提議。離開休養連由蘆花到達毛爾蓋,與周恩來相聚。她在毛爾蓋停留了20多天,一面繼續休養身體,一面護理身患重病的周恩來。
長征途中,周恩來、鄧穎超兩人各在一地,平時很少相聚。那一次休養連慘遭敵機轟炸,周恩來半夜里趕來看望時。與鄧穎超也只是談了幾分鐘話,便又急忙離去,返回紅軍總部駐地。這一次因為周恩來的病情十分嚴重,中央領導才決定把鄧穎超接到毛爾蓋,以便進行照料。
在參加過沙窩會議后,周恩來就病倒了,一連數日高燒不退,飲食不進,被確診是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瘍,急需進行排膿治療。周恩來睡在一張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由王斌、李治兩位醫生護理。鄧穎超就地鋪了點麥草,作為自己的床鋪,與兩位醫生一起做點護理工作。她把周恩來脫下的一件毛背心拿起來一看,上面全是虱子蟣子,結果擠了一百七八十個,血把大拇指甲都染紅了。
經過一番治療和護理,終于從周恩來的腹腔內排出半盆綠色膿液,他的高燒才慢慢退了。當周恩來完全清醒過來時,這才發現鄧穎超待在自己身邊,感到有點意外,就深情地喊了聲“小超”,問她什么時候來的,還問她有沒有青稞麥子充饑。
黑水蘆花,親歷者不忘青稞麥
陸定一、賈拓夫1935年10月于吳起鎮(今吳起縣)合編的《長征歌》中。有這樣幾句歌詞:七月進入川西北,黑水蘆花青稞麥;艱苦奮斗為那個,北上抗日救中國。
從蘆花到毛爾蓋,鄧穎超對“黑水蘆花青稞麥”這句歌詞的感受尤為深刻,親歷者念念不忘地回憶說:
長征部隊進入四川西北部以后,正值青黃不接的時節,糧食問題就更加困難。有時,簡直找不到一粒糧食,我們就到田野里采野菜吃;有時我們只有忍著饑餓。或者吃一些不曾硝過的牛皮和死馬肉,或者打野豬、牦牛充饑。在松潘縣的毛爾蓋住了一些日子,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斷糧的嚴重威脅。
毛爾蓋是當地藏族地區最大的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戶人家。這里的青稞麥田很多,據說收一年的糧食,可供當地人民吃三年。這時青稞還未成熟,但紅軍為了活命,為了能繼續戰斗,我們不得已決定收割藏民的麥子。可是紅軍的紀律是:不得到群眾的同意,是不能隨便拿借東西的。于是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寫著割麥的數目,并且請他們拿著牌子向我們后面的部隊要錢,或作為將來向紅軍算賬的證據。……
收割沒有完全飽滿成熟的青稞麥,假若吃上幾把生麥粒兒,味道甜絲絲的,還有點鮮嫩感覺。但卻不可多吃,只能嘗個鮮。為了籌集糧食過草地,紅軍把這種收割回來的青稞穗子,先用爐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殼,脫出半生不熟的麥粒兒,在鍋里煮熟吃。因為青稞麥里含水分多,外皮又過分柔韌,當時也無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無奈之下,只能煮熟后一把一把往嘴里吞,吃多了肚子發脹,也只能吃個半飽,壓壓饑餓。別看這又鮮又嫩的青稞麥粒兒,如不細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很多人都鬧起胃病來了。
紅軍收割藏民青稞這一史實,親歷者們一直沒有忘記。長征結束后不久,鄧發、舒同、賈拓夫等人,就曾在文章中有過記載和敘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中擔任中革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的鄧發,1936年就曾以“楊定華”之化名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上發表過《雪山草地行軍記》的文章。他在文中曾就“全體動員割麥”的情景,有過具體敘述:“大家知道前面糧食更加困難,所以紅軍當局便命令各部籌備糧秣十天,并幫助一部分負責抗擊追敵之部隊籌劃糧食。此時真有‘不割麥不得食’之勢,除少數擔任勤務之部隊和傷病員之外,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都一齊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每天早晨8時,各連隊就集合,向指定的麥地進發,一群一群的紅色戰士聚集在一塊,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覺自動地勞動著。”朱德總司令“不僅同戰斗員一樣割麥和打麥子,并且割下以后從一二十里遠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來”。“共產黨的中央書記張聞天和年已五六十歲之徐特立、林伯渠,也來幫忙弄麥子”。
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曾這樣寫道:“毛澤東告訴我,他們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蘿卜等蔬菜……他們就是靠這種微不足道的給養過了草地。毛澤東幽默地對我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里拿走的給養’。”
過草地時,身患重病仍不忘鼓舞士氣
過草地時,鄧穎超獨自騎在馬背上,跟隨周恩來的擔架一道行動。有一天,她為了追趕周恩來一行,乘馬突然受驚,把她從馬背上顛落在地,一下陷入沼澤。她不敢掙扎,越掙扎就陷得越深。等了很久,直到后邊的人馬趕上來,這才將她從泥沼里拉了出來。草地氣候變化無常,晴朗的天空,不多會就布滿烏云,大雨傾盆。她渾身上下全都被雨水淋濕透了,嘴唇發青,凍得直打哆嗦。當天晚上,就開始發高燒,還拉肚子,于是就不得不躺在擔架上穿越茫茫的草地。
在進入草地第三天過河的時候,鄧穎超正在患病。因河面有一丈多寬,水深達三尺,所以部隊都停滯于河邊。她躺的擔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隊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級軍官都去看望她。她便喘息著向圍著她的軍官們問:“河水深到什么程度?”來看望她的軍官們異口同聲地回答她:“不要緊,沒有關系。”她仍很關心地對戰士們說:“同志們,大家手牽著手過河才好呀,不要沾濕了衣服呀。這是過草地最后的困難了。”戰士們聽到她的話無不動容,大家都提高了渡河的勇氣。
8月底,右路紅軍全部到達班佑、巴西地區。過草地的六七個晝夜,因為沒有房子居住,部隊全都露宿,也不能燒火煮飯,只能以隨身帶的炒面、青稞麥粒充饑。這些天里,鄧穎超沒有吃過一粒米面,處于極度的虛弱昏迷狀態。到了半農半牧的巴西地區,這才見到幾處藏民村落,見到藏式房屋,大家都感到喜出望外。
這時,鄧穎超和周恩來住在通往秋吉、巴西路上的一個名叫牙弄的藏民村寨。這寨子依山傍水。景色秀麗,也相當幽靜,倒是一處休養的好地方。他們在此住了八九天,蔡暢和幾名女紅軍,都來看望過身患重病的鄧穎超和周恩來。姐妹們看到鄧穎超當時“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為她活不成了,背后都為她傷心抹淚。
回顧長征路,謙虛地說自己“不能算長征的紅軍女戰士”
同是長征過來人,鄧小平說他是“跟著”走過來的,鄧穎超說她是靠黨、靠紅軍、靠同志、靠集體“跟過”來的。
1965年,正值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30周年之際,鄧穎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革命回憶錄《紅軍不怕遠征難》一文。她滿懷深情地回顧長征路,敘述長征事,對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給予熱情的贊頌和充分肯定,而唯獨不表現和突出她自己。她坦率地說:
“長征期間,我正患著嚴重的肺病,沿途受到黨組織的關懷和同志們很多的照料和幫助。我也同樣地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頑強的意志,和戰士們、同志們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難想象。一個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堅持到達了陜北。”
歲月流逝,到了1985年,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前夕。鄧穎超仍十分謙虛地說:“我雖然是長征過來的,可是不能算長征的紅軍女戰士。真正女戰士是像康克清、李堅真等同志那樣,她們當時都在連隊當指導員。而我那時重病在身,屬于休養連的休養員,沒有什么供你們可寫的。”甘當無名英雄的鄧穎超,居然把自己排除在“長征的紅軍女戰士”之外,說她這個休養員沒有什么可寫的。別的姑且不論。但凡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女戰士,都是名副其實的紅軍女英雄!
1985年,鄧穎超的秘書趙煒,根據鄧穎超以前的回憶和平時言談中所涉及的長征的事,整理了一篇題為《鄧穎超在萬里征途中》的人物小傳。趙煒認為:雖然她不承認自己是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女戰士,說自己在長征時沒有做什么工作,但我們國家能有今天,就是靠他們這些老一輩革命者在黨的領導下艱苦奮斗的結果。所以,我們只好說她是“不是紅軍”的紅軍女戰士。
從長征路上能“跟著”走過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就無愧于紅軍長征女英雄的稱譽。鄧穎超無愧于參加過長征的女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