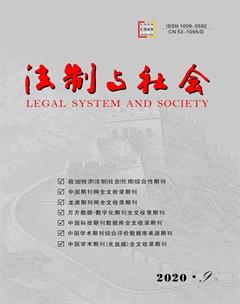淺析《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之適用
王欣
關鍵詞量刑建議權 量刑權 獨立審判權
于金平交通肇事案。一審法院未采納控方量刑建議,作出重于控方量刑建議的判決,控方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抗訴后,二審法院經審理作出又重于一審的有罪判決。這種行為因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之規定而引發廣泛關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以來,《刑事訴訟法》第201條就被視為是將認罪認罰協商結果判決化的默示規則,一時間關于認罪認罰改革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混淆不清,以量刑建議權侵蝕審判權的爭論不絕于耳,甚至有人認為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審判決,力圖以一種獨立特行的方式宣示審判權的獨立性,更有甚者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看做是檢察機關失去職務犯罪偵查權以后尋求權利擴張過程中檢、法權利角逐的一個縮影。
一、量刑建議之權屬認定
從控訴權的發展史看,控訴權是一種由私權演變而來與審判合并行使的權利,歷史上控訴權與審判權集中于一人行使,為了防止這一合并的公權力濫用,公訴權從審判權中分離出來,開始發揮著對審判權的制衡作用。而量刑建議作為公訴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天然具有監督約束屬性,約束本身是基于權利本體而衍生出的一種制衡屬性,這種制衡性與專屬于法院認定某行為違法并判處刑罰的量刑權有本質區別。
從權利屬性看,量刑建議權不等于量刑權。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之規定,法院是確定刑事被追訴人有罪的法定機關,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權天然地包含了定罪權,二者不可分割。而以定罪量刑權為主要內容的審判權是憲法賦予法院壟斷、專屬國家的權力,任何個人、任何機關、任何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而將人民法院的審判權“讓渡”或“分享”給其他機關。在定罪量刑問題上,如同公訴權不是定罪權一樣,量刑建議權也不是量刑權。檢察機關既沒有定罪權,也沒有量刑權。只是一種通過固定證據,分析罪行,請求法院作出罪責行相適應判決的請求權。
從現行法律規定上來看,不論2018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亦或兩高三部出臺的《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于量刑建議的認定都需要明確需經過法院審理認定,并未承認對被告人的量刑前置于審查起訴程序環節。故量刑建議實質為一種程序性的司法請求權,這意味著其可以作為法院判決時定罪量刑的重要參考,但并不具有必然的強制力,更不影響或決定法院審判權的專屬性和獨立性,這也是審判中心訴訟模式的權利設定體現。
二、《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之適用問題
(一)第201條表述之模糊性
根據第201條之規定法院對量刑建議的基本態度是“一般應當”采納,對“一般應當”之理解矛盾早在余案之前就存在。2019年浙江省仙居縣蔡某某危險駕駛案中當地檢察院因一審法院非出于“但書”緣由未采納其量刑建議而提出抗訴,浙江省中級人民法院因此認定一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并依法改判采納檢方量刑建議。該案第一次將第201條適用之矛盾拋諸公眾視野。即法院對該量刑建議是“應當”采納,抑或“可以”采納。。按照文義解釋,“一般”是任意性法律規范用語,而“應當”則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范疇。由“一般”代表的任意性法律規范和“應當”代表的強制性規范混搭為“一般應當”則顯得不明確,含糊其辭,與法律規定明確性原則要求不符。若理解為“應當”,量刑建議的采納就成為法院的義務,悖離量刑建議的權利屬性與法院審判權的獨立性,若理解為“可以”,此時由“一般應當+但書”表述之后,第二款又規定量刑調整似無必要。
(二)架空量刑程序之嫌
量刑調查、量刑辯護、量刑建議是“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201條過于絕對化的強制性規定使得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有了結果導向性,而量刑建議就演變成結果導向的直接依據。庭審結果提前定性,庭審程序成為程序性表演,變得可有可無,認罪認罰案件量刑程序也就淪落為加蓋法院印章以確認量刑建議的背書流程而已,這悖離了自我國量刑程序改革以來,著力推動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適度分離的刑事司法改革之意圖,阻礙了“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的正常運轉。
(三)侵蝕審判權之風險
本文在第一部分量刑建議權利屬性中分析到量刑建議權本質上是一種司法請求權。201條之規定對法院不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規定了較苛刻的條件,過于剛性的量刑建議權披上量刑裁判權的色彩,有侵蝕法院獨立審判權之嫌。
一是規定唯有法院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提出異議,法院才可以不采納。而關于“明顯不當”的認定并未有相關法律解釋做出規定。體現著較大自由裁量屬性,而自由裁量并非專屬于法院的權利空間,同樣可以被檢方所適用。圍繞這個此問題,爭奪自由裁量權的話語權就演變成量刑權的爭奪,從而引發社會種種猜測。該矛盾在余案中充分體現出來。。
二是即使法院認為控方量刑建議“明顯不當”,也不能直接繞過量刑建議徑行宣判,還需要賦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調整機會,只有控方拒絕調整量刑建議或者經過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存在明顯不當,法院才能“依法作出判決”。在此語境下,檢方以量刑建議影響法院審判的獨立性,有變相成為獨立審判權前置性規定的嫌疑。
三是在一刀切高量化指標的司法實踐中,很多地區檢察機關為了提高量刑建議采納率,主動邀請法院就量刑問題舉辦相關培訓會,甚至就量刑情況與提前與法院進行溝通協商。不可否認,檢察機關這一系列做法確實能夠基于法檢和諧的基礎上短時間內提高量刑建議采納率,完成目標量化任務。但長此以往,量刑溝通會向案件協商延伸,腐蝕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頗有“未審先定”的風險,既侵蝕審判權又損害被追訴人利益。
三、應對《刑事訴訟法》第201條困境之思路
(一)“一般應當”“可以”之解的適當調整
對《刑事訴訟法》第201條做出調整,修改“一般應當”為“可以”,刪除“但書”規定,較大程度上還原法院的獨立裁判權。與此同時也應保護以量刑建議為結果的認罪認罰協商制度,法院不采納控方檢察建議時應當說明理由和依據,控方認可的,責成控辯雙方對量刑建議重新進行協商,控方不認可的在法院審理階段由法院對被告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由此使被告人獲得從輕處罰的程序權利不受影響。
(二)有必要對法院改變量刑建議的理由作出更為明確的規定
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與被告人達成的認罪認罰協議,提出的量刑建議具有特定法律效力,法院否定該量刑建議應當有充分理由。《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五款規定法院可以不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其他情形”,但哪些屬于“其他”的范圍,法律及“兩高三部”的《指導意見》語焉不詳。這也容易導致實踐中的檢法分歧。
即如本案,檢察機關認為法院一審未采納量刑建議沒有法定理由,屬于程序違法,因此提起和支持抗訴;而法院則認為檢察機關量刑意見“明顯不當”。正如上文中提出,關于“明顯不當”的認定標準及適用幅度均未有查詢依據,給司法實踐帶來極大適用困惑。
因此,似有必要對法院改變量刑建議的理由作出更為明確的規定。
(三)檢察機關應當更為謹慎地提出量刑建議,避免與法院實質真實主義的沖突
余金平案對檢察權行使的檢討之處在于認罪認罰案件適用量刑建議時應當注意檢察權行使的謙抑性,以及尊重以審判為中心的程序法理,比如浙江仙居縣蔡某某危險駕駛案中一審法院未采納控方檢察建議,但調整的范圍并非“明顯不當”,基于當事人利益與法治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宜過于機械化套用201條之規定。
對類案進行分析,同樣需要適當檢討檢察政策,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過度追求適用比例以及高量化指標的量刑采納率,甚至是隱于其后的爭取程序主導權的意識。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應當將量刑建議權限制于一個接受程度更高的,能夠兼顧司法公正的范圍內。
四、結語
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為契機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后量刑建議權運行中的現實困境,分析《刑事訴訟法》第201條模糊性規定帶來的量刑權之爭,從而厘清量刑建議權、量刑裁判權與獨立審判權,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與審判獨立原則并未發生動搖。基于此,建議合理修改《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之規定,解決現實適用困擾。同時應當注意檢察權行使的謙抑性,以及尊重“以審判為中心”的程序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