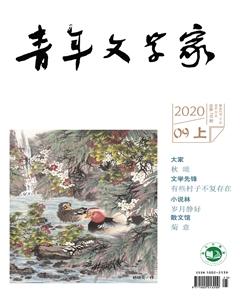鄭老師的父親
田墨龍
鄭老師是我高中時的數學老師。那天下午的最后一節課,鄭老師不厭其煩地為我們講那一道難度很大的題,雖然晚放學十多分鐘,但我相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學仍然沒懂。這其中就包括我。
我當然還是要一弄究竟的,于是就和他一起走出校園,準備適當時機再行發問。校門口,一位老人喊住了他。是鄭老師的父親。
他父親那時四十多歲,但給人的感覺卻不止五十。他騎著一輛破舊的“二八”自行車,前大梁和后車架子馱著自家地里的土產。他是從十幾里以外的鄉下掐著放學時間趕來的,當然,他也和我們一樣,多等了十幾分鐘才見到兒子。他還要趕在天黑前回到家里。
鄭老師心疼他的父親,說不要他再來送,他有時間自己回去取就可以了。“你只要能讓咱們縣多出幾個大學生就行,孩子們都需要你。”
我不由得多看了一眼這位不算老的老人,他心里想的,還都是些大事情呢。后來我們班有11人考上了大學,其中就包括我。那時一個邊遠的小縣城能有這樣的升學率,真是很高了。
大學畢業以后,我在省報謀了一個記者的職位。幾年的打拼,也算出了點小名。一天,主任告訴我:“給你幾天探親假吧,不過順便也要辦點公務。”那所謂的公務,就是修改家鄉一名鄉黨委書記的先進事跡材料。我想,這倒容易,只要事跡典型,我的文筆還是沒問題的。
經過一天的長途奔波之后,我只和父母打了個招呼,就直奔宣傳部看材料去了。那個鄉黨委書記,原來是我曾經的鄭老師。事跡很典型,稿子也沒問題,但就是讓人感覺,少了點什么。“少點什么?”部長說,“問你呀!”
我于是決定去看一看久未謀面的鄭老師。鄭老師聽說由我來改這篇稿子,大喜過望,就把他這些年的經歷,都和我講了一遍。
從新聞寫作的角度來說,他所講的和稿子所反映的,并沒有太大的區別。我感覺少的那個東西,在他這里也沒有找到。正失望之時,我忽然看見他的桌子上擺著一張他和他父親的合照,這倒讓我產生了興趣。像他這樣的人,在這樣的場合,桌子上擺著的,應該是他和某某領導或者某某明星的合照才對。
他見我盯著照片看,也猜出了我的心思。“三年前,我和父親說要下鄉當書記的時候,父親送給我兩句話:“一是‘當官要給老百姓辦實事,二是‘公家的錢一分都不能花。我把父親的照片擺在這里,就是讓他放心。我要讓他知道,我就是按照他的要求來做這個書記的。”我好像在漫漫的黑夜中忽然尋到了一絲光亮——“動力”!對,這就應該是那篇文稿所缺少的東西。于是那篇通訊的標題,迅疾在我的頭腦中閃現——《父親的期望》。后來這篇稿子,獲得了省報的年度優秀獎。
花落花開,我也坐到了記者部主任的位子。一天,鄭老師給我打來電話,說是他侄女考到了省城的一所大學,他要來送侄女入學。
我感覺奇怪,自己的孩子來省城上學,他都沒來送,可是這侄女……
那天,我和他一起陪他侄女辦好了入學手續。然后,我們找了一個雅間坐下,我要解開我作為職業記者的疑惑。
“你也感覺挺奇怪吧?”鄭老師酒剛喝了一口,就這樣問我。“這孩子是我弟弟的繼女,我是為著完成父親的遺愿才來的。當初弟弟要和她媽媽結婚的時候,去征求父親的意見。父親當時是這樣說的,‘你要考慮好她還帶著個四歲的女孩。如果你能像對自己親生閨女那么對待她,我沒啥說的。”“弟弟沒有讓父親失望,視繼女如己出。這孩子長大后也很懂事,就和她媽媽商量,也隨了弟弟的‘鄭姓。這次弟弟不巧出差不能送她入學,就委托我來。我們要讓這孩子感受到我們鄭姓家庭的溫暖。”
“老爺子已經……”“春天里剛剛走的。他走的時候很安詳,只是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似乎是表示對我們每一個子女——都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