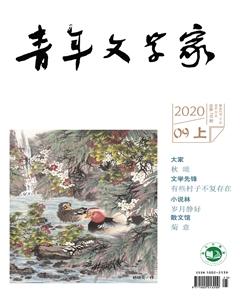塵世的蟬
賀湘君
坐在春寒料峭里,怎生就懷念起蟬鳴?傳說六月天會飛雪。那么,三月天也會響起蟬鳴嗎?分明又是癡人說夢了。舉目窗外長空,春雨仍是沒完沒了,揮之不去的倒春寒,將心情擠迫得逼仄橫起且莫名生懨。
那晚,將看剩的半卷書和涼了水的茶壺收起。新買的《花間十六聲》里掉出一張前幾日隨意夾進去的書簽。“吃茶去”,清冽三字入眸來,有濟群法師的印章。陌從蘇州西園寺里求回來的“西園茶事”。背面寫著:問茶、讀書、靜坐、帶心回家。我已端坐兩個時辰,看風從鵝黃簾子外吹進來,寂寂寥寥翻動我的書頁;也吹過印有牡丹的青花瓷壺,落在素凈的桌布上,悄無聲息地隱匿。我卻忘了起身,去阻止那一刻禪意的驚起。唯有靜坐。
三月天里響不起蟬鳴,蟬聲是夏日絕句。我們一切的行為舉止,包括鬢上顏發,指間算盤,無一不接受自然造化的四季差遣。夏聽蟬聲,冬看雪。你走了很遠的路,于夜里歸來,借著舊時月光審度眼前的屋檐窗欞,看見滿庭階的秋霜。蟬音是墨夜唯一的歌者,將你心口的凸起和凹陷,削平填實。蟬聲,曾幾何時,收藏了兒時溫暖的記憶。
我們總會在花朵熙攘的季節懷念冰雪的單純唯一,也會在寒風凄凜的冬日惦記著春暖花開,做著想去喂馬劈柴、浪跡天涯等不切實際的幻想。鴿群收買了天空的純凈,蟬翼壟斷了世間的夢想,我們浮塵野馬般的人生,亦只是游歷在塵間印在壁上的佛眼,等待一個醍醐灌頂的提醒:“若有人于河中掬一瓢飲,當知,已飲閻浮提一切河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或春風得意高朋滿座,或歷盡滄桑心如止水,或糊糊涂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而我想來應該并為后一類的集合里。我們日日啜飲塵煙得以寄身的紅塵,溜風潲雨是免不了的煩惱。歡顏少,寡意多,生命自有實踐的飽滿意義,也填不滿幽黑隧道的攀爬掙扎。
東晉陶淵明,少時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鴻鵠大志,當夢想鎩羽而歸,他便悲壯地折戟沉沙,優雅的轉身。歸于東籬下,做個自在的采菊人,另辟蹊徑,為世人尋來《桃花源記》的慰藉。不為五斗米折腰,僅僅是一個文人輸不起的清高嗎?我分明看見了陶公生了一爐火,熱了一壺酒,悠悠吟唱著:“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
歸隱,是古人墾拓的一種精神圖騰。今天,仍然有它淡墨輕煙的絕妙風景。它應是一種常人難以抵達的境界,是人人心中甘愿供奉的凈地。現代人也思渴歸隱,與山野僻壤共存不是歸隱的唯一出路。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誠然我們已找不到昔日的南山,我們卻可以選擇與書本、植物、花朵、月光、清茶等為伴,隨時隨地于喧嚷塵世里撈起一片舊時月光。
《花間十六聲》里第十五記寫《金縷衣》,用了大量的筆墨介紹法門寺出土的金縷衣。眼神掠過濃墨重彩明亮亮的詞匯字眼時,腦海里浮現一個清峻高雅的人名:李叔同,亦是弘一法師。他曾作《金縷曲》述志:“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
從風華才子到芒鞋布衲、托缽空門、最后圓寂于陋室繩床的一代高僧,承受了世人幾多狂瀾驚愕?弘一大師病危前手書之偈語:“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他這一生,應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典范,連張愛玲也說過一句:“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的寺院圍墻外,我是如此的謙卑。”這是一種高貴的清醒,留待世人做反復的比較、辨知和參悟。
思想自是不可禁錮的浮塵野馬。抬眼看去,路邊枝頭春意在鬧,夏天仿佛蹲伏在門口那汪雨水里,跨了門檻就攜陽光而來。耳邊便隱約響起“知了,知了”的一聲聲高亢的蟬鳴。
且做塵世的蟬,餐風飲露,亦是一種樸拙圓滿的修行。